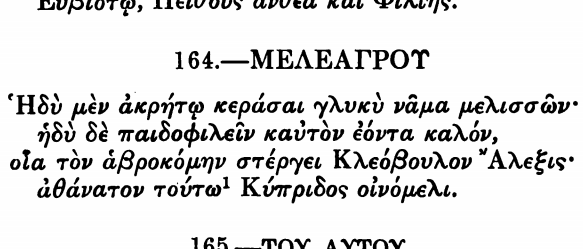高一舊文存檔:共青團之戀(百合注意)
我知道寫的不怎麽樣。那時候我還是個死高中生,能寫什麽好東西。不過就是回頭看看,驚覺那時候文筆還真是細膩,我恐怕再也不會用那種調寫小説了。因此,想要把它保存下來留作紀念。沒有完結,大概還記得結局是怎樣,但沒有寫完,也沒有精神再續寫。
隨便放一張喜歡的anime的圖吧

共产主义青年团之恋
初中必修科目等级考试成绩出来的那个日子,春天尚在苟延残喘。
妈妈告诉阿零她两门科目都是满分时,后者正心不在焉地用筷子夹着一块莴苣。即将出现在成绩单上的两个鲜红a+没能让阿零停下思考她认为更重要的事:并非心血来潮抑或少女情怀,阿零突然对爱情的本义产生了顽固的好奇。她一边把饭扒进嘴里,一边好几次想开口问那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阿零还是把问题吞回了肚子,尽管因此她不小心咬到了舌头。
饭后,妈妈在给单位的阿姨打电话,阿姨刚生完孩子,在住院观察。阿零吃力地拎起书包去自己的房间写作业,本来不该走神,可她耳朵里总是来回晃着打电话的妈妈和生了小婴儿的阿姨,那个一次次被按下去的问题又不甘心地浮了上来,一阵一阵的不安弄得胸口又烫又痒。阿零瞟了一眼时钟,这会她觉得指针好像坐上了秋千,一下子荡到了九点,可是生词还有一大半没抄完。阿零想着该强迫自己快些把作业写完,她打了个哈欠,想起的却怎么也不是生词。
如果提问阿零这个城市的气候类型,她会想上一会才报出温带季风气候或者亚热带季风气候。可是总归是季风区,这一点是不会错的,就像三月和四月,都是货真价实的春天。可是对十四岁的阿零来说,春天好像咧开了该抿着,微微笑着的双唇:陡峭结实的三月在上面,而下面的四月软塌塌的甚至有些臃肿,有个小小的女孩子踮着脚尖踌躇了半天,突然一下跳了过来。
可是四月还是那么快就过去了。阿零记起楼下的肥猫爱躲在车下,露出一条胖尾巴,可自己每当想拽住那条尾巴来捉弄猫咪,尾巴就倏忽溜进车底下抓不到了。如果没有四月又会怎么样?她猛地觉得自己想了不该想的东西,还没反应过来究竟是什么,就感到一阵热气直往脸颊里透。没有四月?那大概就考不到满分了吧,这时候阿零才想起来妈妈告诉自己的事。做贼心虚似的咬了咬笔头,她刷地把作业翻到下一页,出乎意料,原本应该满满当当的作业本上什么都没有。肯定是印刷错误,阿零刷拉又翻了好几页,后面就是还没学的内容了。不知道怎么形容才好,阿零呆呆地托着腮愣在那里。
打完电话的妈妈长舒了一口气,毕竟对她而言应酬那些中年妇女真的是一种负担。她洗了一个玻璃杯,然后像所有中学生作文里的母亲一样倒了大半杯牛奶打算给女儿送去。妈妈没有敲门,而是径直扭开把手进房间,一眼就看到阿零在桌子面前发呆。
“快点写作业。睡太晚明天要起不来的。”妈妈一边放下杯子,一边略带嗔怪地说着。
“老妈,”阿零感到语言又涌上了喉头,挠得刺痒,妈妈转过身去要走,又回过头来。
“什么事?”
“妈妈 ,”阿零觉得嗓子眼直发干,“是不是所有谈恋爱的人都会有小宝宝?”
“你整天在想什么!?大人的事是你该管的吗?”妈妈明显有些生气,声音也重了许多,“早点睡。”
这时,阿零心里又卷起了丝丝缕缕的羞耻,好像小时候偷吃邻居家那些小巧而酸涩的樱桃。
因为自己是学校共青团的支部书记,被辅导员叫去是常有的事。就算是现在回想起那天的事,阿零也丝毫不觉得奇怪。共青团辅导员是三十出头,说话颇为温柔的顾老师,阿零知道她的名字是顾琴,因此,身在旧时代的女校一般,阿零在心里偷偷叫她琴小姐。这个名字总让人想到“曲有误,周郎顾”,至少阿零是这样。第一次听到办公室的其他老师笑吟吟地喊顾琴两个字,恍惚间她的视野里只剩下一片有牛奶味道的光泽,盈盈地浮在自己不常裸露而显得幼稚的手臂上。
在食堂吃饭回教室的路上,阿零撞着了琴小姐。虽说是四月份,老师还没有下令换校服,谁也不敢脱掉鼠灰色的冬季大衣校服换上春秋运动装。阿零一面一味盯着自己的脚尖,一边清楚地感觉到额头一点点变得湿润。这所初中不允许女学生留刘海和长发,因此只是在被阳光烤暖的她空旷的额头两角,有一点点可以躲过纪律委员的碎发蜷曲着贴在皮肤上。食堂的饭菜永远难以入口,纪律委员风雨无阻地戴着红袖章在门口检查。阿零知道有人在背后悄悄骂纪律委员是狗,骂食堂老板是猪,她却对食堂,对检查每一个女孩的头发长度与发卡颜色的纪律委员没有一丝的愤懑或是像往届生一样在学校贴吧拼命辩护的感情。而靠近食堂的操场,灰败得叫人心酸,只有这样的光景才让阿零感到些许眷恋。十四岁,头发柔软而微微发黄的女孩,早早学会了液体式的生活。
而就在垂满爬山虎的墙下,毗邻着绿得暴烈的迎春花丛,琴小姐让阿零跟着她去办公室。
于是垂着头的女孩同三十出头有着充满韧性的肉体的女教师,穿过走廊,穿过枯枝的花影,偶尔穿过一池金鱼。阿零看着眼前琴小姐的影子忽而深厚,忽而被抽干了重量,忽而又残缺得如同精灵。
共青团活动室的窗帘拉上了。随着琴小姐几乎不出声地把门推开,房间里滚滚的寂静犹如海啸。这时阳光从被推开的门外迫不及待地滑进来,蜷缩在法兰绒窗帘的褶皱里。而且,细细看来,这窗帘远没有那么厚重,只是软塌塌地兜着打在窗户上的光线罢了。那面团旗不引人注目地被放在角落里,黄色的五角星被弄脏抑或是打败了一般,懒散地瞧着地上。总而言之,共青团活动室也好,整个支部也好,都在无边无际的倦怠里随波逐流。
琴小姐走进来以后,顺手带上了门。该把灯打开啦,阿零想。可是,琴小姐直接摸黑坐了下来。
尚未长成的女孩的手指有着单薄而稍嫌硬朗的关节,好像只要微微弯曲就能发出羽管键琴那种玻璃似的拨弦声,而色泽又如此淡漠,宛如干涩得发凉的纸浆,活生生地透出一种忧郁,这种忧郁正是如同蝴蝶骨一类的被称为少女的特权的事物。她蓝绿色的静脉清晰可见,清晰是如此锋利,仿佛琴小姐一闭上眼睛就能听见血液碰撞血管壁擦出的火星。所谓陡峭得有如马背的青春,正幽幽地闪烁在阿零的双手上。
琴小姐站起来拧开灯管,让光线盈满整个活动室时,她恍惚中听到若有若无的叹息声在房间里回荡。阿零就在那里等她说话,双脚乖巧地内八字站着,垂着头,并不太光滑的后颈也好,从领口可以看到的内衣泛白变型的带子也好,都落满少女的光晕。
她也总是去想阿零发涩的雏菊味双唇。曾因激动而神经质地颤抖,尔后溢出的红色在脸颊上晕开。倘若谁大着胆子抚摸那时候阿零的双颊,一定可以感受到类似握着鹌鹑那样稍稍用力整个世界就会土崩瓦解的触感吧。她去想阿零认真时好像在和谁生气一样的声音,和她断句时习惯轻闭眼睛浅浅蹙起眉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阿零的朗诵慢慢在她心里进化成了齿轮或者转经筒的响声。
“倒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
阿零猛地昂起头,合乎校规的短发晃了一晃。
“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
这是那次阿零在初一年级儿童节汇演时的朗诵,那么小的孩子哪里会懂闻一多?不过是形式主义而已。但是民主斗士闻一多不重要,革命不重要,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不重要。只有少女的双唇在六月颤抖。
阿零甫一升上初二就第一批入了团,尔后又稀里糊涂成了团支书,尽管说是琴小姐那时就看上了她未免言过其实,但琴小姐也无法否认,女孩粘稠滑腻的乳香如同一条小蛇悄悄没入她已经略微丰满的小腹,除了丝丝缕缕的疼痛,夜深人静时也流泻出诡异的快感。而那女孩就站在这里,脸庞被日光灯照得一片雪白。
阿零并不是被大家叫做美人坯子的女孩子,甚至有人说她长得愁苦:她的额头淡淡地发灰,眼睛过分地大而缺乏神采,鼻尖的形状稍显胆怯,嘴唇又是那样的薄。但是琴小姐却一眼看出了少女眼睛湿润的光泽,仿佛在向命运昭示自己的无辜一般的光泽。而且,无论是额头还是没什么弹性的鼻尖,都像是在诱惑着不幸,这是一张仿佛要拒绝日常生活的面容,却又总是一副奇妙的迷醉神态,这种迷醉绽放在无机质的眼睑上,耳坠似的悬挂在睫毛上。琴小姐或许在少女时代某个清晨见过,让她想起兰波或是波德莱尔,潺潺满城雨或是忘川的绿汤。
“吕谷零,”琴小姐叫这个名字时,总觉得一股气流在温暖的口腔里左冲右撞,“今年六一汇演你主持吧,我私下问了几个同学都说去年你的《死水》很成功。”她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句话,带着一贯温柔而平缓的语调。
“好,老师,那谁和我搭档?”阿零估摸着快打铃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琴小姐让她无比地安心,她的眼睛机敏地睁大着,手指轻轻抚摸自己校裤的裤缝,又在裤缝两边点来点去,模仿着山羊的跳跃姿势。
“这个人选还没有确定,你觉得谁合适也可以和我说。”事实上琴小姐并不关心共青团这些乌七八糟的活动,即使是往年也是走走形式,“一会打铃了,回去吧,别迟到了。”
“啊,老师再见。”琴小姐总觉得一瞬间阿零露出了惊慌失措的表情,谁知道有没有呢?她推开门走出去时板鞋啪嗒直响倒是真的。
琴小姐费力地站起来,从门口探出去:
“别迟到了。”
她可以确定阿零听不见,但是阿零的脚步似乎短暂地一滞,她一定知道了,不仅不会迟到而且在笑。
琴小姐坐回活动室的椅子上,房间里如此明亮却空无一物。她能感觉到吸进的每一口气体都如此地酸涩而辛辣,逼着她流下泪水。她不会屈服!此刻她仿佛赤身骑在马背上,朝着不能触摸的东西抑或朝着所谓道德败坏凛凛前进。被女学生诱惑固然是可耻的,然而在这个国家,女人之间的暧昧甚至没有资格成为禁断,琴小姐无意识地用团旗缠绕着自己的手臂,那一枚被禁锢在黄色圆圈里的星星,在日光灯的惨白淫威下,显得固执而又灿烂。
阿零回到教室的时候,还有整整五分钟才到半点。阿零在学校看似一有空就趴在桌上写作业,实际上她相当懒散。因为看起来在写作业,就能方便地让别人认为自己真的全身心地投入了学习而不是别的,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了。阿零从来没认为自己是多么单纯的少女,她咬着笔头,愈发觉得琴小姐的温柔包含着一股淡淡的腥味。琴小姐宛如一杯被结结实实盖上的温开水,那种盖子外表完好,实际上里面充满了泛黄的醇厚脓液。如果刺破这样的盖子,那么杯子里的东西谁都会敬而远之,甚至连语言都不愿意触碰吧。
无论是怎样的少男少女,都是热爱恶作剧的。阿零慢慢从嘴里抽出沾满了唾液遍布牙印的笔头,一下一下戳着作业簿。铃声穿过炽热和阴冷响彻教室,讲台旁的纪律委员扣下了一小块墙皮。
如果说典型的女同性恋是指那些只被与她们相同的典型的女人所吸引且无时不刻不处在这种诱惑中的女人们,琴小姐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自己是所谓的女同性恋。而且,对于世俗所称的恋爱,琴小姐长久以来都敬而远之。这也是她年逾三十仍未结婚的最主要原因。琴小姐从未读过《浮士德》,更没有思考过花瓣的单双数这类问题,应该可以认为她从来不是典型的少女,也没有少女的那一类担忧。而非要追究背后是否有什么原理,倒不如说她对于被当做美的一类东西,不局限于官能上所能体验到的那一种,更是例如美好的天气,浪漫的婚礼,持有着本能的警惕,并非是警惕那种美背后所埋藏的不祥,而是仿佛这种美其本身就极其无聊庸俗,引着女人,那些脸颊酡红的少女变来的女人,直直地堕落。
琴小姐在某种程度上有自己的打算:让阿零信赖自己,和她维持一段短暂的暧昧关系,至于是否享用她的肉体,琴小姐倒觉得无关紧要,她认为只要那个姑娘能够做到一头扎进她的怀里哭泣这样的事就够了。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琴小姐的打算不啻于空中楼阁:她完全没有方法向阿零传达自己的想法。男人和男童的恋爱毫无疑问是绝对的禁忌,但是女人和女童之间,没有人会认为两个雌性有能力发展出被世人称作恋情的东西,因此连禁忌都不存在。琴小姐知道一个词语叫诱奸,但是她更清楚自己不可能像一个男人一样用阳具侵犯阿零,是的,女人怎么能是诱奸的主体呢?在男人主导的世界里,毋宁说是阳具中心的性话语下,她们只是在过家家罢了。琴小姐并不喜欢思考这些,当然这也不代表她有什么不满,只是作为一个女人,要把对方弄到手难免显得滑稽,但同时她又是老师,多少增加了一些合理性。
与琴小姐不约而同的是,阿零也不认为自己是女同性恋,但是,与琴小姐那种出于警惕的敬而远之不同,阿零对恋爱持有天生的轻蔑。很显然,她并不是那样因为对自身的迷恋而轻蔑一切的典型的少女,而是过早醒悟了恋爱的游戏性的同时又对恋爱的后果一无所知。
对于上次被琴小姐叫去活动室,至少在琴小姐一边不认为阿零感到了丝毫的异样,但毕竟是三十岁还没有结婚的女人,行事在稳重中多少夹杂了一些烂漫的孩子气。她相当天真地想着这一切可以悄无声息地水到渠成。
班长神情严肃地告诉阿零顾老师找她的时候,阿零看了看表,没有想任何快打铃了以外的事。在这个时候被叫出去肯定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可以少在桌子上一动不动地趴一会,否则手臂实在是硌得难受。
阿零欢快地向老师的办公室走去,倘若不是教导主任明令禁止学生在走廊上奔跑,她一定会跑着去。不是说她有多期待见到老师,恐怕仅仅是她今天穿的运动鞋跑起来很舒服。从教室的楼层上了两楼就是办公室,顾老师并不在,这没什么,另一位面善的中年女老师告诉阿零顾老师在共青团活动室等她,她又欢快地走出了办公室。
琴小姐甫一走进活动室,就毫不犹豫地打开了所有的灯。她现在几乎有些说不上来地害怕晦暗,角落里的团旗犹如电影开场前等着看戏的观众一样安静,琴小姐忍不住把它往屋子中间挪了几分,想了想又挪回原处。
“报告。”
“请进。”比起赞叹阿零懂礼貌,还是说这种程序叫人烦躁更实际些。她放慢了脚步不出声地走进活动室,没有忘记背过身同样不出声地把门带上。
她的嘴唇太黯淡了,幸好下巴的弧线很是优美。琴小姐一边想,一边不自觉地抚摸自己腕骨的凸起,慢慢地升起一种粘粘的感觉,不太像是皮肤本身的摩擦力。
“我记得你团歌唱的不错。”琴小姐作出一脸期盼的神情,努力使自己能够注视着阿零。似乎是意识到这样会让阿零很难回答,她又自作聪明地加了一句:“可以现在唱一下吗?”
阿零有些窘迫,没想到老师会突然要求自己唱团歌,她迟疑了一下还是开口了:“我们是五月的花海..........”
琴小姐不自主地愣了一下。老实说,阿零唱歌并不好听,这不奇怪,因为她之前也根本没有听过阿零唱歌。歌声单调,生硬,简直像自鸣钟的声音。
“你从“五四的火炬,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开始吧”。
“五四的火炬,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壮丽的事业,激励着我们继往开来........”
角落里的团旗一动不动,这也不奇怪,因为屋子里根本没有风。琴小姐靠在椅子上,阿零时而远时而近,身影在灼热的胶质空气中闪烁。
顾琴不能这样。她望着唱完团歌茫然不知所措的阿零,冲她笑了笑,以毋需置疑的口吻说:“去把窗帘拉上吧,别吵到了同学,已经午休了。”
“我不是音乐老师,但是对你的歌唱有几点感觉。”
“第一,调子找的很准,这个很不错。”
“第二,声音太单薄,你也有感觉吧?我们要拿出共青团员的气势;第三,你别老盯着脚尖嘛........”
琴小姐一边说,一边鬼使神差般地伸手想摸阿零的头发叫她抬起头,阿零却多少显得有些害怕,向后缩了一点,琴小姐想收回手,又觉得尴尬,只好硬着头皮微微碰了下阿零的头发,只是她确实没注意到,阿零作出了一个类似不好意思的微笑。
已经是五月了,阳光也不再能那么完美地隐藏自己的恶意。万幸,琴小姐记得自己是共青团辅导员,而面前的女孩是团支部书记。
“这样吧,我告诉音乐老师,让她明天开始中午有空的话给你讲讲。”
“音乐老师?”阿零奇道。音乐老师刚刚毕业,有正在热恋的男友,提起她,阿零首先想到的不是尖锐的歌喉,而是她嘴唇的殷红色。
“就是她,”琴小姐假装在看自己的指甲,“今年活动不出意外团歌也是你唱。”
“老师,那,还有什么事吗?”
“有,”琴小姐机械地翻着桌边的资料,“先别走。”
我説一下,結局大概是二人被男生A(這麽個人)發現,慌亂之下沙掉了他埋起來(不要吐槽這個......)。多年以後,琴小姐因病去世,阿零回到母校附近,挖出白骨.......
這個小説沒什麽政治隱喻,恰恰相反,它是反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