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城疫情漫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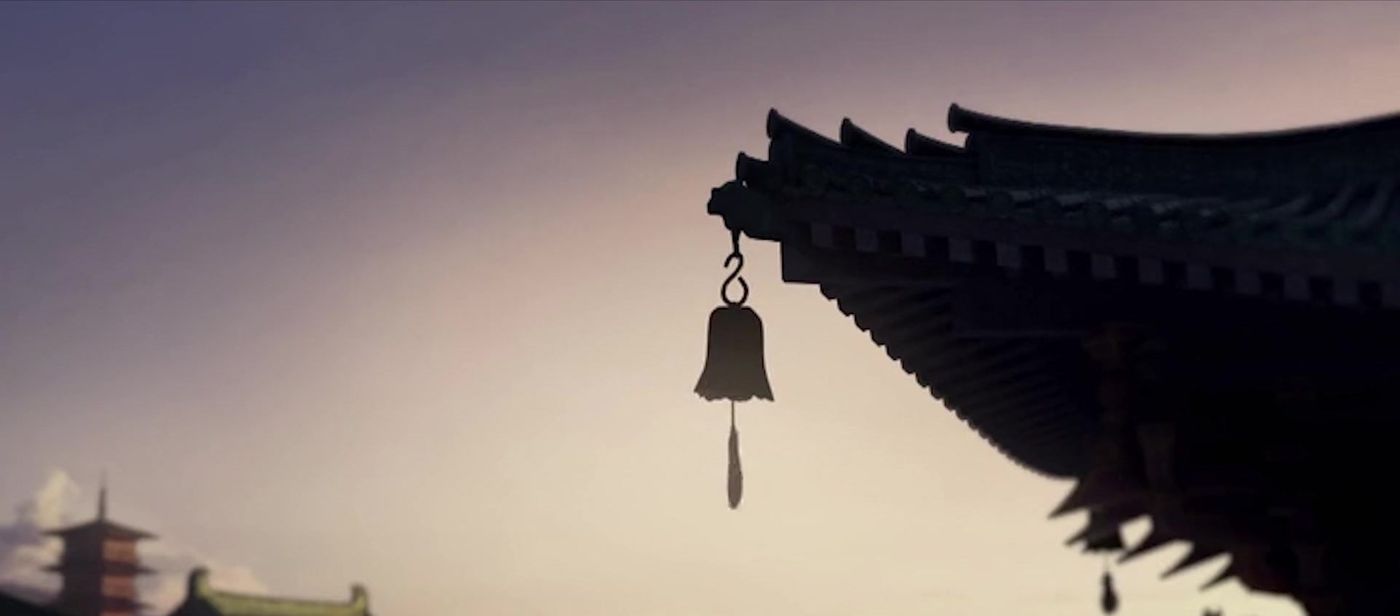
天气上好,阴蒙蒙的天偶尔会有一些蓝色,时不时会下场零星小雨,院子里的草被打湿了,和土结成泥巴,偶有蜗牛攀附在上面。
最近雨水挺多,如同往年墨尔本七八月的天气。这个我记得牢,七八月是我初次登陆墨尔本的月份,绵绵细雨让我曾误会墨城如同中国南部大多数沿海城市,雨量丰沛,温暖潮湿,阴冷的冬日也常常因为没有阳光不能晒被子让我头疼。就如同相声里提到的段子:一个礼拜下两场雨,一场三天,一场四天。雨季之后让我又重新认识了一遍这个倔强的城市——足足长达一个月的晴天,让人哭笑不得。
我大概算了算日子,去年的雨季没有如期而至,结果推迟到了今年上半年,这让我联想到了去年那场受到全世界瞩目的大火足足少了几个月,各路专家纷纷发言寻找大火的缘由,我在网上搜罗一番,倒是搜到一部分那些关于气候变化的言论,被左与右的政客们拿出来当做辩题好好发挥了一番,至于结果是什么,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如今早已被世界人民逐渐淡忘。
现在的主流话题是新冠肺炎,几乎所有的新闻栏里都有醒目的大写标题COVID-19,每个人开口闭口的话题就是“新冠”,以及“新冠”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各种影响。我相信大多数人这一生几乎都没有经历过这般严重的全球性创伤性事件。上次金融海啸被更多人看做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其影响力和今天的疫情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我和老婆吃饭时闲聊,她突然来了一句:“上次人类经历这种大灾难是什么时候?”我粗略地在脑海中翻了一遍我中学时期的历史课本,随口说道:“二战吧。”说完我身子一激灵,仔细地又思考一遍,惊叹地对自己说:“可不是么!”
三月底,维州进入第三阶段政策性防疫,这意味着除了必要行业(加油站,药局,修车行,物流快递,重工类分销商等等)正常运作,其他行业一律关门,这意味着通勤的路上人更少了,更多的人留家工作,或停薪停职,或失业,随之,城市安静的像节日里祥和的清晨,我上班的路上又恢复到十余年前一样通畅,这是人们记忆中那个地广人稀的土澳。为了维持中小企业和居民的生计,议会也通过了一项名为JobKeeper的补助政策,用以缓和“新冠肺炎”对企业的打击。
在第四阶段防疫政策推出前,也就是疫情加重前,我尚可幸运地去上班。谢天谢地我还没有失业,这的确让我花了很长时间用居安思危的心态审视我的人生。一直以来我是个会花大把时间来充实并享受私人时光的人,勤恳地工作并把盈余的积蓄积攒起来用以未来的不时之需,像最为传统的中国人。突然一场可怖的瘟疫事件,不断地敲击我装着传统价值观的脑袋,我发现自己应对风险的能力令人堪忧,便开始不断反思是不是自己也到了对人生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了。我真是个后知后觉的人。
上班路上广播里的主持人探讨关于警察一点五米社交距离惩罚的事件——有人开着车在副驾驶上载着人被警察拦路,警察称这违反了一点五米社交距离的规定。我的天,这算什么?我和我老婆同居一处,开着车载着我老婆去逛超市,这会不会被抓呢?我为此在网上做了研究,政府确实也为此做了解读:同居一处的人除外,驾驶商用车工作的同事除外。事实上,爱戏谑澳洲民众并不满足这种解释,某新闻台对此通过一个搞笑的节目做了实验,为了证明一点五米距离的不可操作性。比如在公车上,前后排乘客必须保持中间空着一个座位才能达到一点五米以外的距离,出租车上斜后座和司机的最大直线距离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一点五米。一家专门为汽车做评估的网站也打出了半玩笑的广告:一点五米的距离只有福特F350做得到。
这个满满乐观和喜剧的世界,怎么能让我们对生活失去希望呢?
办公室里依旧像平日里那么忙碌,特别是电商部门,比平日里的活儿似乎还要多。我在Spotify里听到关于电商平台的广告,比如“待在家里,去上eBay”(stay home是最近电视、广播、街头宣传标语中平凡出现的口号)。尽管新闻上重复出现违反规定外出聚集的人,但是,确实很多人真的已经宅在家里,这自然使得电商平台上的销售不减反增。当然我们这些搞户外产品销售的人,心里非常清楚,这些需求都是短期和暂时的,若疫情不能早早退去,这个虚增的销售迟早是会跌入谷底。对此我深表忧虑。但是,如若疫情不能早早退去,在这个高度工业化的时代,死去的可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谁又不是这个大时代的牺牲品呢?
我们公司是一家中西合营的企业,简单来说一半的投资是本地的,另一半是从中国来的。因而也有不少的华人员工。供货商有不少都是国内的工厂,产品基本上都是中国造(澳洲的经济模式几乎要把制造业逼近黄昏产业,大多数产品都源于进口)。基本上来说,我们就属于澳媒口中常常提到的“被中国资本渗透的企业”。整个疫情期间,像我们这种高度依赖进口贸易的企业受伤最深。前些日子有一个关于澳币汇率跌破4元RMB的截图在我的朋友圈里疯传,相较于去年(事实上去年经济因为贸易战已经变得十分不景气了)我们的产品成本因为汇率一项因素就疯涨了百分之十,更不用提产品本身的涨价。有些供货商甚至提出了下单要50%订金这种“疯狂”的要求,公司的业务近乎举步维艰啊。但是,将心比心,整个行业谁不是在生存边缘挣扎呢?嘴上说别人“疯狂”,自己有时在别人眼中难道不也是“不可理喻”吗?那天我和老友马小途电话里聊天,他在墨城是做建筑行业的,叹气说,开发商的合同是死的,投资额就这么多,可供应商那边建筑材料的成本几乎一天一个价地涨,工地上的工人因为疫情不想开工,老板气得直跺脚,工期拖得久,发工资都跟挤牙膏一样,一直喊着:“别问为什么,干就是了!”我听完一阵心酸,认认真真地说了一句:“兄弟,坚持,活下来就是胜利。”
老撒吊儿郎当地坐在办公室外的院子里,翘着二郎腿说:“好歹澳洲的工作很多还没有中断呢。中国这么庞大一个经济体已经停工好几个月了,对于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他对停工这种事的点评让我的身子一激灵。是啊,如此庞大的一列经济列车,停工数月再想重新启动,那得多大的损耗啊。整个市场的供需平衡又得重新调节,在这个过程中,得多少人为此失业,没有收入,降低消费和市场需求,牵连销售和物流,还不上房贷,牵连银行业,以及其他行业的信贷,还有金融市场,新兴行业……一层牵扯一层,疫情就算得以控制,它所带来的后续影响也将是排山倒海的。想到这些,我对远在故乡的亲人朋友以及广大的同胞多了一份思念和担心。
小树是我高中同学,也是一名三本的大学老师,因为学生不复课,工资从一月份开始一直被拖欠,房贷全是靠爸妈的退休金来补贴,整个人几近崩溃,却依然坚持给学生们开网课。她说,心里不舒服,但是不能对不起那些想学习的孩子们啊。倘若是搁在高中那会儿,以我们俩的交情我必然是要尽全力挖苦她这股人民教师的敬业之情,但是如今当下这悲苦的大环境下,她居然让我差点热泪盈眶。我只是在微信里留言说:姐们,挺住。然后把她的这条消息删除。我是性情中人,我是不能忍受让这种触动内心的言语存在我手机之中,不想夜深人静再翻出这种绝望的对白,迫使自己潸然泪下。
人不遇上大事件,是不会轻易暴露出自己的人性本色。有情义的人会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追求利益的人会四处寻找商机。疫情爆发以来,朋友圈里的确出现了不少贩卖口罩、贩卖消毒液的人,最近澳洲查处不少劣质进口口罩,并颁布法令禁止口罩的个人进口行为。毕竟是中国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换个企业名号继续进口转卖,并打出所谓的各种听都没听说过的机构认证的广告加以宣传,顺带加个价让消费者心安。另一方面,疫情在国内刚爆发时,我们当中有一波热心青年说要组织志愿者回国支援,只是后来因为航班被陆续取消而作罢。还有一拨人在澳洲搜罗口罩,打成包裹无偿寄往中国去帮助从未相识的同胞,直到后来由于太多口罩包裹使得政府临时出台政策,不接受私人口罩捐助。另外,还有一件事,一二月份时澳洲政府要求但凡从中国来的人都要回家自我隔离十四天,不少独居的华人独自在家无人照料,不能出门购物,一是没有生活用品,二是一日三餐靠点外卖。那段时间墨城许多华人自行组织免费送货团队,如若有独自在家隔离的人(因为用微信沟通,所以主要是华人),可以联系这些团队的成员,列好清单委托他们去超市或者餐馆里购买,免费为隔离者送货上门。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来澳十年光景,这种以无私奉献帮助他人为目的的自发组织小团体,我只见华人干过。这和洗脑的爱国主义或共产主义教育没关系,这是华人骨子里的东西。这般国人尚在,中国岂会亡哉?
老撒点了一支烟,他说这是他自己在家卷的烟。过去十年来澳洲烟价几乎保持每一个季度一涨的趋势,在价格上间接迫使居民戒烟。老撒为了图便宜,不想买现成的,于是在超市里买了一大包散烟丝,回家关着门,全家人一边吃着火锅聊着天,一边卷着烟卷,其乐融融。反正家里烟民多,除了他自己,他老婆、岳父和岳母,一群大烟枪。每到想抽烟时全家跑到院子里围成一圈(澳洲室内禁止吸烟),有说有笑的一起抽,还能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全家除了上小学的儿子不抽烟,但这不妨碍全家一起卷烟草的“娱乐活动”。按照老撒的说法,全当是给儿子上手工课了,开发智力,比比心灵手巧,卷得好卷得快会有额外零花钱做奖励。
疫情期间的欢乐都是靠自己。在这悲苦的时期,缺钱缺物,尚且有好心人相助;可你自己不快乐,谁会来帮你?
老撒生性乐观,人高马大,思维简单,人云亦云,每日偷闲刷遍朋友圈和公众号,总是最早的获取“第一手”信息,不假思索地第一时间分享出来。他移民较早,二十多年前就已经登陆澳洲,老早换了国籍,他的英文水平能怎么形容呢?天花乱坠!想到什么就来个什么,说话时手舞足蹈,也不管说得对不对,洋人被他这么瞎比划,居然连猜带蒙都能理解他在说什么,也能欢声笑语地打成一片。我倒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本事,把老撒搁一百多年前,他这就是“洋泾浜”的油嘴子。去年香港闹得最凶时,中国留学生在澳洲多处举行游行,高喊口号:“中国加油”。老撒刷着朋友圈和公众号,突然来了一句:“这些中国留学生,花着爹妈给的钱,吃香的喝辣的,连苦都没吃过,他们知道香港长什么样吗?他们能懂个啥啊?”当天下班回家,老撒在微信上发了个朋友圈,一张墨尔本留学生游行的照片,配了一行字:“中国加油!”
老撒最爱老聊的是自己的家事,比如他老婆生孩子时政府补了多少钱,老婆怀孕时市政三天两头做家访,生完之后来还会来定期探望,老婆常年没工作,政府又补贴多少。然后他打趣地说道,中国人民建设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结果一出国就全实现了。说完他仰头大笑起来,似乎什么都无法阻止他爽朗的笑声。
我也想笑,倒是没有什么恶意,我们总会遇到一帮特别有喜感的小人物,他们简单,随大流,明知好歹却不分对错,选边不站队,因为不愿被主流抛弃而没有原则。这些心猿意马却有趣的新移民,吃着资本主义的饭,爱着共产主义的国。
我们这些远离故土走江湖的人,谁又不是呢?
和老撒相比,小奕理性很多。小奕在公司管财务,每天早上会和我核对前一日的销售情况。姑娘人漂亮,身材高挑,英语发音比词典里的录音都地道,还找了个本地洋男友。小奕的视野比老撒要宽,她勇于也乐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有理有据地支持这些的观点。她理解和同情香港人,她对中国今天的一些发展模式有异议,她对当前的国与国之间地缘政治有一些非同主流观点的见解。她可以搬出很多理论和逻辑,不乏一些古典主义的圣贤思想和与时俱进的超前观念,她有一套自己的价值理念去解释她眼中世界的运作规律。总之,她是那种,书没白读,学没白上的好学生。既然小奕这么优秀,这么有思想,她的生活和人生轨迹应该是明确的吧。其实真不是,相反,比老撒更矛盾,更迷茫。
按我们当今的说法,小奕在国内是个既得利益者,是那些拥有资源分配权的集团的二代。她倘若在国内,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做到人上人;在国外,又可以携着巨大的资源开启另一种超越同龄人很多的生活模式。有些人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做的很杰出,说得就是她。这种姑娘自然是父母中的掌上明珠,真正字面意思上的千金、格格、公主、大小姐。家人盼着她能回国,承接父辈来之不易的资源,这也是小奕人生路上最大的迷茫——关于自我和现实的分歧。
受西方自由主义观念影响颇深的小奕,并没有靠着自己继承来的资源开拓新生活,而是选择了一家不起眼的中小企业做了不起眼的财务会计,拿着无关痛痒的薪水,过着低调的生活。还违背父母意愿找了一个和她未来事业毫无关联的外籍男朋友。只有在年会时喝醉酒的小奕才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分享给我们,她并不敢反对父母,而且并不愿意反对;她不敢数落这个国家的不是,而且也不愿意数落。谁会坐拥着金山银山又骂娘呢?小奕的叛逆如同小孩子吸引旁人注意力一样,简单地哭哭闹闹,让你们知道我的存在,让你们知道我内心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大人们能明白我的理想主义的躁动,然后说几句安慰好听的话把我哄回家就完了。谁没有年轻过,谁没有叛逆过呢?国家不只是机器,人民也不只是零件,没有理想主义年轻人的躁动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人都迷茫,不管来自哪个阶层。想着一,说着二,做着三,我们常常说这个叫含蓄,这其实是一种美化。中国人的分裂是常态。
午饭时间,我把前一天准备好的食物放进微波炉。疫情期间,我老老实实在家把第二天的食物准备好。不仅仅是餐馆大多数关门,外卖公司人手也紧缺,更重要的是物价也在飞涨。除了一些只接受外卖订单的餐馆继续营业,大多数店铺处于无限期关门的状态。开始有人讨论复活节的假期,长达四天的宅居生活是非常漫长的。新闻上说一些州际道路上出现了长途旅行的房车队伍。一些人在FB上留言称这是愚昧的行为,我觉得不少沉默者应该怀有纵容之心,他们要么已经在休假的路上,要么在收拾行李准备出行。
洋人对这次疫情尽管没有轻描淡写,但是心态上还是保持着“不要干涉我的生活”。比如洋人对戴口罩这种行为十分抵触。他们要么觉得口罩是留给弱者的,要么觉得戴口罩的人应该是病人和医生。澳洲政府也同样不鼓励民众戴口罩,原因一是物资紧张,把更多的口罩留给病人和医生;原因二是戴口罩的人走来路上会引起其他路人的焦虑。所以如果你没有生病,特别是咳嗽,请不要戴口罩。好吧,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的焦虑谁来救治?
公司从中国来的货一个礼拜前已经到港,但是迟迟不能来。原因自然很复杂,比如海关方面,码头卸货,路上司机,任何一方掉链子,工作就没法正常进行。但是归根结底原因只有“新冠肺炎”。这四个字几乎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前些日子有一则新闻,说中国来的集装箱在墨尔本到港,但是港口工人不愿卸货,他们担心被传染疾病。这则新闻在华人圈和中国又炸了一回锅,说这是赤裸裸的歧视。老婆愤愤不平地跟我抱怨着这些澳洲人的行为和思考方式。我安抚她,说,当时你怎么评论你们公司那位武汉的同事?人家一没有回武汉,二没有生病,你怎么就莫名其妙心生恐惧了?而且新闻上也说明了,按规定,任何在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货轮不能直接入港,这艘船从中国出发到港时只有12天,所以不合规定啊,码头工人们做错了什么?
当然不用说,这种新闻在中国必然和种族歧视、爱国主义挂上钩。现在中国弥漫着一种诡异气氛,就是唯恐国外不乱。越是乱,中国一些媒体和自媒体越是兴奋,越是碰到中外冲突事件,一些媒体人像是被戳中了兴奋点,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渲染成一波国际性事件,发布出来就能赚取一大波“爱国义士”的口诛笔伐。他们也倒不在乎所谓的新闻从业者的操守,只要读者爱看,他们就能写,我甚至觉得如果法规上不限制尺度,他们会在每篇新闻文章的最下方贴一张成人片美女私房照。这些年,在主流媒体和各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中国的”爱国主义”情怀日益高涨,这种高涨并不是我印象中当年爱国者的情义表达,它本应该是一群热血青年为脑残哈韩粉组织网络圣战,或是爱国青年为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岛而上街高呼寸土不让,或者为了国家的未来手握鲜花集体为自己的理想发声。现如今,它已经成为一种被滥用的情绪宣泄,就像一场山火不停地燃烧,一拨人还在不停地添柴加薪,唯恐火势渐微。更可怕的是,它已经完全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本应该有自己独立思考,忧国忧民的群体,如今也开始变得“满足现状”,“排斥异己”,张口闭口“我爱祖国”,怀揣着”为大国而照顾好小家”的情怀。
吃饭的时候,阿浩发来一则微信,是转发微博的视频,内容是外发华姐怼外媒的日常,然后阿浩给我加了一句评论:”她说的挺有道理;我爱我的祖国。”我顺着他的话也回了一句:“我也爱。”
阿浩是我发小,一个爱读书却莫谈国事的人。他突兀的评论让我无言以对。
吃完饭,我看了一眼街道,昔日拥挤的主街上,车辆稀少,天色渐阴,似乎是随时一场阵雨将袭。
胡哥给我一份文件,关于几份本地供货商即将断货的通知书。上月初,几家本地供货商信誓旦旦说尽管疫情传播严重,只要政府不说关门,他们会和客户们一起奋战到底。可如今,在现实面前,这些商人们也不得不露怯。其中有一份来自本地印度裔经营的工厂,用简短几行字诉说人在他乡辛劳经营的困苦,因为当下困难的情况而提出涨价的要求,以及不太诚恳的歉意。这很有意思,印度人是整个市场里做生意最没有底线人之一。他们的扩张策略一直以来都是用最低的价格占领各个层次的市场,这是我们老一代华人玩剩下的把戏。一个成熟的资本工业系统可没有那么多的价格空间用以让利,印度人敢继续这么玩,只能说他们还有一点法制不健全的优势可以利用。之前本地洋人一直和中国人做生意,因为成本低,一度使得中国货长期占据澳洲市场,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货的质量和产品层次都在逐渐提升,使得廉价工厂向印度和东南亚地区转移,本地商人开始与印度、孟加拉、越南等国的供货商合作,当时这对中国贸易带来一定的冲击。但是长期的贸易关系网和成熟的工业生产链让中国有不可取代的优势,澳洲商人和印度人经历一番蹩脚合作之后(质量不过关,管理系统混乱,交易速度迟缓,商业信誉堪忧等等),最终还是决定回来选择和中国进行长期的贸易往来。
中国供货商与以往相比,整体素质的确有提升。但是因为法制不健全的问题,常常还是遭到诟病,比如代工厂偷取专利的行为,的确严重扰乱了市场的正常运作,很多非常有创造力的公司因而失去了创新活力,产品也在市面上被压成白菜价。尽管我并不支持Trump发动贸易战,但是关于知识产权上的争议,我和我的同僚们的确有不少保留意见。可悲的是,印度人的公司却丝毫不差地继承了这种恶劣的习性。所以从某种角度来看,一些恶性的特质其实与国家和民族文化没什么直接关系,而是源于经济发展规模的水平。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当今一些左派经济学者主张,大力发展经济,许多现实难题必有新的解决途径。
“如果再没货,我们大家都要转行了。”胡哥带着怨气说道。
胡哥是东北人,理科生,务实派,做事干脆不抱怨,有问题就想办法,没办法就找出路,从不知难而退,原则只有一个字——钱。哪里有钱挣,哪里就是天堂;哪里有饭吃,哪里就是乐园。不管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还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只要有利可图,他就乐意往前冲。按照他的说法,“吃别人的饭,还骂别人的娘,那才是孙子。”
但凡利益至上的人,活着都不会太辛苦。胡哥在外面也在搞别的买卖和投资,挣钱的思维随时随地在线。但是凡利益至上的人,必招人嚼舌。无论做什么事,都得先考虑我从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这些事值不值得我做。一旦做了,之后收益一定也要顺利拿回来。这种人自古被定性为“势利小人”,为中华文化所不齿。
我的好友老阮曾经跟我讲过一个经历。他说他初到美国时,跟着朋友去了教堂,闲暇之余上前和一个上了岁数的香港老阿姨搭讪,阿姨问他哪里人,他说中国来的。阿姨先是有些排斥,看他长着一张善意无害的脸,就说:她不太喜欢和大陆人打交道,因为大陆人找她说话,多半都是要有所求。他这个故事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出国时尚年少,早早和同学朋友们断了联系,也不懂得国内那套维系关系网的本事,平日里偶尔发个消息问候老友,少有人回应,凡是有人回应的多半也要先问明白向问何故。朋友们”无事问安,有事免聊”的态度让我对这种情谊失去了兴趣。你们这些人呐,先给自己筑起一堵高墙,在高墙之上经营着自己所谓通向“成功”的关系网,无利可图者皆为墙外人。都说昔日友人皆陌路,世俗难寻一知己,活该啊!你们的墙太高,我攀不起。
胡哥也算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作为中国人,他恐怕算是活得最明白的。只是,国人活得越明白,这世人也就越看不明白。
闲暇时,温妹发来一段我外甥女的短视频,视频中的年仅三岁的小朋友留着金太郎齐刘海,咿咿呀呀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确实被可爱的表情逗乐了,但是没有回复。出于好奇,我搜索了一下五星红旗的含义,上面四颗小星星分别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被环绕的大星星代表的是党中央。突然想问,每个阶级他们都还好吗?都迷茫吗?我又是哪个阶级?
前些日子,我和老阮通了个越洋电话,他人在美利坚,当时我算了下时间,他那边差不多得到下半夜了。老阮说他认识了一个脑袋栓在裤腰带上的人,他决定要随他而去。我说你这是要背叛革命啊。他说不管了,他意已决,这回是要玩真的,这要是还敢回国必然小命不保。我说你还有父母家人啊。他说儿不能侍父母是为大不孝,兄当替我孝之。我说你还有没有别的要说的。他问我,此去他会不会就成了郑耀先(电视剧《风筝》里的人物,共军在国军军统内部的高级特工,解放后两面隐藏身份以求自保)。我说,别闹了,郑耀先是英雄,你顶多是徐百川(《风筝》里的人物,军统高级官员,解放后向共军投降,出卖了当年诸多兄弟)。
老阮最要好的朋友,国内有公职,早年公派美国留学生,高学历人才,不知近日突然为何声称自己坚信疫情背后有大阴谋,决意放弃国内一切繁华和前景,甘愿做一只漂泊江湖的孤魂。下班时,我随意给他发了一则消息,这是这个礼拜的第四条短信,一直未读,亦未回复。
下班时,我高中同学大舒把我和小树拉进一个群,噼里啪啦洋洋洒洒写了满屏的文字,大体意思是质问我:为什么国外反华势力如此过分?我们明明过得很好,他们就是见不得我们好。我开车时没注意到这则义愤填膺的言论,回家时才仔细研读一番,然后回消息说:我没反华啊,我很爱国啊!大舒回复道:不是你,是那些西方人。我说:你看见什么了,让你如此气愤?大舒说:方方日记,现在她在西方人眼里可是圣女贞德。我说:什么日记?谁是方方?
我抬头问我老婆,说:“你知道方方日记吗?”
她回应说:“知道,写武汉疫情的那个。”
我说:“这日记怎么了?”
她说:“没什么,就是说了一些批评党和政府的话,最近在网上挺火的。”
我说:“火?我怎么不知道?”
她扭头不屑地看着我,一脸嫌弃地问:“你知道现在联合国秘书长是谁么?”
我说:“不是那个韩国人么?”
晚上夜深人静,窗外又淅淅沥沥下起了雨,雨棚被胡乱地敲击着,我能感受到被雨水驱赶的蜘蛛、飞虫,纷纷躲在我家屋檐下避雨。世间多灾多难,人艰苦前行,总需要一个避难所。
我打发着时光看着闲书,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是小苗发来的消息。
“熊啊!叫你聚一聚你不答應,估計要等到十月之後,到時候我都要生啦!”
她指的是澳洲最近发布的禁止外国人入境的消息,而她在上个月月初回到了台湾。小苗是我前女友,我们早在刚登陆澳洲时就相识了,在当时最艰苦的一段时光里我们一直相依为命,也算是半个患难之交。尽管因为一些客观因素使得感情没办法继续下去,但是却一直保持着联系。后来她嫁给了一位新西兰人,虽然没有拿到永居签证,但可以和配偶一直无限期在澳洲居住下去。最近她告诉我刚刚怀孕,为了避一避澳洲疫情的风头,先回台湾养胎。
“你现在在台湾吗?”
“是唷,台灣的疫情比澳洲要好很多呢。”
“你还能回得来吗?”
“能,但是要在雪梨轉機,還要在雪梨自我隔離十四天。不是我不想,雪梨的情況太糟糕,寶寶會死的!”
“可是台湾现在也不安全啊!”
“你是指要打仗嗎?我懂。”
“看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能避开最好避开。”
“唉,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呢,有些事我們避不開,也逃不掉。”
“嗯。”
“我們偏偏都趕上了這個大時代,這也算是一種緣分吧。”
“那你可以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會的。你也是。如果有可能的話,等一切都過去,天下太平了,我們在墨爾本見。”
我放下手机的那一刻,热泪盈眶。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作为一个人,在大时代中随波逐流却无能为力。而作为一个华人,我们常常胸怀天下却如同一片秋叶随风飘散。我们常常执着于一件我们心爱的事物或重要的人,可言语和行为上却在现实中扭曲不堪。我们时常迷茫,时常奋进,时常善意,时常世故。我们热爱金钱,却又视金钱如粪土;我们树立理想,却将自己置身于现实大潮当中飘荡;我们寻找信仰,我们甚至一次次击碎自己苦心建立的信仰。我们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人?许多曾经无偿为国人出力的海外华人,回国时却遭到同胞们的驱赶;许多忧国忧民的人提出自己的想法时,却被国人扣上通敌卖国的帽子;许多人面对着国外的不友好又要极力挽回着中国人的颜面,同时却被国人认定为卑躬屈膝的奴才。他们在江湖中混迹着,同时维系着故乡亲友的关系,身虽追求自由主义,却又被主流声音左右。不得不说,我们自古以来都是一群迷茫且背负苦难的族群。世间中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掌控着我们所有人,让我们逃不开,躲不掉,如同近日连续收到那些亲友们时不时对我传来的爱国信息,我甚至认为这是某个势力对我传达“拨乱反正”的讯号。我曾经也认定某个政党或者某个集团无所不用其极地渗透我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我所背负的“华人”这个文化符号本身,既是一种无限荣誉的光环,又是一种束缚前行的枷锁。我们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啊?一边歌颂着自己自信和自尊,又一边诅咒着自己身上的污点,如此的伟大,又如此的卑微。
雨渐停,天未晴,依然阴沉潮湿。周末的清晨一如既往的宁静,躁动的似乎只有人心而已。
我们写作时常在开头描绘眼前或窗外的美景,然后寄情于景,修辞上称为“比兴”。这种浪漫的情怀可以追溯至《诗经》的年代。自古以来我们从未改变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