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王影评|王子不复仇
不知道看完狮子王的结局,感动之余,你有没有觉着好像哪里不对劲。
这个不费吹灰之力的结局让我对着窗外的树愣神了很久,然后回过头就想把这意犹未尽一层层剥开。

全文约7500字,阅读时间7-15分钟。
(1)
我曾经最爱看复仇时刻的痛快,会忘我的拍着大腿扯着嗓门为“正义的角色”加油呐喊。不耐心对抗的微妙,只想快些有个快活的结局和解脱。甚至于我的朋友们都不爱和我一起看电影。
现在Scar坠落悬崖的时刻,我的眼神却和Simba一样的失落,失望和无助。虽然不确定其中多少是Simba的失落失望和无助,还是只是我感情的投射。

为了合理化这个结局,我只能认为,迪士尼一贯的完美大团圆结局中寄托了太多不完美世界中对完美世界的渴望。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一剂避难的麻醉,也是对复杂现实的逃避。
这结局也是一种现实的影射:我们如何在各自的现实中逃避现实,没有巨大的耐心和勇气去直面自己的命运,去直面,悦纳,重构不完美,而是仓皇躲到完美的想象里。我们是如此,所以迪士尼的电影是如此。
尽管如此,还是觉得:这个仓促单薄的结局,没有探讨更复杂真实的人性和命运,过于轻易、刻板、绝对的流放了抹杀了一个角色,一种力量,一部分自我和世界。这过于简单绝对僵硬的是非对错再一次劫持了观众。或者说,这原本困住观众的世界观自身又生产了另一个形而下的故事。
(2)
个体生命和世界本身的内在张力,复杂多层,矛盾冲突的“力”之间的风起云涌,不是过于简化的二元对立、绝对黑白分明的的“善” vs “恶” 叙事能够捕捉的。
即便在“善”与“恶”相对流动的二元对立的叙事里,Mufasa和Scar也是一体两面,被这两个角色所象征的力量不停拉扯,是世界的,也是个体的命运。或许有一些张力没有在意识中注册。但对于“恶”的单纯抹杀也是不符合个体和世界内在流动的“善”与“恶”的持续对抗的。
揭开“善”与“恶”的绝对的二元对立的面纱,“正义”本身往往只是一个视角,不同的视角意味着不同的“正义”。
只是不知道对于“单一正义”/“一个真相”/确定性的寻求多少是天然的冲动,或只是文化的规训。记得第一次听Sanders的正义课,欣赏惊讶欢喜之余,也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他只是不停的抛出迷人的道德问题,然后不停的让学生就同一个问题给出形形色色的答案。没有一个确定的“参考答案”让我急于寻求闭合的认知回路敞开着,像小猫在我的心里磨爪子。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正义的真实的面貌恰恰存在于认知敞开的状态,恰恰存在于多面甚至矛盾本身。电车难题里,到底是让电车顺轨而下,杀死轨道上的五个人,还是转动命运的开关,杀死另一条轨道上的一个人。难题也正是答案本身,它回答着正义天然的多面性,相对性。个体的正义往往只是盲人摸象的局部。
绝对刻板的正义是天然强者的话语,是暴力的合法化外衣。就好像电影里的女一号获得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正义,而其他角色哪怕是企图一点点都是邪恶的,是可以不择手段去消灭的。而如果重新写一个站在女二号视角上的剧本,那么正义的站队也会惊天逆转。女二号也是社会里的“他者”,影射着非主流边缘弱势群体的命运。
这流行的绝对和确定,怕是比Covid-19更为危险也更为久远的传染。
许多个人的,社会的,政治的许多看似无解的难题,其实可能只是被绝对,极端,固化,刻板困住了。
绝对的二元对立,和建立在这种根本绝对对立之上的暴力,像一张网,困住的不仅是对手,同样也网住了自己。把对方置于隔绝的僵硬的对立面,打上了不可理喻的敌对的标签,于是无法看到对面这个人的特质,无法去试图理解ta的相信,于是对面不再是和你一样有着各种无奈却又鲜活生动的人,而是一个敌对符号。暴力,也就在消灭敌对符号这天然冲动中被合理化了。而自己心里这把隔绝的,对立的,仇恨的火只会越烧越旺,直到把自己的心也烧出一个黑黢黢的洞。
如果我承认我的正义是有限的正义,我的正义包含着你的正义,就无需复制暴力,去争个你死我活。如果人人都能有着这样的正义观,人类苦难是不是就有了天然的出口。巴以冲突是如此,性别的、种族的、阶级的、左右的、科学与人文的、所有一切的对抗也是如此。
过去几年,我在性别研究这个领域里,痛苦的解构建构,但最终学会的,却是不再用性别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和个人。而是彻底去掉性别的标签,去看每个个体最真实的存在,用一种更为普世包容的话语对话,去建立共情和理解。
而性别也只是冰山一角,在任何一种我们选择相信的对立中,打破僵局的互相理解和妥协往往发生在彼此扶持的话语里,而不是彼此敌对的话语里。
理想的状况是,无论是在个体或者集体层面上,对立的双方都能放下成见,真正看清彼此,看见彼此同样的恐惧和挣扎,热烈和生动,于是能携手共同逃脱过去编织的牢笼。对抗也就变成了1+1>2的命运共同体的神奇。
哪怕只要对话中的一方愿意放下过往和成见,也能消解很多的对立与仇视。如果我选择不去穿一个受害者的视角,那么你也不再是我眼里的施暴者,于是最起码在我理性的感情的王国里,我理解你的恐惧和你的正义,于是无须复仇,因为仇恨,对立无从而起,在理解中被消解了。那么即便对方依然来势汹汹,也会在对立的消解慢慢卸下怀疑和敌意的武装,艰难而缓慢地在新的话语里脱胎换骨。
但也必须承认这个论证的有限的正确和在现实中可能的危险,也必须承认有时必须经历对抗,愤怒,冲突,甚至毁灭,达到危机的高潮,才会有反思,才能去实现真正的对话,理解,共情,妥协和重建。
对抗和妥协都有可能,是因为人内在有着固化和流变,狭隘而宽广的可能。
我很爱玩狼人杀一类的推理游戏,爱在游戏里看人有时一条道走到黑,让一场游戏江河日下,有时人的灵活又是如何力挽狂澜。
我们都多多少少会被基于种种印象和伪逻辑的闭合认知困住,也会在新的事件和证据面前去推翻重构。
但有的时候在人身上会出现一种基于自我闭合的“迷之自信”:一旦有了一个闭合的解释,哪怕不合理,也不再接受不去理解不再探索其他的可能的解释,并且无比相信自己掌握的就是绝对的真理。
“迷之自信”看起来像一个无解的循环:越是在自我和信息隔绝中偏执狭隘,越是缺乏探索其他可能性的能力和工具,就越是对自己的认知内的小世界无比坚定的相信,就越偏执狭隘而“迷之自信”。或者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是不足之上的不安驱使的自我合理化的循环。
但人是可以从刻板绝对成为流动灵活的,在不停犯错不停走弯路中累积的智慧和勇气,和一颗主动或者被动开放的心灵,终有一天会让我们与自己不完美,不足,不安虚心承认,诚心悦纳,不断和解。“迷之自信”会有进步成为迷人的自信的那天。
而迷人的那种自信,是最自谦的,同时又是最坦然从容的,建立在承认和悦纳自己个体视角的天然不足之上,于是你相信所有可能的相信。完整的视角,恰恰是没有视角,打破界限,江河山海流入。无所是,于是无所不包。我想,以柔克刚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吧,你没有敌人,因为你的敌人都是你的一部分。《道德经》中的“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大概也是说的这个理。
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都在惯性的裹挟下,用习惯的熟悉的方式滚滚向前。遭遇巨大的阻力时,自然的习惯是击碎这阻力的巨石。然而汹涌江河在和巨石的敌对里,自身也破碎成无数的水花。
有时不得不让这碰撞发生,于是河流才能改道,天地才能转圜。但更多时候,河流的惯性如果能够被因势利导,松动一下命运河道的泥土,在新的疆域里,对立消解,巨石和河流得以两全。
而作为个体的水花,被汹涌裹挟推搡的同时,也在彼此翻腾喧哗中汇成历史社会生命的江河:每个水花的选择也决定了江河的流向。
(3)
理解scar角色的复杂性,也是理解复杂自我;和scar和解,和复杂自我和解。
穿着这种非绝对正义的眼睛,我们才能体谅和理解Scar角色的复杂性:Scar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是伤疤,也是创造伤疤,同时也是伤口结痂。长兄Mufasa的名字意味着"king" and "the choosen one", 那么scar就是在“统治与被统治”的绝对二元对立裹挟下的不安和恐惧,是作为命运的弃儿的悲愤,执念和不甘。它来自于,相信着,成为着,创造着,重复着世界的伤痕。










当然对于Scar复杂性的解构,并不意味着抹杀了一切“善”与“恶”的相对区别,更不是鼓励去成为Scar这一具象。
只不过,面对命运种种力量的拉扯,要在每个特殊的语境下去更加耐心、具体、不带评判的斟酌。允许一个更复杂多面的世界在我们的内心里的倒影,或者说是允许我们内心复杂的王国投射出各自的现实世界。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Scar的影子,尽管未必会在命运的路口作出同样的选择。而我们对Scar的厌恶,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这部分阴影中隐藏自我的拒绝和厌恶。电影镜头在看向他者的时候,也是在内观。“自我”其实就在“他者”中间。
Scar之于Simba不仅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也是对Mufasa死因和现实的扭曲叙事,和在扭曲叙事中培植的信念和恐惧,最终成为一个不断自我怀疑,自我评判,自我攻击的声音。
在每个人未曾意识到的地方,因为相信了他者和历史对现实扭曲或片面的叙事,心里慢慢长出了许多恐惧的小魔鬼,和厚重的自我保护的鳞片。然后活在魔幻根据现实改编的剧情里,看不见多面流动的清澈现实本身。
而要和已经住进心里的,来自过往和他者的小怪兽们和平共处,就要认真抓住每一只看个究竟。
复杂多面自我有许多名字:自我本我超我;《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经典文学中所刻画的人同时具有的破坏性,食色等自然冲动,鲜活生动,和内在崇高性。自然自动反应的情绪,冲动,思绪,评判和更包容平和的意识;过往塑造的习惯,思维方式,环境的裹挟,和超越裹挟的选择余地。
幕启,在每一场风暴的中央,看见,命名,承认,允许,理解,原谅,包容,悦纳,热爱多面流动一体的自我和世界,是每一出命运悲喜剧同样的出口。
(4)
在未经审视和批判的环境对人的塑造中,自我只是世界塑造的一个角色。
王子复仇是一个经典的隐喻,父亲的形象,在象征着最具体的父母之命之外,也象征着一切历史过往社会他者和命运加诸于个体的无可奈何。
辛巴和哈姆雷特,象征性的替我们所有人经历了,这样一场个体与外在一切的拉锯和两难困境:是抵抗历史和社会的对个人的命运选择和裹挟,或是选择对各自的历史与社会进行回应。
小狮子的迷失和找寻之后,看似是迷途知返,却因着对父名的/对社会历史的不加批判的继承,于是只是重复了时代,历史,社会,他者的命运,而不能改变历史江河和个体生命的走向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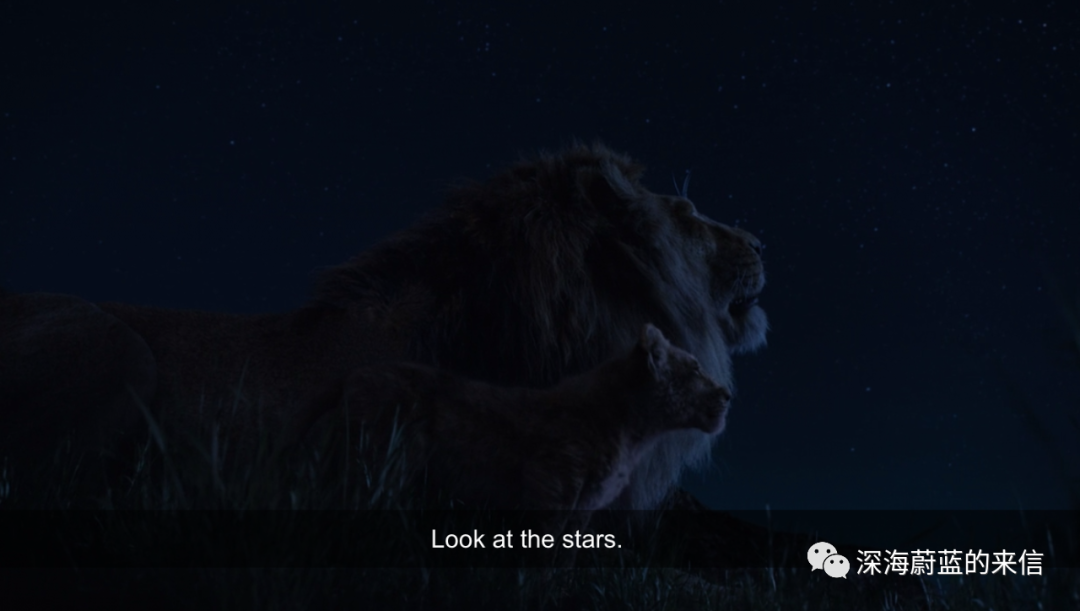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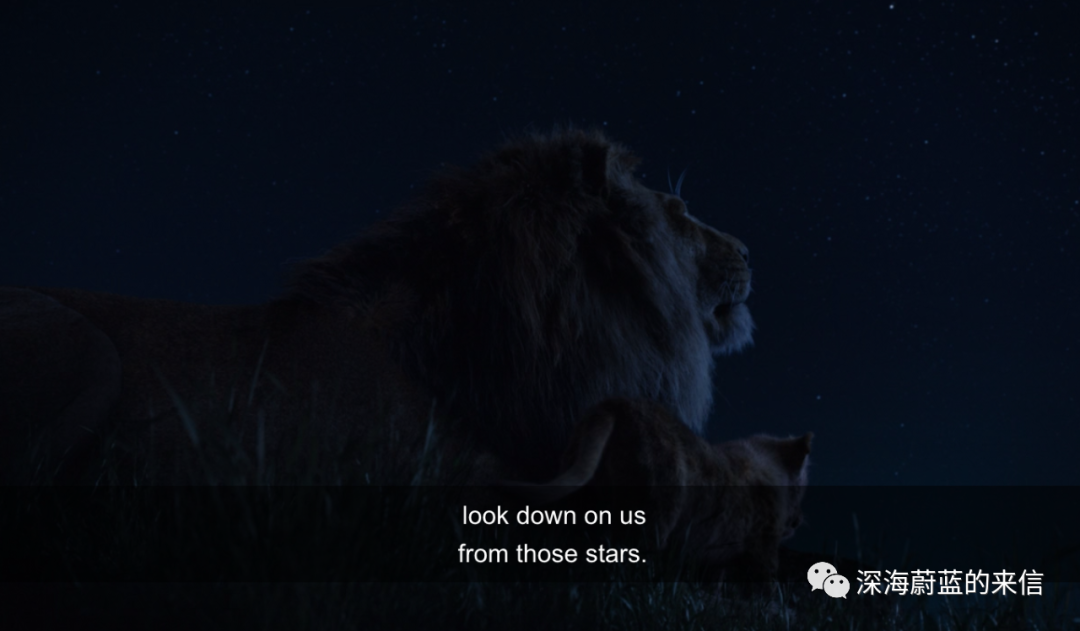




哈姆雷特虽然错过了复仇的最佳时机,却因着这多面正义的对抗,个人与历史社会的真切的拉锯,在与命运的对抗中,改写了命运的流向,虽然流向的是一个悲剧的结尾。
每个人降生在个体角色里,承担着历史的社会对我们的单向选择。这选择里有创伤,有强加和绑架,也有热爱,天赋,和使命,有着个体历史,集体记忆,他者期待,价值预设,有着一切我们选择相信的名字。或者说,我们选择相信自己处在这样一个命运叙事之中。
电影《the Truman show》里的Truman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加批判,我们就任由自己生活在由过去和他者/历史与社会一手打造的剧本里,每个人和事都是演员,推搡着我们在角色里生活。未经审视的自我也只是这世界和命运里的一个照本宣科的演员。醒来的那一刻,在于意识到,我们如何被过往和他者推搡着走进了各自人生的片场,穿上了各自的存在,信念,话语,性格,和视角。
环境语言不停的塑造着人和人的选择。天气,音乐,颜色种种,都可以带出个人的不同面。当我们身在环境中,往往会成为环境本身。而即便我们以为自己有选择的时候,默认的设置和最便捷的选项,认知的错觉,身体的错觉等因素也会很大程度影响这种选择本身。就比如说吃饭这件小事,好像我们拥有很大的自由,但除了食物本身的不同感官体验的重力吸引不同的地域饮食习惯,超市货架上最普遍的或者最显眼的商品,饭馆里的音乐和颜色,被放在你盘子里的食物,盘子的大小,人为创造的“一份食物”的表象,进食顺序的先后,等等环境因素早就写好了每个人的答案。至少在这些因素没有被认识到之前。
而我们说着的书写着的繁复精美的语言,更是不停的定义着我们自身。
因着人是复杂的,多面的,流动的,而话语环境往往在潜意识中塑造了,带出了(bring out) 复杂人性中的一小部分。那么我们能做的,便是去不停的唤醒人性中更为“光明“的那一部分。在policy school里读到的policy nudge里一个的例子,是新加坡后付费的公立医院给患者寄账单时,用怎样的语言去敦促患者偿还账单。“97%的患者如期打款。”;“您的医生感谢您的付出”。把人放在不同的话语环境里,自然的会引起完全不同的回馈。人就像不同的山谷里自然产生的不同的回声。
功利主义的nudge背后,也是柏拉图不同于牛顿的空的空间概念,人总是在一个“处所”中并和“处所”发生着关系。
(5)
自我和世界,也是在在近现代的想象中,才开始割裂。
而“自我”也从不是一个永恒的概念,中国古代哲学的内核是“无我”的,从庄周化蝶,到孔子的天人合一,都是“我”与“世界”浑然一体的。在西方哲学里,“自我”也是希腊时代“物有其自身”之后才出现的哲学概念,而泛神论的原始民族都是相信“我”和“周围”是相互渗透的关系。
即便在“自我”概念被奉为圭臬的近现代,人在婴儿时期也是没有“自我”的。“自我”也可能只是个自我实现的文化想象。
西方哲学里,逻辑的开始就埋下了隐患:确认我就是我的同一律,将始终流动变化的自我确认下来,成为逻辑的第一个起点。但从此在形而上学中将世界二分为本质和表象;“不变”也就成为了比“变化”更高的存在,“不变”成为了实质,“变化”成为了假象。
这哲学基础之上的科学革命,也就命中注定的狂热痴迷单一和确定。
自我,也就从此和世界越走越远。
(6)
但这看似永恒的漩涡内外,我们并不是没有出口:意识到如何被环境裹挟,便拥有了顺着原路回归个体的选择和自由,也拥有了重构世界的能力。
个人被社会和历史裹挟,大概也是通过语言构建的话语。当我们学习语言的时候,其中的古老的价值预设便无意识的成为我们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通过我们叙说,倾听,阅读的古老语言中,价值预设和对世界的想象攀爬进了我们的精神和心灵。
对于世界的想象,解释和预设,以感性和理性的方式裹挟着我们。
在感性中,我们习得价值和与世界。
当我们会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时候,东方集体主义和责任感的价值预设便印在我们灵魂里。当“自由,平等,博爱”在西学东渐中被翻译成汉语的时候,西方现代哲学的自由和自我也就开始了和古老的中国哲学在个体身上的博弈。
话语的巨大结构性叙事绑架着每个个体,在汹涌而来的命运中,低语着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投降,和个体无力抵抗的信念。于是选择相信自己无力抵抗的浪花成为了这排山倒海的绑架本身。
在话语中,世界里的怪物变成了我们心中的怪物,我们心中的怪物也跑出来变成了世界里的怪物。
恐惧创造的一切怪物想象,在话语里自我实现着。关于分隔,敌人,对于强者的资本的想象,对于“统治与被统治”, “强者与弱者”,“善与恶” 的二元对立的想象。当我们诉说着对“强权的资本的”恐惧和仰视的时候,也创造了强权和资本本身。





而绑架和恐惧也只是真实的一部分,是一种叙事方式,是一个名字。我也可以换个方式说,“因为被这个世界爱过,所以不得不去爱这个世界。”
个人就是这样,被不同的叙事对世界的想象和描述裹挟着。
而理性的裹挟则更加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都遗忘了哲学,科学也只是人对世界的合理化尝试,是人对世界的想象和解释。
在牛顿,伽利略,笛卡尔对世界的数学化解释里,时间变成一个单线概念,广大的存在被几何化,真实原野被定义为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牛顿被奉为真理的第一定律,无限运动,假定了世界的无限;在不能测量的空间里,用几何化的方式测量着空,不能解释的都归于上帝。西方逻辑学的单线思考方式--所有这一切,关于存在,存在与否,如何存在,都在话语中设定了我们感知自我和思考世界的方式。
无论是感性或者理性的方式,我们每个人,都如同时代浪潮里的一朵浪花,在历史和社会中行走,走过许多话语的风暴,被这种或者那种话语或者价值裹挟着,同时对抗着这裹挟,"passing thorugh life towards eternity." 或者不停的从浴火重生中醒来,或者在梦境的某一层里安然一生。
而相信本身又是一种自我实现。
(7)
于是我们可以用各自的方式去想象自我和世界,在各自独特而联结的世界里批判和抵抗绝对的裹挟。而这对自我的重新构建和书写,也在普遍联结中改天动地。
看清了裹挟的生发,就有了选择,选择又带来了自由。看清裹挟的脉络,就可以去解构和抵抗,就可以去成为和重建。
解构单一和刻板,抵抗话语的裹挟,同时成为一个逆流的存在。改变自身小世界的内在脉络,重构对自我的想象和话语,也是在重建世界本身。
我们看到的,读到的,经历的一切都在无形中改变了我们的认知。认识和知道也不过是我们经历的一切。我们无形中模仿着自己看到的一切,小说,戏剧,电影,人间事。
这样说来,一个电影批评家可以解构一个世界和无数种命运;一个的小说家,也可以创造一个世界和无数个崭新的读者。
现实的困境是,不停的去打破个体经验的,时代的局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无比痛苦的,也需要很多机遇的事情。如果不是人生剧情里出现了什么巨大的漏洞或者机遇,那么人在惯性裹挟下脚步不停,也难以看见天以外世界的光。
但这不意味着束手就擒。对每个个体的无条件的尊重,理解,接纳,不评判,不干预,和春风化雨重构改变世界并不矛盾。
不仅因为无条件的爱所创设的环境比恐惧的话语更包容,温和,润物无声。爱的话语改写着恐惧,创造着崭新的个人和世界。
也是因为看清话语和环境裹挟之后,无须复制暴力的逻辑去做个体层面的价值干涉,在抗拒和敌对的话语,个体的敏感不安之外,在无痛无忧的梦里,转头去改天动地,重写梦境本身。
要打破一切预设,才能回归真实自由的原野。
历史和社会给你的命运预设的是数字化格式化的刻板问题,打破僵局的方法在于质疑前提。
在芝诺的 “飞矢不动悖论”中: 一支飞行的箭是静止的。由于每一时刻这支箭都有其确定的位置因而是静止的,因此箭就不能处于运动状态。把人困在这个逻辑里的是对于时间的预设。运动天然是依赖于两个时间点的,将飞矢限定在某一时刻的预设造就了悖论的僵局。
只有看清逻辑和命运的预设,来到一个更宏大流动多面的视角,才能超越无解。
于是在最个人的最真挚深刻的自由里,包裹着对历史和社会的最真切的回应和回归。超越“自我”概念的预设,看到人和世界的流动和互相流动,在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张力中,人与他者和世界互为镜像,在各种话语中互相裹挟。于是最出世的也最入世。
最广大的自由,也是超越命运局限后的回归,不似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楼起楼塌式的虚无幻影。而是理解和悦纳命运的黑暗和光明,在内心的巨大自由从容里和命运并肩行走,在黑暗常态里修炼光明,在距离感里全情热爱,在看清虚幻之后努力地真实。
是在自己的历史和社会面前,不执迷也不逃避,是坦然,从容,真诚,勇敢地好奇着自身和世界,热烈而柔情的握住命运执笔的手,一同去重写自身和世界的剧本。

(8)后话
于是命运来敲门,问王子你复仇不复仇的时候,你总是可以笑着问一下命运:您这都是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剧本啊。
reference: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52071768
https://www.sohu.com/a/329273182_268920
https://mp.weixin.qq.com/s/VPn-1fJlyLJ0Bw9JBZMTvw
还可以在这里找到我:
- https://rachelwangjourney.wordpress.com/
- 微信公众号: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