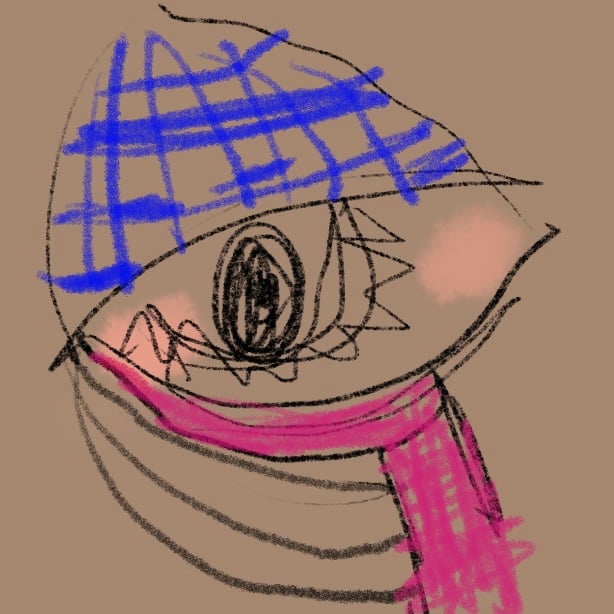参与征文 | 《表扬日》
真困呐。小礼堂里面挤满了,全镇子的人都来了。这是在六月,放暑假之前,小学校要召开全体学生和家长的大会——也就是说,整个镇子的人都包括在内。我马上要毕业,何况从来就心不在焉,老师们只当我病了——反正成绩好,别的他们就不在乎,我可是他们的骄傲——由我躲在“优秀同学”的标牌后面睡大觉。阳光经过楼西面的大窗子照射着脸,小虫在膀子上爬,丝丝地痒,我却当享受。
没有比领奖更好笑的事儿了。昏昏沉沉地往上面走,跟其他无聊的小孩子站成一排,端着奖状证书之类,仿佛孝子对着灵堂,“看镜头:茄——子!”我笑得前仰后合,面部扭曲,别人说这个孩子高兴疯了。
无休无止的是各种讲话:校长,书记,训导主任,年级组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后进生代表;家长代表,工友代表……连学校里成天乱跑的几只猫狗,也被“爱畜协会”会长同学抱着、牵着上台,发表了一通抹鼻子揉眼睛的感言。我困极了,统统没有听到,以上所述是根据多年来的经验。或者也许是我在做梦。
这回的后进生是个小男孩,厚厚的毛线帽似乎要像冰淇淋一样化在他脑袋上。他讲话时我不知怎的,醒了,饶有兴味地看着他,看他似乎要哭出来,望望稿子又瞅瞅下面,而且总往同一个方向。我顺着那目光找去,见一个年轻妇女正襟危坐在人群中间,眼含泪花,激动地大叫,又叫不出声,口水和泪水都闪闪发亮。我很感动。我听他感谢自己的母亲,感谢学校,他要好好学习报答这些恩情。他爱好科学,他要“见证祖国基础科学的辉煌”。念这几个字时他手抖得格外厉害,稿子都掉了一页,他的脸更红了,大概这个高级的语言并非出自他的原手。幸好这就是结束,他捡了稿子便跑下台子,扑进妈妈的怀抱,我看他母子俩人紧紧抱在一起,我想起自己的妈妈,有点想哭。
又困了。可有人来拍我肩膀,是温柔的班主任,“看看谁来了?”竟然是他,刚刚台上那小脸就显现在眼前。醒!他偎在女人腰旁,扭扭捏捏,几个校领导轮番夸赞他的进步,妈妈的脸盛开像一朵山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班主任又叫醒我做什么?来不及多想了,因为我觉得他正看着我,我甚至觉得是他牵引着其他人来到我身边——他要来到我身边。
行动的时候,我像一头豹子那样迅猛。站起来、揪住他的衣领(看他露出细白的脖颈)、拉他跑过舞台、跑出礼堂。他可能又露出要哭的表情,但我知道他没有回头,而且跑得快极了。我们跑过有守卫的地方,从他们肃穆的眼皮底下溜走,到了礼堂水泥地面的院子(集会时他们把这儿称作广场)里面,四下没别人,我一把放倒了他,他就躺在我面前。
他瞪着圆圆的黑眼睛瞧着我,我再也受不了,俯身用手指拨下他的眼帘。他的睫毛好长,像个小姑娘。我就吻他。此前我并没吻过别人。是,我母亲吻过我,但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我发挥想象力地吻着,两片嘴唇和一个舌头以及周围肌肉能做的事情,我都试着做了。他的眼球在眼皮底下转动,睫毛呼呼地在我脸上扫来扫去,像不久前爬在我膀子上的小虫那样,丝丝地痒,这当然更是享受。我真喜欢他嘴里花瓣和浆果的味道,让我想起他妈妈山茶一般绽放的脸,甜蜜蜜的。我跟他脸颊贴着,感觉彼此的热度,隔着夏天的薄衣衫我们像两团火,像棱镜后面的冰块,光天化日——六月的太阳光当真不是玩笑——下,要在这空旷的水泥地上熊熊烧起来。没人注意到我们,大家都在小礼堂里,守卫严格地把控门口,除了我们这样的顽皮孩子谁也不能够逃出。
可我还是有点害怕。我停止了亲吻,站起来;他睁开眼,仿佛明白了,也站起来。我往院子外面走,院门开着(守卫只在小礼堂的大门口),枇杷树下面是一块好荫凉,可我偏偏要在太阳晒得最凶的一块草上,而且我躺下来,并且我脱掉了上身的褂子。摊平在花草上,这草地是一张无比的大床啊!蝴蝶在飞呀,鸟儿在唱呀,我呢,顺手就揪起一根毛乍草,剥掉外壳,抽出内里雪白的芯子,嚼着。这本是春天的美味,没想到这时还有。我扭头找找,又发现一根,拔了递给他,他似乎有些吓到,但双手接过,小心地嚼,就笑了,叹口气道:“好甜呀!”我这才发现他的灰帽子不见了,直直的粗短毛发硬硬地在他额头上方挺立着。我伸脚拍打他腿肚示意他别再傻站着,他就蹲下,我摸了摸他的弧线平滑的发顶(在大会之前,应该让好手艺的理发师认真修剪过),扎得有些疼,就想着如果他的帽子还在,摸起来一定软和。
我闭上了眼睛。心幕上却并不是黑暗。我甚至更加灵敏,察觉到自身和周围的一切——阳光晒得我皮肤滚烫,我想我的臂膀一定微微发红了;夏天旺盛的草花戳着我背脊,痛却舒坦;风有些凉,两个小小的乳头在冷的刺激下变得硬了;视野右边小礼堂投下阴影,劣质音箱阵阵沙哑的低音沿着土地传送过来。这毕竟是我的身体(虽然仅仅是上半个身体)第一次在大自然中展露,什么也不用藏着掖着,在河里沐浴也不像此刻这样开放,我兴奋,又难免有些紧张。甚至忘了:还有一个人在我身边。可忽然,一只小手轻轻划过我胸前,试探一般,不小心似的,触到了右边的乳头,手就立刻缩了回去,我把什么都想起了,睁开眼,看到他脸通红,我笑了,我对他说:不要害怕,你看到的所有东西、这些,全都是你的。他眼里立刻产生一种凶狠的神色,我又闭上眼。我知道他已埋下了他的头,伏在我的右乳上,他在吮吸,他双手捧着那只乳房像捧着什么神圣的器皿。我想他真是个小孩子,那吮吸的力度,如他初生之时本能的动作,我觉得他真是出生不久,他还新鲜。我又想到方才舞台下面他母亲鼓励的目光,此刻也似乎还照临在他头上。
我不由自主地搂住了他,抚摸他的头,密布其上的那些硬刺竟变得柔软些许。我把他的头贴在我胸和脖子之间,下面是草扎着我的背,上面是他头发扎着我心口,我感到非常快活。他的衫子也渐渐地湿了,我把它脱下来,放在我早先解掉的褂子旁边,现在我们两个上身紧紧挨着。他突然把手撑到地上,脸抬起来,望着我,我又闭上眼睛(刚刚偷偷睁开看他呢),我害羞,我怕。他说话了(这是他正经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你怎么不看我呢?”这番轮到我脸红:“我不敢呀。”“是我长得丑,你别看吧。我看你,你真好看,我喜欢看你。”“别瞎说,我看你就是了。”我们就对着看,比谁不眨眼的时间长,结果两个人都眯眼笑了,抱在一起打滚,皮肤上黏了草籽、泥土和虫子的死尸。
太阳已经变成夕照,霞霓染红了地平线以上的天空,鸟雀叽叽喳喳要回巢,晚风一波比一波凉,吹来一阵阵小礼堂中的声浪。我们都觉得不太对劲了,各自抱着衣服(但并不想着穿上)起来,给彼此拍打身上的尘屑。我们不想回去,他早已把他山茶花般的母亲忘了,我更是从来不喜欢所有的人。这时不知是否因为慢慢涌上来的夜晚的黑暗,我又感到困倦,但不是疲惫,只是单纯的晕眩。我下意识地走着。我们没有商量要去哪儿。
我觉得自己必须振作起来!像一条泅水过河的狗刚上岸时那样,我打个激灵,抖了抖身体,又冲他笑笑,把他的手拉着,跑起来。我要带他去学校的办公楼,三层正规的建筑之上有一个小阁,大家都说闹鬼的,我也没去过。他任由我带领,我们跑得又出汗了。爬台阶要比赛!我跨两级,他争着跨三级,却差点没拉伤自己,就这样我们一路上升。旋转的楼梯让我头更昏昏,但还是笑着,装作熟练地在阁楼楼梯口左转,见到“卫生间”,鬼使神差地就进了,洗手池左右两扇门,眼皮已经抬不起,迷蒙中望见“女”的汉字和图案,推搡他进去,到一个小隔间,旋上旋钮。终于到了!现在是一平方米,我跟他在一起,我们的世界——到了。
女厕有大大的窗户,晚霞洒落进来,整个空气里洋溢着粉红金黄的光泽。隔间里有好几个挂钩,我因为身上发热,迅速脱掉剩下的所有衣裳,跟褂子一起挂到一个钩子上,心下登时畅快不少。我想这大约是高级领导之类用的厕所,瓷砖干净得发亮,消毒水味也好闻,更无顾忌,赤条条一屁股坐在地上了。这里是蹲便,所以还要叉开腿以避开屎尿的通道,瓷砖冰凉,但我发烫,故而不觉。他大概惊了,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抬头望他或是低头垂在胸前,不知道自己的眼神对他暗示着什么,总之他一个膝头已落了地,也急忙脱着衣服。什么东西从裤子口袋里滚落,我抬起手指指,冲他笑,他就捡起来,“这是巧克力糖!你吃吗?”我摇头。看他脱光了衣服,整具身体沐浴着霞光,立在我面前;看他已经发育得很好;看他黝黑光滑的背脊……我欣慰,又想哭,却只是问:“你常游泳的?”“嗯,我还会捉鱼。什么时候带你去河边,钻火苗子,烤新鲜鱼你吃呀,那才叫好吃咧!”这时他的神情又变回那个吸奶的孩童,我羡慕,又失望。
不过,他也没再往下说,突然悟到什么似的,又单膝跪地,凝神盯住下水道若有所思一阵子,就来贴紧我坐着,他把手伸到我腰部以下,吻我的额头和鬓角。因为我给吃了毛乍草,现在他口里多出一股青草的腥气,让我愈发迷醉,晕眩就越来越浓烈,我快要失去意识。但出自本能,一手绕过他的肩膀(骨头硌得我生疼,却利于清醒),一手抓住他不太老练又足够成熟的生殖器(“阴茎”,我在脑里的迷雾中念出这个词语,暗暗觉得可笑),放在我最潮湿滚烫的地带摩擦,寻找那个黑暗的洞口,我闭着眼,在光滑冰凉的瓷砖上扭动我自己。他已经开始啃啮我的背,我那只在他头上的手发现他的头发已经湿透,下午的坚硬完全消失了。进入了,我被进入了。我大概也湿透了,睁着眼和闭着已经没有区别,我什么也看不见。一切正常的感觉消失了,只有那个交接的洞口一个异物横亘其中,我能感到它的存在,我只能感受到这个。以它为中心我扭曲着自己。啊,还有心跳,像助阵的鼓点,咚咚咚敲个没完。他的胸膛紧贴着我的,我感觉两颗心要撞上,像两辆失控的车子,两名疯狂的司机将在彼此的渣滓中走进天堂。
过了多久,我们才分开。能够知道的是,分开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街灯星星点点亮起来,我听到人声,分明是簇拥着走向这里,大家一定发现了我俩的出逃,要把我们捉回去了!我又获得了清醒,但死到临头已经义无反顾,我把他抱起来(他可真重,我装作轻松)放到坑的另一边,也就是说,抵着隔间的门,我对他说现在该你了。他拍拍手,胸有成竹的样子。他让我躺在他两腿之间,两个手臂托住我,把我的辫子解开(绳子套在他手腕上)把头发梳向后面,有一些落入便器里,我也不太在意。他俯身吻我,腥气一阵阵翻涌,我几乎想吐,其实真正存在的只有晕眩,但他已经和夜一样冰凉的呼吸又让我感到清新,我无法抑制地吸入这种凉爽。他吻遍我,从每一个毛孔啜饮每一滴汗珠,而且一直小心翼翼,没有张开口伸出舌头、产生贪婪的表现。我越来越无力,要把整个头落入坑中,但他一只手总是托着不让我坠落,另一只手向下游走,滑入我们曾经最亲密接触的所在。我已经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嗅、不能说、不能摸,但终究保有那一片地方的触觉。他的手指,他的器官,我能感觉到;他要挽救我,我很感激。
现在他努力前后震动着他的下体,一边还要确保我身子的稳定,在一平米的空间,中间还隔着屎尿的坑,这是多么艰难的舞蹈。他轻轻把我双腿从内侧掰开(我无法忘怀他手指从我的阴部顺着里面向大腿划过时的温柔,那分明属于一个完全成熟的男人),让我的脚勾住他的脖子(我在濒临昏迷中惊叹无力时我的柔韧度如此之好),天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哪里来的毅力支撑着他的行动。他换了只手承托我,抽出原先那手来轻轻拍打我的脸,而且凑近来对我讲话:“快醒醒,醒醒。”我多想醒过来,像他吻我一样吻遍他的身子,用唇丈量过他脊柱下凹的曲线,再对他说一万遍感谢的话,请他原谅我的昏迷,但我已经堕入深深、深深的黑暗。完全被漩涡卷进之前,我还感到下面汩汩的水流,黏稠地包裹住他的器官,尚且觉得自己还不至于百无一用,但接着来的就是彻底的深渊。
……
我没有昏迷太久。完全无意识的状态大概只持续几分钟,感官渐次苏醒。我濒临昏迷与真正昏迷的样子应当很相似,所以他对着我无感知的身体持续动作、动作,才能发现我真正是异样。我不会知道他当时的情绪和行为了,但在我率先恢复的听觉中,就一直有他低低的呼唤,“你怎么了?你醒醒,你醒过来吧!”我已经听到,但不能给予任何形式的回应。他抱起了我,旋开旋钮。他力气真大,我能感觉到他抱起我是轻易的,后来他甚至单手抱我,到隔壁的房间搬来一把凳子,又回女厕,把凳子摆到窗户旁边,把我放到凳子上,身体靠着墙。他没想着给我穿衣服,这很好,我从来觉得热不觉得冷。他打开了窗户——这实在是英明之举!我立刻重获了嗅觉,甚至从风里分辨出毛乍草腥甜的气味。而且惊喜地发现街道静悄悄,这说明小礼堂里的大会还在进行着。
他一直念些符咒般的言语,我心想:我愿意他为我施法。他在屋里来回走,盘算着什么计谋似的。又一会子,他来这把板凳上同我坐在一起。他也没有穿衣服,但他身上滚烫——这让我明白我虽还感觉热,身体却早冷了。他抱了我好久,大概是他孩童的天真,要把我在他怀抱里捂热,可是没有用,我猜他又要急得哭了。突然他离开我,去打开那个隔间的门,哦!他给我拿来巧克力糖。先剥糖纸(噼里啪啦的很刺耳,像有什么东西在听觉里爆炸或闪烁),那糖大概早被太阳和他的体温融化了,又凝固,剥离不太顺畅,但终于剥下来,他塞到我嘴里。可惜我无法控制嘴巴,更不用说吞咽,只是张着嘴,让巧克力酱融化从我的口角流出,唇上有甜腻的感觉。这回他真哭了,他先用手拨弄我的嘴唇,发现无效,就伸过他的嘴来,他要帮我完成这一次进食。好在是巧克力糖,我们两个的温度很快让它全部融化,他把我的脖子仰起,舌头上甜甜的浆液就顺着食道流下去,制造一出小小欢乐。不知道从哪他又搞来一块手帕,还弄湿了,给我擦脸,擦完脸我很舒服,皮肤上残留的水被凉风一吹,格外爽快。但他却顺着脖子向下而去,仿佛着了魔,又要吻我一遍,而且一面吻、一面抚摸、一面用帕子擦拭,连我自认为最肮脏的角落他也印下他男孩的吻,连我垂下去的手臂他也抬起来吻合着的腋窝,而且始终小心和谨慎。他大概想着,这样能够一寸一寸地唤醒我,我会在他的吻里重生。他吻得投入,激动,又抱起我,粗糙的木凳子不再扎着我最敏感的肌肤,他的手臂在我的膝弯下穿过像溪流穿过桥拱,他一边吻一边又跪下去,把我放在这厕所的瓷砖地上,我发觉到他已经把我俩的衣服都铺垫得妥帖,棉布衫子是他的,很温暖;仿绸褂子是我的,滑溜溜。他压住我身体,又抱着我翻滚,让我趴在他身上。吻了又吻也终于告一段落,他开始单纯地摸着我,捏我的手指、骨节,在我的两瓣屁股上面画圆形和方形。末了,他只是反复摸着我的背,就像小时候母亲对我做的一样!
他要我重生。可是全身都吻过摸过,我仍然不能回应,我除视觉外的感官都已恢复(视觉大概也恢复了,可我无法抬起眼皮),但无法表达。他又坐到凳子上,静静地抱着我,把我放在他大腿上面,把我的手环住他的腰,尽管我能做到的只是把手臂垂在他身后而非身前。起初他把头搁在我肩膀上,连忙又觉得错了,把我的头拥在臂弯里。可渐渐地他的头落在了我的后脑勺上面,中途猛然醒转,觉得用额头或下巴抵着我都不合适,就用脸颊枕在我头上。“他睡着啦”,我对自己用不需要出声的话说,“这样很好。他累了,该睡一会儿。我一直都在睡觉,真难为他。”他虽然睡着,还哭着,眼泪从他的眼睛流到我脸上,沿着我一直流到我们的大腿之间。他的泪水真多,那长又浓密的睫毛一定都闪烁着泪花,泪水沿着凳子的平面滴到地上:嘀嗒。嘀嗒。
我在心幕上重演今天经历的一切,反复地体会,只有幸福。我猛然发觉,小礼堂的舞台上他快哭出来,并非在望向他母亲。他一直都在望着我,只有我望向他的时候,才扭头看他母亲,又把从母亲那儿获得的鼓舞尽数化为望我的勇气和力量。可惜我不能再望他了,我的视觉还没有恢复,我想我要永远地睡着了,但我心甘情愿,和他一起沉入无边的睡眠。不,他会醒过来,他会伤心地哭的,而且他会哭到永远。我想到他将把他的灰帽子再戴起来,害羞地靠在妈妈的腰旁,而校长会夸奖他、让他站上舞台,右手就一阵酸冷的隐痛,接着手指一抽搐,我不由自主沿着他背中央的缝隙向上直摸到他的头,他头发又干了变硬了,扎得我清醒。“姐姐!你醒了!”他叫我姐姐!我说不清的一团情绪纠结着要到嗓子眼,就睁开眼睛,我又望见他!他怎么一下变成个脸部有利落线条、躯干强壮的男子,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大概是因为他常常游泳吧”,我又在心里对自己说话了。而这个男的叫我姐姐,我感到委屈。
不过,我什么也没说,冲他笑笑,请他和我一起去窗台上坐。所有的人还在小礼堂里,不会有人注意到学校办公楼三层半的小阁楼、女厕所这扇小窗、两个赤裸的孩子。我们又能抓着彼此的手,相对而笑了,多么好!窗台离地面有相当一段距离,借了那只凳子我们才上来,但上来就可以晃腿晃脚了——没有孩子能抵挡如此的诱惑。夜晚完全到来,窗外一片漆黑,由于人都在小礼堂里,街灯还没打开(晕眩之中我曾以为它们亮了),只有远处稻田中火萤虫遍野飞舞,我多想再拉着他手一路跑到那丛萤火中间,但不能够。我想他山茶花的母亲还流着泪咽着唾沫盼他回家。我正想着,他倒先开口了:“姐姐,你叫什么?”“嗯?”我一愣。“你叫什么名字?”“啊!明。”“明,明……我叫钟。”“啊!钟弟。”我又要去摸他的头,他却躲闪开,笑着说:“明姐!你的名字好听。明,明……你整个人也好看,我喜欢你,明姐!”他简直抱着一种感激的神情,我怕看,便怒了:“不许你这样叫我!我是明。”他脸上支棱着的线条被窗外的夜色融化了几分,这回惨惨地笑,一颗牙漏着晚风,我又觉得他可爱,自语一般说出声:“钟,我爱你。”他立刻听到并且回答:“明,我也爱你。”并且用两只手握住我的一只,很严肃。“刚刚是开玩笑,以后再不和你玩笑了。”“好,不玩笑!我们唱歌吧!”我就唱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他和着我,“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突然他比我更大声地唱起来:“让我来将你摘下,送到别人家……”
在走廊尽头我们找到一间淋浴房,在那里分别冲洗了身子。望着水从莲蓬头洒下来,我想象它是一场暴雨,并且永远不要停止。于是,当我慢吞吞地扣上花衬衫最上头一粒扣子时,他已经在帘子外面等着我好久,见我出来,一把拉过我的手,带着胜利者的微笑,要和我一同走。我们便一同走着,俨然衣冠楚楚两个小少年,同时从余光我才发现,他其实比我高一些。(他什么时候长这么高了呢?)我喃喃道:“人们该从礼堂出来了吧。”他还在笑:“什么?”我没搭理,因为正凝神竖耳听街道的响动,人声从大路上沸腾着,飘起来飘到三层楼高飘进他刚刚为我打开的窗户飘入我的耳鼓,这时我已十二分清醒,知道这再不是错觉。
我心里惊慌,就挣脱他的手,加快脚步。但到了出口,看见大门外边大块的夜色,有意无意脚下又迟钝了几分。果然,他追了上来。隔着七八层台阶,他叫我:“哎,明!”“嗯?”我转过头去,小楼里没有灯(我们不知道开关在哪),他的脸已经被夜色埋没,我无法看清,甚至他的声音也细弱乃至不可闻:“嗯……没事,没事了。我没有事的!明你走吧。”我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