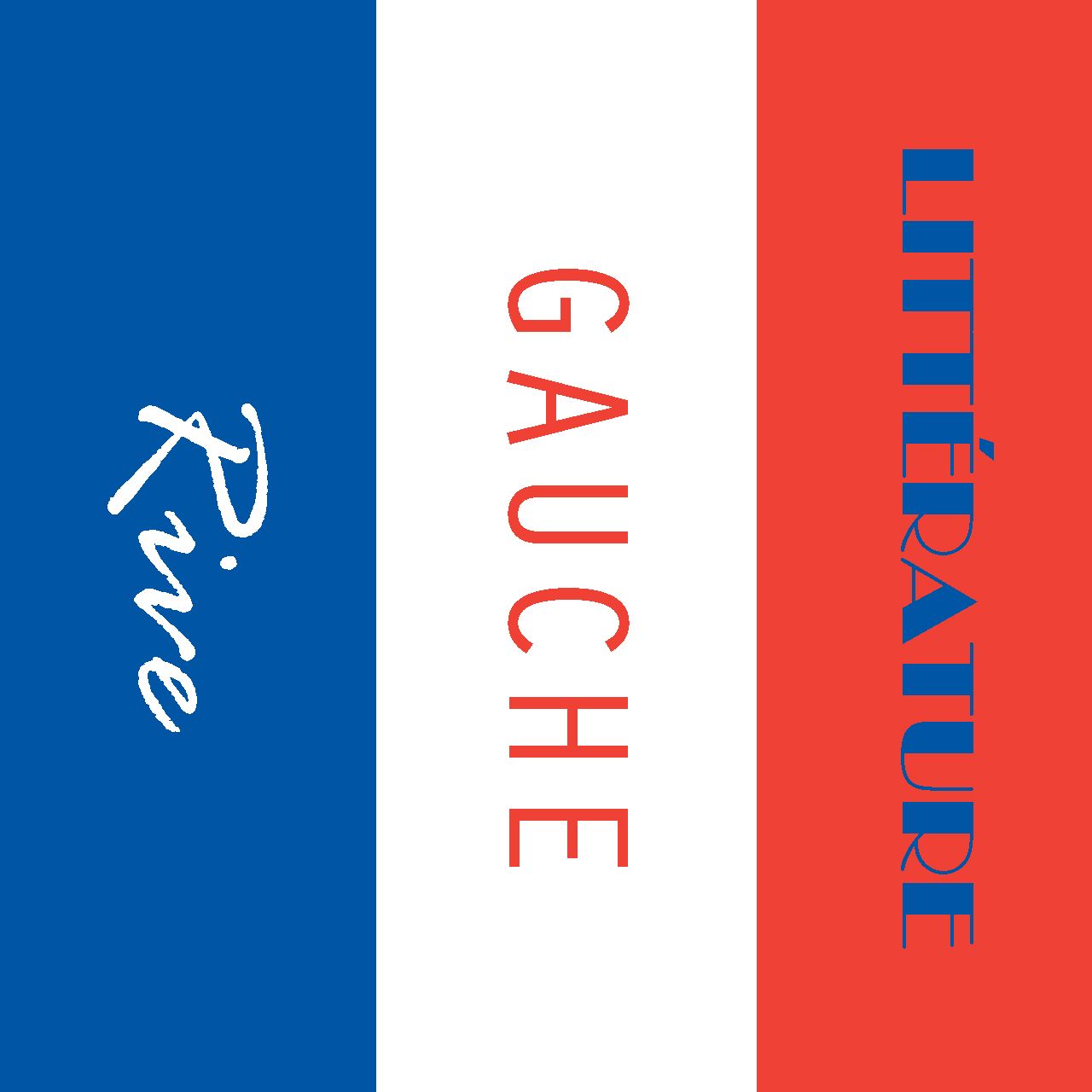短篇小说/父亲

父亲
文/林伯奇
图/Azad Pirayandeh, 2019
全文 共计12255字/预计阅览时间 31分钟
致敬现代主义文学三大巨匠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
“从香港飞往北京的国泰KA900航班即将起飞,请各位旅客……”
“欢迎回国,K先生。”
飞机穿过厚厚的云层,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的跑道上,K望着窗外的风景,微微皱眉。窗外阴云密布,正如他的心情一样;明明刚刚还是万里晴空呢。那厚重的积雨云有如K的眼袋——他足足一晚没有睡觉,眼神里透出来的只有疲倦与焦虑。隔着玻璃舷窗,空中小小的北京城在他眼前逐步放大,变成他儿时在电视与杂志周刊上看见的风景——没有稀奇,或许有些怀旧。飞机停稳,走下阶梯,K深呼吸了一口气——一成不变的空气。北京机场的跑道上,轻风微拂,K提了提自己的领带,周围的景色颇有一股荒凉的感觉。
“世界是一片荒原。”这句话浮现在K的脑海。祖国——这是他阔别了多年的祖国!他不知道多久没有呼吸过这里的空气了,五年?十年?十五年?不论怎样,他总算找到了一个回家的机会,不知是福是祸。堂妹的一通电话带来了来自家的最新消息(不知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而后经过各种周折,终于得到了让这个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回家看看的批准。不论如何,是好是坏,他都要回来看看。
K在机场的厕所里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稍微打理了一下,梳了梳头,不至于看起来那么疲倦,又是深呼吸一口气,冷静一下自己的情绪。随后他便自信满满地通过了海关,走出候机楼大厅,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医院。出租车行驶在机场高速上,K望着窗外的景色,如今连北京的郊区都开始变得这么繁华了——他想,大概以后北京还会再扩张的,向河北扩张,向内蒙古扩张,立足于茫茫无际的大陆之上。
出租车到了医院的大门口。K用着他还不熟悉的微信支付给司机付了钱,随后走出车门,目送着出租车离去。然后他站在医院的大门口,一直没有走进门去,只是在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医院的屋檐上几只鸟飞了下来,向远方飞去,他尝试着数算清楚那是多少只鸟,突然,鸟群拐进了一栋玻璃外墙大厦的背后;该死,他心里咒骂了一句,随后脑子里开始想着太阳系行星的顺序。
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
然后他咽了下口水,转过身来,向医院大门走去。“我真希望现在会有一个噩耗传来,”当K跨进门槛的时候,他想。随后他不停地在自己的意识里复读着《圣经》里的词句。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马太福音,24章36节)
他忐忑不安地行走在医院昏暗而洁白的走廊里,嘴里依然在嘟囔着那些经文。终于,他在一个病房前看见了站着的堂妹;他走上前去,打了声招呼,堂妹惊喜地抬起头来,认出了K;两个人拥抱。堂妹这些年来也到美国去探望过自己,他们这些年来也在别的地方有过会面。K把她搂在怀里好一会,就像童年时那样,随后问:“爸爸呢?”
“他在里面。”
说完,堂妹把病房的门打开。K愣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
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开我!马太福音,27章46节)
父亲的病床位于屏风的另一侧。K走了过去,看见了躺在病床上的父亲。
父亲和记忆里的那个人,确实变了——如今在K的眼前的,仅仅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皮肤干瘪,显现出黯淡的颜色,头发掉光走不动路,戴着呼吸机即将走到人生终点,拍拍屁股走进坟墓的小老头,只有那保持着基本特征的五官还能让K想起那个老爷,这是不会变的。K离开时,父亲远比现在要年轻——那时他的头发还是黑的,身体是强壮的,是充满力量的;但想起那样的父亲,K开心不起来,而看见如今这个小老头反而让K的心里感到宽慰。
当K的父亲年轻时,K还更年轻,但却很软弱;如今K的父亲已经老去,而K仍然年轻,K是强大的。在肉体上,K已经战胜了曾经压倒他的高大身影,看见这样奄奄一息的父亲,K并不感到悲伤,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呼吸,不说话。
眼前的父亲睡着了,但可以听见那面罩下的呼吸声,心跳监护仪上的波浪般的线条反映着这副老旧的躯体里的生命活动。“你们都先出去吧,我想和他单独待一会。”K对堂妹说道,堂妹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随后便出病房了。
K拉上了窗帘,拿了张凳子过来,坐在父亲的面前,仔细地打量着面前的这个老人,打量着他皮肤上的每一块斑点和褶皱。他如同一只衰老的狮子,这病房就是它的笼子;他的皮肤下埋着他的骨头和肌肉,他的骨肉里篆刻着暴力的基因——但他现在再也不能使用他了,他的脑子也不再灵光,变成一个老糊涂了。K感到宽慰。
慢慢地,父亲苏醒了过来。他的脚趾微微动了动,然后是手指,咳嗽了两声,皱纹蠕动着,眼睛缓缓睁开。
老人察觉到这旁边有其他的人。他躺在床上扭过头来,用那浑浊的灰色眼睛看了过去,仔细地辨认着面前模糊的年轻人,迟缓的脑细胞和神经系统被他的意识动员起来在同样浑浊的脑海里搜索着他这辈子见到的所有面孔,终于认出这是他的儿子——K。他也很多年没有见到K了——K从来不接他的电话;每次他要侄女跟K联系,要K回家,K永远是拒绝的。
但他并没有说话。之所以K知道父亲认出了自己,是因为他辨认出了父亲的眼神。
那是一种轻蔑和蔑视的眼神。这个眼神一点都没有变,K永远能辨认出他的眼神,他见到这神态的次数比吃饭还多。这份轻蔑彻底扫除了K有过的骄傲,那份恐惧与厌恶急速地在他的心中升起,他的表情变得狰狞起来,盯着老人那浑浊的瞳孔;但老人不为所动,他还是保持着那份古老的轻蔑。K再一次被它所压倒。
但K不甘心,他决定证明一些什么——就像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他站起来,绕着病床走了一圈,把心跳监护仪的电源拔了下来。随后他又走回凳子摆放的位置,站在那里,靠在床边,俯视着自己的父亲。
他看着父亲的眼睛,父亲也看着他的眼睛;他们四目相对。他们的五官是多么的相似;两人始终保持着沉默。
哼,你能把我咋地!父亲的眼睛对K说道。
K的表情也没有变化;正同父亲一样。突然,他抓起连接着父亲脸上的面罩和呼吸机之间的塑胶管,死死地捏在手里,怒视着父亲,不说话,不让一点氧气流过去。
很快,父亲瞪大了眼睛,惊恐替代了蔑视,喉咙里发出呻吟的声音。但K不为所动,听着父亲的呻吟声他反而捏的更紧了。“不会有人发现的,不会的……”K对自己说道,“他会像任何要死的老头一样,就这样死了,没有人会发现任何事情……他是自然死亡的……谁也不会发现他发生了什么……”
父亲呻吟得越来越厉害;他的肢体试图在病床上挣扎,但是他已经老到没有力气挣扎,也没有人听见他试图呼救的声音了。他的手无力地握住床单,眼球里布满了血丝。“我发过誓,我要用马鞭抽打他冰冷的躯体;我要把他的骨灰冲进马桶里,让他去跟下水道里的老鼠作伴……”K继续对自己说,他闭上了眼睛,不想看着父亲挣扎的样子。记忆从没有边界的黑暗里涌来:皮鞭,皮带,酒精,斥骂和脏话,拳头和巴掌……还有那个孤独地坐在楼梯间、水泥地和传达室小板凳上年少的自己。想到这些,K更加不会放手,他把手攥成拳头,五根手指头死死摁在塑料管上。
父亲的呻吟变得更加痛苦了;他的青筋显现在单薄的皮肤上,他的脸都涨红了。
又是突然,K放手了,放下了塑胶管。随后他又去插上了心跳监护仪的电源;父亲的心脏跳的非常剧烈,他恢复了正常呼吸。
K看着父亲的脸。另一部分的记忆又朝他涌来,那是父亲教自己游泳,带自己去爬山和钓鱼的记忆;这些记忆是愉快的。想到这里,K于心不忍,他后悔折磨了面前这个无力的老人。
他用右手捂住了自己的脸,遮住眼睛,揉了揉太阳穴。父亲被他这么一搞,已经完全清醒了。他缓缓举起自己无力的手,轻轻敲了敲自己脸上的氧气面罩。
K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伸手摘下了父亲的面罩。父亲首先咳嗽了两声,然后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用干枯的声音对K说:“你回来了。”
“要不然呢。”K支支吾吾地说,“我听说你快死了。”
“是的。”父亲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
“那你有什么坐下来要对我说的吗?”K又问。
“只是你很多年没有回来了,我快认不出你了。”父亲说,“我想最后再见到你。”
“我没有理由再回来。”K说,“只是给你个面子罢了,让你不至于死的这么孤独。我也想看看你是怎么死的。我就算在美国给人用枪在脑袋上开一个洞我都不打算再回来了。”
“你堂妹把我照顾的很好。”父亲说道,K扬起了眉头,“坐着吧。我确实想要跟你说一些什么。”
K从很早以前就离开了自己的家和祖国,当那飞往旧金山的航班起飞的时候,望着身下的跑道和楼房建筑,他想着自己再也不会看见这些景象了——也再也不会见到那压在自己心头多年,阴森可怕的影子了——但他最终还是回来了,重新从飞机的舷窗里看见了窗外的陈旧景象。他感到厌烦——因为厌烦,他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和国家,如今这份厌烦的感觉卷土重来。
K想,他与父亲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和好了。他不知道父亲到底爱不爱着自己——至少对他自己来说,这个男人的行为和爱搭不上一点边,那只是他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残暴体现;但K又不敢肯定父亲是不爱自己的,正是那些相对正面阳光的记忆在自己犯下谋杀罪行的边缘把自己拦住。父亲的形象在他的世界里是分裂的,父亲时而是个暴君,时而只是个普通的人;他拥有温和的那一面,他也拥有暴力的那一面。暴力的那一面K无法原谅,但温和的那一面又会让他心软。或许,对父亲自己来说,他的做法是所谓的“负责”,是爱与温和,只是K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罢了。
K想要逃离他的原生家庭,乃至是他的故乡,他一生下来便带着的一切,想要远走高飞。对他来说,这里的一切让他感到窒息和沉闷;他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里,别人说是好的他觉得是坏的,别人说是对的他觉得是错的,别人说是伟大的他觉得是丑陋的,别人说是温暖的他觉得是冰冷的。
他带着一肚子气和叛逆来到了大洋彼岸,定居在旧金山,有时会往东海岸跑;他首先在美国上了几年学,努力学习,把故乡抛在脑后,毕业后换成了工作签证,成为了一名律师。他没有结婚,也没生孩子;因为他害怕自己会变成跟父亲一样的人,那矛盾而尖锐的基因刻在这个家族的骨子里,而他不想把苦难带给另一个无辜的生命。他拿到了美国的绿卡,买了房子,但他没有更换自己的国籍(当然,他以后回家也不是很容易了);至于其原因,我们在接下来会谈到它。
K的女友是一个美籍华人。她是来到美国的第四代移民,祖籍是广东潮汕的,只会讲一点生疏的,带口音的普通话和一点点潮汕话。她对K说她有一点拉丁民族的血统;K不感到奇怪,毕竟她们来到美国已经很多年了;人都知道华人是一个难以被同化的群体,但说多说少他们都与西方世界产生了融合了。不同于祖国的女性,K的女友长着一副充满了西方世界对亚裔的stereotype的脸;倒也不能这么说,相比起中国大陆的人对白人审美的模仿,在外表上极力向高加索人种靠拢,K的女友的肤色和五官对K来说更加自然,偏向于亚洲传统女性的风格,有一种朴素的韵味;但她的精神并不如在儒家宗法思想下成长的亚洲女人一样;她完成了从精神到物质走向自然的过程。这是她最吸引K的地方。她出生在东海岸,也是为了逃避家庭的影响而来到了旧金山。她是一个私人教师;在一场当地的华人社区联谊会上,他们认识了;和任何情侣一样,他们开始一对一约会,确立关系,然后是同居。看着她,K自己的心里有一种微妙的感觉,仿佛自己夹在一个尴尬的峡谷之间一样——他来自并出生在两人共同的祖国,讲着中文,然而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女友却好像比自己在意识上更贴近传统的民族身份(尽管她并不懂标准中文,但是在行为和气质上她仍然贴近亚洲),这只是盎格鲁-萨克逊世界的刻板印象对人塑造的结果,K这样告诉自己;但是,女友——就好像迪士尼出品的花木兰一样,她出生在海洋文明之中,拥有着另一种文明的继承权,而作为移民的K在这个世界里永远是局外人,他无法被另一个文明所接纳,尽管他尝试去融入。
有一天晚上他们在同一张床上;女友躺在K的怀里,她问:“祖国是什么?”
她从没有去过太平洋的西面。
K说:“你在问我祖国吗?”
“是的,祖国。大洋彼岸的祖国。”她说。
“那里有很多自行车,永远都很多,还有电单车,”K翻了个白眼,仿佛要把他的视线投向他的大脑来寻找记忆,“虽然现在柏油马路已经被铺上了,但还是有很多路是用水泥铺的。小鸟把鸟屎拉在车子挡风玻璃上的几率会比美国低。大街上贴满了标语,提示最新的政策。”他随后又说,“祖国很大,城里一个样,乡下一个样,就像奥斯汀和某个肯塔基小镇的区别一样,要我说这个国家每个地方的共通之处,我只能想出来这些。”
“如果我们生活在祖国,我们会是怎样的人?”女友又问。
“我想我依然是城里人,而你会是乡下人。”K说,“那里,什么都有,又仿佛什么都没有。我实在讲不出关于那里的准确概念。”
“我想有一天到那里看看去。”女友又说。
“你可以去啊,只是恐怕我陪不了你。”K说,“那里是我的家乡,是我的出生地,但那里对我几乎是一篇只长着一点点杂草的荒原。”
“到底什么是祖国?”女友问。
K的喉咙卡住了。他的大脑里浮现出了爱尔兰,浮现出了巴勒斯坦,浮现出了中国的大山的场景。祖国是那般抽象又那般具体;具体是因为它确实放在那里,它不是以色列国,也不是库尔德斯坦,它像是一个——“lavatory,”K对女友说,“所有人都要去,尽管会对里面的环境不满,里面沾满了小便、脏厕纸和没冲干净的排泄物,但还是必须要去,不得不去。”
K的女友想要去寻找那一切;然而K想要逃开那一切。他们两个躺在床垫上,穿着衣服,呼吸着,女友像一只猫一样蜷缩在K的怀里;床边的黄色灯光和窗外都市夜景里的万盏灯的颜色相似,灯光打在女友的皮肤上,把她的眼睛、睫毛和嘴唇照出一种透明而柔和的暖色色彩,K看着她和她的眼睫毛,对她的额头吹气。薄暮降临在旧金山的城镇,窗外的天空显现出一种和海的颜色相近的深蓝色,云也一起被染蓝了;远处的金门大桥华灯彩照,车来车往,黄色的灯光与蓝色的天空呈鲜明对比。
“关于你的遗产,”K对父亲说,“我不想要你的一分钱,你的一分脏钱。我说到做到——我离开时我说今后我不再需要你的一分钱,现在我也不会再要。”
K没有说下去。他闭上了眼睛,想象一个场面:父亲会从病床上暴起,怒斥他,斥责他不配得到一份他的财产,他是个逆子,他应该要搭乘最早最快的航班滚回美国去,不要再跟他待一分钟——你不爱我,我还不爱你哩!
“可是孩子,”父亲有气无力地开口了,“我已经跟律师说好了,你拥有我的财产继承权,自始至终都有,我甚至没留给你的堂妹。曾经你想要我不给你的一切,现在我都要给你了。”
“我会把遗产捐给儿童基金会,捐给艾滋病防治机构。”K说,“把你的这些财产最后交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很好,我可以独立生活——这也是你过去一直盼着我要做到的,不是吗?你没有必要现在再装出一副爱我的样子——如果这是你临死前最后想拿来安慰自己的一些行为,告诉你自己你对不起我或者是你还是爱着我的,我更不会成全你了。”
“你可以随便怎么处置,”父亲又说,“只是我把它交给了你,你会一直拥有它。”
这话脱口而出让K感到有一些气馁;说不定讲一些话刺激一下他,他的血压一上来或者喘不过气来,这老头就一命呜呼了!不过这不是K演的,这是他的真情实感,他确实想这么说。
当K说出自己的梦想,讲了自己对未来的职业规划和目标,认为自己想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什么,而他那时的眼睛里流露出的便是那一模一样的轻蔑,他嘲讽着K的理想,并要求K去选择他为K预备好的道路;当他在教堂妹怎么梳妆穿衣,教她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淑女的时候,父亲则是那么愤怒地呵斥自己,说自己想怎么样把自己的人生搞废了都行,不要连累别人;甚至胁迫着要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父亲从来不懂自己。或许对他来说,自己是在为K准备了最好的道路,自己的教育方式是最正确的,K的不接受只是他年轻的叛逆,他不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始终是封建家长制下的包办思维。父亲从来不了解自己,从来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K想要的就是他停止自己的所谓“馈赠”,他不需要这种馈赠,如果说是那严苛的教育的话。或许,这严苛的教育培养出了K,让他能在美国成为一个律师——但如果是以牺牲自己的幸福为代价,K宁愿自己不曾出生,他宁愿自己不曾来到这个世界上,要以自己的童年阴影为代价来换取物质上的丰盈,又要因为那些痛苦从过往的家庭体系里摆脱出来。那些关于皮鞭的记忆充斥着K的噩梦,他有时觉得自己没有成为一个瘾君子或者是从天台上跳下成为一滩肉泥已经是最大的幸运——涉及到肢体暴力的部分其实频率不算高,但是记忆深刻;而父亲的语言暴力,那些对K的人格侮辱和苛刻要求(为了培养K的“独立生活能力”,他让K的约会上迟到了半个小时,仅仅是因为交通出行的问题,他拒绝为K提供任何交通便利),那些父亲的装清高趣味也同时要求了K的生活(他明明只是个油腻无比的小资产阶级小市民!),让K在孤独中度过了他的半生(受人格障碍的影响,他缺乏正常交友与恋爱的能力)。
“你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父亲问他。
“没有,都没有。”K说,“我要与你背道而驰——我不想要你的所谓责任感。我不想为你传宗接代,让你的血脉继续延续下去,我也不想变成和你一样的人。这一切是时候停止了。”
“那真可惜,”父亲说,“你奶奶还说想看着你结婚生子呢。看来现在连我都看不到了。”
“那是另一件事。”K说,“我想活得轻松一点。我知道你以前很累,为了操心我的事情,你一个人要养活我们一家,我想轻松一点。”
K这么说,父亲反而显得有些宽慰。“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已经管不住你了。”他说,仿佛是在宣告着K的胜利。
“这是你要的结果,”K说,“‘像个斯巴达勇士一样’,这是你教我的,你应该承担你的教育带来的结果。你看看你——你说你盼望着我的独立,但是你的控制欲又是那么强……不要怪我太冷漠或者是冷血,这是你一手造成的结果。我已经实现了彻底独立,打出了我自己的天下,你现在后悔与否,都没有用,也与我毫无关系。”
“很多人,和你一样,去到了国外,”父亲有说,“他们还是会顾及自己在国外的言行。因为什么?家人——家人依然维持着他们与故乡的联系。他们知道自己的存在会给家人,给家族带来什么影响,会有人因为自己受到影响——好的,还是坏的。但你不一样,孩子,你完全不要脸,这么多年你对我不闻不问,就算你不能回来你也从来不给我打电话写信——因此你完全自由了。”
那句“你完全不要脸”反而让K变得兴奋了起来——一种喜悦与憎恨混合在一起的兴奋,他死死地盯着父亲的眼睛。
“之前你堂妹已经跟我说过你将要回来的事情了。”父亲说,“本来我以为这次我会见到自己的孙子孙女的,看来是没希望了。”
K的父亲在他自己眼里是个完全的失败者。他的事业失败,他的家庭失败,他的教育失败,到了晚年他只是个孤独而龌龊的糟老头子——这是他应得的,K想。
K想起自己在美国发生过的一件事情。那是一个周末的傍晚,K在旧金山的一家大型书店里闲逛。他走着走着,来到了亚洲文学区,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书。这是一部中国非常有名的作家写的文集,里面包含了他写的散文,短篇小说和诗歌,书并不厚;书是英文的,从中文翻译而来,为西方世界的读者们带来另一个世界的了解窗口。
K站在书架前读了读。文采很好,只是相比起这位作家在国内为人所熟知的,早年的先锋风格,如今他的文字读起来更像是对他早期作品的拙劣模仿,里面充斥着反复的意象,仿佛他已经江郎才尽,没有更多的文字,老调重弹,只是一个过气的畅销书作家罢了。
K突然注意到他的身旁站着一个人,穿着灯芯绒料子的西装,戴着眼镜,俨然一副学者的模样。K又把书翻回到最前面的扉页,面前的这张脸印在了书扉页的作者肖像上。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正站在K的面前。
“久仰大名,幸会幸会。”K对他说,作家保持着礼貌的微笑。
他们在书店里聊了很久。他们聊起了诗人海子,聊起了《牛虻》和《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聊起了海明威和斯蒂芬·茨威格。
“我也一样,多年前就来到海外生活,在法国、挪威都住过一段时间,现在在美国也许只是做短暂的停留。”作家对K说,“我也很多年没有回家了。”
“没有办法的事情。”K说,“我也是没有办法,不过我倒是一点不想回去。”
“大概是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总有一天,我还会回到家乡的。”作家这么说,然而在K听来,这样的话有些无力,“不过,既然国内的人个个都知道我的名句,那我也没有遗憾了。”
“只是我想知道的是,您早期的作品以简洁先锋的风格出名,您是那时文笔最具有锋芒的作家,广播里天天都要念您的作品,您几乎是华语世界的聂鲁达,您会描写生活和浪漫主义,也会去针砭时弊……”K说,“但我不理解,恕我直言——您现在的作品却显得格外苍白,几乎只像是炒冷饭一样,不断地翻炒过往的文字——您自来到海外生活后,几乎就再也没有新的作品了,虽然您还有出版投稿新的作品,但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的文字。”
“我今天很开心,”作家看着K,对他说,“可以跟人用中文聊天这么久。”
“什么?”
“多年来,我在海外都是使用英语或者别的语言来生活,今天有一个人可以用母语来跟我对话,聊天,我感到非常开心。”作家感动地说道,“我远离我自己的语言很久了。我的舌头长在汉语上,我写的都是方块字,然而在异国他乡生活了这么久,我对我的母语已经感到生疏,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那么好地掌握自己的语言,用钢笔与笔画共舞——大概是因为如此,我就写不出更好的作品了,只能凭借自己对过往世界,对过往语言的记忆来完成我的写作。”
是啊,语言——一个作家生活,建立在他的语言之上;如果他失去了自己的语言,那他的生命就已经结束了;更何况是一位来自远东世界,第三世界的作家的文字。他们的文字不是national,而是ethnic;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事物。语言凝结着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是一个人的意识的宝库,在他们的谈吐和写作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故乡的情感,可以从中窥视到他们的童年。那象征着自己的文化背景;只有在那一语言之中,他才能完美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尽管也有一些特例——詹姆斯·乔伊斯用英语写作(因为他根本不懂古老的爱尔兰盖尔语),米兰·昆德拉用法语写作(但他也同时没有放弃用捷克语写作),但他们的语言是活着的,是纯净的;然而K眼前的作家却要面临着语言死亡的困境(尽管有人会说这是中文语言的进步与革新),他无法确定这语言属不属于自己。
对K来说也是如此;这是他没有去更改国籍的原因。连接他与故乡的,不是那抽象的亲情,而是语言,是陪伴他长大的语言。他不想像那些沙文主义者一样吹嘘这语言有多么博大精深,多么优美和cultural——对他来说,自己的语言是朴素的,这就是语言的最宝贵之处,不需要任何消费主义的形容词为它装饰点缀,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项自己与生俱来的财富。在K的记忆中,故乡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留恋,唯独语言——这语言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更改国籍那几乎是一种逃避,对自我意识内核的逃避。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伟大的文学家,他实现了语言与文字的超脱;而K和作家则面临着生理性失语的危险。
他们离开书店的时候,作家把那本文集买了下来,在书页上签了名,当作礼物送给了K。两人分别的时候,作家对K说:“Adieu au langage.”
“Adieu au langage.”K也对作家这么说。
当K再见到那位作家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有一些年了;他是在香港的一场文化讲座上再一次见到了作家。作家作为讲座的特邀嘉宾到场,在讲台上作出了流利的发言;此时的他,比起像一个学者,他更像一个年迈的数学老师,讲解着他对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看法和他的海外生活,他在台上侃侃而谈,发言结束后,所有人一起为他鼓掌。
散会后,K找到了作家,作家也认出了K。他告诉K,自己后来又离开了西海岸,去了东海岸居住,又在欧洲待了一段时间;现在他已经回国定居,在香港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拿到了国内的居住许可,专心于学术研究。
“我已经一把年纪了,当不了什么游子了。”作家对K这么说,“不过至少,我捡回了自己的语言。”K很想反问他一句:这样做有意义吗,捡回语言?这不是捡了玉米扔掉西瓜——还不是一种对自我精神的背叛吗?
“你爱我吗?”K问父亲。“你爱过我吗?”
“我当然爱着你,爱着我的孩子。”父亲说,“难道你觉得我没有爱你吗?我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了你。”
“对我来说,那不是爱,那是你的残暴。”K说道,“不过你甚至不会说‘我只是爱你的方式有问题’,你依然把你的残暴当成你‘最好的礼物’。对我来说……你只是个控制欲爆棚的施虐狂老古董罢了。”
“没有我对你的严苛要求,你怎么会有今天的成就呢?”父亲说,“看着你能自己养活自己,你有一技之长——现在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就算你对我说再恶毒的话,我也心满意足了。你或许会很恨我,恨我那时为什么要那样对你……但我不后悔,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宁愿你从来没生过我,老头。”K说,“如果这就是当你的孩子要付出的代价的话——投胎到谁家,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如果你我还有下辈子,我还当你的爸爸的话,我依然会这么做。”父亲说。
“前提是你先别在地狱里被魔鬼折磨得死后也没有安宁。”K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你只是个虐待狂罢了。”
“K,你还记得我曾经带着你游泳时候的事情吗?”父亲问。
“你是说你把我抱起来从空中扔进水池里吗?”
“不……我是这么跟你说的。”父亲说,“做人啊,要像鸭子一样,在水面上看起来安安静静的,水下的脚蹼在动。”
那是一个下午,阴天。K独自在东海岸的沿海公路上驱车。那条路应该是马萨诸塞州127号公路,从贝弗利一直开到格罗斯特;K独自开着车走在新英格兰的平原上,周围的风景令他想起了爱伦·坡在《厄舍府的倒塌》的一开头提到的阴沉景象,天气和北京差不多——整个空气都弥漫着让人抑郁的气息。周围的草地和森林绿油油的,长满了蒲公英和野雏菊,却提不起一点生机,融入到背后的同样呈现出忧郁的颜色的大海当中。K开车的时候揉了揉太阳穴,喝了一罐雀巢咖啡,打开了收音机。广播电台正在直播NBA的球赛,目前是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正在对阵底特律活塞队。体育解说员兴奋地重复着一个三分球的成功,他激烈的声音提起了K的情绪。
汽车开进了城镇;路标上说,这里叫做“海边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by-the-Sea,Massachussets)。
海面上漂浮着几艘游艇,有人在船上和人行道上钓鱼;一艘渔船开回港内,船工们正在收拾他们的渔网。K以二十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在公路上,就在那时,他看见了一个男人在人行道上反复徘徊。
那个男人看起来神情低落,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卫衣,站在海边的人行道上,抽着烟。他看起来几天几夜没有睡一个好觉了(也许他刚刚经历一场失恋?),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没有刮,有很深的黑眼圈。他就那样在海边徘徊着,不说话,有时会凝视海浪和海岛。K停下了车,把车窗摇下来,看着那个男人。
他是那样疲惫,看上去就像一只连续几天觅食不成功,躺在冰块上歇息的海豹;但他就那样站在那里,看着大海和那些游艇,浮浮沉沉,犹如一个人的人生。他所望着的,正是辽阔的大西洋;海水拍打在海岸的石头上,然后又被卷回到大洋当中;海鸟盘旋在蓝绿色的海面上,日光有时从云间显现出来,随后又被云层遮盖了过去,而这个男人就站在那里,看着。
他大概是个天主教徒,K想,说不定还是个爱尔兰人。这个以WASP价值观为基础立国的国家并不是他的精神家园,只是他随着自己饱经风霜的祖先漂泊到了新大陆,仅此而已。他就这样站在这里,望着大西洋,仿佛隔着海水他就能望见大洋彼岸的祖辈土地,看见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的城镇,看见和马萨诸塞一样的森林和草地;听着波涛他就能听见爱尔兰的竖笛乐声。
收音机里仍然播放着NBA球赛;解说员宣布,波士顿凯尔特人队胜利。K深受感触,他拿起一个照相机把眼前的这一幕拍了下来。
“我请你给我一个机会。”父亲对K说。
“什么机会?是让你重新做一次父亲的机会吗?”K说,“这个我给不了你。”
“不是。我请求你给我一个死的机会。”父亲说。
K震住了。随后他俯身贴近父亲的耳边,对他小声说,“我刚刚明明完全有机会送你去见阎王。”
父亲不说话了。他沉默了一下又说,“既然你这么恨我……我并不后悔我自己的人生,即使会被你杀死。这个机会——是我对你最后的馈赠了。”
K沉默良久。“你知道,我是个律师,现在冷静下来想想,”K说,“你也没几天了,或许让上帝来鉴别你的灵魂是最好的选择。你说你给我一个机会——但其实这是你的愿望,我不会满足你的任何愿望。你想安乐死的话,我们现在启程去瑞士,签证还没发下来估计你就一命呜呼了。”
说完,K对自己的父亲摆出了一个厌恶的眼神,随后拿起自己的西装外套,准备离开。他走向门口,父亲突然在身后用干枯的声音对他喊道:“K!”
“什么事?”他侧过身来问。
“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要吗?”父亲开始歇斯底里了,尽管他的声音有气无力,但他已经发出了自己最大的声音,对K命令道,“K,你要像一个勇士一样!像斯巴达的勇士一样!”
“那不是我的任务,那是圣彼得的任务。你只是……我妈的丈夫罢了。你永远都会比我早死。”K冷冷地说,随后他打开门,走出病房,把父亲留在了他身后的门里。
没过几天,父亲去世了。K留了下来,和堂妹筹办了父亲的葬礼。
他们来到了墓地,请了一个牧师,按照K的父亲的心愿以基督教的方式举行了他的葬礼。那小小的骨灰盒里写着K的父亲的名字和他的生卒年月日。那一天,北京的天气依然是阴沉的,西北风刮过墓地,吹动了墓地旁的柳树的树梢。父亲生前的亲朋好友们都到场了,他们沉默不语,有的人掏出手帕抹掉眼泪。在他们眼里,K的父亲是一个卓越的人。
K没有哭,他也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就像那个爱尔兰人看着大西洋的波涛一样,听着牧师念的经文和祈祷。他的心里没有什么波动——如果硬要说,那个笼罩在他心头的乌云终于消散了。K的堂妹代替了他在葬礼上发言;他不想就这个男人的死表现出任何浮现于表面的情绪。
如今,这个男人与自己天各一方——他曾经高大宽厚的身体,现在就放在一个小小的骨灰盒里,闭上了自己的嘴,与历史上的所有人一样沉入静默。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摩西一样,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原点,回到了土地当中,与所有的祖先们共聚一堂。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他在死人的世界里得到了满足,他再也不用操心任何事情,也不必在意这个世界和他糟糕的儿子K会怎么看他了。
K的脑袋里此时此刻只挤满了各种名人名言。“父母是隔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帘子,父母在,你看不见死神,父母一没,你直面死亡”,据说这句话是马尔克斯写在《百年孤独》里的,但又有人说不是;不论如何,在接下来的人生里,只有K一个人去面对那坐在地狱里最黑暗的深处的魔鬼撒旦(尽管他的前半生也是如此)。但有一句名言,K确信是说过的,那就是王尔德的那句:墙纸越来越破,而我越来越老,两者之间总有一个要先消失。(My wallpaper and I are fighting a duel to the death. One or the other of us has to go.)
这时K又想起父亲死前的轻蔑眼神;他现在看着父亲的骨灰盒的眼神和那份轻蔑大概也是一样的。或许,那根本不是什么轻蔑的眼神——仅仅是一个老头子死前的漠然罢了。
葬礼结束了;人们逐渐离开,K和堂妹一直站在那里,看着父亲的坟直到最后。人全部走光了,他们还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随后他们也走了,把老父亲抛弃在这一片荒凉之中;唯有那棵老柳树和他作伴。
“我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的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效忠,我将支持及护卫……”
K举起他的拳头,对着旗帜说道。
2020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