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日记20200219
妈妈今天通过小区业主团购了十斤饺子和够喝两个月的奶粉,冰箱冷藏柜不够空间了。爸爸出了一趟门领取食物。他说:“小区里花照开,树照绿,只是不见人影。”
今天人们都很吃惊腾讯大家账号被注销了,所谓“你儿子被赐死了”。我想人们不是在吃惊一个言论很自由的账号被“赐死”,而是吃惊一个网站运营公司自己旗下的账号,也就是离“审查机制”那么近的一个账号,也会被直接消灭。在截取的文章目录里,还能看到“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我们需要真相、科学和文明”这样的标题。
发声有用吗?我喜欢豆瓣er“一位青年妇女”说的话:“这两天开始见到发声的力量。江山娇被“问”到注销,给女医务人员剃光头的虽然还没认错,但其他地方估计不敢再模仿;越来越多女性开始认识到月经不是羞耻,发偷拍女性上厕所照片来辱骂“月经不羞耻运动”的微博号也被骂到注销,并且西安交大好像已经找到当事人准备处罚;一线女医务人员的卫生巾需求也得到了重视和帮助。虽然帖子还在被删,上面的big boss们也没有被骂出什么动静,但很多事情已经在发生改变了,哪怕是最微小的事。“
她还写:”文字马上就会被删,那发帖还有什么意义呢?至少对我来说,我看到了,因为这些文字我思考了之前未曾思考的事,我有了从前不曾有的希望和勇气,那这个帖子就产生了改变我生命的意义。只要影响了一个人,发声就产生了意义,更何况那些文字影响的绝不止我一个人。”
“耳目闭塞也是一种传染病,没有谁能幸免”,这句话来自腾讯大家被删掉的文章之一。我想此刻我唯一可做、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停止地看,而且要边看边记录。
在武汉,有一位豆瓣er描写ta所知道的一位百步亭的中风患者,脑梗发作,因为无法排除患有新冠肺炎而一直无法入院治疗,今天患者的女儿打电话来说父亲去世了。患者女儿几日来对ta讲述了很多绝望的情绪,报死讯时她说:”社区说我爸爸目前还是疑似,按疑似处理,从4号脑梗发病到现在,15天时间,得不到救治,活活被拖死“。这也是一位连“1”都成为不了的武汉病人。
武汉外的湖北地区,陆续出现一些消息。一个是仙桃市针对医疗卫生单位的红头文件:禁止上传资料到qq、微信群;禁止讨论疫情、发表个人观点;禁止转发疫情信息;禁止未经允许擅自接受电话、现场采访,“以防不法分子打探内部工作信息,进行恶意炒作。”
二是咸宁有社区发出通知,要求居民除治病外一律不许出门;所有物资每户五天只配送一次生活必需品;家人之间必须隔离,夫妻须分床睡觉,分餐吃饭,在家戴口罩,每日测体温。几日前网友在看到“一家人打麻将被打砸桌子”时就调侃说,这样下去以后夫妻还要分床睡了呢!结果才过几天这个预测就实现了。
三是鄂州有一个人在微信群里晒自己老公当官给家里发了很多物资,附上的图片里有油、米等食物,还有口罩。在前几天有人炫耀自己父亲托人让其突破封锁离开天门后而“大意失荆州”之后,不知道这位是否也要“大意失鄂州”了。
另有一则很荒诞的消息,是现在中小学都开通网络直播授课。结果许多老师反应课件受到了屏蔽、直播间被封禁。医学生理课老师在QQ上讲课几秒钟之后就因为“涉黄”而被封,政治老师上课因为涉嫌政治话题被封直播室,还有讲近代史的历史老师也不能幸免,就连语文课也有人说“鲁迅的文章尽量不要讲”。有人问:“国家教育部钦定的教学内容,怎么在网上就成为了遭受屏蔽和封禁的对象?”所谓,“学校网课直播屡遭封禁,我们的互联网有病”。
昨天有一则稍纵即逝的报道,“农明日报”的记者调查发现火神山工人拿不到工钱。大概是作为回应,今天出现了“火神山工人坚决不要工资“的官宣,令人作呕。
今天还看到了历史学家罗新与“剩余价值”电台对话的稿子。他说,“当然我们对失去的生命,对仍然处在痛苦之中的、前途未卜的人们感到伤痛,但大家说的“愤怒”主要不是来自病毒的直接打击,而是病毒间接地帮我们把另外一个世界的另外一面捅开了。“ 罗新还说很有可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会是更黑暗更糟糕。他写下“一生所学、只为此刻”,要等待,在这下面的时刻里我们要怎么度过,我们要面对什么考验。这句话让我更加认清未来,我想此时的我是需要有这样的人与我谈话。我多摘抄一些在底下:
“剩余价值:从2017年年末开始,权利被拿走被破坏的情况一再发生。从自己的住所被破门而入,到因无法回到出租屋而被驱逐,我们好像一直都处于一个被剥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安全,即便是看病,也是有关系有特权就有床位。很多我们所信奉的东西完全失效了,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最后的结论就是我要买自己的房,我要买自己的车,我要变成有特权的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也是为什么李文亮去世让大家的情绪达到了一个高点,就是你始终是一个被剥夺的人,然后现在有一个被剥夺的人作为一个牺牲者,死在了他受剥夺的起点上。那天群情激奋,大家都说我们今后就要做一个说真话的人,如果不能说真话我们就不说,但这样一种美好的良善的愿望能实现吗?当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抗争、怎么去奋斗,去争取我们说真话的权利?
罗新:所以我在微博里说,天亮之前会更冷更黑。也就是说,你以为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了别人,别人和你一样愤怒,别人和你有一样的情绪,有一样的认识,甚至有一样的决心要改变,但是接下来面临的情况可能会让你很失望。这些人的声音你再也听不到了,这些人的脉搏你再也感受不到,你可能感受到的是来自一个更强大的力量的压制。
很有可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也许不会是短短的几个月、一年、两年,而是相当长的时间——是更黑暗的,是更糟糕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写“一生所学、只为此刻”?就是等,在这个时刻你怎么度过?对我们的考验在这里。
剩余价值:从愤怒到真正的行动之间的距离太远了。
罗新:对。在现代世界我们怎么行动?在现代体制下,个人或者没有很多资源的人怎么行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除了争取自己做一个干净的人之外,很难有别的行动。直接的街头政治时代,恐怕已经过去了。连小区的管理都如此网格化、如此极端,一个大的人群做什么行动真的很难了。但是我们这次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体制应付不了任何危机情况,而危机的情况并不来自我们上街去游行。
剩余价值:它可能应对的最好的危机情况,就是大家上街去游行。这个事情也会让我们看到治理里面有很多不均质不平衡的地方。过去我们认为,你的信息对于管理者来说完全透明的,你买火车票飞机票都有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甚至你上车还有人脸识别。可为什么当一个列车上出现疑似感染者的时候却无法找到他?原因就在于,这些信息是掌握在治安系统里面,而不是掌握在卫生系统里面的。而卫生系统想要调动这些信息要走一个漫长的手续,这个手续甚至长到还没有发一个微博有效。
这挺让人绝望的。我们上交这些信息、让渡这些权利,本来是为了有一天能够更好地被服务和被保护。事实上完全相反,当我们需要被保护的时候,这些信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罗新:系统不是没有用,系统是做单一用途的。这其实就是周雪光教授在访谈里说的,当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时候,地方反而瘫痪了。他们有那么多资源,却调动不起来。权力只有一条线索,权力本身是集中化的,在这种情况下,上面一根线一收,底下的线全都绷着朝上,横向的东西没有了,而社会真出问题的时候需要横向的力量。
剩余价值:我们国家已经没有社会了,因为它长期抑制社会的成长。所以这次我们就会发现,武汉一开始在那种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志愿者是可以组织起来的,他们其实构成了整个城市物资运送的毛细血管或者通道,但是他们可能受到的阻力恰好是来自政府的,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
罗新:我们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总是不容易被充分尊重。越是到现代社会,我们社会的各种功能越是丰富。但是当权力、资源、决策过于单一和集中的时候,当我们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就意味着所有功能都要停摆,这是现代社会承受不了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小村庄,大家这一天晚上都不吃饭,都来做同一件事,是可以的。但在这么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一旦某些功能停摆,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当媒体不发达或者媒体被管控的时候,这些伤害是看不到的。比如武汉有那么多透析病人现在不能做透析了,比如一个妈妈带着自己得了白血病的孩子在大桥上哭。这些人的利益全都被牺牲掉了。他们都跟病毒没有关系,他们不是携带者,不是有危害的人。他们应该获得同等的尊重,这是我们人类生活的本质。”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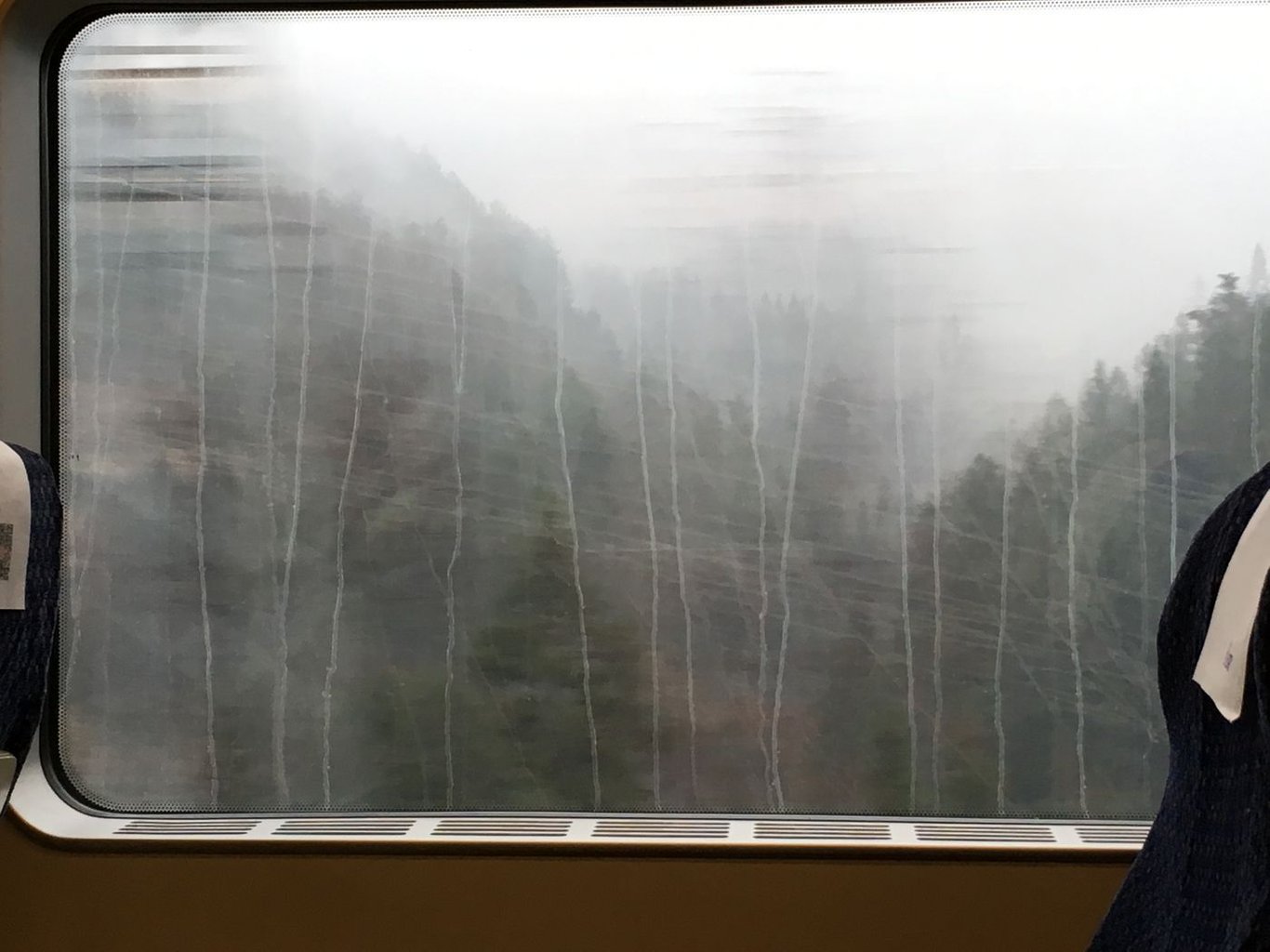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