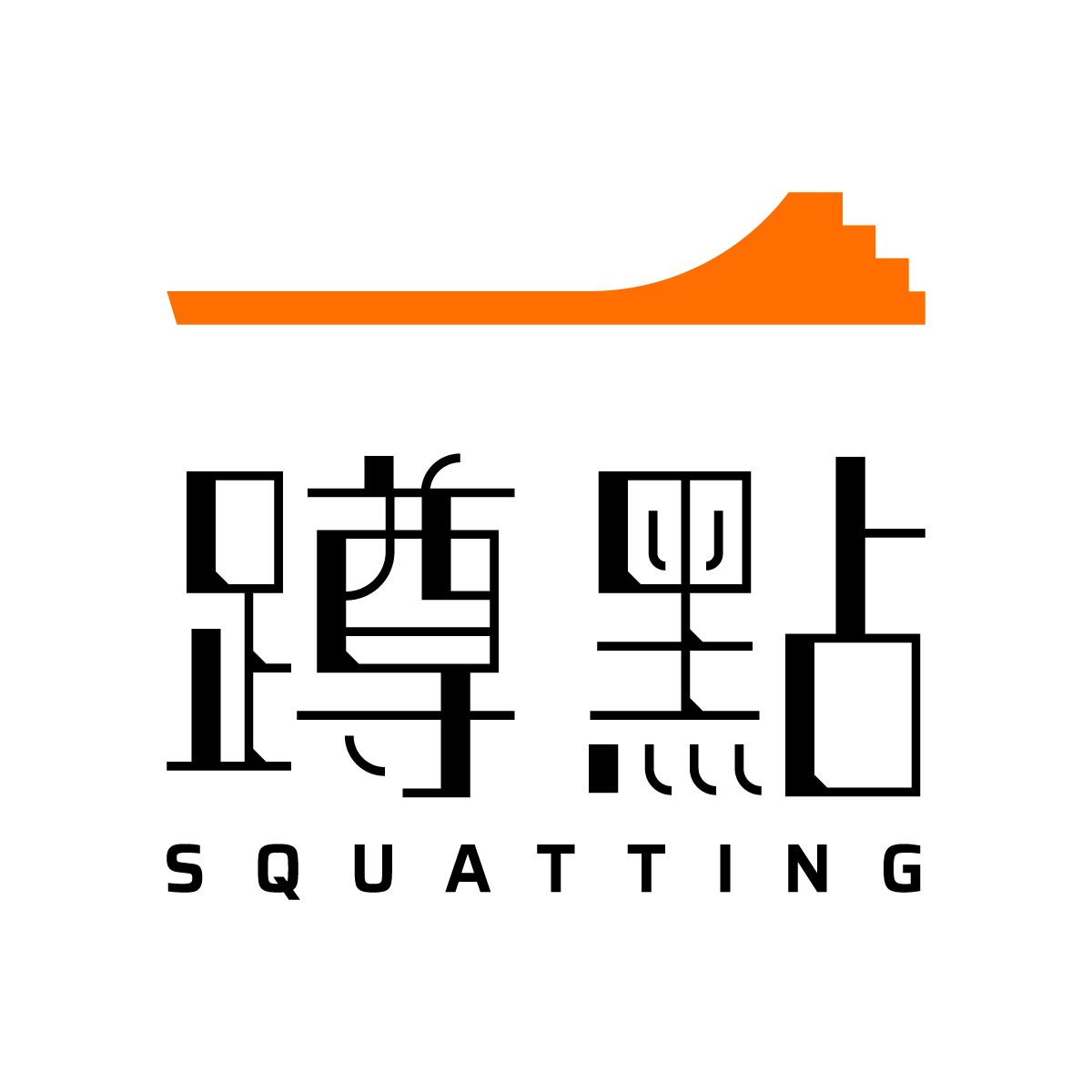【富士康連環跳十週年專題】訪潘毅(下篇):十年後的今天,工人依然是主要力量
编按:蹲點和潘毅的訪談上篇談到富士康連環跳事件在勞工史上的意義,潘毅認為富士康連環跳事件意味著中國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期。中國工會在工人權益受損時一再缺席;在此轉捩點後,工人越來越無所依靠,而不多的的支援之一來自學生。在訪談下篇,蹲點繼續和潘毅教授討論從富士康調研中延伸出的職業學校課題、新型「零工」工人與富士康產業工人的異同,以及今天在工人無依靠的情況下為何學生仍是支援工人運動的主要力量。 以下為Q&A訪談記錄 蹲:蹲點,潘:潘毅
從富士康到職業學校:工人階級的小孩沒那麼精英,更互幫互助
蹲:您在富士康調研的時候發現有很多職業學校(以下簡稱:職校)的學生?
潘:當年下去調研以後才發現:怎麼有些工人那麼年輕呢?再仔細了解,他們是職校的學生。
蹲:它是如何變成了您近年來關心的話題?
潘:不單是我,也是我的同事、學生關心的話題。我們覺得這是一個新發現。
以前不知道,下去之後才知道原來放寒假、暑假,平日都會有職校的學生在富士康實習。職校要求學生完成半年到9個月的實習,總共三年職校的生涯,最後一年是要做實習,不去就畢不了業。
當時沒人從勞動用工的角度去研究職校,所以我們就轉向去做這個研究。做這個研究也是明白到,部分第三代/四代工人會從職校產生:現在我們已經很少能夠找到一個考不到大學/高中就馬上去打工的人,現在的人考不上都會去職校讀一讀再去打工。所以我們會覺得職校是(工人)教育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如果在這一個環節學校在勞動保障教育方面做好一點,對中國工人的發展會很有幫助。
我從工廠知道這個現象,然後就進入職校做研究。我們過去幾年都去了超過十幾間職校了。職校是一個很值得研究,或者是一個很需要提供服務的地方。因為他們最需要這些教育服務,比如你需要做性別教育,他們就是16-18歲左右,這個階段你做性別教育就很好。
職校裡面的大部分小孩都是來自農村,或者是城市農民工、城市比較基層的家庭的小孩,因為大部分其他階層家長不會送小孩進去。我覺得如果我們是很關心這些階層的工人、學生,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提供服務的場域。

蹲:這些潛在的第三代/第四代工人和第一代的工人在意識方面有什麼不同?
潘:他們還沒有開始打工,只是有一些實習經驗,以及平日、週末打的一些散工。勞工意識方面,我覺得他們是更早熟的,對比我們以前認識的工人來說,他們更知道外面打工的世界是怎樣的,知道打工一點也不好玩。有經歷過實習的話學生就知道他畢業之後只能找這些工做,所以他一方面早早就接受到這個世界是這樣的,有一些固化的遊戲規則,另外一方面很可能培養互助和團結精神:如果不抱團,那更加沒有人可以給我提供幫助了。他們的同學關係十分密切,會一起用QQ群來交換一些打工的訊息。週末的時候他們要去「搵食」,他們一定要知道這個城市附近哪裡有得打工:哪裡可以端盤子,哪裡起了新樓盤可以派傳單。
我看他們的打工信息是完全沒有壟斷性的,是互相分享的。我們還可以見到一個情況就是,他們生病的時候都是互相幫助。甚至他們有些人的家長做建築工人因為交通意外受傷了,他們也會在之後舉行籌款活動。學生那麼窮都可以籌集到幾萬塊來支付手術費。
我會認為,來自底層的學生,他們需要互相支持,所以沒那麼計較,是義氣子女。不是說每個人都如此,但工人階級的小孩沒那麼精英,沒覺得我有機會往上爬要壟斷資源,那就大家一起玩咯。
蹲:在性別意識方面呢?
潘:在職校裡面女生比較敢講話,男生反而靦腆。他們有很多學生組織,積極參與的那些其實是女生。這是和以前不同的。
女生對婚姻的態度比前一代再更有多樣性一點,她們不會覺得婚姻是唯一選擇而因此有憂慮。對比我寫《中國女工》的時候接觸的18、19歲的女工,她們就在婚姻考量上就多一些焦慮:又想打工,又覺得自己要嫁人,或者家裡要求他們嫁人。職業學校那些18、19歲的女生,有時問她們想幾時結婚,她們會說30歲。
蹲:職校的定位是什麼?
潘:職業教育。我們在一個社會主義年代的話,國企廠真的是需要技術工的,在職業學校就是做學徒學東西,然後去企業頂替父親的職位,所以學生是有前途的,職校學生是不會覺得自己比大學生差的。
但現在整個世界變了,職校就是成績不好、考不到大學的學生才去。那麼就要學一門手藝,但技術就是視乎哪一類職業學校,有一些好的技術學校才有技術可學的。我們去到貴州、甘肅、蒙古,有些學校就真的沒有技術可學,如果開電腦課程,學校連軟件都沒有。
職校參差分化嚴重,去到差一點的職校未來都沒有好的工廠、企業可以選擇,所以就送去富士康實習。甚至送進富士康已經不差了,富士康有給錢,送去一些企業就沒錢,甚至要給錢。職校女學生喜歡去做護士,很多醫院給不了足夠的實習位置,學生去的時候還要給錢。

蹲:學生進去工廠實習後會不會有工傷保險?
潘:沒有,問題在於他們是學生,不是工人,不受勞動合同保障。通常的作法是學校和企業去買份商業保險。雖然實習條例都有規定,工廠不可以叫學生做高危險的職位,上夜班,但是工廠如果有24小時兩班制,他們全部都會叫學生做夜班。我覺得職校教育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大家可以去關心。
新型「零工」:在零散化、異化程度方面,和產業工人沒什麼分別
蹲:中國這幾年都有一些所謂產業的「升級」,「升級」到服務行業,我們會見到一些零工出現。您覺得這些新型的「零工」,同以往的產業工人有什麼不同?
潘:我覺得會更加難組織咯。但是,在僱傭關係零散化、異化程度方面其實沒什麼分別的。
蹲:您說「沒什麼分別」有點出乎意料,是什麼意思呢?
潘:所謂的沒分別就是這些工人都是賺幾千塊(收入低),工作時間很長,勞動還是不作為一個尊嚴來源,還是沒辦法覺得勞動是一個自我實踐的追求。在資本主義關係下,無論工人去到哪個行業,他都面對這些共同的特徵。
稍微不同的地方是行業差異。如果我們說的是快遞,就是每天開著一輛車在街上跑咯。表面上好像很自由、不用困在工廠裡面,好像行動上是更有自由。但事實上你知道其實你是沒有的,跑慢一點,人家評價你,你的評分就會被降低。媒體每天都會說這些新興的服務性行業工資高,但你要比較工作時間。在富士康,在製造業有日班夜班,工作時間表是定死了,所以你就做十個鐘頭左右。但你去做服務行業零散工作的話,工時可能會長達14個鐘,16個鐘。
平台、快遞這些彈性的工種我們有關心,同時我們也關心更性別化的工種比如淘寶客服。消費者在淘寶買東西的時間通常是十一二點,夜晚,下班回去沒事做就消費了,那消費者問就淘寶的客服(通常是女性),問她尺碼多大多小,人家會即時回覆你。所以你看,其實有很多見不到的女性的勞動在半夜三更服務著我們,我覺得我們要關心的。所以你問我有沒有分別,我就覺得整體其實是沒什麼分別的。
有行業性的差異,會影響到組織上的差異。不同的行業需要去思考不同的組織模式,通常見到其他國家的經驗就是,工人越是集中在一起,它組織之後爆發的力量會更大。如果是幾萬人的工廠的話,都有一個潛在的組織力量在,但需要摸索。早十年八年我們摸索的是製造業工人的組織方式,近五六年我們開始摸索一些通過新經濟、服務行業、數碼相關的經濟的組織方式。這些的工種雖然零散化程度高,但數量都越來越龐大,我們有幾千萬的數碼勞工。我會覺得要摸索一個新的組織方式,當然最理想的情況是不同行業的人可以互相支援。

蹲:工作零散化對於對工人階級意識形成有沒有影響?
潘:有,但是我們要抓住問題的核心:工人階級意識的提升最主要的是勞資矛盾足夠激烈。工人意識不是抽空想像出來的,而是說碰到問題的情況下他要去解決但遇到挫折。比如說我是一個自僱的快遞人,但是我開摩托車出去遇到交通意外,沒有勞動合同,沒辦法判斷工傷,嘗試去求助卻發現工會沒辦法理你,到當地勞動部門的時候發現公司和員工沒有履行勞動關係,勞動部門可能不受理你這個勞資仲裁事件,所以你根本就沒有辦法。
工人是在面對這樣一些具體的事件的時候提升自己的反抗意識的,提高他覺得要追求合理的一個制度的意識。所以對我來說零散化本身會有影響,但是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地方就是我剛才說的勞資矛盾夠不夠,他們有沒有辦法引出來集體行動,在行動的過程去理解這一項行動的意義。階級意識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發展出來。
連結工人運動:學者難有作為,但學生還是大有可為
蹲:那到目前為止學者、學界有沒有想到一些合適的組織方式?
潘:學者、學界是很難有作用的,組織方式是靠工人自己摸索出來的。學者一定會越來越沒有作用,2010年那時候有很多學生學者可以組織在一起,現在的政治環境下是越來越難。作為一個學者他有些什麼信念和堅持才可以令他承受這些壓力呢?這個都是有待摸索啦。我們只是看到空間越來越小,工會又不作為,學者在之前那個階段可以幫到很多忙,現在這個階段有困難工人就只能靠自己。你剛剛說有什麼新的組織方法,那不就是靠工人自己去摸索。但我都相信很多工人階級出來的學生,他還是會投入去支援工人。
蹲:為什麼學者較為被動?
潘:階級位置總是有一些影響的:就是學者始終不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工人階級的進步性來自於我說的勞資矛盾、結構性位置。在遇到問題的時候資本當然不會幫工人,政府能幫多少不好說,社會也沒有相應的可以支援他的機制;這樣的情況下,作為一個工人階級無論承受的壓力有多大他都會採取行動。
學者相對處於一個比較優越的位置,要他去犧牲所有的東西去貢獻,而不是問題燒到自身沒路可選,很難。所以我會覺得在國內的情況,不是說沒有,一個社會總會有一些公共知識分子,總會有一些有良知的人,但一定數量的、有規模的學者,在國內我還見不到。
蹲:相對於學者,為什麼學生會比較進步?他也可能去走中產晉升路線呀。
潘:我想這取決於兩個位置:一個結構性的位置,一個能動性位置。結構性位置指的是越來越多大學生畢業之後面對的壓力和現在打工一族分別不大,除非你是來自很精英的學校——大學生有農民工化的現象。還有就是能動性,能動性位置離不開結構性位置。在中國,這個結構性因素就是我們始終會有一些社會主義的遺產,就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傳統,革命傳統是告訴我們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裡面,工人應該是有地位的,作為一個勞動者的基本的尊嚴是需要的。因此追求平等、追求自由的這個基礎,相對比資本主義社會其實要來得比較有基礎的。一旦結構性的位置和能動性相互結合,我們會見到中國的大學生長遠支持底下階層,不只是工人,還有農民。
對這個力量,我覺得相對是樂觀,雖然知道接下來的政治環境會很惡劣,但這個左翼的力量,我覺得相對比其他地區要更有基礎。

蹲:那對大陸的左翼青年,老師覺得他們當下可以做些什麼?
潘:調研報告隨時都可以做的。現在做不到大規模,但是可以以小組形式去調研。比如說疫情期間有很多地方的大學生、中學生下去接觸一些清潔工人,做了一些互助小組出來,這都是很有鼓勵性的一些例子。在中國大陸,我覺得只要願意做事情,還是有很多空間和可能性。
蹲:您對我們這樣一個左翼媒體有什麼想法和建議?
潘:我覺得左翼的意涵就是連結底下階層。怎麼連結呢,第一步就是認識,要了解他們的世界,第二步才是和他們共同去摸索出一些改善的方法,我覺得第二步比較遠,第一步做了再說第二步。再到第三步寫文章才會貼地落地不抽離,左翼的思想很容易離地,自己想像自己在做一些很進步的東西,但是那些東西和人的生活離得很遠。
期待你們可以摸索到第一步和第二步的高度結合。
——End——
可以關注telegram蹲點廣播站:https://t.me/squatting2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