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关系和纯真博物馆
2019-02-10
“死亡永远在路上,但在它悄然降临夺去生命的有限性之前,你不会真正意识到这件事。我们憎恨的正是那可怕的精准。可是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才会以为生命是一口永不干涸的井。然而每一件事都只会发生一个特定的次数,一个很少的次数,真的。你还会想起多少次童年的那个特定的下午,那个已经深深成为你生命一部分、没有它你便无法想象自己人生的下午?也许还有四五次,也许更少。你还会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也许二十次。然而我们却总觉得这些都是无穷的。”
这是在保罗鲍尔斯的小说《遮蔽的天空》里在波特死后,他的妻子姬特回忆和他生前关于死亡的讨论。
关系破碎的那一瞬间就像一次死亡体验。曾经你觉得每日相处的日常是没有止境的重复,你以为那些孩子般的天真快乐是可以无限续杯的冰镇可乐。关系断裂之后,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琐碎细节,都再也不会有了。关系破碎不只是决裂的那一瞬间,而在决裂之后,你会无数次体会到,你与曾经亲密无间的那个人之间的快乐的次数已经用完。破碎只在那一瞬间,持续的震荡才刚刚开始。
失恋博物馆(Broken Relationship Museum,我更愿意称之为破碎关系博物馆)的藏品里有一把斧头,一个失恋的柏林男人,用它砸烂了前任的所有家具。在她被赶出家门,立即与新女朋友去度假的期间,他买来这把斧头,每天砸毁一件她的家具。这把斧头成为他宣泄无处可诉的愤怒和安抚伤口的疗愈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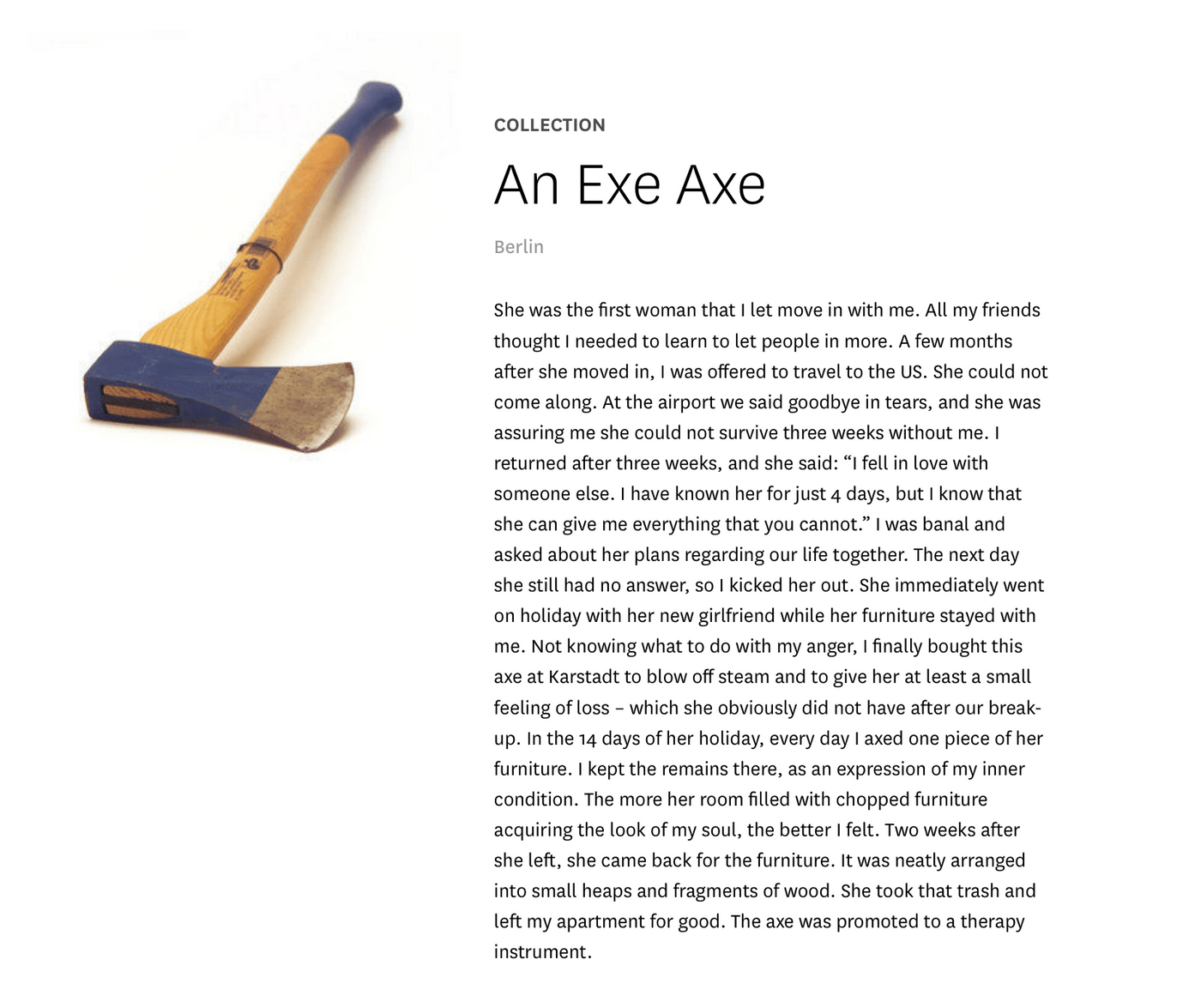
失恋博物馆里这样的藏品非常多,他们还带着决裂时丝毫未减的愤怒。比如那件脸部裂开的神色怪异的小矮人。
“离婚的那天,我看着他神色傲慢地向一台新车走去。一怒之下,我把那个矮人雕塑向他新车的玻璃门扔去。小矮人砸在车窗上,被反弹到了沥青路面。矮人形成抛物线的镜头,我永生难忘,因为它定义了爱情的结束。”

除了愤怒,展品里也有一些即使最后关系破碎,但依然带着彼此高光时刻温暖光亮的物品。没有欺瞒没有背叛,它们大多是因为事故或疾病而嘎然而止的。其中有一把钥匙,它旁边的注脚写着:
“一直说爱我的你,送给我许多小礼物。这把开启心房的钥匙,是其中之一。但是你却总是别过脸去,不肯和我睡觉。直到你因为艾滋病死去,我才真正明白你说的爱的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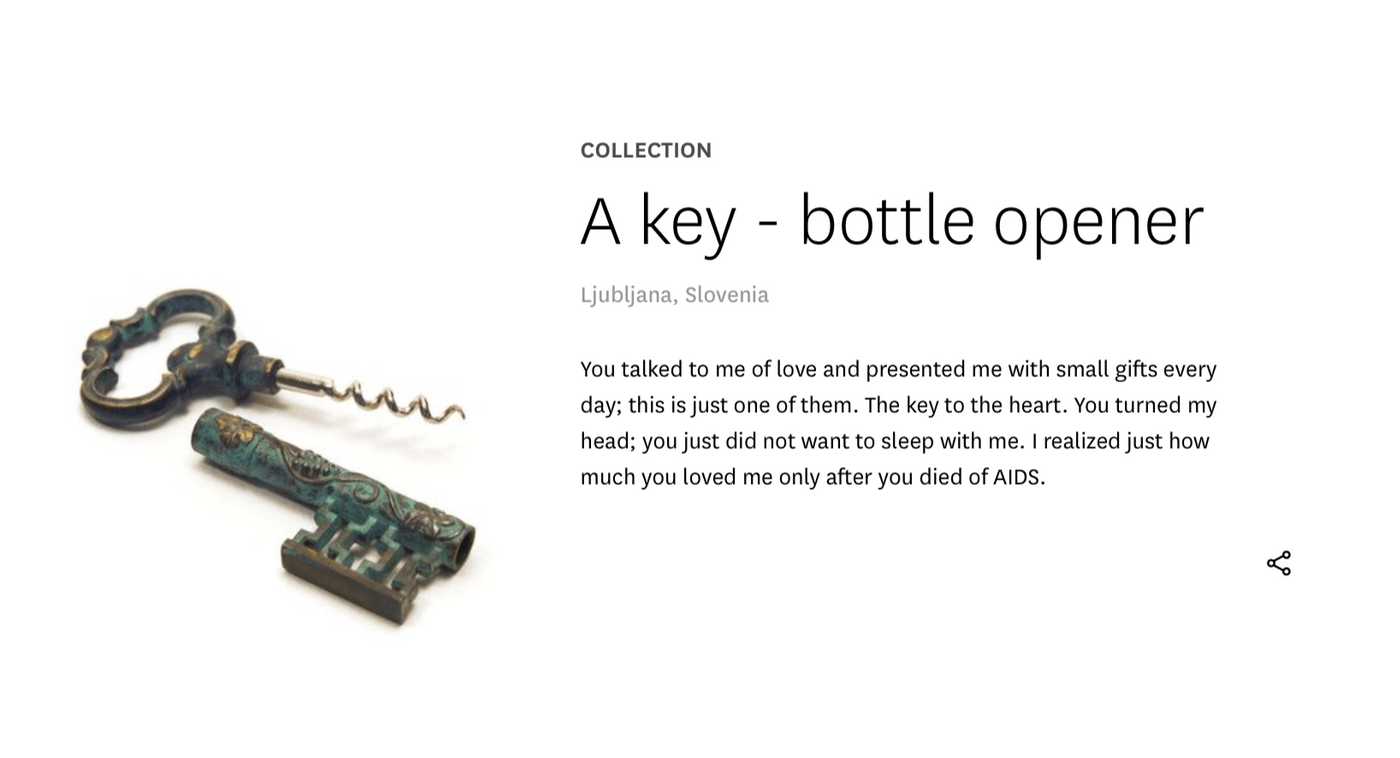
还有一张照片游乐场过山车上的一对情侣照片,特别触动我。
照片上两人并排坐在过山车上,一个脸上是兴奋刺激又有点害怕的表情,另一个眯起眼睛淡然处之。不知什么原因,他们都没有及时拷下所有游乐场拍下的照片,而等到照片中的女主角试图去寻找那些照片的时候,系统早已自动删除了当时的记录。而那个曾经坐在她身边的人,在他们一起度过最快乐的一年后,在他们的订婚仪式前一周,去世了。
人心不可捉摸,人生变化无常,带有特殊记忆的物品成为人在关系破碎之后唯一可以实实在在握在手里的东西。我们总是赋予这些物品某种意义,并在其中投射自己没能在亲密关系中实现的欲望,对物的掌控感多少能消解一部分关系破碎之后的失控感。这件物品从此成为一种隐喻。隐喻是危险的,因为你赋予它某种价值,让它成为一个中心,爱情开始于一个隐喻;隐喻在此时又有点黑色幽默,爱情也结束于于当初截然相反的隐喻。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帕慕克在《纯真博物馆》里描述的凯末尔对和所有芙颂有关的一切物品的那种迷恋。凯末尔在和门当户对的茜贝尔订婚后,念念不忘清贫的远房姑妈家的女儿芙颂,并因此最终和茜贝尔悔婚。几年后当凯末尔终于找到在他订婚晚宴后消失无踪的芙颂,芙颂已经嫁作他人妇。但此后的七年里,凯末尔几乎每晚都去芙颂家拜访。他会时不时偷偷拿走一件“带有芙颂气息”的小物件,而后买一件新的替代品送回她家。有时候是饭桌上的小盐瓶,有时候是浴室里用完的香水瓶,甚至是芙颂在不同时间点不同的情绪下掐灭的4123个烟头。
持续七年的拜访,凯末尔终于等到了芙颂离婚的那一天,他们似乎可以重新开始。在他们婚前去巴黎的旅行途中,芙颂决绝地开足马力撞向一棵大树后离世。凯末尔在此前后收集的关于芙颂记忆的物品装满了他和芙颂约会的迈哈迈特公寓,这些藏品构成了如今伊斯坦布尔楚库尔主麻街角的那间纯真博物馆。
去年第一次读《纯真博物馆》时,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凯末尔对芙颂没有来由的痴迷。但后来不经意在拉康的理论里找到一点头绪。
拉康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里论述过一个概念:“objet petit a”,大意是人作为主体把对自身的匮乏或是虚无具体化,变成某种珍宝(treasure),投射到他人身上,从而去他人身上追寻它。它是欲望的对象,也是欲望的成因,它成为人的生命重心,成为某种意义,让人一次次追寻。Objet petit a呈现为一个具体的人或者物品,实质上它是这个具象之下的一个空洞,无法得到,无法获得。
对凯末尔而言,芙颂可能就是他的objet petit a,他在芙颂身上追寻的是一种in you more than you的东西,正因为无法得到,才能成为他一生追寻的珍宝和意义。他收集的承载着他关于芙颂的某种记忆的物品,都是他的objet petit a,是想要得到又无法得到的欲望。Objet petit a的不可追寻也在于它总会在你将要得到的时候溜走,甚至是你阻止自己得到它,故意错过它,甚至故意破坏它。我有点腹黑地想,如果芙颂和凯末尔有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圆满结局,她也会难以免俗地从红玫瑰变成蚊子血。作为objet petit a的珍宝一旦得到手,便会失去赋予它的意义。芙颂不幸的死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却是凯末尔的幸运,他得其一生去追寻这个定格不变的意义。
如果说纯真博物馆里收藏的是凯末尔得以一生追寻的意义,那破碎关系博物馆里收藏的则大多是失落的无处安放的意义。说来残酷,因为事故和疾病而无疾而终的爱情,多少留给活着的人不断以积极的方式重写记忆的空间。因为背叛而告终的关系,太需要幽默感才能从那个人造成的阴影中走出来。不论以哪种方式结束,关系破碎之后,理智上知道这段关系已经结束,可情感上却依然对对方保持依恋,情感还没有脱离那种惯性。人常常会在分手后感到好像失去了一部分的自己,并且是我们认为的更好的那一部分自己,甚至我们失去的是那个in you more than you的意义。
李沧东的电影《燃烧》里,申惠美告诉李钟秀:对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布希曼人(Bushmen)来说,有两种饥饿:Little Hunger 和 Great Hunger。Little hunger是生理上的饥饿,只要填饱肚子饥饿感就会消失。Great hunger是人生意义上的饥饿,是意义的缺失。
去年三月,我遇见了我认为可以在他身上赋予意义的那个人,感觉的人生意义上的饥饿好像也可以和他一起填饱。后来分手后我主动见了他三次,最后一次是我找到工作匆匆离开里昂搬到巴黎,他来火车站接我。他向我走过来的时候,看着他的脸我再也感受不到一丁点快乐,我好像成功地把那份意义从他身上剥离了。我把让我感受忘我快乐和狂喜的他,从他身上剥离了。我们的关系在最后的见面定格,变成一个失去生命的固定标本。它被装进了一个小盒子里,就像被收藏在博物馆里的物品,失去了所有的生命力和延续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