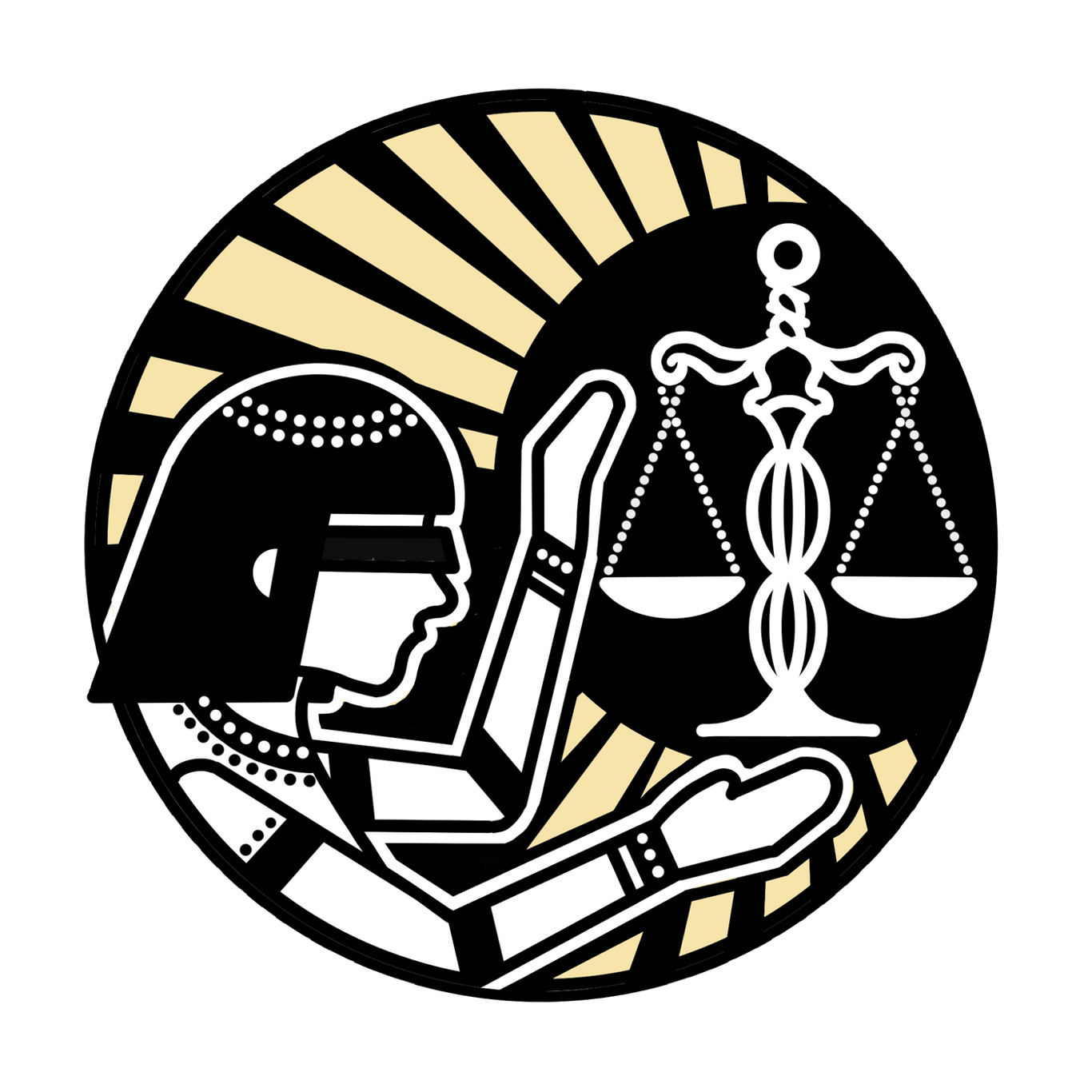媒介、公共事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转变 |《地理媒介》笔记 𝟜

广播电视、公民与城市的关系
20世纪后50年的迅速发展与家庭私人空间的转变以及新媒介事件类型的出现紧密关联在一起。
二战以后,私人家庭成了媒介使用(观看电视、收听广播)最主要的中心,广播电视生态推动了资本主义从战时生产型经济向以私人家庭为中心的基于生活方式的消费经济转型。除此之外,电视也成为了战后政治的重要推动力:原本长期紧密的城市群体被更为松散、更具移动性和多样性、并且在空间上更为分散的各种关系所替代;政治成为一种越来越围绕着组织化媒介展示的专门职业。
媒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城市街道,创造出一种以公众围观和分散性的反馈为特征的媒介事件。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街道的“不文明”和“不安全”被视为城市衰退的象征,这对全球政治共识作出了挑战,在那个时期,社会运动将公共空间作为主要的接触区域加以广泛使用:比如游行抗议、静坐示威、艺术表演等新的社会行动和公共展示进行公共传播。这些创新的公共生活形态与广播电视快速发展建立起来的公共文化条件密不可分。
电视网络设施标志了将公民与城市关系重塑为大量私人关系的独特转变。电视成为了“通向世界的窗口”,观众可以在遥远的地方“安全”地与各种公共事件“保持接触”(哈钦森 Huttchinson,1946)。电视利用其新的传播能力生产出空间上更为松散的社会同时性体验。不过人们也在逐渐意识到,“通向世界的窗口”允许观众看到的内容是充满选择和偏向的(Gitlin,2003),主流媒介本身也构成了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渠道的稀缺性使“把关”和“再现”问题成为了批判的焦点。

无电视直播的革命
广播电视逻辑中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事件”本身越来越多地为了媒体报道作出相应的策划和调整。信息供应、控制报道、媒介审查制度共同发挥作用,尽可能地快速几乎成为了第一要务。“快速反应”正在逐渐被整合进“私人生活”领域。
“9·11”事件告诉我们,第一,我们需要强调“集中运动”(campaign,既可指军事,也可指政治和市场营销行为)的逻辑已经全面“渗透”到各种规模和类型的公共事件。第二,原本主要限于军警等权威部门运用的“快速反应”传播,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包括“恐怖分子”和“激进分子”在内的其他主体所采用。第三,电视将深处家庭环境的受众与外在世界的事件勾连起来的“中介化”过程,也不可简单地理解为“真实”和“再现”或“主动参与”和“被动观看”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常被用于控制管理的目的。
占领网络化公共空间
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2006)从宏观上区分了“工业信息经济”(industrial Information economy, IIE)与“网络信息经济”(networked information economy, NIE)。电影、音乐、出版和电视等传统媒体被认为属于“工业信息经济”:它们需要相对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来支持信息生产和发布过程。
两种不同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网络信息经济”:一是电脑从数据分析计算的工具转变为无处不在的媒介和传播设施,二是相对廉价的全球互联网连接。电脑在同一设备中综合了内容获取和内容生产的功能,足够数量的用户能够用软件和硬件方便地制作各种相对内容无损的数码拷贝并将这些内容以很低的成本加以传播。
网络信息经济不仅对传统媒体行业发起了冲击,其“去中心化的个人行动”特征推动了更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迁。作者认为,城市公共空间的网络化已成为探索尝试与具身他者发生关联所需的社会技能的关键实验场所。

将大量人聚于特定地点仍是获得媒介注意、举行官方庆典仪式以及开展非官方社会运动和政治抗议的重要手段。现在占领公共空间依然能按照原有的模式获得广播电视媒体的关注,但有两个关键因素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公众集会的组织发生了变化;其次是集会者在多大程度上能产生并传播自己对行动的叙事。
快速动员的能力曾是军方等高度集权机构的特权,而各种数字网络已经使其他社会性动者越来越多地具有同样的动员能力。占用公共空间的行为常常使参与者自身发生转变,改变了个人和集体想象的界限,并创造或增强了各种政治凝聚力。
地理媒介的构成
地理媒介的各种功能不仅处于城市空间更构成了城市空间,使得多样的、强烈的且反复的“反馈”流在事件发生时塑造了公共事件。
城市和数据之间的形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2006)提出了“增强空间”(augmented space)的概念,指被不断动态变化的信息所覆盖的物理空间。这样的说法优点在于没有被特定的技术、平台或者内容所局限,按时了构成城市最重要的基础仍旧是物理现实。纷繁复杂的数据流和各种技术增强背后始终是固定的形态在发挥作用。
地理媒介不仅重造了物理、物质、具身和面对面的交往;同时也改变了虚拟、非物质、非具身和远距离的存在。在各种实践和远程传播形态已经常规化的情况下,面对面交往只是许多社会交往方式中的一种可选形态。
如果能有效地结合城市的历史资源和数字网络的连接和散播功能,公共空间就成了考察公共传播新形态的“前沿领域”,供行动者试验新形态的公共传播,包括行动者之间试验性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