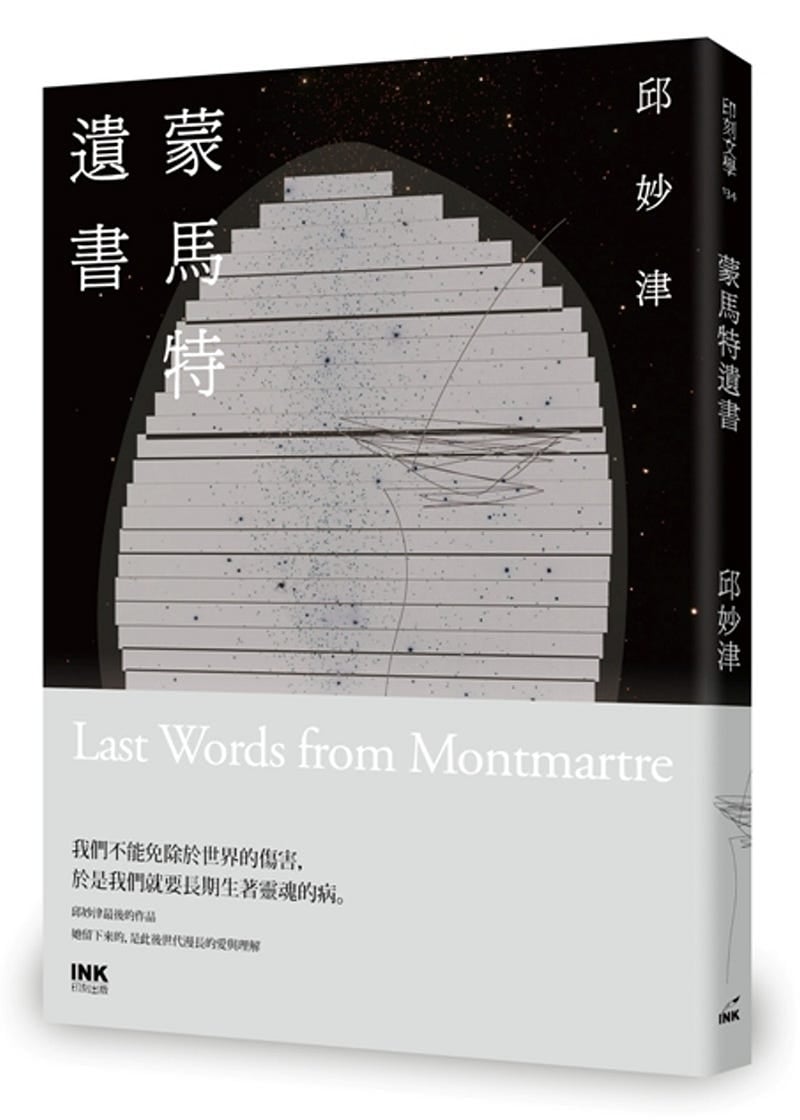【文本分析】賴香吟《其後 それから》與邱妙津作品的對應部分(三之二)
很多人對五月的印象是,善於傾聽,善於撫慰,善於給人能量。
不過,到底是在哪裡岔了出去,她很快便感覺到了五月笑容背後的匱乏與不安…… 五月自殘的傾向是很早的了…… 相較於心靈所敏感到的痛苦,肉體顯得非常小,靈魂太巨大,承載不了……
— — 《其後》第一章「活動中心」
五月在外人眼中,「看起來活得很好,幾乎可以說,生機勃勃,像個勁量飽滿的電池小熊」。雖然內心有強烈焦慮和痛苦,可是五月竭力隱藏一切,不讓身邊的人苦惱。賴與五月因志趣相投(閱讀、電影、寫作)而熟絡,傾談多了才窺探到五月的陰暗面:
當大多數人感覺五月亮得像星,蹦蹦跳跳如小猴的青春時期開始,她便飽受五月死亡黑影威脅,一天到晚要提心吊膽她是否又傷了自己,擔心五月碰到足以致死的大小事,是的,純以表象,一般眼光來看,有些事可能真小,小到太宰所說:碰到棉花也會受傷,膽小鬼(弱蟲)有時連幸福也感到畏懼。
— — 《其後》第一章「活動中心」
到底五月心靈上承受著怎麼樣的痛苦,會令她不惜自殘,以肉體的痛楚轉移注意力?
關於同性間的愛戀,她看五月作品《手記》,才知道當年以為五月都想過了,夠勇敢了,沒什麼困擾可以打倒她,沒問題的 — — 這個預設是完全錯了。
五月總表現得強韌。寫在《手記》裡那些核心底處的困難,五月到底有沒有講過呢?
— — 《其後》第一章「活動中心」
看完《手記》,我心痛於五月對性別焦慮如此之深,遠遠超乎我所知道的程度。
— — 《其後》第五章「春暖花開」
讀到這裡,我似乎重新搞清《鱷魚手記》的重點 — — 作為潛伏在人群之中、假裝成人類的「鱷魚」,這事本身就造成了極大的焦慮和痛苦。
但坦白說,第一次讀時,並不是那麼容易同理,畢竟在她把「拉子」(LESbian)這個詞引入華文世界之前,就已經有不少男子氣的女同志存在於台灣(例如,比邱小一年的陳雪,從她的作品中,得知她年輕時也曾有男子氣的同性戀人),而顯然不是所有T/同志都有她那樣的焦慮。所以,即使邱的焦慮源於同性傾向,歸根究底,邱之所以深受驚人程度的焦慮所苦,是因為她有極其敏感的內心。
「自殘」這種行為,看似自我傷害,但設身處地想,用肉體痛覺轉移注意力,其實也是一種求生存的手段 — — 至少,這樣就能以一種可承受的痛苦,取代心靈難以承受的巨大痛苦,終究是「減輕痛苦」的一種行徑。就如我們一樣,賴只能「試著理解」,但人的想像力往住受限於自身經歷。
本文第一部分提到賴與五月在台灣見了一面,之後賴收到五月的來信。
從台北回來沒多久,收到五月字跡混亂的信,讀起來糟透了;我愈來愈面臨到五月的危機。連著幾封純淨得宛若遺言的信,除了別人的傷害,她重提我之於她在什麼位置,什麼意義,甚至說出了她對我的需要;這類語言,在過去,在我們之間,是被禁絕的,現在,她宛若自言自語,歌詠吟唱,吐露出來,那已經不像真正向我需求什麼,而是一種眷戀,一種回首。
這使我感到恐怖,迴光返照的絕美。我看過她很多低潮,但這次分外緊張,我在面對一個死神相隨的人,用她自己恐怖至極的說法:死神就睡在我的枕頭邊。
— — 《其後》第五章「春暖花開」
這短短220字敍述,蘊含了巨量訊息:大學時期,賴就深明五月對自己抱有何種情感,但賴不允許她明說出來。因為極其珍惜與賴的友誼,在能夠控制自己情緒的時候,五月是有小心翼翼把這份情感藏在心底的,還一直在交女朋友去滿足自己的愛慾(這在下面引述《邱妙津日記》時會討論),把賴珍而重之放在「神交」的位置,從不敢逾矩。賴在第二章提過:
她們小心翼翼要作對好朋友,反倒失卻了以往的溫暖,誠實,幽默。她們不得不彼此覺悟,存在就是折磨,承受不了,唯有禁斷。
— — 《其後》第二章「門」
所以,當看到五月「重提我之於她在什麼位置,什麼意義,甚至說出了她對我的需要」時,便知道五月已經情緒失控,狀況不堪設想。
理解,同感於另一個人的靈魂,不忍心使之受傷害,想如善待自己一樣去善待對方,這是否只限定於身心互屬,情感占有的兩性之愛?後來我讀柳美里披露於《命》,與東由加多的情感聯繫:一種並非情人也並非親人的依賴與信任,一點都不覺得難以理解,而是一件自然的事。我無論如何不能無感於五月的受苦,那其中有太多我們的同質性,我們的歷史,儘管這共感並沒有投射成彼此適合的愛情,但我能在這時刻別開頭去當一個徹底的陌生人嗎?有沒有愛情故事可說,歸根究柢還是與人有關,而非只是與性別有關,如果同性無愛,異性也未必有愛,那時我漸漸清楚了,愛不愛,歸根究柢只是等待對象的獨特性。
— — 《其後》第五章「春暖花開」
她們下一次見面,就是五月(在四月)來訪東京之時,也就是《蒙馬特遺書》中Zoe與小詠溫存的片段的原型。
櫻花季節,花飛漫天,死亡黑影相隨,該如何抵抗才能不使之成真?我們之間,一對和解的朋友,彼此已經知道在對方心中的分量,也都明白情感必須是一件誠實而強韌的事,不管那以什麼定義,即便是朋友,也不是隨便說說而已。
那個春天,我無論如何只希望五月能活下去,至於她要變成怎麼樣的人,都無所謂。
— — 《其後》第五章「春暖花開」
賴在這個時間點,對於五月如何看待自己、到底抱有友情抑或愛戀,已經不再計較。也許因為如此,在《邱妙津日記》裡,邱敍述這段回憶時,是確信賴對她抱有愛的:
愛是一種「體驗」。這是我去看K(賴)及看完《貝多芬傳》之後的體驗。如同K對我所示範的,人一生的愛是無限的,人會因各種理由去愛許多人,然而愛是一種「體驗」而非其他部分的內容,如果愛真的發生了,愛的關連是不能抹除、取消的,愛的關連性是不可遺忘、不可斬斷的,任何的取消、斬斷都是對生命的傷害。
⋯⋯
徹底尊重一個人的生命,像我對待K那樣,尊重她生命所要呈現的方式。除了我自己成為一個更「穩」、更有條件去給予愛的人以外,我到底憑什麼把愛當「禮物」給別人呢?
⋯⋯
K這三年的長大對我的意義是:一個人或許很容易需要我的靈魂,卻要等到她能真正面對自己的內心及獨立的生命意義之後,她才能真正接受我的生命及愛我的愛。真愛的現象或許經常、偶而會出現,但真愛的生命之於我卻是第一次在K身上開花結果。從此之後我的生命及我的愛之於她的意義是再也不會有什麼改變了,K是第一個知道如何愛我及敢於來承擔愛我的生命及我的愛這件事的人。
— — 《邱妙津日記》1995年4月13日
讀完《其後》再讀這個有點眩暈,但我實在不該深究「希望一個朋友不要尋死」與「很需要那個朋友的靈魂」是否等價 — — 站在賴的立場看,比起朋友的死亡黑影,這誤會肯定屬芝麻綠豆小事。而我們都知道,這是邱死前與她最後一次相聚。讀邱的日記,我想邱覺得賴已經為她做得夠多(可能比大學時期溫柔百倍)且非常感恩。然而,最後邱還是敵不過情緒病,遺下賴一人在世上悔恨自己當年有何不足:
我不是不明白,但總也有做不到的時候。或者,我的的確確錯了,如果我知道那就是我們最後的時間。彼時走到那裡,我已有了點信心,她行的,她會走過危機,我不以為死亡帶得走她。我解釋得太冷靜,太自我中心,雖然我知道只需要簡單的安撫,言語溫柔,偏偏我沒做到。我可能也因為有了信心而對她提了些要求,不能這樣不能那樣,了無新意,拉著人要活下去的言語。
— — 《其後》第五章「春暖花開」
以下將對比《蒙馬特遺書》的片段,與《其後》賴的敍述不一樣的地方:
走出咖啡館,我們手牽著手走在小雨點裡,身邊是密密麻麻的日式小酒館,忙著打烊的小商家,短短狹狹的街道,好溫暖的夜晚。
— — 《蒙馬特遺書》第十七書
當年她們真的有牽過手嗎?
賴在《其後》說的卻是:
天色向晚,春寒料峭,我們疾疾走過公園,穿得單薄的我打起哆嗦,五月執起我手,放在掌心搓揉想幫我取暖,我不慣與人這樣親暱而抽回了手,瞬間閃過一念:錯了。
五月臉上浮出受傷的神情,她想對我生氣,那生氣是久遠的,又是無奈的。回程電車上,彼此親善而壓抑著屬於自己的傷口。
— — 《其後》第五章「春暖花開」
五月連賴的手都無法觸碰,那,在壽司店裡的甜言蜜語,肯定也是虛構故事情節:
我拘謹地坐著,把雙手交握在併攏的雙膝上,不敢轉頭看一眼身旁的小詠,不敢亂動,生怕一動,這來不及吸蘊的幸福感就要渙散,我像一個慶典裡腼腆的新郎或新娘,頭頂上飄撒著七彩的花粉…… (想親你一下。)我很小聲地說。 (好啊。) (可是我不敢。) 坐上位子,她仔細地幫我挑選適合我胃口,而我也可能吞嚥得下的東西,盤總是兩個,她先將其中一個吃下,再將另一個壽司中的芥末挑去,把我怕的魚刺也挑去,放下筷子看著我,陪著我,細嚼慢嚥地消化完那個她處理過的壽司,然後,才又轉向前方去挑選新的食物。
— — 《蒙馬特遺書》第十七書
最後Zoe與小詠的別離,邱也是寫得唯美柔情:
我不願她送我到機場,不願再面對與她別離的場面,我獨自在新宿摸索著直達機場的高速列車,搭機回巴黎。(倘若有一天東京再發生大地震,所有的人都失去身分,那時,重建的行列中,我將不會認領自己的名字,我將不再開口說話,除非是你將我自人群中領走,因爲,我不需要開口,你也會認得我吧?)耳邊再次響起她的聲音,我從高速行進列車的窗玻璃上看到她的臉,我的淚水撲簌簌地滴落,這次,眼淚及哭聲都被釋放出來。
— — 《蒙馬特遺書》第十七書
然而,在五月離開東京的前一晚,其實她與賴沒頭沒腦地大吵了一場:
……接下來的爭執到底說了什麼,完全沒有記憶,就連潑開來吵的題目是什麼也沒有印象,大約就是各自為自己控訴吧。我們原本就各有各的問題,因為自己不能完整而悲哀,在寬容自己的人面前,悲哀任性地轉成了憤怒。對誰憤怒?根本不是對對方憤怒,但我們就是喊叫起來了。
沒道理吵成那樣子的,我們根本不是因為對方,也不是因為此時此刻而吵,然而,好不容易堆砌起來的堤防畢竟潰堤了,長久由無數情緒石礫所積累而成的枯山,大雨沖刷,滾滾石流,淹沒了我們。五月開始嘔吐,哭泣,她那滿臉亂七八糟、完全放任自己失控的模樣,如同她在電話裡對著我嚎哭的聲音,壓垮我當下脆弱的心防。
— — 《其後》第五章「春暖花開」
賴為了冷靜下來,她遺下五月離開了住所,踱步至天明。
我很受挫,覺悟到要照顧一個心靈脆弱的人,我得極端穩定。五月說要到東京來,我以為自己能做到,相信性別不會阻擾我們,看來若非我高估了自己,就是低估了五月,到底是同性愛戀真正無法超克,還是因為五月現在太脆弱,一根羽毛都可能使之受傷?
很多年後,在閱讀心理學書籍求援的階段裡,我看到這樣的一段話:不管多麼深愛自殺的人,到死亡那一刻,最持久的關係也常已磨損,枯竭,或完全斷絕。
磨損,枯竭,完全斷絕。看看這些醜陋的字。我對自己懊惱不已。疲憊如浪襲來。
— — 《其後》第五章「春暖花開」
冷不防,草率一別,竟成千古恨:
打開房門,我預估看到的是一個累到睡著的五月,要不就是又恢復沒事伏在桌上看書寫日記的五月,我想我們應該還能朝對方擠出一個微笑,我以為我們會言歸於好,彼此修復,就算她不要我送她去機場,起碼我們可以好好告別。
然而,打開門,沒有人,陽光從窗簾穿射進來,映照出空氣裡塵埃細細翻飛,彷彿那是唯一的動靜。床鋪被褥摺疊整齊,地上的嘔吐物也清乾淨了,我的房間回復平常模樣,但那收序是五月的風格,那片刻,我竟然想起最早她景美房間的模樣,物與物的秩序。
她離開了。這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五月竟然還能像以前一樣,說走就走。我搥胸頓足,不該這樣放下她的,她的狀況那麼糟。
— — 《其後》第五章「春暖花開」
從《蒙馬特遺書》與事實的落差看,我猜邱書寫這些段落時,是抱著文學創作的心態下筆,將美好的想像包裝成小說情節。讀完《邱妙津日記》,我更傾向相信賴之所言:
……我相信我們之間的承諾,寫,然後,活。五月向來總會比我早一步踢翻這個世界,儘管這一回合如此險峻。
即便如此,我仍然無法同意《遺書》的寫作是為了接下來自殺而作的留言,一個早已篤定的計畫,甚至是一場淒厲的死亡表演。相反的,我認為《遺書》充滿了求生的努力,對死亡的爬梳何嘗不是為了克服死亡。寫成了,是要走過這個關卡,而非寫完了即可赴死。儘管後來的發展看起來像後者,但那實在是另一樁現實意外的結果。
— — 《其後》第六章「那一天」
邱盡了所能對抗情緒病以活下去,只是不幸敗北了。
本文最後一部分,將會談及《邱妙津日記》中邱積極向生的線索,以及對《其後》一書的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