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东北直男观察报告》报告
三个月前,笔者曾批判某大众自媒体的《东北直男观察报告》,撰写文章《观察<东北直男观察报告>报告》,分析了“东北”认识装置的运行机制。值得补充的是,认识装置的运行是可逆的,输入a可得b,则输入b同样可得a。该自媒体近日的新一期阅读同样达到十万加的推送《社会人渣鉴定指南》,就是这一点的证据。黑人只是黑人,只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维持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东北人只是东北人,只有中国资本主义体系所依赖的地区不平衡关系下,他们才会因身上的区域和阶级烙印成为可被鉴别的“绝对直男”和“社会人渣”。在此,我们重新阅读这篇三个月前的旧文,依然可以感到它未曾衰减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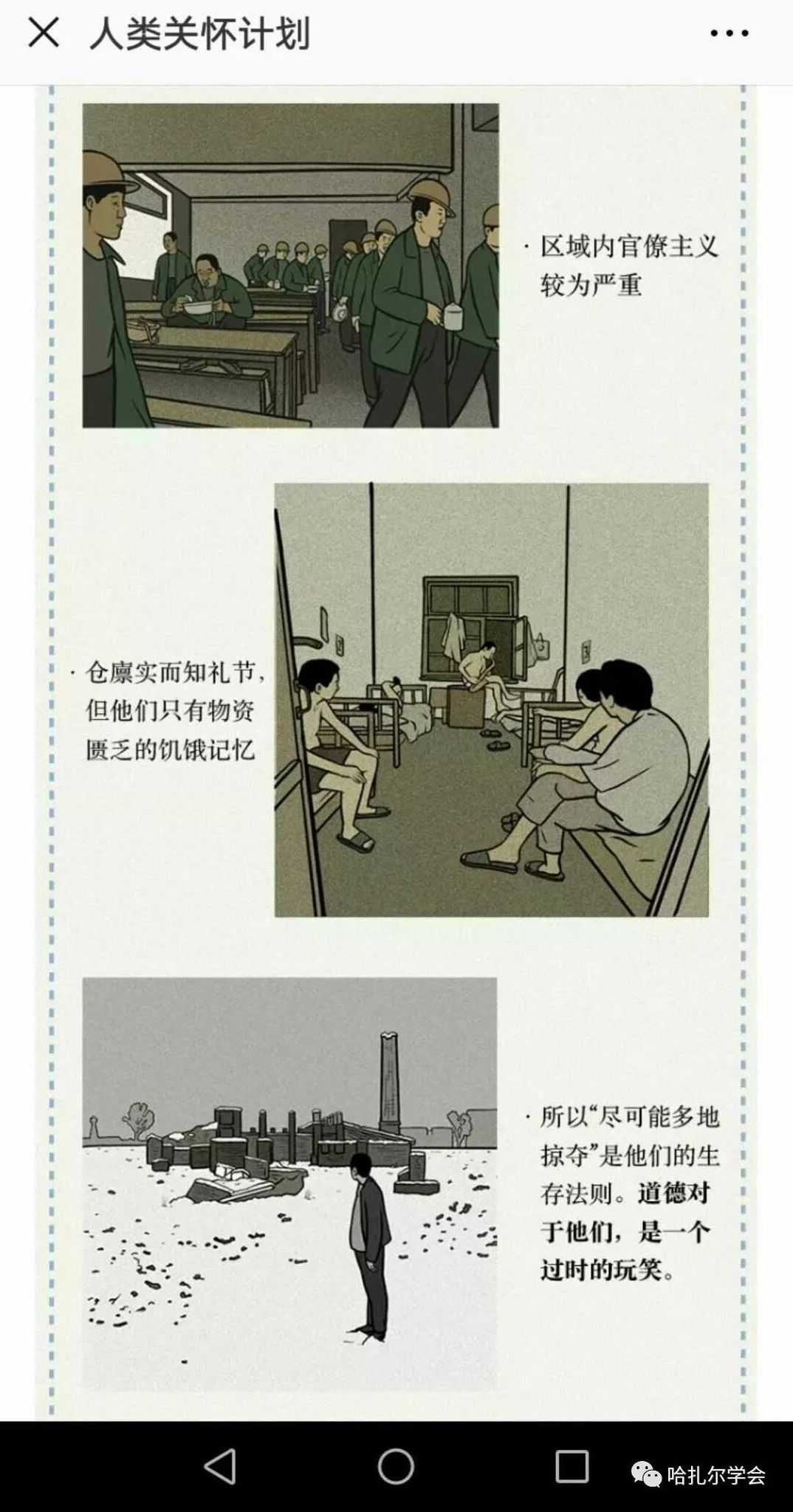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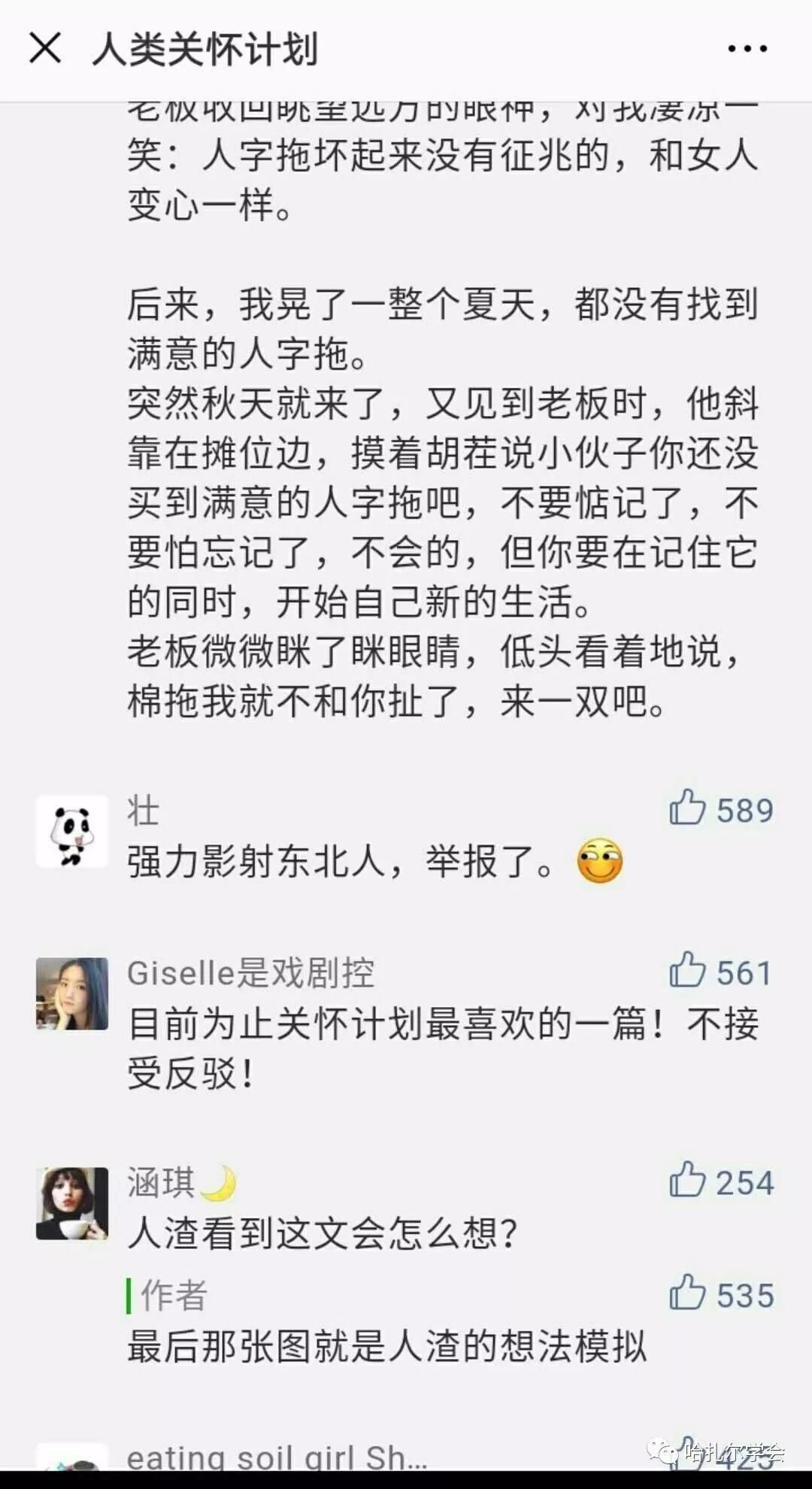
5月31日,微信公众号“人类关怀计划”发布了一篇名为《东北直男观察报告》的文章。到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10万+的阅读量。这篇报告,使用了两大认识装置——“直男”和“东北”,我们不妨从“直男”开始,走向“东北”。
近两年,“直男”作为一个形容词,在某种暧昧的负面意义上被广泛使用。“直”表示性取向本是“硬译”自英文中“straight”的类似用法;则“直男”的涵义本来无非是“爱好女的男性”。然而,“直男”很快从一个“概念”而演化为“符号”——这一能指的所指包括不能或不愿去理解女性的心理;经常倾向直接表现工业社会及农业社会式的“男性气质”,从而似乎落伍于当今这个据称已成为“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等等。这种所指的漂移,引起了一部分男性的愤怒,他们认为,“直男”的负面色彩,正来自“女权”或“同性恋平权”等性别议题的嚣张强势。
抛去对性别议题的负面价值判断,这样的认识倒是符合直观的。出于类似的“直观”,一些汉本位人士对《狼图腾》等文本所宣扬的“输血论”也提出了“丑化汉族,美化草原民族”的指控。然而,在“输血论”中,草原民族真实的、鲜活的身体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只能以“血液”形式存活于汉族或曰“中华民族”的身体之中;这是一种中原完成对边地的真正彻底占领的“宣言”,也是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di)族(guo)”想象中,“一体”对“多元”的征服潜力被释放出来的一个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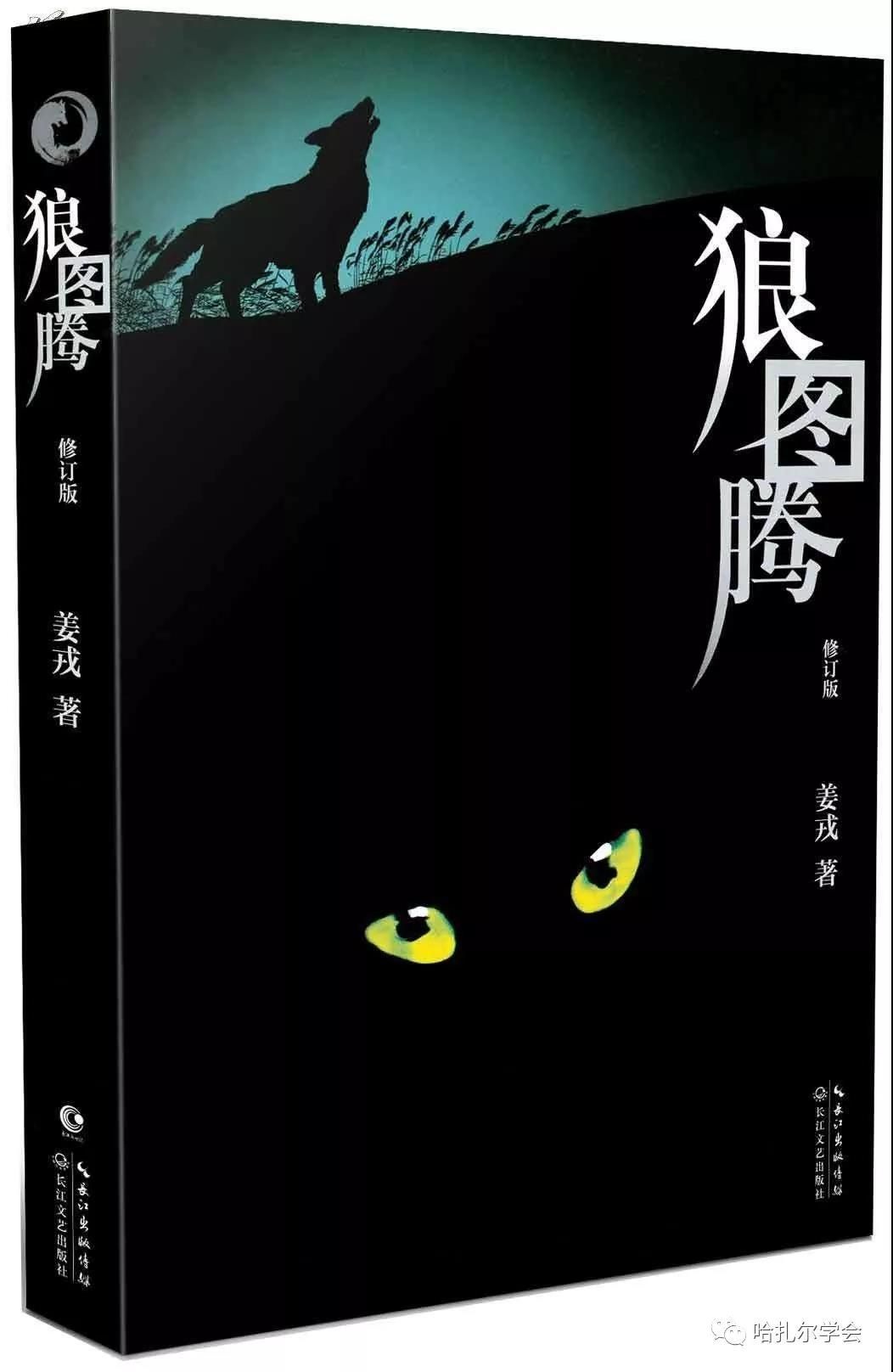
而就如同以上对“输血论依然是汉本位思想”的论证一样,“直男”话语也依然不难被识别出是一种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话语;在这里,“直”的程度成为了评价和调节当代“男性”(注意引号!)“德性”的尺度;这样,在“直”对面的“不直”也就消失了;对于当事人来说严肃认真的其他性取向也就不再成为一种真实鲜活的实存;不那么“直男”的男性只是更体贴、理解女性的“男性”,而也只存在这一统一的“男性”。这一话语在根本上堵塞了性别的社会建构理论的发展空间,比一般的男权话语更好地阻止了挑战现有压抑性性别关系的行动中的革命潜能;人们所能做的只是在给定的性别角色中调整自己的气质!因此上,应用“直男”话语时的“男性”也就只能依然是那种以父权制家庭家长为原型的男权的男性;一个“不那么直男”的男人,只是在用“温柔”的方式,更精致而不是更拙劣地行使男权的男人。在运行这一整个话语时,阴’茎都成为不在场的在场。它只是在嘲弄暴露狂式的行为,而并不排斥腰部以下鼓起的暗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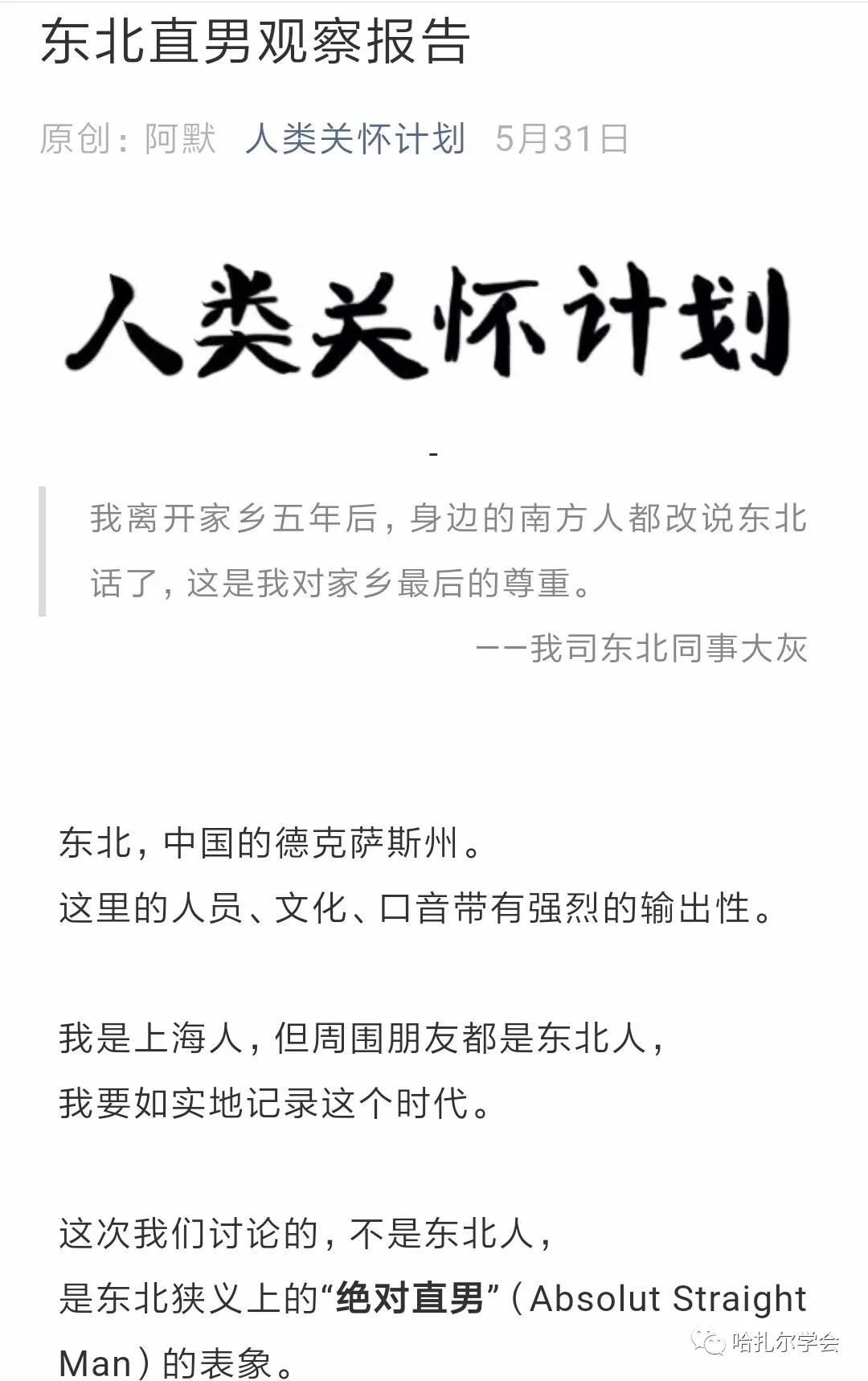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要关注的这个文本就显得更加有趣了;在这篇阅读十万加的《东北直男观察报告》中,开宗明义地说:“这次我们讨论的,不是东北人,是东北狭义上的‘绝对直男’(Absolut Straignt Man)”[原文拼写如此]。对此有评论说:“不能写一篇文章写的一个地方的人的缺点,别人质疑的时候说:我写的可只是你们那的‘绝对直男’,这个绝对又是谁定义的呢?”这个评论可谓准确地点明了这个文本中两大认识装置的关系:一旦文中传递的特定“东北”话语遭到质疑,“东北认识装置”失灵,不能成功“询唤”主体积极认同反东北意识形态时,“直男”认识装置就可以适时发挥作用,掩护“东北”撤退;“直男”形象的微妙负面涵义,成为了对东北进行东方主义书写时的“免责声明”。
不仅如此,“直男”与“东北”话语的重叠并置在上述防御性功能之外还有进攻性功能:“直男”话语本身被同步嵌入对东北的认识结构和东北的自我认识结构之中。关于后者,有自称东北人的评论者称:“现在东北的这茬小x崽子已经没有老东北范儿了,扼腕叹息啊”——“文中描述在事实层面有误差”的阅读体验,竟然以对“事实没能靠拢文中所述”的遗憾这一方式表达出来!可幸的是,这条评论得到的支持不算高。而关于前者的例子,文中和文后评论更是俯拾皆是。让我们只选取一个最巧妙的片段来看一看——
在“感情生活”一节中,以“交往过2个东北籍男友的小鲁”之口说出:“东北直男不爱戴套,他们觉得避孕这事得随缘”。我们是否有必要指出,东北地区著名的,同样经常被用来渲染东北之“没希望”的低出生率,以及和这种低出生率相比,也并不算高的人工流产率呢?当然没有必要;因为对“不爱戴套”的“东北直男”做出的这种评价,正像作者所说,是“价值不亚于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在他60岁写出的忏悔录”的思想性文本,而绝不可能用统计学等实证主义方法加以证伪。“不爱戴套”这种毫无疑问对性伴侣不负责任的恶劣行为,其负面色彩的“直男性”十分鲜明,而又在这一处表述中进一步获得了“东北性”,同时也以自身为中介进一步印证了东北之“直男性“。作者在另一处又说:“我对上海直男的观察,作为参照实验组放进去了”,那么,这处表述其实就是在说:“姑娘们,不要去与不爱戴套的东北直男交往,来和那些坚持戴套的上海男性约炮吧!“东北人的粗暴男权,正是理想中温和男权的他者;而以我的有限观察,东北尽管和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一样,至今还是一个男权社会,但如此虚伪无耻地行使男权的东北男性,还是比较少的。
与八十年代比较,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线性的有方向的“时间”并不曾消失或“终结”,而是被“空间化”了。那“落后”的与“先进”的,由过去抽象的“制度”、“文化”、“思想”,而分别找到了各自的“肉身”。对此,戴锦华曾在距离现场很近的时代就观察到了最初的症候;她在《隐形书写》中指出了“南国的发现”(特指东南沿海,这个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心,而不是整个地理上的“南方“),与“告别北方,走向南国”的潮流。不过,与之后的发展相比,这种倾向还只能说是一种初步的表征;很快,“南国”这个能指,以及它的“市场经济-自由多元的文化-丰富的日常生活”等一串相关的所指链条,就不再需要直接出场,而是成为了一种“方法”,被用来系统地改写“中国”各个地域和族群的面貌。多重“中心”和“边缘”的对立,很快在文化现象被日益彰显。而在这些地域中,又以东北的文化面貌变化最为剧烈。

对此,刘岩曾概括说:“作为一种文化表象,‘黑土地’的意义在于为90年代日趋同一化的中国历史的想象图景开辟了一处非异族的‘异度空间’,一段挥之难去的历史被再现为一种空间形象,而这一空间本身则被彻底地褫夺了历史”。在国家与大众舆论的合谋下,东北的文化形象成为“毛时代的时代特征、农民的身份特征与东北的地域特征”(刘岩概括赵本山形象时语)的复合,“体制”下的东北工人,从昔日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集体性伟岸形象,而被想象成小农式的一团散沙式的依附者,从而在失去“体制”后只能表现出夸诞叙饰、虚张声势的“义气”与“暴力”,或曰“社会”。有趣的是,尽管作为对人的形容词的“社会”确实来自东北,而在东北的原始语境中,这同样绝非是一个正面评价。事实上,在老一辈东北人口中,游离于计划经济体制外的个体被称作“社会人”,它的对立面是“单位人”,而随着单位制度的解体和大下岗,多数东北人却被迫离开单位走进社会。可是,在当代的“观察者”眼中,老一辈东北人视同冰炭的“体制”与“社会”,却正是一回事:东北人之“社会”,早在他们还在“单位”中时,就早已注定了!

也正是这种认识,才能把对同一群东北人“公认”的这两条自相矛盾的认识调和起来:一方面据说他们无比热爱“体制内”,热衷于“编制”,继续主动寻求依附和秩序;另一方面据说他们又都非常“社会”,热衷暴力和破坏。在我们所观察的这个文本中,这一点当然也得到了延续。
当代中国中“时间的空间化”,还有另外一个症候,即被认定的“落后地区”,本地人在反驳对该地诸种“落后”现象的描述时,往往要强调:“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而在向往“先进地区”时,也会同样以时间尺度,畅想多长时间后可以达到如此的境地。在《观察东北直男报告》下,还在坚持反驳的东北人纷纷说:“时代气息太浓郁了吧,这好像是二十年前的东北。新一代的孩纸没人大金链子小手表了,都当笑话看”。于是,东北早已得救,东北的问题已经成为“过去”。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篇《报告》等铺天盖地的传播“东北“话语的文本,并不是在揭开一个过去的”问题“,而恰恰就是今天的东北问题本身的一部分。
据说,这篇《报告》的作者之一“猪蹄蹄小朋友”正来自东北,在篇末评论中,也有大量的自称东北人者表示正是如此;而更多的东北人表示“略有偏差但我不care,我们东北人有幽默感”;这的确是一种东北人特有的幽默感,正如黑人有着他们特有的文体特长一样。不是社会结构使得黑人的发展必须依赖“身体”,不是意识形态氛围使得东北人融入圈子必须“幽默”,正相反,是先天的优势!在这里我真要先画一个十字,感谢上帝对东北人的优厚赐予了。
事实上,“东北”话语的流行正是东北之沉默的症候;而东北人其实也并没有积极地自我东方主义;他们的态度,一方面是随声附和,另一方面更是时代认知的错位。该《报告》有一条高赞评论说:“猪蹄蹄小朋友,在地域自黑界的地位,和扬卡洛夫在自黑民族界的地位相当”。这可完全说错了,以扬卡洛夫写作中最常见的“女文青进藏”母题为例,他指出“康巴汉子”们可以通过主动迎合她们的东方主义想象,来获得性满足;这种“自我东方主义”作为代价,改写了文本中所叙述事件的权力关系,看似懵懂的被动者成为了主动者。而在文本外,他的读者们则就像故事里的“文艺女青年”们一样,为他对本民族的“虚伪”、“龌龊”处的“自黑”而满足,从而被动地落入了意识形态陷阱,而没有发现扬卡洛夫其实是他的大多数读者们所不能接受的藏民族主义者。而东北人们,如这位“猪蹄蹄小朋友”,并没有主动利用东北话语去改造自己身边的权力关系;他们只是让看客们满意而已;这在根本上,是东北人没有可以与扬卡洛夫的藏族意识相比拟的“东北人意识”。
据说,“任何地域问题都可以用娱乐性的语言结构来消解”,“要想解决标签,首先得认识到标签形成的原因,而不是一上来就否定现象,拒绝讨论”。的确,“否定现象”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指出现象”并不是谈论“现象”者的目的;认识装置的制造和顺利运行才是他们的真正事功;而面对这些认识装置,“娱乐性”的语言结构尽管羞羞答答,却还是最终进入了他们的内部。黑人只是黑人,只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维持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东北的异性取向者只是东北的异性取向者,只有中国资本主义体系所依赖的地区不平衡关系下,他才成为“东北绝对直男”;而《观察东北直男报告》,也就同样构成了维持这个体系与这种关系的诸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环。以上,就是我对《观察东北直男报告》所作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