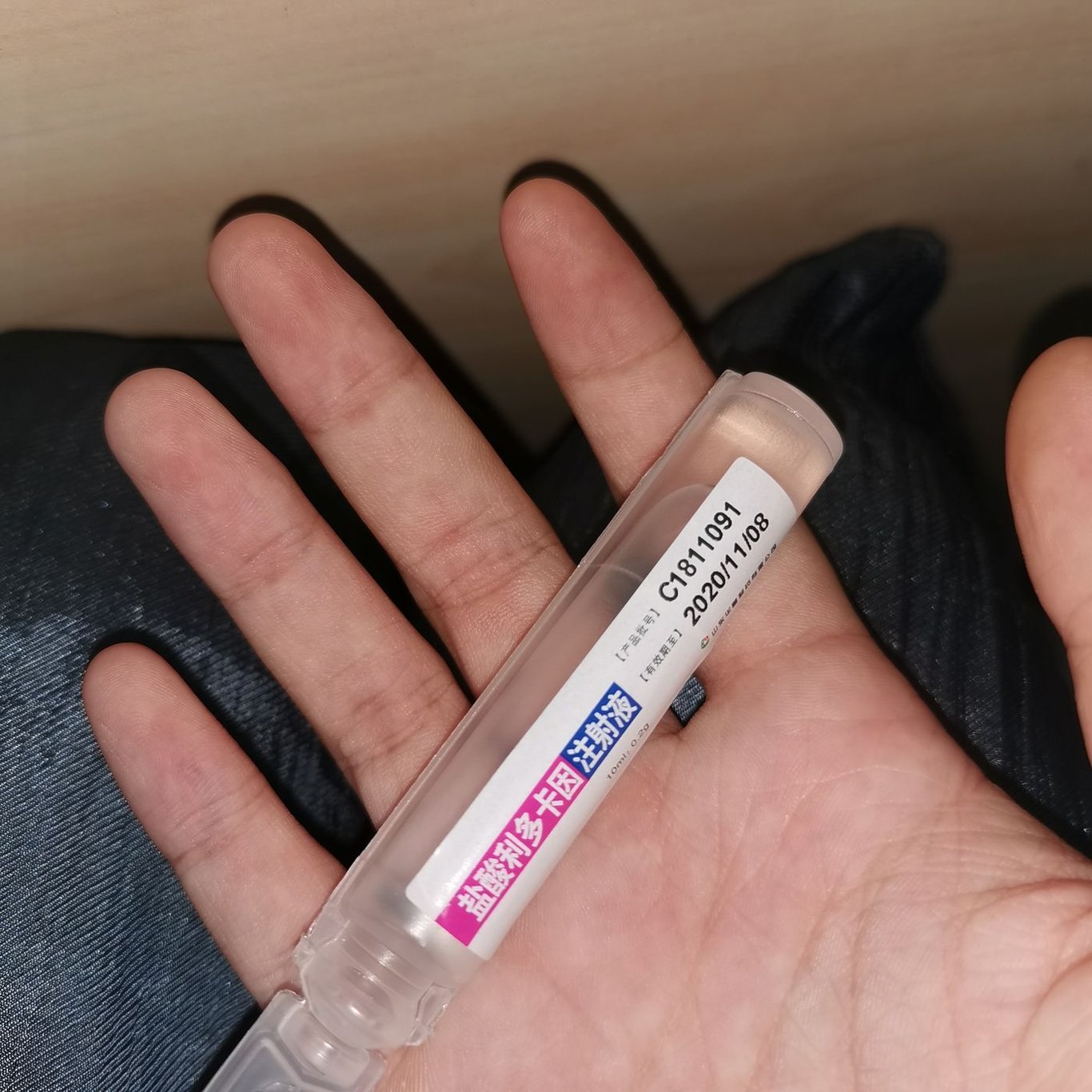她和发光的二极管
思思很瘦。
如果她穿一条吊带的裙子,你会看到她胸脯以上,脖子以下的部位有突出的胸骨,连着两边不对称的锁骨一起,在吧台的昏暗灯光中像一排发光的二极管。她随着厅内的音乐跳起舞时,整个身体的骨架上镀有一些忽明忽暗的光影,或是说,一些姿态。
01.姿态
第一次,推门进入她的领地,抬头是五位浓妆艳抹的女孩。穿制服的、穿黑丝的、穿亮片的。“把她们放到club门口大概也会引来目光的”,当时这样想。她们有一些耀眼,但不是基于装扮,而是某些姿态。姿态的暧昧无法捉摸,大抵是融入在一种定向于异性的场合中相互跋涉。而当时,她们正对着几位大腹便便中年男人。那些男人操着不地道的普通话,间歇夹杂一些充满岛国气息的元音辅音——总之是我听不懂的——这样的氛围。
没有开口,有些不知所措。我看到过她很多次。有时候是在家楼下散步,有时候是路过买一包烟,有时候就是单纯的想看她。
我们推门进入,她说:入场购票,喝酒另算。环视那个局促的空间,和感觉被打扰到的其余顾客,我们离开了——一种并不在于吸引我的氛围,或者其中的谈笑与推杯换盏的暧昧并无我插足之处。不合时宜的尴尬,像小孩撞破父母看色情电影:早知如此,但还是容不下面面相觑。
第二次更有趣一些。在她的据点门口抽烟,六月份的上海充满梅雨的湿热,空气夹杂水气,凌晨一点也是一种让人无法安逸的混沌。
我们相隔五米距离,同行的男性Z在她的旁边踱步,并不停跟我递眼色。
他说:“让我们来猜测她是老板还是打工妹”
我说,是老板,因为她每天都会在门口抽烟。
他说,一定不是老板。“以她的姿态,看起来不像老板”,“顶多是个打工的”。“为什么?”惊讶于这种经验之谈,“我能看出来”Z这样回答道。
于是他要跟我打赌,赌约是夜晚的宵夜钱——总觉得这样不太合适,尽管我并不认识她。
Z的行为很直接,直接到吸引她先向我们招呼三字经:“进来玩”。
一下让我有些语塞。要知道这种开场白在这样的场景中充满一些未道明的规则,进来玩,花点钱,做什么,不知道。
我问她,“我也可以吗?”,她说,只要付台费就行。
“你是老板吗”
“我?我肯定不是啦,哈哈哈哈”
我赌输了,可能在于我没有经验。
02.经验
同样的经验在临街的其他门店中也有缺场之时。路过一家入口极小的店铺,门口站着高壮的男人,男人招呼路过和带有打探意味的Z说进场,问“怎么收费?”,男人说“799一位,男的收费,女的免费”,Z又问“可以叫人吗?”,适逢门口走出一位制服女孩,男人指着她说“可以,你看她,150”。
我一下子又涨了一些“无用”的经验。原来“叫人”是这个意思?原以为是可以付一人入场费,叫别人免单进入,但是显然太天真。人民币150块,超出我想象的便宜。
我又想起来她很瘦那一点了。如果被一个男人呼上巴掌,她会怎么跌倒?感觉这样的情境会在我脑中不断地循环。150块的话,可以承担被暴力的风险吗?这样想的同时,又显得我很龌龊和局限。
于是我问颇有经验的Z,“150块能做什么?”
“喝喝酒,唱唱歌罢啦!你以为可以做什么!”
12月初时,去杭州见了一位中年男人S。见面的理由很有趣。几天前收到对方的微信“我竟然在三四线城市的夜店,抱着一位小姐给你发微信”。
S显然更富有经验一些,问他体验怎么样,他说“你跟我见面,我就告诉你。”
然后我们就见面了,在杭州西湖的漫步道边,碰见后开口有些迫不及待,“你到底怎么点小姐的?”
S还是语焉不详,说“你干嘛这么好奇?请不要总是用你做访谈的方式来跟我聊天”
“好吧。”
他说:“地方太小,那些小姐,没意思,长得丑,不好玩。”
于是又问他:“什么样的好玩?”
他说:“要有得聊吧,有的就坐在那里,喝酒,不说话,唱歌也不行”
“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肢体接触?”
他突然就笑了,一种有经验的大人看向没经验的小孩的笑。然后瞬间正色:“她们都不穿胸罩的,所以在场是随便来,但是出台的话是另一回事,按理说,陪酒和陪睡两种东西。”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我想听的是细节”。
“你知道这些干什么?”
“我就是好奇。”
“细节我可以示范给你看。”
然后脑海里“不过如此”的四个大字飘来飘去,最后变成脱口而出的三字经“我很贵”。
而后于是我又聊起思思,期望用交换故事的方式来获得信息。
23岁的女性打探35岁已婚男性的夜店经历,想来这是一种荒唐的对话和荒唐的情境。
03.情境
最受用于我生活的一条规则,大抵是关于个人关于情境的定义:只有当你将情境定义为真实时,它才会对你产生真实的效应。
最后一次见思思时,我真的作为一个消费者拿到了入场券。同行的还有我的哥哥H,可能某种程度上,H也是我的入场券。
这可能是她的策略,也可能是她的自然。我们没有开场白,她倒也乐于被我“盘问”,当然,我们也消费了不少的酒。
她说“我从来没有接待过女孩子,你是第一个”
她说“我当然更愿意跟女孩子聊天啊,你看,这样我们就很自然”
她说:“你不知道噢,刚刚你进来之前,有一个神经病!他真的很夸张,每天晚上都要来,找静静发酒疯,虽然他们有些事,但是也不至于这样吧!”
这是一种像跳动的光线一样的说话方式,如果对此回应,我应该先问“静静是谁”,然后再问“神经病是谁”,再问“他们有什么事”,再问“他到底干嘛了”。但她讲话很跳跃,没有一一地回答问题,只是自顾自地讲。
哥哥是做音乐的,被她知道这一点后又是另一波话题,“你认识那个谁吗?就是在XX酒吧的键盘手啦!你们一定要认识一下,他也是我的朋友啦,我们经常一起玩”
我问她,“都怎么一起玩啊?”
她说“就是过来这边啊”。
在那个情境里,“过来这边”和“一起玩”好像就有了不同的意思。像我们第一次推门而入的情境,它是异性恋中心,甚至男性中心的,还有从上而下的凝视。
她一下又特别兴奋,说我是她认识的新朋友,让我下一次也“一起玩”,我说“可以不付台费吗”
她迟疑了一下,可能是对于拒绝的抗拒,说“那我们要常见面噢!”。
然后她又说了很多故事,什么老板不喜欢她啦,什么她很不懂事啦,什么自己在这边其实不受欢迎啦。
“但你很漂亮啊,我每次路过都会看你”
“我知道啦!我就说眼熟你吧!”
“那为什么老板不喜欢你”
“她每次都说,我只配扫地!因为客人有时候有一些要求吧,我真的做不来的!”
然后我们就笑了。在那个情境里,突然不言而喻那些“要求”是什么。好像不用道明,也不用指清这确切的含义。
我总认为女性给我更多的安全感,在于她们言下之意的信任。在西湖边,在酒吧门口,在吧台前,面对思思、面对S、面对Z,他们的语焉不详都带有强烈的性别特质——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客人、作为一个花钱的人、作为一个服务者,或是别的意义上的女性,Ta已经天然地带有了一些不用具体描述的立场和想象空间。
04.想象。
而后跟她告别。我知道我终要回到我的世界里去。
出门哥哥跟我说那些都是她的话术,大概要营造对于“做不来”的事情的矛盾感。
“你知道嘛,可能她一开始说做不来,后面做来了,客人会更兴奋一些。”
我当然也有这样的猜想。但大抵认为我是一个女性,对她不构成威胁。
想起丁瑜在书中写珠三角那些女孩的故事,她们肆意的、天真的又世故的落入平凡人所不齿的猎网里,在这个圈子里打转。她们同样有作为女孩的欣喜和快乐,买漂亮衣服、化妆、做脸、美容。这是一种女孩们都能够共鸣的瑰丽想象,在这些想象中,被模糊的、充满玫瑰色的图景,却是难以从道德高地去审判的事实深渊。大概珍珠亮片、高眉骨、深眼影和鲜艳的红唇,是一种“耻辱性”的装扮和标签。
就像她性感、感性、调皮、迷人,是作为同性的我也同样会被吸引的身姿。再者,她并不贵,我们占有她的时间,来获取自以为更丰富的精神慰藉,或者满足我的好奇心。
她完成工作,顺利下班,度过更轻松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