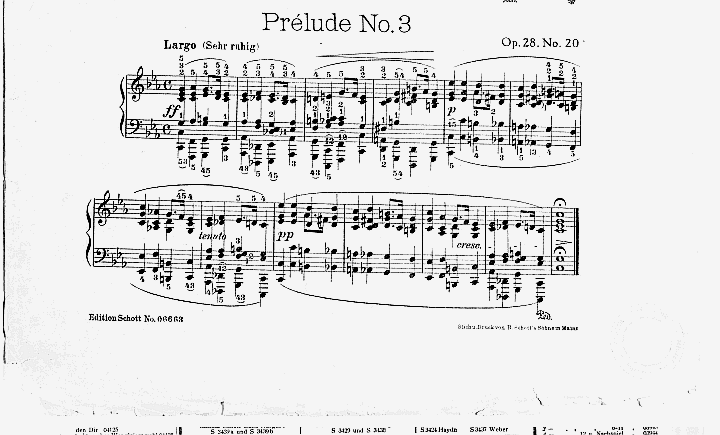故事:废弃草稿
4.埃及之夜
夜如何其?
夜未央,
庭燎之光
我在少年时期一次高烧中的梦中决心为普希金的故事写一个结尾,我梦见灯塔,海浪,或者暴雨与晚霞。那座举世闻名的巨大灯塔屹立于法罗斯岛之上,熊熊火光穿过月下流动的黑云,一如金黄夕阳辉光照耀四散奔逃的碎雨云,被蹂躏的大地和蓝色云层间架起彩虹,四下里波诡云谲,牵着礁石的麻绳发出长啸。暮光也许是神灵流出的鲜血,暗淡天幕上的星星想必也和我们一样奔忙争斗,永无停息。
第一个人或许是罗马军团的老兵,他的绝望远不止妻子这个幼稚的托名。我听说一种来自扎尔莫克西斯森林的鬼怪袭击了他的心智,这种鬼怪不具形体,却总是能潜入他的梦境,在梦中他最亲爱的朋友和家人都变成了仇敌。
第二个年轻学者名叫阿里斯,他或许不是一个人,
幕启
合唱队上,通奏低音,风声。
托勒密王朝的某一个日子,伟大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外,一座高雅的希腊风格神庙正在霞光中沐浴。大理石柱间走出一位高贵的白衣女祭司。她名叫安苏萨(Anthousa),美貌,清瘦,眼中燃烧着病态的黑色火焰。这位年轻的女先知自少年起就被怪病折磨,身体虚弱无法长久活动,但却有洞悉和谐与神谕的天赋,神庙微热的烟雾和清冷的睡眠正适合她的生活。此刻她正在等待弟弟阿里斯(一位年轻学者)来访。
安苏萨(白衣花冠,摆放烛台,点燃,唱起一支古老的歌谣):
我的船夫,我跨越群山只为寻找你。我的船夫,载我渡过深渊与冰海,我将自群山中到来,无论你在哪里。
阿里斯匆匆走来
——好可爱!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今天你来了,就是应该庆祝的节日。
两人坐下来,在逐渐黯淡的水雾当中吃藏红花染色的小蛋糕和椰枣。暴雨和白天已经结束,岩石地板上有一片山峰形状的水渍,还有大风驱赶小猪一般的碎雨云流过天空。“扑”地一下子蜡烛都灭了一半。他像小时候一样靠过来和姐姐说故事,安苏萨笑着把手指插入弟弟的卷发里。
——今天学院里又有什么好玩的?
——不,我先跟你说那个老头子的海龟汤……
我听说,死亡有一千张面孔,没有人能认出死神,只有濒死的人才能一眼看出那个准备带走自己灵魂的身影。
为什么我们俩总是在一起聊这些东西……死亡是天空,死亡是轻盈的,但是在神庙中我们不会直接说出神灵的名字,就像图伊斯托一样——如果你直接喊这些埃及人的名字,他们会非常恐惧或者狂怒的,他们会保护好自己的名字。
城市已经习惯了在灯塔剧烈的呼吸中生长,姐弟俩又一起在神庙的长明火下读纸莎草抄写的希腊文学,他们屏住呼吸,想象着库柏勒女神的怒火,想象斑点的小鹿皮衣,缠在神圣的茴香上的常春藤和空中转圈的响板,还有酒神祭里乱舞飞扬的头发,以及女神面前彻夜的侍奉,那时月亮看着这一切事物。身边是索具和船只的吱呀声,远处牲畜的叫嚷,暗夜里发光的骨头,暗夜圣甲虫和黑猫细小的动作中,他们好像回到了北方崎岖多山,熟悉又陌生的希腊故乡。像这样他们度过了很多荷鲁斯庇佑下美好的夜晚,阿里斯初到学院,有时候事务繁忙,姐姐会派人去送些众神祝福的供品给他吃。
他们都喜欢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安苏萨眼中有火焰,朗读欧里庇得斯的自白:
“我把思想和概念借给艺术
我以此独自把同样的智慧灌输给周围所有人
使得这里每个人都进行哲学思考
从未如此聪明的料理房屋、庭院、田野、牲畜
人人都不断地研究和思考
为什么?为了什么?谁?在哪里?怎样?什么?
这会到哪里去?谁从我这里夺取?”
——这多美好,多伟大,只要去听歌队的咏叹,就可以一眼看见每个人的生命中缺失了什么东西,那些拥有智慧和美好心灵的人就会被点燃。
“我不觉得这一定是好多。”阿里斯说,“就好像给我心中种下了无数骚动的种子,无论我做什么都开始思考这是什么,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学院里面的师长说学习知识可以让我们达到平和宁静的快乐中,但是我研究的越多,这些怀疑和思考越多,连明确的论点都消失了,只有谁会从我这里夺取的恐慌。
“不,阿里斯,你这样是被经验的知识蒙蔽了双眼,变化是虚妄的,不要忘记那些永恒的东西。你看,当我祈祷的时候,当我用心灵的语言直接阅读世界的时候,星辰和夜光流云还在焦虑地纠缠燃烧,我却已经进入了神明的肃穆。
——我总是感觉灵感在枯竭,不是提供给别人的通灵,而是神对我说的话。我好想缺乏一种精神,像是过早衰老,就好像鲜血不是理所应当地提供给祭坛,好像万物的生命不是那么轻盈闪光。我总是要去阳光底下转转才能集中思绪。
太热了,阿里斯责怪姐姐不在室内休息,总是跑到海滩上被晒脱皮。
太热了,就像天上是太阳,我穿着灰烬,尼罗河——融化的白雪而不是天上的雨点来湿润埃及的平原田地,最伟大的古都慢慢陷落在不断流动的泛滥平原上。太阳!尽管供奉的塞拉比斯(Serapis)已经足够强大,但是只要走出那些巨人腿骨般的石柱,站在亚历山大港郊外的洪水与平原中,太阳的光芒就吞没一切。太阳,必须知道名字才能召唤的神灵或魔鬼,让黑发的罗马人、绿眼的加拉太人和光头的含族女子都忍不住打颤的死白光之荒漠。安苏萨想起前不久有一个本地人借着劣质啤酒发疯,认为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当着妻子的面把孩子杀死说要做成咸肉。区(toki)里长老给他的判决是破开肚子绑在河滩上被晒干,以彻底清除他体内黑麦角的邪恶汁水。弟弟听了,突然说有点羡慕那个男子临终前的安宁。
——我有时候会想,老师说追求知识的幸福是最高的快乐,快乐就是至善。但是思考只能像埃及人写字一样停留在一根不断变换的线上,我总是无法像智者一样思考……如果神灵能在一瞬间清除我体内无关的黏液和感觉,哪怕是一秒钟的知识都无限快乐吧。
姐姐忧心忡忡地吩咐奴隶再拿点小西瓜过来。
有一天阿里斯兴奋地来到神庙,靠在活生生的柱子上等待人们散去(许多本地人一生都被一个遥远而不可名状的名字支配),他告诉姐姐要讲述一个真正的故事,没有众神的意志无法发生的那种命运。
于是他们简单地焚香,向神灵祈祷,在飘着莲花的洗手盆里洗手,然后找一个舒适的姿势坐下开始讲述:
大约是在某一位温柔的贝勒尼基的时代,有一位罗马老兵解甲归田了,按照
——我想说一种感觉,但是忘记了应该如何表达,就是那一种感觉。
黄昏时她高贵的身影穿过花园,让人想起古代的乌尔城里迦勒底贵族少女走下神庙的台阶,他想象那些姐姐踩过的石砖已经化为无穷无尽的灰尘,被数百年的风分散到旁遮普到大希腊的各个角落。
——你一定在说:他漠视世界上所有的谜团,他在粗暴和傲慢地拆解我珍视的一切。但你不理解……我不是那样,我不是眼睁睁看着你被人四处移动,困在这神殿的柱子之间精疲力竭。你在暮光和朝霞之间、在感觉细微的颤动和迷失之间寻找精确的不动的神谕,以此为君王百姓提供预言。我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在集体的花园中,在世俗喧扰的一小块僻静之所寻找同样的东西,寻求理性的安宁,寻求平静享乐的麻醉,对于我个人,还有让你恢复正常的秘密……你知道的,那些原子的运动——我多爱你呀,我那么爱你,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还是沉醉在自己沉默的游戏里面,嗨!你心里还在嘲笑我吧,你还是那样对我,从小就是。‘你还是那么幼稚,你什么时候才能不依靠我啊……’等等、等等一直在这么说,这么多年我已经在搭建作为一个男人的世界了但是你还是欣赏着自己的天赋指责我,这不公平,你没有那么爱我。‘他趁着我不能说话的时候一直说,他很卑鄙’,对,我就是要在你不能反抗的时候说出来,全部都说出来。小时候我围着你,那些……你知道那天下午我为了找到你说的花妖走了多远吗——你不在乎,我知道你在乎我,可是没有那么在乎……
——为啥我们在这无人的荒原里依然离的那么远。我爱你胜过一切,我把对你的爱放在最脆弱的地方,你却一直在嘲笑我的柔软,我们之间甚至没有过平等的离别。
——为什么你不能睁眼看看这个城市,你想让我在广场上振臂高呼对吗?已经变了亲爱的,你想的都回不来了。民众们不能有耐心听完哲学家的论述,只能用越来越宏大的口号刺激自己,广场上的声音永远是从卢西塔尼亚到米底的伟大开场,面包和牛奶已经不可能满足人民了。醒醒吧,现在是帝国铁蹄驰骋海洋,希腊人在百年前就屈服于马其顿和色雷斯人,可是我们的政治家还在人群中许诺黄金和远山。原则一次次被推翻破碎,最终只剩下城邦间的无聊游戏。我害怕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向人们许诺鲜血、地狱和其他东西。
年轻人啊,不要把感情倾注在绚烂夕阳上,因为日神的火球明天依旧能升起,但你的青春将随着一次次日出熔化破碎。
——你无法逃避,你无法逃避,你永远无法逃避,有的木头想要燃烧,但它注定长满蘑菇而腐烂。
因为他们愚蠢而傲慢,因为只有年轻人的死亡才是体面的退场,老年而死只能是化为污泥融化消亡。
——我这么近地看着你的脸,但是只能沉默
——亲爱的,这些话只有在戏剧里才会被全部说出来,可是这是生活
(欧里庇得斯)
双重性,行动上她的自我毁灭和心理上他的自我毁灭
顺便,自我毁灭是自我发展的一种形式
外面是太阳
我穿着灰烬
没有你,星辰燃烧的火光只不过是指引末日的路灯
阿里斯的独白:
我消磨了岁月,岁月不曾原谅过我。
我早已死去,如果没有未来的风暴。
何为想象的边界?你依然没法写出的旋律,
飞翔的鲸鱼,紫色的天空,等等
合唱队:千年后巴比伦的地狱火。
1.死亡盛宴:
这段对话发生在塔尔索斯到安条克一个不知名的村子里,也有人说只有在被誉为世界之半的伊斯法罕,才会有这样瑰丽的故事。
不过大多数人怀疑一个诺斯人是如何漫游到东方的,据说我们的讲述者是一位著名雅尔的儿子,他的祖先曾经在传奇般的英格林家族手下建功立业,于是他追随着先辈的足迹来到东方开始冒险,但是我的朋友想要保证这位不知名的诺斯雇佣兵是一个普通牧师的儿子,或许是因为一个罗斯女人,或许是厌恶家乡,强壮却敏感的年轻人来到远方漂泊。诺曼将军和希腊国王对他来说并无分别,意大利或是伊庇鲁斯的财富也没有贵贱,只是黎凡特灼热的风沙让可怜人大病一场,从此他经常会说一些这样荒诞不经的传说。他的同乡觉得过于远离故乡的那块石头,已经让他的神智受到了损坏,于是他们偷偷为罪人的灵魂祈祷。
我曾经服过一位暴君,他的宫廷在西西里,这市场到处都是暴君,建筑和残忍的民主,甚至路边最虔诚的苦行僧,这样获得土地依然会是一位暴君。
白天站在敌人身体上打消的君主,可能在无数个夜晚因为恐惧惊醒,观看血腥触觉的国王,也许在惶恐地等待被背叛的最终结局,但是我的王宇他们都不懂,他是天生的宝骏,如果说他出生那一天,莫西拉陈年来苍白的唇只火光冲天,好像有无数只乌鸦飞起小时代。
夜色中年代的酷豪的人们投你pension,它唯一一个姐姐康斯坦斯也发起高烧,于是一切都确定了国王万岁。他12岁就正式加冕,不久之后国王就失去了病死了。最凶残的野兽用最really的爪牙面临知道来自天涯海角,残忍忠诚勇士是如何聚集到国王朝霞。有一个漆黑的巨人,没有能谁能看见他的表情。
马格里布的毛拉总是在擦拭着削铁如泥的泥人,还有据说通晓希腊人的摩尼教徒,当然也有像我们这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有人说王公就是暴君的逃学,这是不准确的。
王公就是保军身体的延伸恐惧,从经历辉煌的王冠卖淫所有的房间走廊,密道和暗门,到在每一个人头上,恐惧来自于王功本身,来自于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同志和死亡的历代国王,不知是计尽,而是王在午夜来来回回飘荡在宫殿所有角落的脚步上,不是应该,而是本身就是欢乐家乡的花园和雕塑上彩排的阳光。
据说服役太久的卫兵会因为这太过刺眼的阳光侵蚀了市场,不是七彩灵力的长效的海风,而是复活节宴会上国王喜欢最狂野的喜鹊的舞曲,国万岁。
我每次听到这些曲子都想哭,一拉琴回缓往复越来越快,每次快要达到顶点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一轮我所在地板站不稳的鞋跟,贵族和小姐们起床嘘嘘一幅缠在一起,就想冲我王宫顶楼的螺旋楼梯。再来一曲。所以著名的传说是真的,所有的敌人叛徒和不忠者只会有一个下场,那就是被邀请到威尔王公的正厅中参加一场死亡盛宴。
宴会始终没有开始,据说暴君要极其所有的客人,于是那些凶狠的海盗,骄傲的隐忧诗人,各怀鬼胎的贵族,狂热的教室,乃至一些不知为何享受国王仇恨的平民都被他做成了防腐的标本,整齐的摆在地空中,指着华丽的正听也不再使用了,但是拼花地板打理石的巨大长桌,黑色的看不清材质的意思都保持着心结。
有时候谷王会让我们把一具具保存完好的尸体都搬上来,尝试合适的做事。太好了。
他会坐在长桌一端的往座上长久盯着往昔的敌人,看着尸体空的眼睛盯着墙上反复地不死挂,很令人眩晕的彩色马赛克,然后就要说再细细的最后一段日子了,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衰老的速度加快了是非,有时候会觉得这座王宫的魔法能让人永远年轻强壮,也许我们的国王也是这么想的,他不需要婚姻,有时候一个蒙面的女孩被送入王宫出来的却是另一个,据说他的亲人是用邪恶力量的女巫,让国王的敌人总是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出错,他也不再需要政府国内的风尘,如今真是先恐后为他陛下度它的威名,让境外的敌人恐惧辗转难免。
当一直节约王国海的丹麦人,备受下送到御前10,他甚至露出了些许遗憾的表情,我们好像忘记了国王没有继承人,至于康斯坦斯唯一的应许来自于他派来的刺客,年轻的埃斯克说他获得了加他是一个秋天的黄昏,蒙面的蓝营女子,秋天都像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秋天有时丰富式的庭院。
我来自东方,他说卡特就像雄鹰寻找山间最名贵的玫瑰在他妈诗歌nana,只有苏丹最喜爱的有才能的芬芳和玫瑰的花纹,用敌人的鲜血浇灌,岛上的花纹就会生长绽放巴格达和叙利亚的城市中流动的黄金。I can't bother can call when I leave me。但是我们的沙漠里奔跑的是血腥味的风法兰,克人永远要向我们学习。
战争你们唯一可吹嘘的只有残忍和无耻,他一定是个女巫,我能在那双黑得吓人的眼睛里看见秋蝉的黑猫,盘旋的乌鸦是个太阳,分开三轮的海啸,以及其他荒诞不尽的东西,那天晚上我无论如何都睡不着,闭上眼睛就像枯乏清真寺里的日出,响亮哨的船对开他的眼睛,他递给我一把匕首,只想抢到你贵州的女子,可见他裸露的背上靠他的伤痕和血迹,明确的任务反而消极了一点恐惧,甚至为卫队的其他人都投来艳羡的目光,没有人想过为抗的可能性,我的命运就像我们赖以生存的面包,一步步接近它,地板湿滑可不能紧张,稍后他们会把他的躯体剖开,取出柔软的内脏是留下动物一样,鲜红的带点粉色的内壁,香料、水、石灰一样,最复杂的过程是一遍遍忘脸和其他皮肤上涂抹油脂和糜烂。
想象着这奇妙,人们想身体干燥有毒,永不腐烂,要尽力保持皮肤的柔软和紧致,保存下他们死前球的可怜表情,究竟是王国古老的记忆,还是随着包群一同复活的一个国王却不向自己的客人失去先前的勇敢威严或者努力,而这位东方女子的头仿佛中国的绸缎黑发浓密,仿佛被炉子的森林眼睛他突然回过头来双眼睛被挖掉,空洞的血淋淋的眼光就这样望着我,好像听见了尖锐的逐渐增长的笑声,就像等他的一朝中涌出陈先生的蚂蚁,心血终于碰见了出来,我们发出满足的太,我们故事讲述者得到消息并不比城中百姓早,抱拳的死亡声音即将开始,王陛下长久等待的最后一名客人已经到了,舌头的房屋挂上了将会禁止的一角装饰,有的市民携全家向洗头了,他们传言宝君开言之日,愤怒的上帝会让整个城市盛入冬季铁灰色的胸巨浪之中。
也有人说等待他们的是庞贝古城的命运,只有天花才能敌情,实实在在积累的罪恶,我并没有下令惩处造谣者,百姓们大吃喝大喝正穿正穿的球,从叙拉古和墨西拿培训上来,人们彻夜跳着亵渎神灵的舞蹈有三个街区,小规模失火,和锅炉的十字军的冲突中,实际上伤亡咆哮的冬季风暴卷走了一家修道院的房顶,过多提前的想象会损害你深远的美妙吗?
暮色四合终身,华裔的大厅里熊熊燃烧着巨大的白色蜡烛,据说那是生孩子心里最纯洁的头部油脂制作的火光和分享,让最强壮的卫视也感到眩晕,浓烈的白枫瑶海的城堡,地板上被油烫着处女的鲜血,物业将至生虫花圃的客人们一动不动端坐在大地里,是常州的两个,前些日子女子还没有干燥,此时挂着两道血痕的脸,几乎有且可爱,国王万岁。
王冠利剑长跑,像一个兴奋的孩子一样看着同桌的尸体,于是主人已经求助,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门口,很快最后一位再无法动荡的客人即将入
那里有一本很长的书,据说读了几年。书的后面大半都是极具重复性的,而前半段充满各种诡异的变换,海上、钢索,机械能和巨大的旋转结构,总之是又冷又湿的汗。很难想象之后的日子都在变换的方块中度过,你可以认为这是简练的哲学,或者无意义的随机组合。
那些黄昏天空中的吊桥被拉起,缓慢漂流;组成城市的数百个小岛在水中分开、旋转
诗歌起源于语言的某种前体,并渴望超越文字的形式,(所以总是不完备的)
童年的诗,经验落后于意识
尸体:指三个人冒险,一个人罹难。将死者的尸体送往火葬场的时候发现这是自己的肉体。唯一的特殊点在于是三个而不是两个人
小孩:小孩子不理会我带着口水的吻,他不躲避但是用微小的肢体动作表示并不喜爱。但同时他疯狂嗅我的皮肤、头发、汗水和衣物,燃烧黑色火焰的眼睛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创作自由:如果我们认定作品不是作者写的,而是某个高于我们的实在选择某个个体,并假借其创作的,那作者过去和未来的自由都与作品无关,因为这是某个更高的意志在负责。但是如果坚持作者对于作品的神圣占有,那创作自由只有在匿名之下才能存在。否则我未来的行为、未来的作品、一举一动都影响对当下作品的理解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