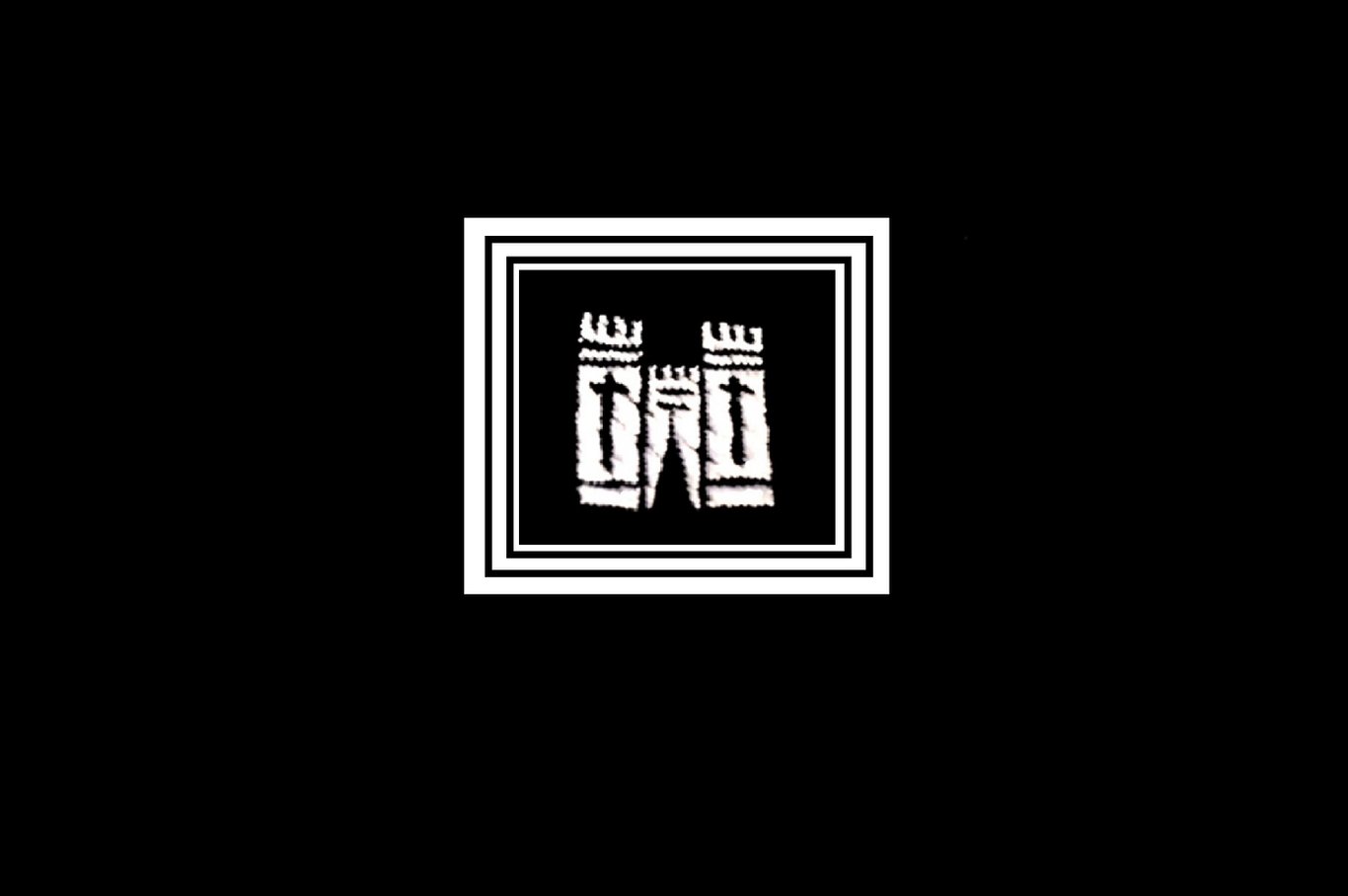所谓问题,所谓答案
少年时期,我曾经这样设想自己对终极问题的回答:
生命也许只是随机、无意义的增殖现象,但不排除存有一个终极目的的可能。这个终极目的或许存在于对于知识的究极探询背后,或许被某种我们尚未获知的超自然力量所决定。但无论答案是什么,只能贡献自己的努力让文明存续,让社会发展下去,以俟在未来求得答案。为了这一份探知究极意义的可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总好过全盘接受所有一切的无意义。
这也许是我在我的成长环境和文化背景中能得出的最自圆其说的答案。一个表面聪明、故作高尚的答案。我曾经认为,对于究极意义的态度和回答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一切:他的情操、价值和一生的方向。
后来我发现了它的荒谬。我并没有给出一个坏的答案,而是从根本上回答错了问题。最要紧的问题整好反了过来: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要你有什么用?
而且不要误解,在这个问题中不包含任何一点超越性。如果世界是一台轰隆运转的机器,它就在问你可以在生产体系中做一颗怎样的齿轮、你的腰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其他齿轮的不停运转提供需求。如果它的面目是一个国家政治体、或任何一个集体,它就在问你可以为它争取捍卫哪些属于集体的荣誉,维护多少现存的秩序和合法性。如果它是一个家庭,就在要求你的责任;如果它是一部电影或者任何形势的文化产品,它就在要求你付出该死的注意力;如果它是一种思想、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它就请你去做传播践行它的载体。
原来世界的每一个部分,都对你如何做人——做一个有用的人提出了它的要求。你做出回答,而它用那个相对应的尺度为你打分。
回答若是得到高分,则会得到它分配给你的更多经济和社会资源;若分数不及格,则取消对你是一个合格的人的认可。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努力工作以“自食其力”,以做出“对社会的贡献”,以分配应得的社会地位与尊严。这成为了现代社会将公民纳入其秩序管束的最根本方式。
所以就去工作,按照要求完成一项又一项它提出的任务。无论现代社会的劳动成果多么有益或有趣,都将人变成一个只能在单一尺度实现价值的工具。没有几个人是在为了文明,为了共同体的存续而工作。绝大多数人为了掌控生产资料的资本的繁殖而工作;为了适应资本社会的结构,人被迫将自身的时间与技能资本化,在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即使是公共领域的工作,也多遵照工具理性设定了严格指标和绩效,通过分工与职级消去了高尚事业的感召力。
一个人努力工作所得到的褒奖:一些钱、升职、一些假期、一些年会上的无聊节目和它维系的集体感。其背后是上令下达、资本竞赛、攫取资源的一场大戏,人从此空洞的奔劳中耗尽自身。
这样一个体系压制着人们对于非现世意义与价值的追问。它给人下达了不容质疑的定义:一个不断通过生产和消费的螺旋扩张自身,直到吞没一切的秩序的一员。一如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物,终其一生通过复杂的生化反应将无机物质纳入DNA的复制与增殖的秩序。
从根本上讲,这个秩序——即所谓的现代性——已然成为人类文明的福利和繁荣的依仗、是善的化身。它构成了一个稳态策略体系。每个个体按照它所规定的策略行事,就可以得到秩序所许诺的回报。在常规情况下,这回报的丰厚程度大大高出挑战秩序或者失序所能得到的程度。自然,任何对它的否定和扰动都只能造成混乱和衰退。
那么在这样的秩序中,我怎样还能继续坚持曾经作为少年做出的回答呢?我建构于怀疑论和关于人类总和的朴素善念的回答否定了它从工具与竞争的角度给出的现世意义。从实践上讲,这也就意味着拒绝它所安排的日常劳作,拒绝占据一个在这样的秩序中合法分配资源与尊严的角色——而我的答案却同时还要求着我还要为了(在我一个怀疑主义者眼中有可能不存在的)终极价值去劳作。我不敢相信,得坐拥怎样的特权才能做得出这种选择?
更不消说,如此空洞贫瘠的文明和共同体的发展能等来怎样一个拥有超越性价值的未来?难道会是最后审判日吗?它的明天或许配不上我的殚精竭虑。
于是我只好在再回到心中默默修改我的答案。当然不是去迎合它空洞的召唤,而是去回答另一个被这世界践踏在脚下的问题。
人的目的,或者说我的目的,不再和人类的总和有关。它只能是关乎个体,关乎每个人身上还没被那个极具侵略性的世界秩序所开垦的那部分。如果社会结构定义了一个标准化的,功能性的“人”,那么我被迫去找寻、记录并维护所有的“非人”以及能够让“非人”存在的条件。
这不是仅仅是提出一个未经触碰的“生活世界”,然后把它和现代的工作相对立。在后工业时代,我们生活已然是被机枪打成了筛子一般被外在于人的世界秩序侵蚀殆尽。更不要说在那之前的传统中,生活还从属着比目前世界的主宰更为可怕的东西。
因为一个有存在焦虑的智慧生物的迫切审美需求,必须弄出一个什么东西来显现人的自主性,与人和人、物、思想之间真正的交融与断裂。去重新发现,从头审视。从时间河中拾起一次改变命运的傻事,和少女从西山日暮归来呼出的白雾。和着新曲吟诵旧诗,或者沉醉于指尖拨出干净篮球时的摩挲之感。把它们都用最熟悉的文字的最陌生的形式写出来,疯狂地写。把人类的抗争和恋物的历史写给未来的平凡心灵。然后在和你偶然的对视中发现横行的秩序在彼此身上的雕刻失败的废墟。
如果在现实中重新发现和建立的还不够,那么就只好去凭空幻想。哪怕拥抱梦想中的幻影,用致幻剂欺骗自己,甚至是拜倒在命运女神的脚下。怎样都好过眼看自己淹没在这潭死水里。
怎样都好过像海的女儿一样用歌喉去换取无声的隐忍与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