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 ︳二零一七年的記憶
有些記憶會不斷反覆地被想起。是無助的、是哀傷的、是重要的、是需要被寫下的、是值得被寫下的,也是應該要去面對,去整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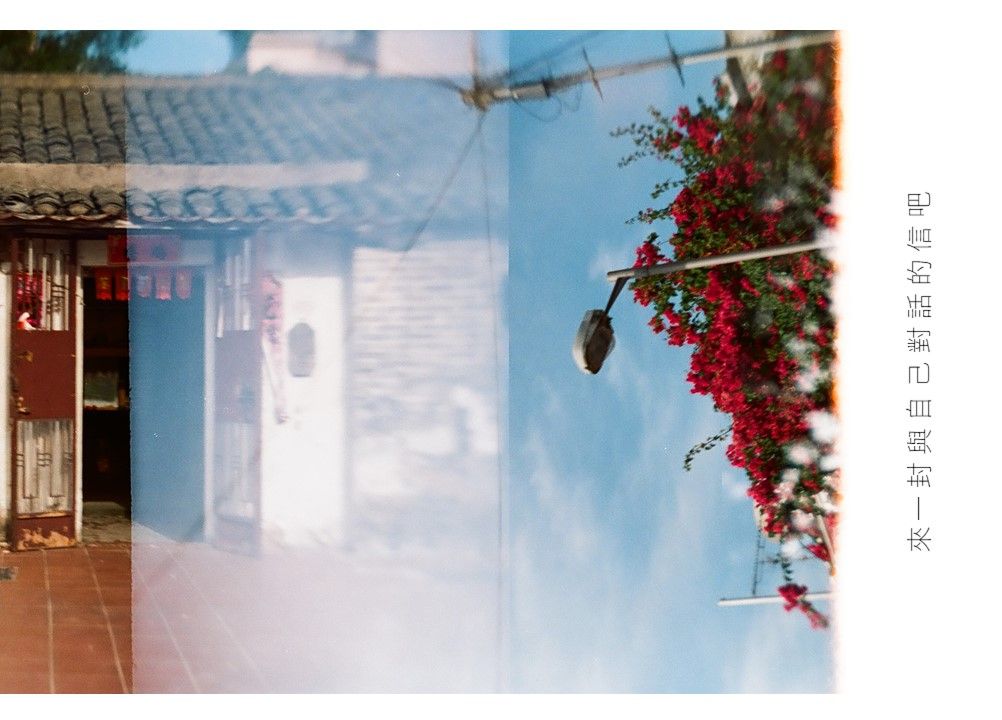
二零一七年大概是我暫時一生中淚水最多、最難過、最彷徨無助的日子吧。
半年經過了,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切都好好的,但這刻才知道,回想起來仍是會難過得流下眼淚。
想起我畢業那天的畢業典禮,二零一六,好像是十一月,我自己坐上巴士,默默流淚。友人的爸媽,問為什麼父母沒有來。那時媽媽適逢病發不久,與我穿著畢業想袍的合照,一張也沒有。
到了一七年,忘了是六月還是七月。悶熱的夏夜中,收到一個醫生的電話,妹妹因情緒狀況由大學轉介,已見了她好一陣子。她說妹妹應要入院治療,她兩度嘗試自殺。
當時我是什麼反應已經忘記了,大概是彷徨吧,只能問做因青少年工作而有入院經驗的友人,了解入院環境和程序,會發生甚麼事等等,過程中像是丟了魂。次日就陪妹妹去了醫院,被轉入青山E2病房。自此開始了一個月每天6點下班7點到家晚餐,然後8點再坐車去醫院探病半小時,10點半再回到家休息。住院三星期,家人一直不知道,厲害吧。
到了八月,是八月吧。有天家中出現了兩罐氣體,我悄悄地扔了,她說是自殺用的氣體。那天晚上,說了很多,也哭了很久。只記得一段話。
若果你死了我也去死你會怎樣?
:我無法阻止你,也不會阻止你,這是你的決定,而我也不會傷心。
:其實你現在的傷心都會隨時間而沒有,你記得要找朋友傾訴啊。
:以前我想死但沒有做是因為我找不到死的原因。現在我知道了,死是不需要原因的,正如生存也沒有原因。
生死的意義到底是甚麼呢?我甚至認為她說得很合情合理。她的精神科主診醫生當然完全無法理解我為何可以認同妹妹的想法,亦質疑我,指責我們都沒有重視生命的重量。唯獨以前的T督導,卻明白我被說服的原由,及當中我的無力感----原來我接受妹妹這套想法也不是奇怪的。
他說:
點解人地可以決定佢要點死? 人地憑咩決定佢生存係一定有價值? 憑咩決定佢自殺係一定係殺? 殺,不過是一種死亡的決擇。
當然不代表我們兩個認同自殺,只是我們都感受到這些人當刻切切實實的想法,他們從心底就認定的念頭,並不盡然一定是抑鬱症作祟,能單靠藥物、說服和陪伴而會改變的信念。
一天晚上,她掛了我電話,我找不到她。父母終於知道了。我出現驚恐反應,手腳麻痹、呼吸困難,第一次叫白車。最後在酒店找到了臉頰通紅的她,她說是通宵喝酒。到很後來的後來,才知道是吊頸導致的紅點。
八月,仍是八月吧。父親手機突然收到她傳來的有數字的短訊,像是密碼。她又失聯了。結果聯絡酒店查詢,被發現昏迷。去到時,她已經坐在救護床上,半昏迷狀態。次日我一直和醫生討論強制入院的問題,又要處理酒店裏那兩罐氣體,與酒店經理的對話又讓我難過得哭了。觸發點就是酒店經理硬塞回開封的氣體給我,而我,也不知道可以如何棄置啊。都是滿滿的無力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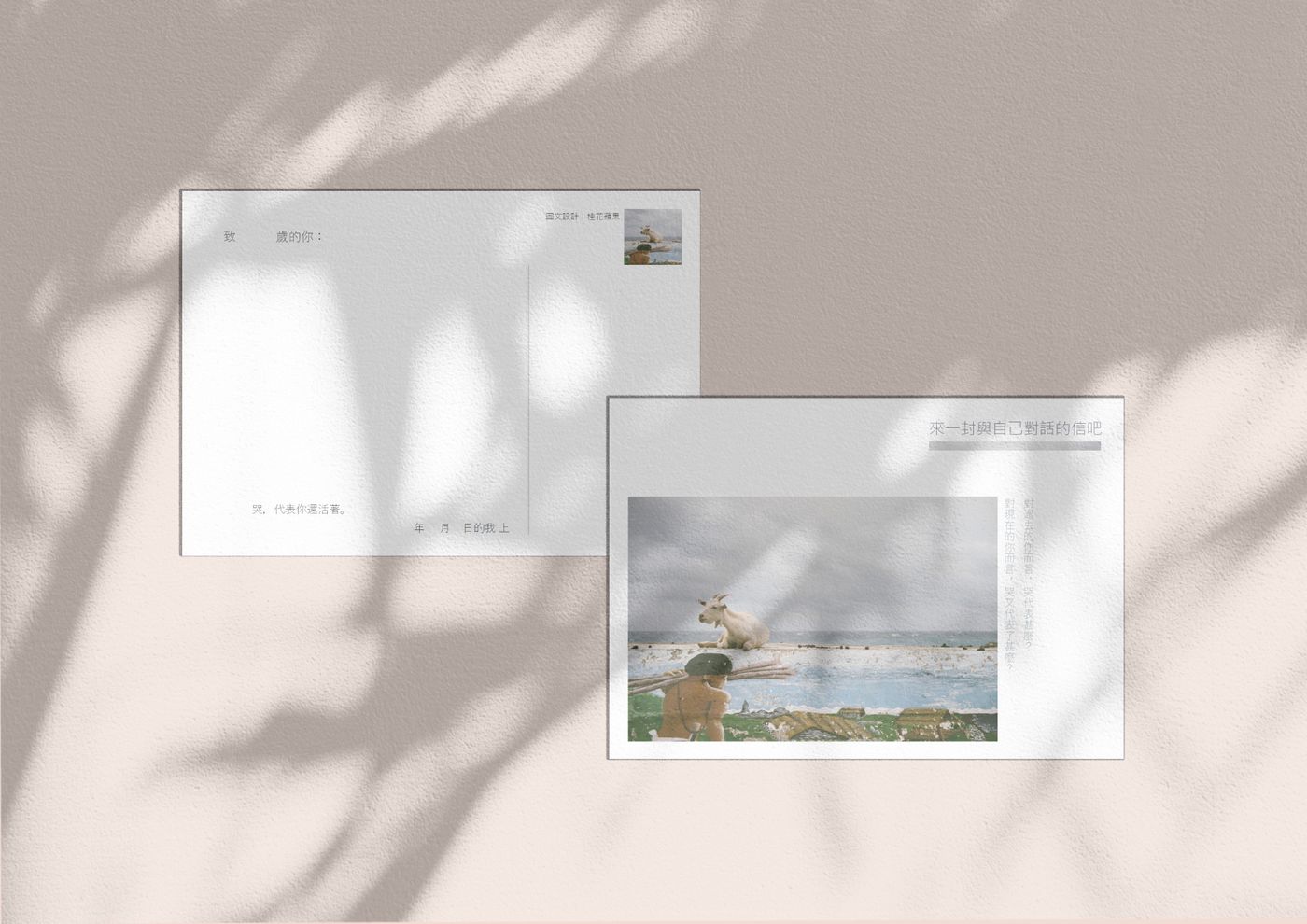
記得和她一起坐上了白色的救護車,那醫院的味道,坐在黑椅上的等待----又開始了晚上探病半小時的日子。在那一段的日子裏,一直在糾結和爭取著出院的安排(當中的爭紮、與醫院處理方向的衝突––––只確保人不會死在它面前等,有機會再與大家分享)。
最後,我十月辭職,和她去台灣,開始了半年的打工換宿生活。
T督導知悉我這個決定後,祝福我:
假若環境、藥物與新經驗,依然無法令她想自殺的念頭有改變,她至少讓你陪她走過了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可能是對她而言,一段最自由的時光。
還記得一切順利,妹妹情緒狀況穩定許多。到12月準備回港兩星期過聖誕,上機前夕的晚上,發了夢––––夢中我們正準備出境。走著走著,她走上了樓梯,開始奔跑,我只見到她的背影。她在我面前跳了下去,身體折成扭曲的形態,都是血,死了。醒來我驚恐得一直哭,去了找他,最後在他懷抱中入睡。
原來,潛意識中依然有深深的恐懼。那段日子的記憶深刻而又模糊,大概多少年後,想起還是會難過吧。(嗯,二零二一年的今天,整理記憶時仍是會覺得難過和恐懼。)
原文寫於2018.0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