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回我的语言
语言
口头表达、公文报告、制图说明、演示宣讲……表达沟通一直是我擅长并喜欢的。并没有刻意去培养这些能力,但它们在职场上默默地为我保驾护航。不知不觉走到2018年底,在公司做了几个抛头露脸的报告后,我突然感到浑身不适。当我演说着那些跟公司企宣部门约好的内容时,一个声音在我脑中隐隐响起:
这根本不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啊。

那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一旦脱离了公司企宣的框架,我自己的表达就变得很僵硬,观点模糊,语言也不流畅;于是我报名参加了好些不同的写作工作坊。纽约新闻媒体行业发达,写作爱好者多,相应的训练课程也多,我因此接触到很多方法论,也在写作班上遇到了一些朋友,由此相约每个月聚一次,做些写作小练习,分享彼此写的文章,互相督促鼓励,一同进步。
之后的一年多,我都在磕磕碰碰地写英文。分享会里的朋友兴趣点各不相同:Kerry喜欢写小说,Miriam喜欢写诗,Kohzy喜欢翻译中文散文,Shan喜欢写故事小品,Jessica喜欢写日常(slice of life)。我自己的写作主题和体裁很泛,虚构的,非虚构的,说理的,抒情的,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写不出来的时候干脆画成漫画。写完在分享会上读一读,大家点评一下,笑过就算。
好巧不巧,不久之后疫情爆发。那时纽约的大多数人都还在无知无畏地出街聚会,我参加了一个海外华人写作营,共同记录自己所在地的疫情状况。写着写着我突然发现,尽管很久没正经写过中文,我时不时自造一些语汇也不带怕的,遣词造句有种回到主场的从容,与英文写作时的谨小慎微截然不同。

然而跟华语圈再次接轨之后,我才体会到中文网络之喧嚣、管制之严厉、地区对立之严重。许多微信公号上关于疫情的文章我还来不及引用,就被举报删除了,完全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触碰到了敏感的神经。回到华语世界让我很割裂。一方面,我欣喜地与自己的母语重逢:文法、词汇,都不必细想,俚语、典籍,张口就来;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一堵无形的高墙,还没张嘴就不自觉地自我审查。
2020年春天,不少被删除的文章被转来到 Matters,进而让我了解到Matters的创立初衷。我也便在这里注册了帐号,在这里最早的个人介绍是:
希望有一天我们都可以自由地用母语写作。
冰火盛世
回想起来,2008年对我来说是十分压抑的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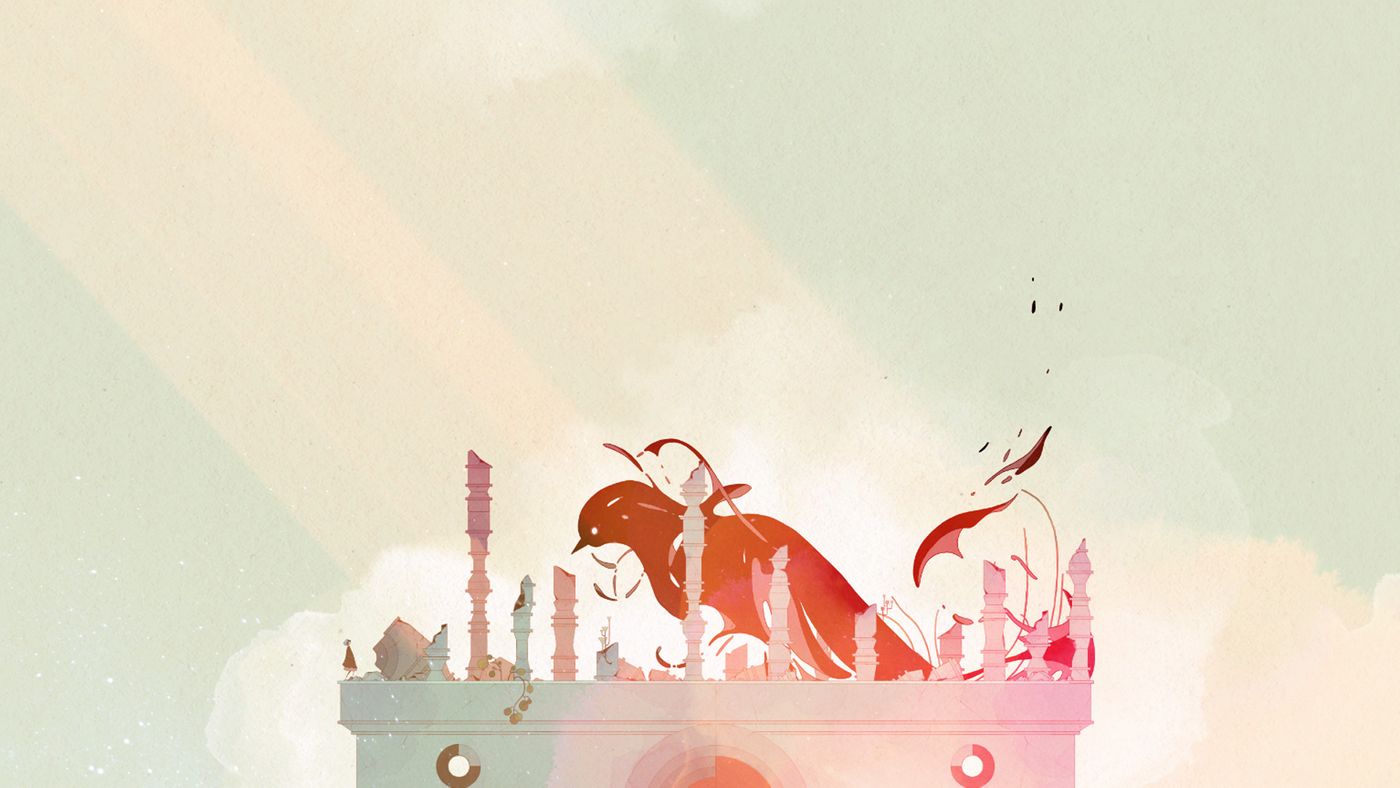
三月西藏暴乱的时候,我发现跟国内的朋友通邮件如果谈到西藏,他们会收不到。从此以后,我跟使用QQ或163邮箱的朋友渐行渐远。
五月汶川大地震,无数帮助受难家属发声的异见人士受到打压甚至逮捕,调查志愿者受到警方骚扰,作家谭作人因起草《5.12学生档案》倡议书而被判刑,艺术家艾未未因组织搜集死难学生名单在成都的宾馆内被公安袭击,且在此后的数年 “被失踪”,软禁,监视,诽谤。
八月他们终于如愿举办了奥运会,听说他们费尽心机让北京蓝天重现了一段时间,解封了被封禁的网站,还划出了场地供人们抗议、示威 😂 虽然没有任何示威申请得到批准。
十二月,《零八宪章》发表签署,之后刘晓波被捕,直到2017年逝世都未再得自由。
讽刺的是,国内倾向于把2008年称为公民社会元年,说是在灾难中看到了民间团体志愿者力量,听说此后NGO、NPO在中国蓬勃发展。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10年欧州欧债危机,西方社会弥漫着颓靡的气氛,而中国此时从自卑走向自负,开始了盛世中国的美梦。
很多与我一同出国的朋友都在2013年前后回国了。中国发展势头很猛,不少朋友都说我不回去是错过了千载难逢的风口。也许吧?可是我的个性也不是那种懂得在风口卡位的人。我不觉得我回国能发财上位实现阶层跨越 😂 反而被人占便宜还说不定呢。
港台京三地作家陈冠中写了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盛世:中国2013》倒是让我在那些年时刻保持警醒,不被虚张声势的繁荣迷惑。
墙内墙外
今年三月读到一篇报道,说身在俄罗斯的人不相信普京入侵了乌克兰。甚至当他们自己的亲人从乌克兰打来电话告诉他们炮弹就在身边落下,他们也宁愿相信克林姆宫的官方消息。很多人在撕裂与沮丧中愤怒地与家人决裂。
这则消息让我想到还在国内的亲人,不禁泪目。其实我们都习惯了不对彼此说太多深刻的话,思想的鸿沟似乎已经难以跨越了。危机尚未落到我们头上的时候,电话里说说吃喝玩乐的琐碎事情,似乎关系也可以就这么维系着。然而当危机降临,当事件恶化到必须表明立场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亲人吗?

我感到自己已经无法再回避使用母语,并且我必须使用母语来说一些重要的事。
政治的陷落,是從語言的陷落開始的。
當你無法誠實、公開地講出自己的想法,「公共」的基礎就消失了。當表達退回私人領域,交流、爭辯的基礎會流失,思想、判斷的品質也會萎靡。更進一步,若每個人都從公共隱身,組織與連結無處可依,共同體也會趨於潰散。
最要緊地,放棄了語言的你,還可能不自覺地,成為極權體制的一部分。
當我們放棄自己的語言,就已經成為了「非人化」機制的一部分。要抵抗這種機制,首先就是抵抗這種機制在我們自己身上運作的可能,反制恐懼,拿回自己的語言。
就在上周,在我那个英文写作分享会里,我向写友们道了别。我告诉他们,基于以上原因,我在可预期的未来会主要投入中文写作。
写诗的 Miriam 出生于美国哈西迪猶太教家庭,整个社区非常保守传统。然而她选择成为了一名科学家,是家族中的异类。她说她很能理解这种割裂的感觉。这次分享会上,她送我了一首诗,我爱不释手,于是翻译如下。

The Sea | 海洋
In this neighborhood, people yearn for heritage
这里的人们渴望历史的传承
Cherish words, phrases, scraps of a lost language
对那些单词、短语、失传语言的碎片 如数家珍
They hunger for old music,
他们想听的是古老的音乐
Tell me I’m lucky to have a reservoir to draw from
而我是多么幸运,拥有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汪洋
Because, where I’m from, the language isn’t dead
因为在我的生长的地方,古老的语言还很鲜活
These words were the amniotic fluid in which I materialized
这语言的羊水孕育了我
Where an angel taught me a song for each letter of the alef beis
那里的天使教会了我——每一个字母都有一首自己的歌
I was born underwater, thrashing to the surface
我出生自水底,脱胎于水面
I crawled out of a sea of words
再缓缓爬出这言辞之海
Choking, gasping, wringing melodies from my hair
哽噎着,喘息着,我从头发里挤出旋律
I offer you the songs stuck to my skin
让我把那些仍紧贴在我肌肤上的歌送给你吧
Burned into my brain, engraved on my heart
烙印在我脑海,镌刻在我心
In a language I can refuse to speak but can’t stop understanding
我可以拒绝说这种语言,却无法不听懂它
Sharing them makes me feel less like a stranger to myself, so I offer you
说出来与你分享,让我觉得自己不再那么陌生
因此,喏——
Polished memories with the pain sanded off
这是打磨过的回忆,抹去了痛苦
Smooth-stemmed stories from which I’ve
如同被剥掉了刺的荆棘
Plucked the thorns of guilt and shame
丝滑的叙事脉络中,不再有悔恨和羞耻
Are they still authentic if there are no sharp edges to wound you?
只是,当它们无法再刺痛你,它们还是真实的吗?
And where do I put this pile of thorns I’m holding?
而我手里的这把小刺又该安放于何处呢?

我的语言安那其
我的母语应该是成都话,但外婆家在重庆,我也会模仿重庆人说话。读书时期在江南,那些年又看了很多台湾综艺,所以普通话说出来有点台湾腔和沪杭地区的混合。最近遇到一些北京来的朋友,又沾染了点儿京片子。
刚刚来到 Matters 的时候,鉴于这边港台用户居多,我考虑过用繁体书写。但是繁体字写出来其实是有地域感的——台湾人把 taxi 叫做计程车。我在写那篇 DAO的模型推衍 时通篇要用 taxi 举例,我发现我超不习惯说“计程车”。写了几个段落之后,果断找了个繁简转换器改回了简体字,并把计程车改回成我习惯的 “出租车”。
但我也知道港台把 software 叫做软体,而大陆翻译为软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更习惯说软体。🤣
综上所述,我的语言就是现在这样有点大杂烩的样子。
V神在谈到去中心化的时候,提到过语言是无中心的。就好像你没法强迫美国人像澳大利亚人那样说英语,我们其实也不能用「标准普通话」来胁迫任何人。语言的首要目的是沟通,其次是美感,再次是风格。所谓的官方标准语言,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树立权威,把使用语言的人分为三六九等。
基于这样的考量,我决定先让自己舒服,按自己习惯的方式来表达。遇到沟通障碍的时候再做调整。这算是我的语言安那其吧!

最后来唱首歌

起初他们...
起初他们镇压学生运动,
我沉默,因为我不懂政治。
之后他们迫害藏族和维族,
我沉默,因为我是汉族。
然后他们监禁维权律师,
我沉默,因为我没有维权的需求。
当他们攻击宗教信仰的時候,
我沉默,因为我不是教徒。
当他们打压LGBTQ平权运动的时候,
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同性恋。
当他们抓捕女权运动倡议者的時候,
我沉默,因为我没受到过性侵。
当他们噤声独立记者和民众质疑的时候,
我沉默,因为我在等官方通报。
当他们关押无症状感染者的时候,
我沉默,因为我的核酸检查是阴性。
最后当他们來抓我的时候,
再也沒有人站起來为我说话了。
这篇文章中所有的插画都来自游戏 Gris的截图。感谢 Gamer Walkthroughs 的详细分镜介绍(有剧透,慎入)。这是一款美哭了的单女主冒险游戏,强烈推荐大家去玩!在 Steam,Google Play Store 和 Apple Store 都有售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