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监工与慢直播:「众声喧哗」下,被享受与被消费的
2020行至年终,各大机构评选的网络热词相继出炉,其中,“云监工”频繁出没于「十大网络热词」榜单中,与之并列的多是“后浪”“网抑云”“打工人”等。
国内疫情早期,4000万人同时在线,通过一个固定机位观看雷神山医院建筑工地的现场直播,让云监工迅速火爆。在当时的情境里,“监工”建构出一个“身临其境参与其中”的想象共同体,也使慢直播成为了现象级的议题。
而“双十一”的快递发货直播,与年初呼应,让云监工再次获得全网热议:不到三天,直播观看人数已有8000万,流量高峰来自11月1日凌晨,超过800万“尾款人”熬夜在线观看包裹在流水线上匆匆“赶路”......
那么,千万人都在“监工”的慢直播,究竟有什么魅力?云监工背后都反映出哪些传播学和社会学内在逻辑?本文从三方面提出问题并深入思考,希望从中得到答案。
一、云监工与慢直播观众群体等同吗?
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用户沉溺于信息密度低的慢直播视频中?
三、当下社会环境下,平台是否更加容易「造景」,以塑造消费者的「共识」?
慢直播与云监工是一回事吗?
首先,先简单回顾下慢直播的发展历程。
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63年,当时,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拍摄了一场慢电影《沉睡》,在片中实时记录了诗人约翰·乔尔诺5个小时的睡眠过程。

这一概念随后被纽约地方电视台WPIX借鉴,用于营造圣诞节日气氛:工作人员的圣诞节循环播放了一段圣诞柴火在壁炉里燃烧的影片,全程12个小时,吸引了 100万人观看。
如果说上世纪慢直播的艺术意味其实盖过了记录实景,那么,2009年挪威的一场慢直播则算是彻底打开了“云监工”的大门。当时,挪威电视台为纪念卑尔根铁路诞生百年,用摄像机记录了整整7小时火车行驶的旅程,没有经过任何后期处理,一路吸引了大约120万挪威人收看,人数相当于当时挪威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至此,慢直播这种别样的镜头记录形式逐渐被新闻媒体所关注。
2010年后,风靡北欧的慢视频风格开始在英国流行,当时,有些英国人热衷于花费好几个小时,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别人钓鱼、织毛衣或者看火车行驶一段漫长的旅程。
2015年,英国BBC第4频道成为这种慢电视的试验基地,电视台推出慢电视节目系列,用2小时的运河旅程、3小时的国家博物馆畅游和3个30分钟的无解说手工制作过程,来表达简单生活中的艺术和当地流行文化。
“毫无修饰叙事中的未知部分永远抓着观众的心。”第4频道总监哈瑞森如是说。在慢电视的内容中,观众更容易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获得某种平和与身临其境感。有报道说,有位观众在观看了5天的火车行程之后,在火车到站那刻,他拉开家里的窗帘,开始找行李准备开始一段旅程。
同期在中国,央视网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合作开办iPanda熊猫频道,24小时直播大熊猫生活,看团子们打打滚吃吃竹子,偶尔还会见证一场群架,虽然整个环节中唯一有互动性的是文字直播员,但熊猫铁粉们依旧乐此不疲。

那么,我们所说的云监工与慢直播,是同一回事吗?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慢直播是一种媒介传播形式,而云监工是一种内容消费形式。
雷神山和火神山建造直播与双十一发货直播能够成为现象级的全网热点,使云监工概念一再被推上热搜,依靠的不仅是慢直播形式本身的吸引力。
如果说之前的慢直播是抓住小众兴趣,主张愿者上钩,那么,后来的云监工更多是媒体精心设置议题,调动起大众兴趣。视频本身并无剪辑,但选题是专业人士精密策划而成的。
学者Daniel Dayan和Elihu Katz将这类精心策划过、附带传播脚本的议程称为“媒介事件”,这并非一个新概念,在电视时代早已出现,它指的是类似大节日的体验,是“关于那些令全国人乃至全世界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
但在直播这种互动形式支持之下,媒介事件不仅能够塑造群体共识,而且变得更加有参与感。[1]克莱·舍基在《认知盈余》中说过,人们的自由时间除了仅仅用于内容消费,还应更多用于内容分享和创造,且分享和创造的价值远大于消费。慢直播更像一场长时间的全民狂欢,也正因为提供给了受众更多“分享与创造”的可能性,也使得受众群体更大众,触及情绪更多元,参与目的更加丰富。
所以,如今的云监工,更多是把重心留给了受众。在雷神山医院直播之前,慢直播给予受众的更多是“云卷云舒”之感,而云监工更像是慢直播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衍生品,前者重新定义了后者,延伸了后者的信息可供性,但依旧属于后者。
观众为何热衷于在慢直播中当“包工头”?
之前的慢直播主要体现的关系是:受众与媒体、受众与本我。在这个基础上,如今的慢直播又加入了两种互动类型:受众与受众、受众与视频元素。
先说受众与受众的互动。其实这点与普通的直播形式趋同,但不同的点在于,慢直播的第一文本,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表达舞台,其信息密度很低,大量留白与不确定性赋予了观众对第二文本进行自主建构的能力和需求:在漫长的视频中,受众成为慢直播中的表演主体,而此间的互动文本则成为消费内容的主要视听语言。[2]
在这其中凝炼出的梗是提升受众参与感的灵丹妙药。
在雷神山医院建设的慢直播中,“摇摇你的小红旗”“大家吃饭了没”......种种通俗易懂的短句弹幕就像是入门暗号,帮助观众快速找到归属感和共鸣,而评论区的接力互动更强化了受众对观看慢直播行为和自我表演的认同。
到了半夜,评论区陆续出现“打卡撤退”,同时不断有人“接班”;熬到凌晨4点,观众们甚至开始在评论区“叫卖早餐”,其他观众纷纷“点单”;成语接龙、诗词接龙等评论区游戏则是更进阶的玩法。

其次,受众与视频元素之间的互动同样值得回味。
双十一发货直播,数百万人在评论区刷屏,为199摇旗呐喊(199是菜鸟无人仓里编号「199」的机器人,它与其他1000名同伴一起,在仓库中每日为“双十一”消费者发出85万件包裹)。

“哪个是199?”“199快出来”“199初始化了”“来了来了它来了”......这些评论区留言体现出符号化的重构:受众将无生命的个体(比如挖掘机、送货机器人,甚至施工现场的三棵桂树)进行解码再编码,将一些无法轻易理解的事物(数字化物流)消解为相对易懂的一系列符号(199)当中。
这背后是某种饭圈的逻辑:观众身处“粉丝”的位置,把一个普通的内心幻想的形象转化为具体的、具有公共潜能的文本。这看似在为“偶像”打call,实际是通过对“偶像”的支持,实现自我意识的表达。
这种自我情感的投射,类似自娱自乐,其实也是云监工和慢直播的另一种诠释:我们不仅在观看他者,也在享受自我。很多没有耐心观看慢直播的人,不就经常将这种无聊行为总结为自娱自乐吗?
继续深入思考,在这种“观看与被观看、互动与被互动”的视听享受的同时,“消费与被消费”的逻辑关系同样值得关注。
50年前,鲍德里亚的经典理论就说明:“被消费的不再是物品,而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3]那么,观众解构视频中无生命个体的过程,又何尝不是一种消费?消费着互动,消费虚构出的意象,消费编码后的剧情,也消费着我们投射在直播中的情感。
在这里,消费品的特征不是它首先具有物质性,而是它演化成为一种“物的符号”,是一类个性化的意义对象。[4]
讨论到这里,其实也就必须直面现象的另一边:我们在观看的过程中,对物的消费是否具有能动的意义?又是否过于关注于微小之物,而消解了一些我们原本该注意的事物?(就像是为挖掘机打call,是否忽略了背后操作挖掘机、昼夜无休的工人?)
这种离场的介入给我们带来的究竟是踏实感,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虚幻的满足?[5]换言之,我们是否是在平台的引导下,被动的消费呢?这就引出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云监工走红,媒体造景发挥了多大作用?
“造景”并不是新鲜词汇,上文提到的媒介事件就已经体现出了造景的概念。那么,一场媒介事件如何精准引爆?媒体和受众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一直以来,典型的一类造景就是:放大事件本身的力量。这需要它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比如,它已经处在堪称“历史性时刻”的时代背景之下。
在这个层面,可以使用媒介事件的3C脚本作为分析的基础。3C脚本即:
竞赛(contest):发生在竞技场、体育场、演播室等场合,有输或赢的结果,如电视辩论、奥运会直播、各种锦标赛、创业大赛等;
征服(conquest):围绕人类的巨大进步来展开,比如“嫦娥”探月、石油开采;
加冕(coronation):这是对各种庆典的直播,比如奥斯卡奖等。
“两神山”的直播拿到的就是竞赛和征服的脚本:这是一场“中国速度”与病毒的比赛,也是人类在工程事业上的突破。借助这类媒介事件的力量,能够使全社会快速凝聚共识,形成共情。
而另一类造景则偏向于,通过强力手段人为制造符号,并且通过广泛且长期的营销烘托气氛。这次双十一直播,就是基于商业目的和商业力量而凭空出现的,这是一种纯粹的造景。
相比之下,后者的风险更大,因为受众的情感基础不牢固,容易达不到预期效果。然而,今年的慢直播却实现了现象级刷屏,它为什么能够引爆网络?
一是因为购物节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消费者们早已蓄势待发,期待在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日分泌快乐激素,另外,这场直播选择的时间与内容也刚好切中消费者的心理。[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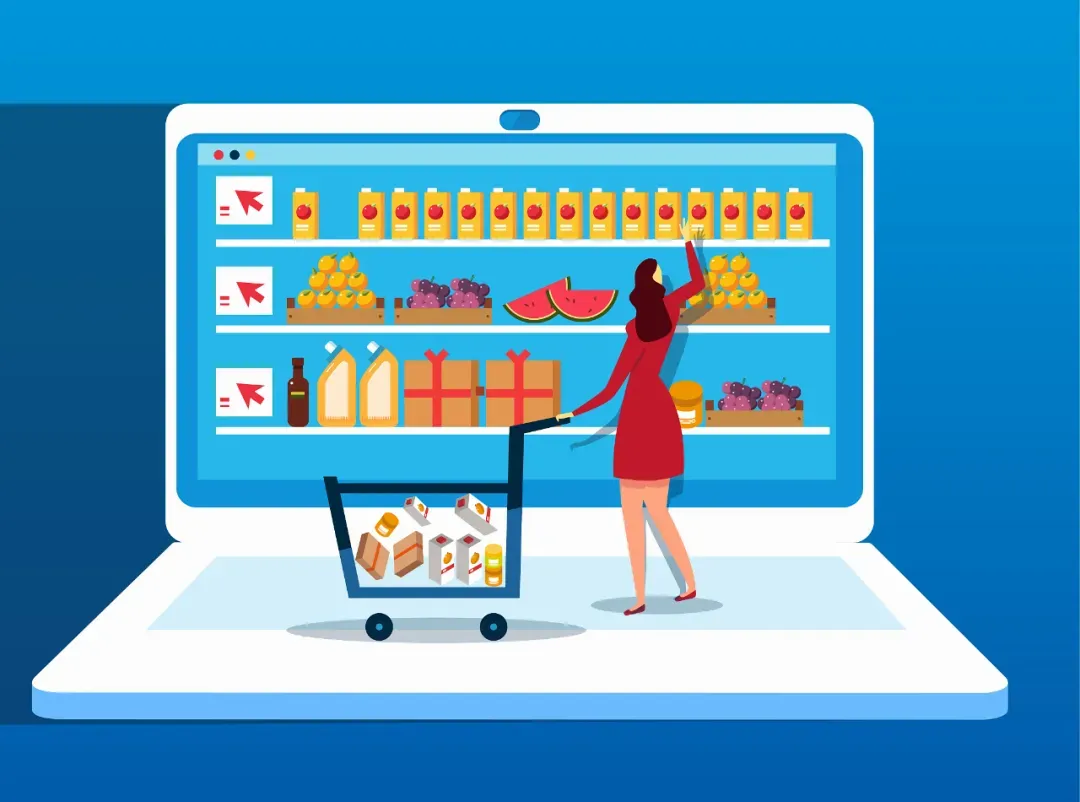
在知乎“为什么双十一百万人熬夜围观快递发货直播”的问题下,网友们表达出他们的各式心理:
“我等这一天付尾款等了足足有小半个月啊!真的恨不得一下单就能收到快递,看到机器人们都在加班加点有序发货,我终于松了口气,看来不用再为自己心仪的产品牵肠挂肚一天看三遍物流信息了。”
“百万观众这个数量级,让我莫名产生了一种原来不光我一个人吃土,还有成千上万的人陪我一起吃土的错觉,一下子感觉就舒服多了!”
“我去看快递发货直播,一开始是十分好奇,后来看着看着,就觉得真是自豪,豪横豪横的自豪感。”
在互联网时代,媒介事件之所以会产生强烈的冲击力,用户对它投入的巨大时间精力功不可没。
我们无法忽略受众在意义的塑造上同样具备强大的力量。结合来看,受众心理、平台造势、内容价值、媒介技术......这些都是媒介事件造景成功的必备条件。
在当今的互联网内容生态中,平台与内容生产者似乎都在追逐快:图文内容要精简带梗,视频则强调短和倍速,然而,快是受众取向的唯一吸引力吗?现象级慢直播的出现与云监工的走红都在验证一点:无论快慢,能否让受众在其中收获某种共识,获得对其身份的宽慰与认同才更关键。
在社交媒体时代获取关注,短平快,或许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慢有慢的美妙与独特,相比之下,慢直播更加能够完整地见证受众自发的力量。在这个被构建出的想象共同体中,受众取代视频内容登上主舞台,体验着观看与被观看、消费与被消费的过程。双十一直播的高流量也引发新的思考,当慢直播不再只是观众在镜头背后享受自然风光,而更多被人际之间的互动与解构所填充时,这到底是“慢且乐之”的共识塑造,还是被消费主义不断裹挟的必然结果呢?
参考文献
1.宋成. “慢直播”与“饭圈文化”:“云监工”的传播学解读[J]. 新闻与写作.
2.C 刊网.(2020). 慢直播的显性表达特征——直播生态关系的模式重构.
http://www.ckan.cn/lunwen/qikan-13749.html
3.张琴.(2019). 符号、认同与操控:反思消费社会下的网络直播.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9/1129/c430943-31481575.html
4.宗城.(2019). 鲍德里亚诞辰90年 | “消费社会”必然导致人的虚无吗?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994473
5.张曙光. & 陈慧敏. 技术、社会、心理互动形塑“新型消费社会”[J].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9)
6.界面新闻.(2020). 爆买剁手之后,我们的快乐为什么越来越贬值?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35011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