爐子內外 | 「有時,我希望康奈爾沒有錄取你」


三位溫州人,從小城走出,來到歐洲、北美、香港求學。人生的路交叉、交匯,在過往的生命裏蕩起漣漪,不停蹄地向未來延展開去。曾經的故鄉,過往的夢想,也終將被埋藏在心底。
香港,是我們都鐘意的寶藏城市。淩晨薄扶林道上呼嘯而過的大巴與的士,向我們展現這座不眠都市的無限魅力。花花綠綠的口罩可以遮住半張臉,卻遮不住熔化後滴落的欲望。那些不眠的清宵裏,即便我們閉上眼睛,香港依舊自轉,人們照常高歌。
我小心翼翼地觀察著身邊的港大學生。人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和迷惘——回不完的郵件,改不完的CV,掃不完的「安心出行」,讓好多人在車水馬龍中迷失了自己。白夜裏,欲望五光十色;黑夜裏,人心斑駁陸離。他們或是意氣風發地磨平自己的棱角、將自己形塑為「精英」,著急地成為一個大人,或是不知道自己將駛向何處、原地徘徊,或是因無法接近過於宏大的理想而苦惱不已。那些無人問津的痛楚,就像Gourmet Canteen的柑桔檸檬蜜一樣,時而淡,時而濃。多數人卻也無非是出於想要的太多,心甘情願地把自己囚困在浪漫謎底裏。
走到今天這一步,如何才能對自己誠實?

1|三個溫州人,與跨越三大洲的名校
無耽 | 我在浙江溫州的一個普通家庭長大。有幸家人重視閱讀,小時候家裏帶著我讀的第一本書,應該是《聖經》《悲慘世界》或《小婦人》,自此也比較向往一個重視人文社科的世界。在小城相對封閉的環境裏,我一直覺得高考才是我走出來的機會。但在中考失利後,我去了一所較普通的高中,也因此對人生規劃有了更多思考。在高中時感受到體系裏個體的糾結和掙紮,由於家裏的華僑背景,我在高三時選擇了離開體製,「出走」到歐洲準備大學申請。我當時一直很想考上一所具有人文精神、博雅教育的傳統名校。在種種機緣巧合之下,我選擇了法國社會精英的搖籃——巴黎政治大學。現在我在英國劍橋大學學習德法研究,即將完成我的本科學業。在這兩所所謂的名校裏,我發現自己對社會階級化下的精英文化有很多不適應,也有很多質疑。而在歐洲的漂泊,也讓我常追問並革新自己對世界、自我的認知。關於未來規劃,我想家裏人對我是沒有具體期待的,因為他們並不清楚我學的是什麽。我自己可能想做記者,或者更廣義的文化工作者。
問笛 | 我也在溫州長大,從小被放在一個精英的模子裏培養。在長期的理科競賽學習中,我慢慢發現自己和體製內教育有一種氣質上的格格不入。我開始懷疑為什麽要無止無休地追求考試排名,為什麽要依照成功的單一定義而痛苦地形塑自己——人生的意義是什麽?我這一生到底想做什麽?我逐漸意識到我對哲學的熱忱,與對更大的世界的向往。高考的失利和高考後的一路翻車,讓我陰差陽錯地來到了香港大學,主修哲學。從溫州來到香港,我如同突然被擲入了一個熔爐——一個東西文化相互交融、多元價值相互碰撞的熔爐。在這樣一個自由開放卻也險象環生的環境裏,我快速地成長起來,嘗試去理解、去欣賞和自己成長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的想法,分享各自在人生岔路口的抉擇,共同探討人生哲學,因而我看到無數的可能性向我展開。這或許也是為什麽在港校的求職焦慮潮流中,我依然沈浸於博雅教育的魅力,依然執著於人類思想文化史的探尋。我更加深入地思考自己希望在這個蔚藍星球上留下怎樣的痕跡,秉持成為一名心懷天下的理想主義者的life mission。這個學期我在聖安德魯斯大學神學院交換,繼續對spirituality和人類信仰體系的求索。

以列 | 我是在南京出生的溫州人,和問笛是很好的朋友。我其實一直很為自己的溫州人身份驕傲,直到在南京度過童年、回到溫州讀初中時,我不會講溫州話,班上的同學暗地裏叫我「那個南京來的同學」,我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被marginalized了。初三時,我申請了公立獎學金項目,赴美交換一年,隨後決定在美國繼續念高中。申請大學時,我對生物信息學充滿了熱情,希望以後能夠背負科研重任,浪跡天涯。在讀完一年生物專業後,我開始慢慢意識到學術之路的艱難與自己能力的有限。隨後,我毅然決定要轉專業。目前我於康奈爾大學主修計算機科學,輔修生物學。受疫情影響,上一學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學交流學習。像大多數溫州人一樣,我出身於一個普通的經商家庭。我的父母希望我能成為一位科學家,但是我想成為一位普通的碼農。


2|那些年,我們的學術夢
問笛 | 在高二升高三的暑假,我參加了復旦大學的哲學暑期課堂。我在「自由而無用靈魂的棲息地」感受到了一種契合,一種思想共振時被理解、被接納的感動。受到這一群復旦人的影響,我心裏萌生了一個非常單純的學術夢。我希望自己能夠在人類知識體系的邊緣開拓,去探索真知。當時我念高三,以列剛進入大學,兩個人都有著特別純粹的學術理想,每天聊人生哲學,討論細胞結構、RNA和蛋白質的起源之爭,我還教他敲過代碼。當時他和我說自己想要「背負科研重任,浪跡天涯」——現在想起當時的那份純粹,感慨良多。
但在進入港大學習哲學後,在某些方面我觸碰到了自己能力的邊界,在另一些方面我也發現了自己的一些閃光點。我也意識到學術圈的環境並非是我所想象的伊甸園——性別、種族等各方面的偏見與歧視,學派之間的紛爭與排擠,都是真實存在的。在對比中,我也深刻地感受到大陸學術環境的短板所在。全英文教學的環境讓我越來越難以用中文討論學術。我不大清楚在這個時代,還有多少人願意把學術當成一份誌業。Master, PhD, researcher, lecturer, associate professor, professor… 這一路上有多少坎坷,「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所看到的,是每個人對於機會成本的衡量。在江邊散步時,我問Dr. Michael(我和以列的外教)如何看待機會成本的問題——三十歲PhD畢業時,身邊本科畢業就去工作的同學可能早已買車買房、走上所謂「成功人士」的道路了。他是這麽回答的:他在牛津大學一路讀完了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etters的本碩博,是因為他明白自己對學術的熱愛是一種falling in love,因而很少糾結於機會成本。

我的父母對我是有期許的,他們會有多少歲前應該買車買房、結婚生子的觀念,可是我目前並未把這些列入我的人生規劃。我也不清楚自己如果選擇了學術道路,它將通往哪裏,我能走到哪裏。港大焦慮的求職環境、做學術所要求的身心投入,讓我慢慢開始質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和機會走學術之路,是否可以在風雨飄搖中穩住一方書桌,是否可以「接受時代對我的態度還依舊選擇堅持」。而我對更貼近社會現實的工作也充滿熱情,目前的理想是成為一名探索並夯實人類信仰體系的spiritual leader。總而言之,我看著自己從當初一個搖擺飄忽的理想主義者,變成了一個相對現實的理想主義者。我不知道在遙遠的未來,我會不會變成一個理想的現實主義者。
以列 | 在高一的時候,我聽說了物理學家加來道雄的超弦理論,看了電影《星際穿越》,對物理學產生了非常濃厚的興趣。當時我還嘗試去自學這些理論,最後自學未遂。和問笛的經歷很像的是,在高一暑假,我獲得了到復旦大學高分子科學系接觸科研的一個機會。我了解到一個很出名的材料叫石墨烯,讀了一些論文,做了一些跟石墨烯相關的實驗。石墨烯可以做成超級電池,我想這是可以為全人類服務的一項事業。當時我真的覺得自己適合學習材料科學。在大學申請時,我也選擇了材料科學專業並收到了錄取。而高三的下學期又是另一個轉折點,我接觸到了生物信息學,了解到了BLAST、保守序列對比等,當時我又想轉去學生物學,盡管當時美國大學差不多已經全部放榜了。在現實中,我也有半學術的經歷。今年暑假我在上海的3M的食品安全部做了實習生,當時我主要的任務是研究金黃色葡萄球菌的基因,去設計一些質粒基因的引物,比如血漿凝固酶、腸毒素的基因。我花了大概三個月的時間做這方面的研究,總體來講還是挺喜歡這種科研工作的氛圍。至於為什麽我轉到了CS(計算機科學)專業,後面我再具體講一下求職、移民等方面的考量,簡而言之,這是出於學術夢的破碎,而非出於學術夢的轉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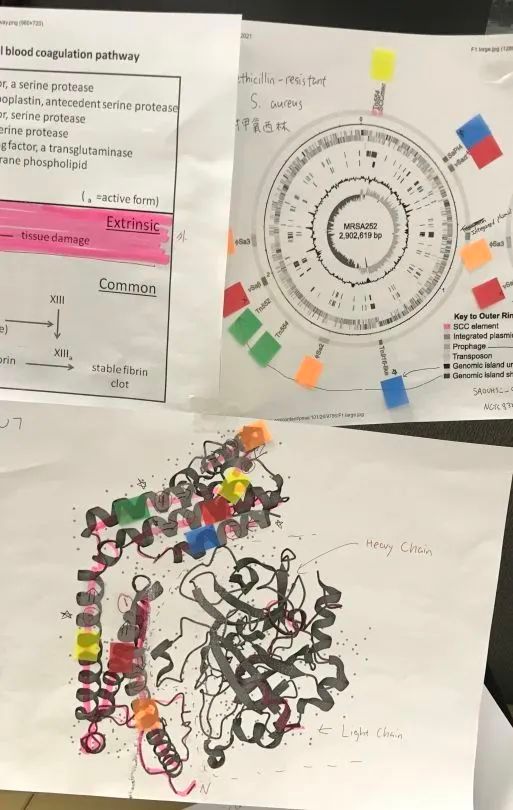

無耽 | 最初在我眼裏,成為學者就像錢鐘書、余英時那些老一輩大師一樣,我似乎把學術與那個黃金時代相捆綁,把它當作一種逃脫框架化的現實生活的方式,並沒有把它和比較實際的一些職業道路相掛鉤。來到巴政後我才發現,現在的文科學術很大意義上也只是一種標化的研究方式,背後其實有很多的利益糾葛,比如說選題的背後有市場才更可能有funding。在人文社科方面,我慢慢感受到在一些田野調研中,我們的確可以接觸到一些令人震撼的社會現象,但是以學者的身份參與到這些事情當中,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改變社會現狀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從社會文化方面講,我曾有很單純的一個目標,是想破除一些刻板印象、講出更多人的故事。後來在新聞產業實習時,我發現新聞上的文章也好,學術研究也罷,很多時候不一定真正能做到追求真相、追求真理,反而是在加強誤解和刻板印象。這大概是我當年的學術夢以及現在對其有點失望的想法。
3|名校與我們而言,意味著什麼?
無耽 | 我覺得我們選擇了名校,對名校無疑是有所期待的。同時名校對我們也是有期待的,比如我們未來將要貢獻學校的就業率、平均薪資的一部分數據。
問笛 | 之前和朋友聊這個話題。這是名校光環帶來的不太好的現狀——如果一位名校學生過於在乎畢業生平均薪資的這個數字,把金錢當成衡量自身價值的唯一標準,ta的很多想法很容易被這個數字局限。
以列 | 我跟問笛有相同的感受,我們到了名校的確會頂上光環,但這個光環是非常沈重的。大二快結束時,我在找實習。和我一起做小組作業的一個大一同學拿到了微軟實習的offer,但是我被拒了。當時我因為這件事而非常難過——進不了微軟的我真的配得上康奈爾嗎?但是,如果我們想開一點的話,也不必糾結自己會不會辜負母校的期望,母校可能並沒有期望你做什麽。
無耽 | 對,其實學校對我們可能也沒有什麽期待,我甚至感覺學校根本不care作為個體的我。學校作為一個institution,它有很多硬性的指標要去爭取。但是從我作為個體的角度思考,我也只是巴政/劍橋幾千幾萬學生當中的一個。尤其是作為一名國際學生,我們和大多數本地學生的成長環境不同,更不必說這裏的精英氛圍。曾經有一次我約了巴政校長的office hour,校長告訴我巴政並不是培養精英的工廠,你們進來的時候就已經是社會的0.01%了,我們能做的只不過是讓你們大多數在這條道路上的人繼續留在這個social status的 track上,但是我們並不能確保這一點。他當時跟我講完這句話時,我更深地意識到了自己從小城溫州走到這裏,已經是非常少數的幸運兒了。在劍橋,我也更加體會到了高等教育產業化中,其實學生和老師都被這個功利的系統所異化。在大學這個微觀社會中,我們被放到了一個整體精英濃度、文化資本濃度都很高的環境中。但每個人的socioeconomic status都是不同的,每個人的機會成本、能夠獲取的資源也都是不同的,這一點毋庸置疑——可是為什麽這會讓我們顯得比較vulnerable呢?
思考了一段時間後,我開始感覺到自己對名校光環的種種糾結慢慢開始消退了。現在我拿到了劍橋教育學的碩士offer,以後希望能將自己本科學到的社科人文知識用在研究更能實現社會正義的教育政策上。但是,我本以為本科這幾年的試錯真的能夠讓我放下虛榮心、摒棄名校光環,去選擇一所title不是很大的學校,目前卻也在迷茫中更想留在名頭更大的學府裏以給到自己一些安全感。


4|Where did you see yourself in 10 years?
问笛 | 一方面,我很感谢港大给我提供的平台和资源,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结识了很多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人,每一天都能给我eye-opening的探索机会;另一方面,我也发觉有的人选择名校只是为了一个title,把这里当成交钱换一个degree的地方。港大的内地生比例是10%,但是商学院的内地生比例是35%。香港的商学院以及世界各地最好的商学院,以及现在的一些金融求职机构,越来越像是生产同质化精英的大机器,轰隆隆地吼着“我们要霸占中环街头”。拿这些求职包装机构来说,它们专门做藤校、G5、香港三大的学生的生意,像是一道生产流水线,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当成工件打磨加工,让你从准备简历到笔试、面试,从拿到internship offer到手握return offer。在欧洲、北美、澳洲的中国留学生,从世界顶尖的商学院毕业后都成为了香港中环街头“一模一样”的金融打工人——这可真是“大道相通,殊途同归”。
之前我和我的adviser说,我觉得自己在这焦虑的求职潮流中是一个creep。Socialization的过程在我身上非常失败。通过长期的探索,我慢慢意识到自己的life mission是做一位spiritual leader,尽管我尚未找到一条direct path。我在电影公司、保险公司、NGO、国际组织、社会企业做过尝试,不断进行trials and errors。我还考虑过商业咨询。当时我的counselor张熹在亚太生涯规划年会上请教顶尖生涯咨询大师Dr. Mark Savickas,有学生在咨询行业和学术(更准确的说,应该是a spiritual path)之间纠结,问他怎么想。他问这个学生最喜欢的书是什么,张熹说是黑塞的书(《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Dr. Savickas的第一条回应是, “Do what you love, and money will come.” 他的解读是,我在纠结是去追求外在的认可和成就,比如高薪和名企,不甘心自己落后于同龄人,还是放下世俗标准,追求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场对话让我茅塞顿开。

不過,「money will come」可能引發的誤解是,錢依舊被當成了衡量在do what we love過程中實現自我價值的標準。有一天和朋友聊到這一點,他把這句話改了一下, 「Do what you love, and you will not care when money will come.」後來和一位港大校友聊天,她又把這句話改了一下, 「Do what you love, and opportunities will come.」 她的言外之意是,當你真正在做自己熱愛的事情時,你整個人、整個靈魂都是在閃閃發光的,自然會吸引身邊的很多人,他們中有的願意offer opportunities去幫助你,有的和你成為了誌同道合的朋友。
以列 | 我對問笛剛剛提到的金融求職機構感觸頗深。我剛上大學時,從未有過求職的顧慮。當時我覺得我去了一所好學校,好好讀生物學,去一個好的實驗室,再好好讀碩士、博士,就會成為一位優秀的科研人員。後來,一個求職中介的宣講改變了我的想法。現在想來,我覺得它在做的更多是販賣焦慮。中介告訴大一就要開始準備大二的實習,大三暑假要找一個big name的實習,然後大四拿return offer,後面再拿到綠卡,簡直是一條龍服務。他也講了各個公司實習生的錄取率、競爭有多激烈等。我被販賣了不少焦慮,也意識到自己面臨著一系列選擇——我要學習什麽專業?以後從事什麽工作?是回國還是留在美國?其實這些問題是每一個美本留學生都是要考慮的,畢竟從美國回到國內工作是一張「單程票」,以後如果想從國內回美國工作就比較難了。想留在美國的話要趁早,就如那些求職機構說的那樣,找好的internship,爭取到return offer,最後申請綠卡留在美國。我選擇了轉到CS專業,和那次求職宣講還是有很大關系的,我想自己以後還是要做一些比較踏實的工作。而如果繼續讀生物、做科研的話,大概率是要讀到博士的,而且即使讀到博士,還要面臨一個僧多粥少的問題。其次,針對目前的國際形勢來說,像生物這樣的「敏感專業」對國際生不是很友好。
那為什麽我要做碼農呢?剛剛問笛說「Do what you love, and money will come」時,我的第一反應是But he didn』t mention how much money。我們沒有量化這個問題,沒有具體考慮過我們的經濟能力是否能滿足一些即將到來的現實需求。我是有一種中國人的傳統觀念的,即讀完書以後要成家立業、結婚生子,這些規規規規矩矩的事情都要做。所以當時我就想,如果我去讀生物的話,我以後會有多少收入?我是否能付得起房貸?是否能給予我的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想得這麽遠了以後,我就越想越焦慮,後來就有了這樣的一個意識——我還是做碼農好了,做一個收入穩定的「新農民工」,至少生活的變數不會這麽大。
5|從Life mission和家庭、社會期待談開去
以列 | Life mission是一个可以变的东西,但我们通常觉得还是要有一个life goal。目前对于我来说的life goal可能就是留在美国。前几天我跟一个美国小哥聊到这个话题,他说:“你留在美国的最好办法应该就是找个美国人结婚。”
我的人生规划很朴素,或许也很肤浅:我遇见了我喜爱的人,我希望能跟她成家,希望能跟她一起生活,做一辈子的爱人。但是这些都不是徒然就有的,我们需要有资本去支撑。有了资本和资历,我们才可能照顾好一个我们在乎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我就会考虑到一些非常琐碎的东西,比如说以后在哪里买房、在哪里工作,乃至生几个孩子。我跟我第一任女朋友当时就聊得挺多的。她是北京人,希望以后能留在北京。我们甚至讨论了要在北京的三环以内买房,然后生一个孩子,送到北京最好的国际学校读IB课程。当时我的想法很天真,但这段经历让我有了一种固化的想法,会觉得买房是刚需,结婚生子是刚需,给孩子在教育上的投入也是刚需。当时我就树立了一种不能算是激情、但比较固执的想法,就觉得我现在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以后生活做一个良好的铺垫。所以我觉得恋爱、结婚生子也算是对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也让我想到之前所讲到的资本,不管是金钱还是cultural capital,有很多东西会让我觉得挺难逾越,许多东西的实践都需要实际的过程,需要资本的积淀。我还是有那种比较传统的成家立业的决心的,我也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出人头地。我觉得这也是温州以及我们的家庭背景给我们的一种无法根除、融入血脉的思想观念。
无耽 | 讲到这里,社会环境对于我们的socialization,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驯化,其实并不仅限于所谓名校大学生了。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也是更极致地在感受社会角色在我们身上的一种轮换和融合。所谓社会期待,其实并不只是出于我们身上的某种标签,或出于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自己感受到的压力。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对家庭有较强的归属感。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衡量未来secure与否,或者是说要做出某种选择,可能多少都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一定的标化考虑。大学毕业要去找工作,从要养活自己到要成立自己的家庭,中间要考虑到薪资如何、能力如何等问题。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现实的社会化、驯化的过程。所谓名校在这一点上,可能可以带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更多选择。
作为温州人,聊到家庭话题我确实深有感受。在海外遇到老一辈的温州华侨时,我很能感受到他们的传统与保守。我自己因为家庭情况比较特殊,在观念上有点背离所谓的温州传统家庭观。处在一个alternative里,我会害怕家庭架构里对于个人的剥削和异化。或者是说我作为一个女生,如果我20多岁就要准备结婚生孩子,不说个人牺牲,但确实会觉得把自己困在了一个角色里面。我觉得后来我选择去国外“冒险”,不愿将自己的人生规划和职业导向或者家庭导向捆绑,是和跟这段成长经历有关的。但在国外或者名校感觉到的现实里,其实也有更多的对于“家庭观念”迷失和体会到的不确定性。说到在海外,温州人群体其实是更加浓缩。有意思的是,我现在能更强烈体会到的反而是温州人的“买房情怀”。这一点我以前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意识,直到我在欧洲开始要四处搬家。可能因为经济上的因素或者是说强烈的不安全感,就是说作为一个波西米亚青年在大城市里的漂泊之感,让我当时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豁然开朗,“以后想买房”的想法突然就有了。当然是因为以前天真了,以前可能比较抗拒的一些东西,似乎都慢慢地在年龄成长中逐渐被我接受并被消化。
另外一点,虽然肯定也有年龄焦虑,但是我希望自己还能默默地对这种年龄期待作出抵抗。我在去巴政前gap了一年,目前是身边同学里年龄算大的,以后也想在学生的身份里多待一会儿,可能也是因为不想让所谓的年龄期待束缚我,或者说让它捆绑我身上的社会标签或是所扮演的角色。我当时gap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以为我没考上大学或是只是一个无业游民。虽然这只是一年的差距,但我发现自己开始慢慢地不在乎年龄的概念,也相对能去消解这种年龄压力。我感觉在社会变化当中的社会期待其实也是在变化的,我们可以作出个人选择,也可以选择和社会期待相处的方式。

問笛 |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是如何以自己認同的方式存在(exist in a way that I identify with)。我覺得自己從小到大,在家庭、學校、社會給我的規訓當中,我一直在按照他們的標準去成為一個他們更認可、更喜歡的孩子。但是後來我發現是每個人有自己的標準,我沒有辦法成為一個讓所有人都認可或喜歡的人。不管是讀了那麽久的理科競賽,還是在大學期間還在想著要不要去學金融,在做了很多所謂為了迎合大人的事情之後,我真的會慢慢地去感受自己身體的變化。當我嘗試做一些自己不認同的事情時,我的身體通常是最清楚的,是抗拒的,那或許就不能再往這個方向勉強自己。
我在大陸看到的身邊的很多家庭,並不是很幸福和睦,因而我對於選擇商業精英的既定人生軌跡有許多質疑,對傳統的買車買房、成家立業的價值觀念也有很多不解。後來在學習神學時,我有幸領略Christian marriage的意義、愛的意義,才意識到那個non-religious的環境中一些問題的癥結所在。最近我發覺,一些過去讓我感到迷茫的問題,比如要不要進入business world工作,現在於我而言已經不是問題了。我想這是一個好跡象,是在成長的過程中保持思考、保持自我覺知。
如果你問剛入大學的我「為什麽選擇學習哲學」,我可能會回答說,哲學的學習給我提供了思考問題的更多perspectives,讓我能更好地抓住問題的本質、批判性地思考;而現在,如果你問我「為什麽選擇學習神學」,我會告訴你,神學的探索讓我接觸到了存在的更多spheres,思索如何在paradoxical and dialectical的意義上更深刻地活。

在某種意義上,我選擇去了香港讀哲學,後來又去了聖安讀神學,這一路是在嘗試掙脫傳統家庭、社會結構的牽引力。但我不久就意識到我跟他們的聯結是分不開的,我自己都是無法斷舍的。比如說,我不喜歡大陸的那種職業文化和人際客套,來到香港後在只有我一個大陸人的環境中實習,我的老板就坐在我旁邊,我不必對「領導」懷有畢恭畢敬的態度,但好像我還是整個company裏面最懂如何尊敬領導的一個人。在聖安的課堂和日常人際交流中,我時常感受到mindset的差異。我的一些回答和提問經常會讓對方驚訝或驚喜,這或許是出於我從小在一個non-religious的社會中長大,受到中國傳統觀念、文化及Eastern philosophy的影響。
無耽 | 謝謝問笛的分享。如此說來,我覺得我們在名校裏可能最想實現的是自己的 nurture的狀態,而不是說真的想在這裏成為某一種人。但同時,走到更大的世界也意味著自我期待的變化。或者從比較物質的角度來看,所謂說上名校改變人生、提供新的出路,其實更多是一種個人資本condition的重組。我們所面對的不確定性是不同的,從condition upgrade的角度來看,我們有可能接觸到多元的人和各色的履歷,在這種interaction當中,或許可以慢慢實現思維上的break free。
以列 | 再回到之前提的溫州人的傳統觀念。我不知道這適不適用於你們的父母,但在我父母的認知裏,他們會覺得我畢業以後應該回溫州創業。我不知道這是什麽想法,因為我當時常常告訴他們自己希望會留在美國。上海、杭州、北京這些城市的房價太貴了,我還房貸的話一還就是二三十年。進大廠難,工作和創業都難。我想如果作為獨生子留在國外的話,我估計我父母會生氣。但是我也沒有辦法,我是為自己而活。不過話說回來,如果能在溫州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糟糕的選擇。
無耽 | 這講得特別貼切,特別家庭期待這一塊。我們當然想在這個世界的某一個地方建立起自己的一個家,只是已然感受到溫州的小世界對我們來講並不是很compatible。
我之前也讀到一篇文章,講的是我國某個卷煙廠裏有很多流水線工人是海歸名校畢業,或者是中國的985、211名校的畢業生。當時我十分驚訝。後來聽朋友分析說,這是地方產業發展跟不上地方人才培養的現狀的體現。從就業期待上看,可能這些學生並不想做特別高強度的工作,但也需要考慮工作中社會福利保險的支持等,那麽這個地區可能最適合這些標化性考量的,就是國有企業的卷煙廠的工作。即使這份工作並不是很self-rewarding,或者是說有personal development的成分在,但是它符合了這樣一些人才在回鄉找工作時的一些硬性要求。我想,可能溫州對於我們來講也是一個這樣子的環境。但是對我們當然更加特殊的,總是有一種回歸家鄉的情結吧。只是目前這個情結也會與許多我所追求的和看重的東西相沖擊。我只能說在最近的幾年裏,我會希望在一個更多元的環境裏尋找自己,也更好地認識這個世界。

問笛 | 是的,很贊同。我覺得溫州對於我來說是我長大的故土,同時也是現在就很難回去的一個地方。很多時候都會意識到它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記。作為一個參加過高考的學生,在十八年體製教育之後,突然來到港大,新事物太多了,到現在每天還都會發現新東西。我自己有一顆很大的心,很喜歡與來自多元背景的人交流,因而感覺自己只要往外走一步,就會越走越遠,很難回頭了。加上自己讀哲學與神學,我對學術自由、宗教自由的重要性的感知也越來越明顯。去年五月,在香港待了八個月後我回了趟內地,感受到了非常強的reverse culture shock。我慢慢覺得這曾經是我的一個家,是一個我會稱為故鄉的地方,但它也只是一個我在物理意義上可以回去的地方。想法層面上,我已經很難在往回走了,一嘗試伸出觸角去交流,就時常碰到厚障壁。
當然我也知道,沒有父母的養育和經濟支持,沒有體製內的學校教育,我是走不到今天這一步的。沒有他們把我托舉起來,以及我自己努力地掂腳、嘗試起跳,我是沒有辦法來到今天這個平臺上的。我一直覺得自己特別幸運的是在18歲的時候來到了香港,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感知不同文化、不同社會、不同的mindsets,覺察以one-aspect story的角度看待彼此的弊端所在,看到誤解如何衍生出偏見、歧視與沖突。這並不是說我們能得出哪種社會製度更好的定論,而是說能看到更多選擇、思考什麽是自己更認同的。能走出來是我的privilege,我不想也不能炫耀自己的privilege,而是一直在敦促自己思考如何能pay back to society。就像柏拉圖所描繪與踐行的那樣,一個真正的philosopher應該在走出洞穴後回到洞穴,帶更多人走出去看到太陽。
無耽 | 這也讓我想到我在實習中的經歷。我在巴黎一個獨立新聞媒體實習,主要cover世界各地當地語種的新聞翻譯,而我是這裏的第一個中國人。當時許多稿件的選材和編輯過程中,我常能感到自己滿懷熱忱、想講出一些更original的故事,但最後還是被老板編輯成了可以說是響應主流偏見的文章。和老板同事聊天,還是能感受到他們的刻板印象和固定思維。我當時才意識到,即使是在巴黎一個這麽多元的地方,能接觸到各類信息的傳媒精英,還是無法很好地去講這個世界的故事。夾在跨文化交流和固有偏見之中,我發現自己對新聞的熱愛,更多的源於這種想去講好一個故事、想去表達的激情。
我在巴政學到的一個關於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理論,叫想象的共同體。可能我們這種所謂的身份認同,它是一種基於記憶、語言等想象出來的共同身份。在現實生活裏的人際交往裏,很多時候我們都是通過找共同點、在一些方面求同存異,來建立與人與人之間的聯系。
6|人生議題:我們想成為怎樣的人
無耽 | 我進入巴政以後,聽到的最多的就是「我想改變世界」,很多人會把來巴政讀書當成自己改變世界的計劃中的一部分。我記得我在我的 personal statement裏面也講到跨文化溝通,以及我期待的未來的中國。巴政有個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雙學位項目,我也聽過一些梗,講的是這個項目裏法國人和美國人的區別:入學時,大多數美國學生比較現實,似乎總會選擇學CS和Econ,以後會去做finance,打算進某銀行或某律所,很直白地說自己一年想賺多少美元;法國學生就天真地眨著眼睛,熱情澎湃地用他的法式英語說自己未來想解決難民問題,實現世界和平等等。但是,幾年之後,這批美國學生和法國學生畢業時,他們還是會走向趨同的職業道路。剛到法國念書時,我從飛機上下來,給海關看我的學校錄取證明。海關叔叔就一直給我豎大拇指,甚至給我鼓掌;坐出租車的時候,司機知道我是Science Po的,就再三用他的 broken English和我的broken French說,他覺得我未來前途一片大好。而在劍橋我感覺到的就是,無論你學習的是什麽科目,似乎所有background的人都願意往consulting,investment banking,finance或者law的方向走。
盡管巴政在法國社會受到諸多認可,我身邊也有法國人批評其精英氛圍實在是太「嚴重」了。巴政本身也有被解讀成法國院校美國化的一個產物。大多數法國和德國的院校,大學排名不一定特別高,但公立大學也能確保給平民子弟或者是寒門學子一些比較好的資源。但是當巴政真正跟國際教育接軌時,就形成了現在這樣的產物,為了QS rankings等國際教育上的互相承認,慢慢形成了教育產業化。一起形成的也有幫助你求職、找實習的一些機構構成的產業鏈,在我很多非常義憤填膺的法國同學口中也就是capitalization,我們也會開玩笑、就把一切都怪罪於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
問笛 | 這麽說來,不管你作為一個foreigner在法國社會如何打拼,還是有很多東西是很難融入、很難跨越的。
無耽 | 我覺得差不多是這樣的。這個問題對我而言,我不可能處在一個隔岸觀火的狀態。因為首先我並沒有融入這個圈子,其次我發現真正與社會接觸的首先通常是我的移民背景。我在國際教會,發覺很多人過的也就是平行的生活,就像在平行世界裏生活一樣。

以列 | 那天我和問笛在上海,我和她講起在美國讀高中時,一個同學和我說,二三十年後,我們同齡人或許會成為世界的領導人。如果這一天真的到來了,想想是挺震撼的,也在很大意義上不能「平行」了。無論是港大、巴政,還是藤校,它們都在培養政界、學術、體壇的精英。這個社會其實已經有了一個大致的結構,我們也應該慶幸能活在這樣的時代。
問笛| 對,我記得當時你和我說「We are competing against our peers.」我笑笑,說:「No. You are always competing against your will.」
我們今天聊了很多,從回首小城溫州、家庭背景,到反思名校與精英教育、思考未來的道路。我們自己和外界都對我們有不少的人生期待。但歸根結底,我們為何來到這裏、要前往何方,歸根結底還是出於我們的will,不論是自己最初的想法,還是不斷內化的外界欲求。
而我們的人生議題終究還是關於我們想成為怎樣的人。名校的大環境對我們的價值觀固然有深遠影響,這包括正面及負面作用。有時,我希望康奈爾沒有錄取你。倘若你去了一所專註學術的文理學院,或許能更堅定地走自己的科研道路。但是如果你從高中開始就認定自己在「competing against our peers」,那或許還要在「competing against your will」的道路上走更長的路,如是說來,我們的很多will也不能單向歸咎於名校給我們帶來的欲求與焦慮。
我想我們心裏的那顆種子是很重要的。土壤質地固然有所不同,但能結出什麽果實還是取決於種子本身。我們希望以怎樣的方式存在於世上,希望以怎樣的方式無名於世,抑或以怎樣的方式改變世界,的確取決於我們想成為怎樣的人,這也是為什麽我覺得your will matters。
文 | 無耽 李珵瑜 王好
圖 | 來自網絡
編輯 | 張宇軒
matter編輯|邢奕萱
圍爐 (ID:weilu_flame)

文中图片未经同意,请勿用作其他用途
欢迎您在文章下方评论,与围炉团队和其他读者交流讨论
欲了解围炉、阅读更多文章,请关注本公众号并在公众号页面点击相应菜单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