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兹别克斯坦与流亡俄罗斯人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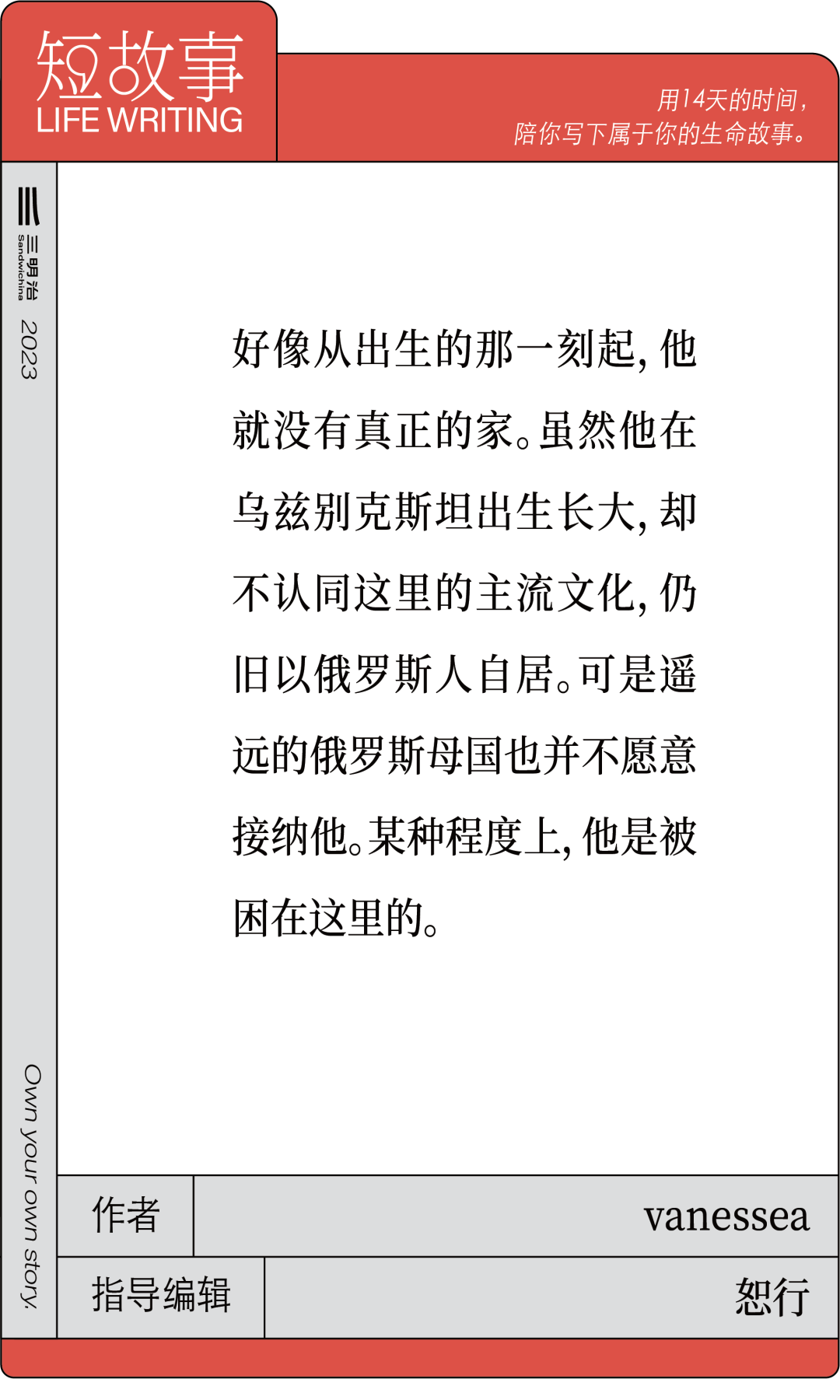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走进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青旅,我以为来到了俄罗斯。耳边全是俄语,眼下也尽是俄罗斯人。
这间青旅刚开业一年,设施配置完备,除了客厅与厨房,还设有一间办公室。公共空间里的绝大部分被俄罗斯人占领,更确切来讲是俄罗斯男人。客厅的电视上播着介绍格鲁吉亚的俄罗斯旅行节目,办公室里有人在用俄罗斯语开视频会议,而打开厨房的冰箱,里面堆满了切到半截的红肠,还有一锅没盖盖子的罗宋汤。
对于此番景象我不算毫无准备。预定网站上就有评论指出:“这家青旅整体很好,只是许多因为战争常住的人,不会讲英语也不愿意社交,影响气氛。”很显然,被指代的是俄罗斯人。他们来这里是为了躲避兵役的。
俄罗斯男人从外表上来讲绝对不是最有亲和力的群体。他们大部分块头不小,留着胡子,衣着算不上邋遢但也随意得有些过分。他们趿着拖鞋在楼道里穿梭,仿佛在宣示主场。我感受到作为闯入者的拘谨,但又夹杂着同情。青旅就算设施再完备也不是真正的家,六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只有一张床的个人空间。如果不是没有其他办法,应该没有人愿意长期住下来。
我很快发现,这群男人并没有看上去那般不可亲近。那两天我正好也有一些在线工作要完成,和他们共享着公共空间,很快就熟悉起来。其中和我最聊得来的是一个叫Artur的年轻人。
第一次见到Artur时,他坐在共享办公室里我旁边的位置,敲着键盘。他穿了一件北欧花纹的毛衣,胡子修理得很整齐,气质要比其他人文静些。
“你也是程序员吗?”他瞥到我打开的编程页面,伸过头来问。
“也算是,”我回答,“我是做研究的,关于人工智能。”
Artur曾在网上自学过人工智能的内容。我们讨论起基本的算法,他竟然对逻辑回归、随机森林和神经网络这些概念都了然于心。不过那只是为以后的机会做准备,现在还用不到。他目前是一名软件开发工程师,为一家俄罗斯公司远程工作。他的英语词汇量不大,但是表达能力很强,能将有限的词汇拼凑出准确的含义。
“你在这里有多久了?”我问Artur。
“在塔什干已经三个月了,之前还在阿拉木图住了三个月。”他回答。
去年九月底,俄罗斯开始面向全民征兵,Artur便立即申请护照准备离开。他在十月份成功去了哈萨克斯坦的城市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公民有三个月的免签,期限用完后他又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
在如今的世界阵营划分下,可供俄罗斯人选择的目的地极其有限。他们被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排斥,战争打响后很难再获取签证。由于国内的教育与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绝大部分俄罗斯人从未出过国,也几乎不会讲英语,因此很难在一个过于遥远的国度独自生存下来。地处中亚的前苏联国家乌兹别克斯坦成了最优选项之一,地理距离近,生活成本低,民众普遍会讲俄语,而且对俄罗斯公民无限期免签。
“像我这种情况被征兵的风险最大。”Artur解释他为何如此紧迫逃离。他离开兵营才不久,疫情之前的两年都在特种军部队服义务兵役。因为有作战经验,他极其有可能成为这轮征兵的入选者。可是在部队的经历让他深知俄军内部管理的混乱。他不愿意杀戮,更不想白白送死。
“我知道他们有多蠢,许多做法简直就是给敌人送子弹。”Artur说得有些激动。“我努力生活了二十多年,并不是为了一个这样的结局。”
今年初,Artur曾服役的连队中了埋伏,死了五十多个人。他曾经的指挥官也在其中。
他没有再往下说,换了个话题,邀请我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吃晚餐。那是另外两个俄罗斯人,年纪都比Artur稍大。两人在俄罗斯国内时曾分别是电工和交易员,后来都通过Artur找到了IT相关的远程岗位。他们和Artur在阿拉木图的青旅相识,然后结伴来到塔什干。
我们沿着塔什干的主干道往餐厅走。街上是清一色的乌兹别克产雪佛兰轿车,排出的尾气在空气中徘徊,从四周将我们环绕。乌兹别克政府为了保护本国造车厂,通过加关税的手段变相阻止外国汽车进口。
这并不是一座富有吸引力的城市,大部分建筑都是上世纪60年代地震后由苏联重建的,没有吸引人的伊斯兰古迹。来乌兹别克斯坦的游客大多只是借助塔什干的机场进出,并不会久留。我也不例外,明天就要去古城撒马尔罕。
我们走进一家餐厅,装修是乌兹别克式的富丽堂皇,当地人很喜欢闪闪发光的东西。Artur和朋友们经常来这里,对菜品很熟悉。我在一众乌兹别克特色中看到了俄罗斯红汤,猜想是苏联时期传过来的,指出来问他们味道如何。
“还不错,但是和俄罗斯当地的完全不同。”其中一个朋友回答。
“你应该去俄罗斯尝一尝正宗的。”另一个朋友补充。
我点头答应,又问他们是否想念俄罗斯的家,打算什么时候回去。没想到三人不约而同地否认。
“我现在是一个世界公民。”Artur郑重地说。他的确想念在俄罗斯的亲人,他的母亲和姐姐还留在家乡城市布鲁赛克。但他很享受现在的生活,再也不想回到那座小城。
他打开手机地图,将俄罗斯西北部放大,找到布鲁赛克,指给我看:“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里什么都没有,连条像样的河流都没有。”
刻板印象中的俄罗斯人爱喝白兰地,可Artur却对这家餐厅的草莓奶昔情有独钟。神奇的是,奶昔竟然也有酒精一般催吐心声的效果。
Artur讲起自己的故事。他出生在那座闭塞的小城,上了一个不怎么样的大学,学了一个没什么用的专业,曾经打着杂工,对未来充满迷茫。改变的开始在于疫情,他在家无聊便自学了编程。因为战争被迫离开俄罗斯后,他又找到了如今的远程工作,从普通软件工程师逐步做到小团队的主管,工资翻了三倍。半年前,他绝对想象不到今天能在这里,做着喜欢的工作,与世界各地的人交朋友。
“过去的这半年,真他么是个奇迹!”Artur感慨道,又吸了一口草莓奶昔。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许久,直到餐厅打烊来催我们离场。我们沿着同一条道路往回走。夜晚的塔什干要比白天时漂亮,道路两侧亮起了彩色的灯光,而拥挤的车流已经散去。

从塔什干到撒马尔罕的列车是苏联时期的遗产。我买票晚了些,只剩下价格稍高的一等座。座位很宽敞,黑色的皮质座椅厚实柔软,只是因岁月而敞开几道裂痕。
我旁边坐了一个金发女人,穿黑色高跟,涂淡紫色眼影。她把一盒乌兹别克糖果伸到我面前。“你要不要尝一个?”
我拿起一颗道谢,并顺势和她攀谈起来。她也是俄罗斯人,来参加律师行业大会。往年俄罗斯的律师行业会一般在欧美旅游城市举办,今年因为签证限制,只得选址在塔什干。会议刚结束,她要趁机到撒马尔罕玩两天。
我和她谈起在塔什干遇见的俄罗斯男人们。她并不避讳这个话题:“他们都是来逃兵役的吧?”
她的语气有一丝疏离,好像这件事和她全无关系。她的一些律师朋友在征兵之初也曾逃离俄罗斯,但最近回去了。俄罗斯政府近来重视起人才流失的问题,出台政策保护高端人才,确保他们不在征兵范围内。
“当然,这需要学历达到一定标准。”她又补充。在塔什干的青旅里,似乎并没有谁属于这一范畴。
列车沿着丝绸之路的方向行进,两侧是棉花田。因为是春天,田里还没结出棉花,但枝叶丰茂。那天的阳光格外好,衬得万物祥和又充满生机,让人觉得战争这个概念实在过于遥远。

我向来喜欢到每座城市的露天集市拜访。在撒马尔罕,我选择了比比哈努姆清真寺旁的大巴扎。路过一个卖香料的铺子,戴圆顶帽子的大叔叫住我讲起俄语。我猜出他在推销自己的商品,但还是比划着想弄明白具体内容。
“你需要帮助吗?”一个清秀的年轻人从旁边的铺子走过来,“我可以帮你翻译。”
他叫Roman,有精致的五官和纤长的四肢,披一件绣东亚花纹的棒球外套。
不出所料,大叔在介绍自己的香料,红色的可以煮汤,黄色的可以炖肉,全是当地天然原料,还可以免费送给我一小包试用......可我只是好奇闲逛,拿这些实在没用,只好道谢离开。
“我是俄罗斯人,不要因此而讨厌我。”这是离开香料铺后,Roman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当然知道,他刚刚帮我翻译过俄语。不过单从外表看,Roman和塔什干青旅里的俄罗斯人风格差异巨大,而且讲起英语来也没有半点俄罗斯口音,反而像美剧里走出来的人物。
我们走出巴扎,朝着雷吉斯坦广场的方向去。我得知Roman刚刚21岁,是个“环球”旅行者,靠在线教英语谋生。说是环球,其实只能在俄罗斯护照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过去的一年,他曾旅居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三天前刚落地乌兹别克斯坦。
他不是来躲避兵役的,我注意到他的左手少了两根手指,应该本来就不在征兵范围内,但他还是不愿意留在俄罗斯。战争最开始的两个月,他还没有出国,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孤立感令他窒息。国际品牌在俄罗斯的门店纷纷关张,一些在线平台也开始限制俄罗斯用户,就连开户地在俄罗斯的信用卡也全都被冻结。
“我现在用的是白俄罗斯的信用卡,我到那里住了一个月才取得开户资格。”Roman向我解释。他还想在乌兹别克斯坦再办一张卡,为此他也必须在这里再住上一段时间。
然而他离开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炮火。Roman在圣彼得堡出生长大,但几年前,因为克里米亚半岛的旅游业发展,他的父母投资了那里的房地产,举家搬到一所海边的房子。克里米亚虽然被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是乌克兰的领土,实际上却被俄罗斯占领。开战以来,乌克兰频繁往半岛上投射导弹,虽然突破不了俄罗斯的拦截系统,但还是会在半空中爆炸,发出震天的轰响。
我们终于走到了雷吉斯坦广场,这里曾是古代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广场由三座经学院组成,建筑表面以深蓝和松石绿为主色调,以金色点缀其中,绘制乌兹别克特色的动植物图腾。已经是傍晚,落日余晖给本就恢弘的穹顶更添一分光彩。
才相处一会儿,我就感觉到Roman是个不太寻常的人。一方面是近乎浮夸的热情,另一方面又是不谙世事的天真。他很容易对所见所闻大加赞叹,使用的形容词在我看来总有些过头。
我们来到乌鲁伯格经学院门口,Roman对着高耸的宣礼塔赞叹。一个穿制服的警卫来到我们身边,问我们愿不愿意登上塔顶。那里一般不对公众开放,但只要我们付10美元,他就可以破例带我们上去。
“真的么?这将是一次特别的体验。“Roman兴奋地看向我,以为我们是被选中的幸运儿。其实这不过是警卫赚外快的常规操作,大部分外国游客都会被询问。我早在旅行攻略里读过,但不想在此时戳破扫兴。我们如Roman所愿登了上去。
”我真的很开心认识你,虽然只是一个晚上,我觉得我们已经共同经历了很多。“下回到地面后,Roman对我说。如果是其他刚认识的男生说这种话,我会提起戒备心,但对于Roman却没有。一方面,他一贯用词夸张,而另一方面,我隐约感觉到他属于性少数人群。
我的猜测很快被证实。我们在广场前的台阶上坐下,讨论起当地的反同性恋法律。乌兹别克斯坦至今沿用苏联时期的法律,对同性交往处以上至三年的刑罚,而民间也有针对性少数人群的暴力事件发生。
”虽然如此,但我觉得没什么危险。“Roman的语气轻快,“乌兹别克人长得矮,我一只手就能把他们撂倒。“他应该是在开玩笑,但又好像带有一丝认真。
这种特殊的幽默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消受的。许多时候,我实在庆幸乌兹别克人不怎么听得懂英语。这样的感受在第二天达到了顶峰。
分别的时候,Roman约我第二天再去游览夏伊辛达陵墓群,可我已经与一个当地朋友约好,去探访一座传统村落。我向Roman表示他可以加入,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我们三人雇了一个司机,往深山里开。村子的名字叫吉兰,在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的边界上,居民全是塔吉克族人。那里的海拔很高,交通不方便,与外界几乎隔绝,还保留着最传统的房屋与生活方式。这是乌兹别克人都没怎么听说过的地方,但我在一本书里读到,便一直想前去探访。
盘旋的山路很不好走,但沿途的风景值得一路颠簸。到达一片开阔地带,司机停车让我们出去看。只见碧绿的山峦层叠,围绕着中央的一潭湖水。湖水是绿松石的颜色,泛着淡淡的光,静谧又深邃。
Roman向我展示他今天的服装,一件绣红色甲壳的绿毛衣:”这是自然的颜色,我特意为今天选的。”他跳到公路边的台子上,让我以景色为背景拍照,摆出一连串戏剧化的表情和动作,引得司机和朋友都有些不自在。朋友曾经在国外生活十几年,是乌兹别克人中相当开放的,但还是难免对Roman的一些行为感到不适。
车又开了许久才到村子里,司机预计车程两个半小时,但最终用了四个小时还不止。村里的房子大多是尘土的颜色,由泥浆和着草木砌成,只有门窗框刷成鲜亮的蓝色。我们沿着贯通全村的泥土小路走,经过在路边琢食的公鸡,听见牛圈里传来的哞叫,也碰见骑驴的老人。驴子身上披的花布格外惹眼,蓝色条纹,印大朵红花。
村民没怎么见过外国人,对我们很好奇,但又大多害羞,就躲在窗户后面看。父母带着孩子,一家人一起观望。Roman发现时就笑着朝他们挥手,对方往往迟疑一下,也笑起来挥手回应。
路过一间种苹果树的院子,男主人邀请我们进屋喝茶。这是当地的传统,对远道而来的客人要尽最大努力招待,不管是否相识。这不是我们在这个村子里第一次被邀请,但这家男主人的确是最热情的,我们跟着他进了房子。
客厅的陈设很简单,地上铺一张花地毯,中间摆一张炕桌。男主人和我们讲话,他的妻子负责端茶。不只有茶,还有馕、干果、蛋糕、烤包子和自家种的苹果。正值封斋期间,主人和朋友在太阳落山前都不能进食,就只看着我和Roman吃。
他们三人在一起说俄罗斯语,不时会给我翻译几句,但大部分内容我还是听不懂,只能观察他们的表情。Roman很有表达欲,同男主人热情交谈,面色愉悦,但突然就做出夸张的惊恐状,双手举在胸前,把身子往后缩。后来朋友告诉我,那是因为主人邀请我们晚上留下来吃开斋饭,烤全羊,而Roman是素食主义者。朋友似乎对Roman如此反应颇有微词。
男主人倒是没表示出来不悦,继续热情招待,临走的时候还给我们装了满满一袋苹果。“愿真主保佑你们。”他在道别的时候祝福我们。
Roman很想回应这份好意,决定以自己的方式也进行祝福。他曾和我说过在学习占星和魔法,已经取得二级巫师的资格。此时他决定给这家人以巫术的祝福,念着英文咒语,转着圈子上下比划。可以看出来朋友十分希望能阻止他,而我则庆幸咒语是英文的,这家人都听不懂。
从村子回到撒马尔罕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但我还是和Roman一起去吃了晚饭。我第二天就要离开撒马尔罕,继续向西,Roman执意要为我送行。他特意找了一家能看到雷吉斯坦广场夜景的餐厅。我们在炫丽灯光的映衬下吃一种叫manti的当地食物,造型类似粗犷版的小笼包。Roman要了把牛肉馅替换成南瓜的素食版。
我问Roman今后的计划是怎样的。他说自己也打算去乌兹别克斯坦的另外几座城市,等成功在银行开户以后再去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再然后呢?”我又问。我好奇他的“环球”旅行打算进行多久。
“再然后我还是希望能完成本科学位。”Roman的语气竟然严肃起来,一改往常的跳脱。
四年以前,他曾在加拿大留学,念新闻与传播专业,但大一还没有念完就遭遇疫情,学业被迫中断。他就是在那段时间开始做在线英语老师的,慢慢积累起了稳定的客户群。他也逐渐想明白这个专业不适合自己,打算换个专业重新申请大学。可是等到疫情结束他重新申请,俄乌战争开始了。已经有一所法国大学和一所波兰大学分别因为签证限制拒绝他。
“我是肯定不会留在俄罗斯读大学的,”Roman解释,“以后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都不会承认俄罗斯的文凭。”
目前他又申请了一所奥地利的大学,还在等消息。“学校在阿尔卑斯,抬头就能望见雪山,你要来找我旅行啊。”他的语气里满是希望。“好啊。”我笑着回答。Roman兴奋起来,又开始计划去巴黎找我的行程。
旅行中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和另一位旅行者萍水相逢,共度几天时光,热切地约定再次见面,但实际上再也不会见面。我早已适应这样的游戏规则,只是偶尔反思自己的虚伪,可Roman似乎要认真得多。
分别后我还总是收到他的语音消息,多次重申我们的“友谊”,同当面交谈时一样,语速飞快,情感充沛。我的回复越来越简短,他也就慢慢停了下来。后来他的instagram动态里又出现了新的“朋友”。照片里他的笑容很灿烂,可我却感受到孤独,掩藏在表面喧嚣之下。过分热情又夸张的言谈是保护色,而一个又一个临时“朋友”则是消解的方式。

我乘着拥挤又破旧的夜班火车来到希瓦,这次行程中最靠西的城市。希瓦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埋藏在卡拉库姆沙漠里,曾是九死一生之地,如今却被开发成一处别致的旅游景点。这里的古建筑丰富而集中,可是由于位置实在偏远,交通网络又落后,大部分游客并不会到访。
即使如此,俄罗斯人的身影还是随处可见。他们信奉东正教,此时正是复活节假期。对俄罗斯的普通游客来讲,因为签证限制,乌兹别克斯坦也是热门目的地。他们穿着从纪念品商店买来的传统服饰,穿梭在古城的大街小巷。男人戴绣花的穆斯林圆顶帽,女人穿鲜艳的扎染真丝长袍。这些服饰穿戴到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身上,竟然也不显得太违和。
毕竟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的纠缠由来已久,早在沙皇时期就被俄罗斯人征服,后来又被纳入苏联。希瓦古城也正是在苏联时期演变成如今的模样。苏联政府秉着“个人服从集体”的原则,将内城的居民全部搬迁至城墙外,只留下经营民宿和商店的人家,打造出一个露天博物馆。
在同一套行事逻辑下,大批俄罗斯人也在苏联时期被安排到乌兹别克斯坦落户,发展当地农、工、文化等产业。这是联邦内对人力资源进行整体分配的一种方式。苏联解体以后,其中的大部分回了俄罗斯,但也留下一批滞留者,大多聚居在塔什干。我接下来要去见的就是其中一位。

在乌兹比克斯坦的行程已接近尾声,我要回首都塔什干再住一天,从那里乘飞机离开。我在沙发客网站上联系了Yura。沙发客是一个在线平台,帮旅行者和愿意免费提供住宿的当地人建立联系,相当于没有金钱交换的airbnb。我不是那么需要一个免费住处,只是被Yura简介里的摄影项目吸引,发送了借住请求。
Yura是俄罗斯人,但是在塔什干出生长大,是一个胶片摄影师,正在进行一个关于世界各地旅行者的摄影项目。他接待来塔什干的旅行者,为他们拍摄肖像,并让每个人用母语写下一封讲述自己故事的信,希望最终集结成摄影集。从四年前开始,他已经招待了近百位旅行者,而这些旅行者也都在他的页面上留下了好评。他很快通过了我的请求,并邀请我参与他的项目。
“沙发客的目不是免费住宿,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希望你理解这一点。”他特地在信息里向我强调。我表示同意。乌兹别克斯坦物价低廉,住一晚青旅只要十美元左右,我使用沙发客本来就是为了与当地人交流。不过后来我发现,这种交流并没有我设想中的轻松。
我跟着谷歌地图找到了Yura的住处。那是一片老式苏联街区,堆叠着一排又一排的灰褐色筒子楼。走进Yura住的那一栋,空气里弥漫着阴冷的霉味,楼道里的墙皮一块块开裂脱落,地面和台阶都是裸露的水泥,沾染着不知多久没被清理过的污渍。
来给我开门的是一个高大的男人,穿着一件松垮的白色背心和同样不合身的牛仔裤,给人不修边幅的感觉。两撇复古的小胡子,让他看上去像是苏联老电影里走出来的喜剧人物。公寓的陈设也同样像是苏联电影里的场景,不论家具还是摆件都像是从旧货市场上淘来的苏联老物件,只有客厅墙上挂的民族花纹地毯透露出一点乌兹别克风情。
“我刚做好了早饭,等你一起吃。”Yura热情地邀请我进门。因为面积限制,房间里并没有正式的餐桌。我们坐在阳台的折叠小桌上吃类似酱油的当地调料制作的炒面,配上生的青萝卜片。“我本来想加一点鸡蛋,但是家里正巧没有了。”他有点抱歉地说。
阳台是封闭的,连着客厅,除了折叠小桌,还摆一台木质三脚架,上面固定着一台胶片摄像机。三脚架对面放了一把小凳子,大概是给被拍摄者坐的。一间简陋的摄影工作室在此设立。
公寓只有一间卧室,我要住在客厅的沙发上。沙发也上了年头,破旧的布面有几处露了陷,能看见内里的填充物。Yura解释,这是他的宠物狗Chandra的破坏成果。Chandra是一条看不出品种的黑色小狗,很怕生人,在我进门的时候一直冲我叫。但Yura保证她很快就会对我亲和起来,提议吃完早餐后一起去遛狗。
我们带着Chandra来到小区的街心花园,遇见的其他遛狗人Yura都认识,总会打上两句招呼。“你有没有发现遛狗的全是俄罗斯人?”Yura问我。他解释说乌兹别克人因为宗教原因,不喜欢狗,认为他们是不洁的生物。虽然牵了绳子也带了嘴套,但还是有人看见Chandra时会躲闪。Yura于是一遍又一遍地用俄语重复:“我的狗是一条好狗,不伤人的。”
除此之外,Yura对乌兹别克人的一些其他做法也不甚认同。四月底塔什干的太阳已经有一些狠毒,路边却没有几颗遮阴的大树,只剩下许多光秃秃的树干。Yura说乌兹别克人很喜欢砍树,拿来卖钱,苏联时期种的树后来都被新政府砍了。“乌兹别克人没有长远发展的眼光。”
Yura还讲到乌兹别克文化中对女性的禁锢。这里的传统房屋有点像四合院,围着中间的小院子在四面搭建。所有窗户都在朝向院子的一面。“朝向街道是不能开窗子的,因为他们害怕家里的女人被看见。”
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不同种族之间的融合。当地穆斯林女性是绝不会外嫁给俄罗斯人的,也只有极少数乌兹别克男人会娶俄罗斯女人。即使世代生活在此,俄罗斯人也不会学习乌兹别克语,生活圈子局限在俄罗斯人群体内部,并失去在政府等公共机构的工作机会。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回俄罗斯生活呢?“我问出来一个有点天真的问题。
Yura回答:”没有那么简单。“他的家族在好几代人之前就迁移到乌兹别克斯坦。他在这里出生长大,只有乌兹别克国籍,去俄罗斯要申请签证,而且条件苛刻。他二十出头的时候曾尝试到莫斯科打工。那是一段地狱一般的日子,每天要像奴隶一样工作,但是工资很低,生活成本又高,他最终决定回到塔什干。
好像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真正的家。虽然他在乌兹别克斯坦出生长大,却不认同这里的主流文化,仍旧以俄罗斯人自居。可是遥远的俄罗斯母国也并不愿意接纳他。某种程度上,他是被困在这里的。
”那你的祖先是为什么来乌兹别克斯坦的?“
”我只知道他们是在苏联时期过来的,具体为什么我父母没有告诉过我。“
看我有些惊讶,他又解释:”我的父母从来不和我讲这种事,他们只是尽力生活。“
遛完狗,Yura接到父亲的电话,叫他过去一趟,说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不方便在电话上讲。他决定带上我同去,顺路给我展示塔什干的城市风貌。路过院子里的一辆老爷车,他停下来指给我看。他说这辆车属于他,但是今天不开,要乘公交。其实我很怀疑这辆看起来快要散架的汽车是否还能开动。
Yura父母的房子在另一区域的筒子楼里,楼道的味道更刺鼻,房间的规格也更狭小。他的父亲拄着拐杖来开门,我在厨房里等待,听他们在客厅里争执。十分钟之后我们就离开了。
原来Yura的父亲丢了价值相当于100美元的现金,认为是被Yura拿走的,于是叫他过来盘问。100美元是个大数目,他的退休金每月也只有200多美元。Yura解释说他没有拿过,估计是被患有阿尔滋海默症的母亲放到了哪里。父亲不愿意相信,两人的争执没有结果。
Yura的父亲一直看不上这个“不务正业”的摄影师儿子。母亲对他要更加疼爱,但如今深受阿尔滋海默症的折磨。遛狗的时候Yura就已经接到母亲的好几个电话,每次都是哭诉弄丢了刚领的退休金。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耐心解释,退休金不是弄丢了,只是还没到该领的日子。
我有点想离开了。我虽然一直乐于体验生活,可这样的生活实在过于沉重,而Yura又多次强调“沙发客重在人与人的交流,不是一个免费的住所”,让我不敢自行安排活动,只能继续跟着Yura完成他的日常事务。他说有一个德国客人曾经生硬地甩开他,要去市中心观光,回来以后就被他礼貌地请离了。
我能够理解Yura,他被困在这座城市,困在这样的生活里,太需要一个出口了。和世界各地旅行者交流是他排解压抑的方式。可是经过长途旅行的我此刻也非常疲惫,无力再进行他需要的交流。
让我打定主意离开的是厨房里的蟑螂。我原本只发现了一只,叫Yura来确认。他不以为意地捏起来,扔到地上,随意踩了几脚,也不去处理尸骸。他说蟑螂不会伤人的,叫我不要怕。他曾经尝试清理过,可是整栋楼都有问题,他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发现灶台上的黑色污点全都是蟑螂的尸体,我原本以为只是油渍。
我找了一个借口,告诉Yura我要提前离开,不在这里过夜了,但还是对他的摄影项目感兴趣,愿意参与。他挽留了一会儿便也同意,开始给我展示他的摄影作品,
作品里人像是黑白的,用古老的胶片照相机拍摄。Yura将卫生间用作暗室,冲洗胶片,再扫描到电脑里保存。在我之前,他已经为81位旅行者拍摄了肖像。照片都未经过美化,将人物脸上的毛孔细纹,和眼底的期盼不安都悉数保留。我看得很入迷。
Yura展示照片的时候也会一并讲述对每一位客人的回忆,像小孩子清点珍宝一样认真。他特意在一个男人的照片上多停留了一会儿,那是他之前接待过的唯一一位中国人,是一位计划横跨亚欧大陆的骑行者。他接待过的大部分客人都是这样的硬核沙发客。
终于到了拍摄时间。Yura播放起摇滚乐,把天花板上的白炽灯关掉,打开墙上的红色装饰串灯。房间里的气氛马上变了,陈旧的家具竟然有了前卫的风格,杂乱的摆设也变得鲜活而富有艺术气息。Yura的状态也和白天截然不同,他哼着摇滚的调子准备胶片,布置场景,调整相机,好像甩掉了日常生活的重压。
Yura用的胶片照相机是机械的,曝光时间要一分钟左右,并且需要手动输送光源。他叫我眼睛看着镜头,双手放在膝盖上,不要动。他按下快门,随后来到我这一侧,环绕着我转动光圈,好像在举行一场神圣的仪式。我在炫目的灯光下努力睁开双眼,余光瞥到Yura,他的眼里也有一种类似于光的东西。
夜色已经很深了,我向Yura道谢离开,打算在机场附近找个酒店睡一晚。明天我将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去往下一个目的地。我随时可以抽身离开,但更多的人没有这样的幸运。
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往机场的方向去。司机讲起俄罗斯语,我还是听不懂。可是那片我从未踏足的土地,已经不再显得那么陌生。人类命运之间的共性总是要比差异大。不管是作为一个辉煌时代的余烬,还是大国博弈的牺牲品,总是个体命运在时代的角落里被悄然改写。
一排又一排的筒子楼很快就在夜色中消失。路上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除了汽车的远光灯,照向幽暗无底的远方。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
阅读更多作者作品






支持三明治,让更多个体表达与独立创作被看见。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