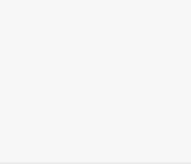畏死
哲学专业的第一门课永远是逻辑学,而逻辑学的第一课永远从这样一个经典的三段论开始:
- 人都是有死的(mortal)。
- 苏格拉底是人。
- 因此,苏格拉底是有死的。
逻辑上固然白水一样清晰,大前提却有得可玩味:将人理解为有死的存在是在说什么?
神明,不管存不存在,假设其存在,大抵是不死的。石头土块自然也谈不上死。但是比我们低级的动植物,至少明面上看也是会死的。然而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的死是特殊的,因为——1)只有人类能够理解死,动物至多是直观地意识到我们称之为死亡的这件事,它们没法将死亡概念化并对其进行思考;2)只有人类会担忧死,动物至多是恐惧,而人类会因为死亡而操心和预先筹划;3)只有人类因为死亡失去的最多,人类对未来有期盼,对过去有怀念,对此时此刻有知道自己此时此刻在此地活着的认知,而动物至多有痛苦和舒适以及最基本的情绪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死亡是只有人类才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人都躲避不掉的问题。但是即使我们在内心深处都知道这一点,似乎人类却往往试图逃避死亡这件事,比如我们的办公楼电梯不仅没有四层,连十四层都没有;比如我们会讲究在什么日子、什么场合、当着老人或者小孩不要提到死亡,好像我们不说,死亡就不存在一样。这种日常的对于死亡的逃避,在我看来,有三个层面上的问题:
1)首先,这是一种懒惰,也就是说,一个人宁愿让自己懵懂一点,也不愿意思考真正艰难的问题;这同样是一种懦弱,也就是说,一个人宁愿给自己构造一个明知自欺欺人的环境,也不愿意面对令人不适的现实。
2)除此之外还是一种惋惜,因为一个避讳死亡的人不仅坐失了好好安排身后之事的机会,正如我们后面会讨论的,还放弃了好好打理生前之事的机会。
3)日常对死亡的逃避还令人难以在突如其来不得不面对死亡的时候从容不迫地面对之,要么过度恐慌,要么过度轻率,皆非理性的人所当为。
克服这些弱点,正是需要一个人训练自己思考死亡。
那么让我们仔细思考死亡,首先让我们思考为什么我们如此拒斥和恐惧死亡,为什么死亡是一件坏事情。
- 有一个“我”。
- 这个“我”会死掉。
- 死掉对于“我”来说是不好的。
如果不是“我”,是随便哪个人死掉,我顶多感觉惋惜,不会恐惧;如果我不会死的,那么当然死亡是别人的事情,与我无关,我也不会恐惧;最后,如果死亡不是一件坏事,甚至是一件好事,那么我也没有理由恐惧。这三个命题连贯地构成了我恐惧死亡的原因,缺一不可。当然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直观地觉得,这都是废话,当然如此——正因这样,绝大多数人才都会恐惧死亡,而尽管古往今来很多哲学流派试图超越死亡,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看法是正确的。不过还是让我们一一分析一下他们都提出了哪些试图让我们“无有恐怖”的解决方案。
首先是否定命题1,否定“我”的存在。这个传统向上可以追溯到原始佛教,最近的代表人物则是英国哲学家Derek Parfit,他们试图通过种种论证让我们相信,根本就不存在值得为之大费苦心的“我”这么一回事,如此一来,对于死亡的恐惧也就可以消除或者至少减轻。论证可以列举很多,尤其佛教徒可能很可以讲不少,我来举这么个例子:
1)想象有一组传送机,在北京的你走进去,它会实时记录下你的每一个分子、原子的状态,然后摧毁你的每一个细胞;与此同时,在伦敦有一台机器,可以在一瞬间重造你的每一个细胞,其中的每一个分子原子的状态都延续了前一时刻北京的相应状态;从体验上来说,在伦敦走出传送机的人任何特征都跟在北京走进传送机的人一模一样,甚至他会感觉自己前一刻的思考、感受、记忆都是连贯的。通过这种成熟技术,你实现了每天随时在北京和伦敦之间穿梭,好像哆啦A梦的任意门一样。那么,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每天穿梭来穿梭去的你,是不是同一个你呢?听起来似乎问题不大。
2)想象某一天这套机器出了个故障,把你从北京运到伦敦的时候,在伦敦已经再造出一个人走出体验机了,但是北京这边的机器没能把这句身体摧毁掉,走进去的人原封不动从同一扇门走出来了,眼睁睁看着在伦敦又多了一个“自己”。过一会儿机器修好了,工作人员走过来跟在北京的这个人说,“请您回到机器中,现在需要把您的每一个细胞都摧毁掉。”你说,“这不是杀人吗?”工作人员说,“不是的,我们谁也不会杀,你也不会这样死掉,你已经在上海了。”你说,“凭什么你说我在伦敦我就在伦敦?我此时此刻就分明在北京。”工作人员说,“您之前同意使用这台机器的时候怎么就没有觉得有一个人会被杀掉并且这个人就是您自己呢?”你(按照一个哲学家会建议的方式)说,“我刚刚是以心理活动连续性为依据的,但是至少我依然保留着我的心理活动,所以我还是我,不能被杀掉。”工作人员说,“不用担心,我们提供成熟的解决方案,我们会暂时给在北京的这句身体植入一段其他人的记忆,让这里的这堆脑细胞以为自己是另一个人,然后再消灭掉这些细胞。”
我们的直觉似乎陷入了紊乱,不论是心理活动的连续性还是物质身体的连续性都无法用来定义在我活着的时候持续存在而死后就不再存在的“我”究竟是什么。相关的哲学流派据此建议,既然我们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当我们恐惧死亡的时候都搞不清究竟是谁死了,那么我们应当可以看开一些,这句身体死掉这件事应当并不比随便哪一具身体死掉更让我恐惧。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买账,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论证至少有以下几个严重的问题:
首先,我没法用严格精确的语言定义一件事物,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存在,或者我们可以当它不存在。举个例子,当代许多理论认为,性别是无法被明确定义的,不论是看染色体还是看性征还是看身份认同还是什么别的,都可以找到反例。这件事有争议,不过即使我们认可这个论点,并不意味着从此上卫生间就可以混用了,性别依然有着在生活中足够直观且重要的意义。
其次,当我们在讨论对死亡的恐惧的语境中说“有一个‘我’”的时候,这并不是在做一个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论断——“存在一个东西叫做‘我’”,而是更多地在做一个现象学报告——“我感觉有一个‘我’”。即使上述论证可以成功地证明“我”真的不存在(正如有些学者真的在理论上认为性别不存在),也不意味着我不能合法且有意义地说“我依然感觉有一个‘我’”。二者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并且,在一种笛卡尔式的意义上,如果我可以说“我感觉有一个‘我’”,那么至少存在者一个什么东西,不管你叫它什么,在感觉着“我”的存在,即使这种感觉如论家所说是一种颠倒梦想。这就是所谓的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既然我在感受着我的存在、思考者我是否存在,那么就一定有什么存在着,否则是谁在感受和思考呢?
最后,在实践层面上,即使我可以真的合理地相信“我”不存在并且我不应该感觉“我”存在,这并不解决我们的问题——不管应该不应该合理不合理,我就是感觉我存在并且我会死。这就好像一个人头疼,所有最好的医生用尽一切手段证明他脑子里的每一处、任何一个细胞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人依然头疼,他没法证明自己头疼,没法让别人理解自己的头疼,他甚至可能完全相信自己没有任何健康问题,但是这些都没法改变他感到头疼的事实。正如“看开点”无法解决这个人的头疼,“看开点”也无法解决我们感到我自己存在并且会死这个事实。
第二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否定命题2,也就是承认“我”的存在但是否定“我”会死。这里当然包括很多种可能,比如有人许诺天国的永生,有人讨论不尽的轮回,还有人寄希望于现世飞升。基本上可以说,人类所有的宗教狂热或者宗教式的狂热都源于通过否定或者“超越”死亡来解脱于个人此生必死的苦恼。
我不想去挨个儿纠结这里面的细节,但是我想关心的是这些方案是否真的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当然或许一定的慰藉作用是会有的,就连身故责任给付都能对于死亡的悲怆和恐怖起到一些慰藉作用,何况宗教呢,毕竟是几千年优胜劣汰下来专业提供麻痹作用的东西,镇痛的劲道还是很强的。但是镇痛并不是解决问题。让我们分几类来谈——
首先是永生的问题。如果给你一枚药丸,吃下去可以活到自己想要的寿数再死,那么我猜大多数人都会是想要的;但是如果是一枚可以彻底让人不死的药丸,恐怕还是应该慎重考虑。至少你应该考虑考虑,在未来无限的时间中,你都准备干点什么呢?当然你可以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做事,但是请不要误解永恒的含义——那是超越我们想象极限的,那意味着当你已经把所有人类可能做和不可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之后,依然有无限的时间在等着你。我们知道,对于π来说,不论你取它的前多少位数,在这之后,所取的这部分都会重复出现无穷多次,这大概就是永恒的恐怖。这就是古希腊人为什么会一边叹息人生短暂一方面把“不死”称为一种最恐怖的诅咒。
其次是轮回的问题。实际上所有讲轮回的宗教,其主旨都是告诉你如何超越生生死死的循环,因为轮回实在不是什么能给人安慰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你在此世所经受的所有对于生老病死的烦恼,都会被未来无穷的你自己(不论是在什么意义上)重复承受,而除非彻底跳出其外,否则死亡的恐惧不会随着一个你变成一串香肠一样不计其数的你就消失,只会无限倍增。只有中国的文学家会去讴歌“生生世世为夫妇”,所幸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否则会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不论你此时此刻是多么真心实意地爱对方。
最后是关于好人上天堂的问题,对于一些极端的方案来说,天堂的永福是超越前面所说的永生之痛苦而无法为此世之人想象的,只有等人升了天堂才能理解。对于这件事我其实没什么可说的,既没有信得过的证据,又没有讲得通的论证,有人愿意信,那就信呗。有一位神学家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我相信,正因为荒谬”。这确实是宗教的基本精神,说到底它是要去信的,而哲学的理性批判揭露的种种荒谬性对于一些信徒而言恰恰解释了为什么要去信仰,也即“人类的理性已经不够用了,剩下的只能靠信仰去解决”——尽管在我个人看来,这只说明它已经荒谬到甚至放弃诉诸于理性而只能号召人去信仰的地步了。
让我们转向第三大类回应,否定命题3,即认为我确确实实会死,但是这并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分成几层来处理。
第一层是一种最流俗的观点,据说来自古希腊的伊壁鸠鲁但是实际上很可能是一种误解,这一派的说法可能出乎意料地简洁——死亡根本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件事,因为当死亡发生时我们已经不在了,既然如此,死亡怎么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坏事呢?某种意义上这话说得不无道理,比如一个通过跳楼解决问题的人,不论跳楼这件事的后果需要别人如何承担,这些都已经与他没有关系了。对于这个观点,同样简洁并且同样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尽管死亡的发生本身对于我来说可能并不再是一件事,但是死亡的后果对于还活着的我来说,却是一件确实值得担忧的事情,因为死亡会让我对未来的所有预期全部清零,会剥夺原本可以对我敞开的所有可能性,会让我继续守候我所珍视的人和事变得不可能。这就像是,如果你的基金跌了,你不可能说“因为当一笔钱已经赔掉了的时候,就都已经不属于我了,所以赔钱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
第二层可能更接近伊壁鸠鲁的真实意思,他认为,如果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无以复加的完美,比如我们是德性上完美无缺并且已经不假外物地过上完全快乐的生活的人,既然我们的生活已经无以复加地好了,那么今天死明天死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差异,所以对于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来说,死亡根本不算件事儿——其他人则会继续恐惧死亡,而且因为他们不够完美,所以他们很有理由感到恐惧。这个说法会有两个问题。首先,它对我们这些凡人来说基本没什么用,我们毕竟不可能做到完全无欲无求还能完美地快乐,但是这当然是一个虽然实践上无比重要但是理论上比较次要的批判。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在于,伊壁鸠鲁式的这种完美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一个人,即使自己的生活充分完美了,他依然有可能会关爱其他人,那些因为不够完美而恐惧于死亡的人。而一旦一个人因为关爱那些忧惧死亡的人而感到不悦(否则就不叫真的关心,顶多是看着),那么他的生活就不再是完美地无可附加地快乐了。因此一个人要想让自己脱离死亡的恐惧,就只能选择对于所有尚未脱离死亡恐惧的人完全漠不关心——这恐怕不是一个我们愿意承受的代价。
第三层可能比较接近庄子的看法,那就是死亡让我们周全,并且让我们得以从生的劳累中解脱出来。庄子曰:“以生为首,以死为尻”,又曰:“大块劳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他认为,正确地认识死亡,意味着需要理解人生没有死亡作为终结是不圆满的,而且经过劬劳的一生之后,我们也应当能得到安歇。但是这个理解听起来很浪漫,却有很大的问题:首先,安歇通常只有在你想安歇,并且安歇之后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干的情况下,才是好的;让你永久休假,这往往不是什么好事。其次,更重要地,如果死亡真的如此浪漫安适,首先需要有一个什么东西能够去经历这种安适,能够去享受这种休息,然而这对于一般的休息成立,对于死亡却不成立,不要忘记,我已经没了,讨论休息是没有意义的。叔本华的一个解释也与此有关,他认为生存是如此痛苦,以至于只有通过不再生存才能少一点痛苦,而对于个人而言死亡可以将人拯救出痛苦。然而苦与乐是对于存在着的人才有意义,超出这个前提,“无痛”何以比较好,会陷入“究竟是对于谁比较好”的问题。或许我们至少可以承认,在一些情况下,死亡可以避免活着的人承受更多的痛苦,但是这更多是在讨论作为特例的安乐死,而不是普遍的死亡本身。第三,生命固然莫不以死亡为终结,这种必然的终结在何种意义上是好的却并不明确。
第四层应当也是一个古老的看法,最近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Bernard Williams,威廉斯认为,如果我们意识到永生的可悲和恐怖,正如我先前讲的那样,那么我们应当意识到,有死性mortality是一种恩赐而非诅咒,因为正是我们终将死亡这一点把我们拯救出了永生的恐怖前景之中。伊壁鸠鲁也讨论过这一论点,他认为那些妄图通过相信自己的生命会延续下去或者灵魂会继续存在而获得舒适感的人,实际上没有琢磨清楚;一旦人意识到灵魂不死是多么可怕,就会感到恰恰是我们会死亡这一事实令人觉得无比轻松,我们终于可以逃离literally无期徒刑了。我实际上非常同意这个看法,但是我并不认为这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并且实际上我认为威廉斯意识到了问题,而伊壁鸠鲁没有意识到。请注意,威廉斯讨论的是mortality作为一种大好事,而不是death作为一种大好事。我终将死亡这一性质是一个好的性质,并不意味着当死亡发生时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一个性质跟一个事件在范畴上都不是同一类,伊壁鸠鲁将这二者混为一谈,是犯了范畴错误。尽管威廉斯认为,对于有死性的这种深刻认识有助于让人减少因为怅望永生而产生的恐惧,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可以消除死亡这件事本身带来的恐惧。
这就把我们打回了原点,对于三个命题,我们都没有什么好的反驳或者绕过的方式,所以不得不继续面对令人恐惧的死亡。我们之前提到,死亡对于我来说不好的地方在于:首先,死亡会剥夺我的未来,我未来的所有可能性,和我如果不死可以拥有或保持的东西。其次,死亡也会剥夺我的过去,因为过往的一切都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当我死掉的时候,这些就都烟消云散了。最后,死亡将我置于一种对于不可知的恐惧中,这种不可知并不一定是因为我假设还有一个死后世界而我不知道有什么等着我,死亡的不可知完全可能建立在承认死后就是“无”的基础上——“无”恰恰是最神秘幽暗的,我们根本不可能想象“我”不存在,不论我们闭上眼睛设想出一副这样的图景,我们都已经预设了一个安置这幅图景的时空背景,而这个背景中总是有一个隐藏着的视角。脱离某种“我”的视角,时空背景不可能成立,任何图景的想象也都不可能成立,所以对于“我”不存在的情景,我们根本上不可能想象。
海德格尔正确地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有意识无意识地逃避死亡,让自己埋头在各种需要操心的事情中沉沦以至于没有时间和心思去思考死亡,这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必死性会将人从熟悉的世界中连根拔起,摧毁所有的意义大厦,将人抛入一片“畏”之中。当你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逃避性、不可知性和巨大的损失的时候,你在一生中想要的一切都变得苍白无力,它们都没法让你超越死亡,没法让你平静下来面对死亡,因此你只能选择让自己遗忘死亡才能继续过日子。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如果你知道到头来做不过是挨一枪,那么在幼儿园门口捅一个小朋友还是一百个小朋友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区别。对死亡的恐惧之所以可怕,不仅是让我们自己的日子没法过,更可怕的是这种恐惧会让人丧心病狂,任何道德和价值似乎都没法在死亡面前约束一个人的行为。每个人可以自己想想,如果你确切地知道自己一个小时以后就会死掉,做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一点,那么除了留遗嘱和跟爱的人道别之外还会做什么?恐怕不见得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很可能都是平时被道德和社会规则约束起来不敢做但是在死亡面前终于不需要顾忌了的事情。
有些人试图通过某种自欺欺人的方式“超越”死亡,我并不是说这些人做的事情本身不好,但是我疑心他们的尝试文不对题。有些人寄希望于自己的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可以让自己的“某些部分”在这些后代身上“存活下去”。这是一种非常虚妄的看法,后代过的生活是后代的,不是你的,一厢情愿的想象再热烈也无法让人像幽灵一样附体在后人身上。后代对于你的记忆和想象,假使存在,也是作为他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他们记忆和想象成什么样子,与你无关。况且,这种选择要想成立,必须依赖于每一代人都做出同样的选择,而即便真的如此,也未免有“纯粹以人为手段”之嫌。另一些人试图让自己融入某种“不朽”,似乎当自己生出一个不死的东西时,这个东西就携带着自己的一部分永远活了下去,像是《哈利·波特》中说的“魂器”一样。不可否认,正是这种执念促使一代代人去搞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乃至去投身各种看起来恢弘伟大的事业,想要通过让自己融入到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东西中,借它的“不朽”来超越自己的死亡。然而创作者总是会忘记,即使作品有自己的生命,那也是它们自己的生命,它们一旦降生就不再属于作者。上述种种尝试,或许可以带来某种面对死亡的慰藉,但是正如杜冷丁不是抗癌特效药,面对死亡的安慰并不解决死亡本身的问题。不论一个人膝下有多少子孙、桌上有多少作品,他都还是只能自己面对属于自己而无法与别人分享也不能被别人夺走(海德格尔语)的死亡。
然而海德格尔建议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正是死亡这种迫使人重新掂量自己生活和社会价值中的一切的力量,反而给了我们每个人一种机会,去做出那些关乎自家性命的抉择,去决断什么对自己来说才是真正重要的。正是因为死亡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如此地真切而本己——这是现象学的黑话,意思约莫是“根本上面向和关切自己”——,正是因为死亡的恐惧如此强有力地迫使我们摒弃外界强加给我们的东西,给我们一个机会珍惜我们所仅有的不知道有多长的未来,才更加使得我们能够有动力去为自己真的认为重要的东西——在死亡面前依然被我们认定为重要的东西——而做事情。这就是海德格尔那句非常有名的Sein zum Tode,“向死而生”。
请一定不要把这个口号理解为心灵鸡汤。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洞见,面对死亡而存在下去,意味着要保持着对于死亡的沉重的清醒认知来去自己一个人做出究竟什么对自己重要的决断。这件事的沉重有两方面,一个方面是海德格尔本人所提到的——你自己的死亡归根结底只能你自己去面对,因此此种“向死而生”的决断只能由你自己做出,别人帮不了你。当代大众文化俨然在比任何时代都更强地剥夺一个人摒除俗见来为自己做出决断的机会,甚至你的特立独行、你的“要做不一样的烟火”、甚至你之前所听说的“向死而生”,都是迫使你被其他人推着接受他们的选择的机制,“我要不一样”这是不止一个产业。然而其他人都无法帮助你面对自己的死亡,海德格尔告诉你,为了在自己的死亡面前做出自己的抉择,你必须为自己的决断来负担对自己的全部责任,这自然非常沉重。
另一个方面是海德格尔致命地忽视了的,那就是他人的存在及其分量。当海德格尔把重点放在你自己为自己做出决断和重估价值的时候,他忽视了你的决断对其他人的影响,似乎在面对自己的死亡时,别人都消失了。然而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鉴于我们无法经验自己的死亡,我们对于死亡的所有认知实际上都来自我们认识到其他人的死亡。假如我们面对自己的生命做出价值重估的时候忽视了其他人的生命及其价值,这就走到了对死亡的认识的对立面上,否定了自己的前提——我们正是从他人面对死亡时展现出来的生命价值中,才学会了死亡值得恐惧这件事。这一致命错误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海德格尔在三十年代一度成为了纳粹——他当时认为德意志民族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做出决断,所以必须呼唤能够做出这种决断的人也就是元首,并且犹太人和其他民族是可以被牺牲被当作不存在的。或者用个比较近的例子,正如之前所说,如果我面对死亡就是决断认为多捅几个幼儿园小朋友比较赚,鉴于整个价值体系是我自己重估的,凭什么说我错了呢?
实际上,我认为死亡的问题真正危险的地方,在于其道德后果。死亡是深渊,不仅吞噬你对于自己的所有日常的欠反思的价值锚定,同样将你眼中整个世界的天柱地维都吞噬进去,给你留下一片绝对的价值虚无。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人生感到虚无,危害相对较小,顶多祸害自己和家人;一个人感觉整个世界价值虚无,可以做出任何罪恶滔天的事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一个人被死亡惊吓到麻木以至于感觉自己连死都可以无所谓了的时候,才是这个人最可怕的时候。一个热爱自己的生命但是意识到有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的人,可以是英雄。一个看轻自己的生命的人不大可能看重任何其他人的生命,这种人是最危险的祸害。不过或许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死亡可以摧枯拉朽地抵挡一个人日常凡俗的道德观念,因此任何真正坚实的道德观念,必诞生于一个人经过死亡恐慌的洗礼之后。
这意味着,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和价值决断如此值得珍惜的时候,应当同等地意识到其他人的生活和价值决断也如自己的一样值得珍惜,每一个他人都跟自己一样有着对死亡的恐惧和这一切,每一个人都不能被当成仅仅是一件工具,并且在做出决断的时候,除了为自己负全部责任,也需要为被自己影响到的其他人负全部责任。这令人想起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论述,他认为只有通过为了什么东西“以命相博”,一个精神才真正成为了自己成全自己的东西,只有通过直面死亡的恐怖威胁而做出究竟什么东西真正重要的决断,一个精神才配得上成为自由的精神,否则那就只是一个随着饮食男女的本能和庸众的专制而漂泊的东西。就此而言,“向死而生”在海德格尔那里的含义究其内核已经包含在黑格尔论“主奴辩证法”之前的环节,只不过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并不存在黑格尔所说的在此之上的整个向上运动的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对于黑格尔而言,他所说的精神绝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精神,而必然是一种根本上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从而死亡的问题也不再是一个“我”的死亡,死亡的问题以及在此之后的过程,对于人类精神来说从来就是普遍的。这同样让人想起福柯临死之前的教诲,只有面对死亡,对真理的坚持言说才展现出其熠熠光辉——“当你接受使自身生命暴露无遗的直言游戏时,你便采取了一种与自己的特殊关系:你冒着死亡来言说真理,而不是在真理无法言说的生命之安全中休憩。”
或许这就是对死亡的不可消除的恐惧给我们带来的积极的东西——它是我们向真正的理性、真正的道德和真正的自由上升的驱动力。一个自由的精神,必须是一个勇于直面死亡之恐怖而不致慌乱溃败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