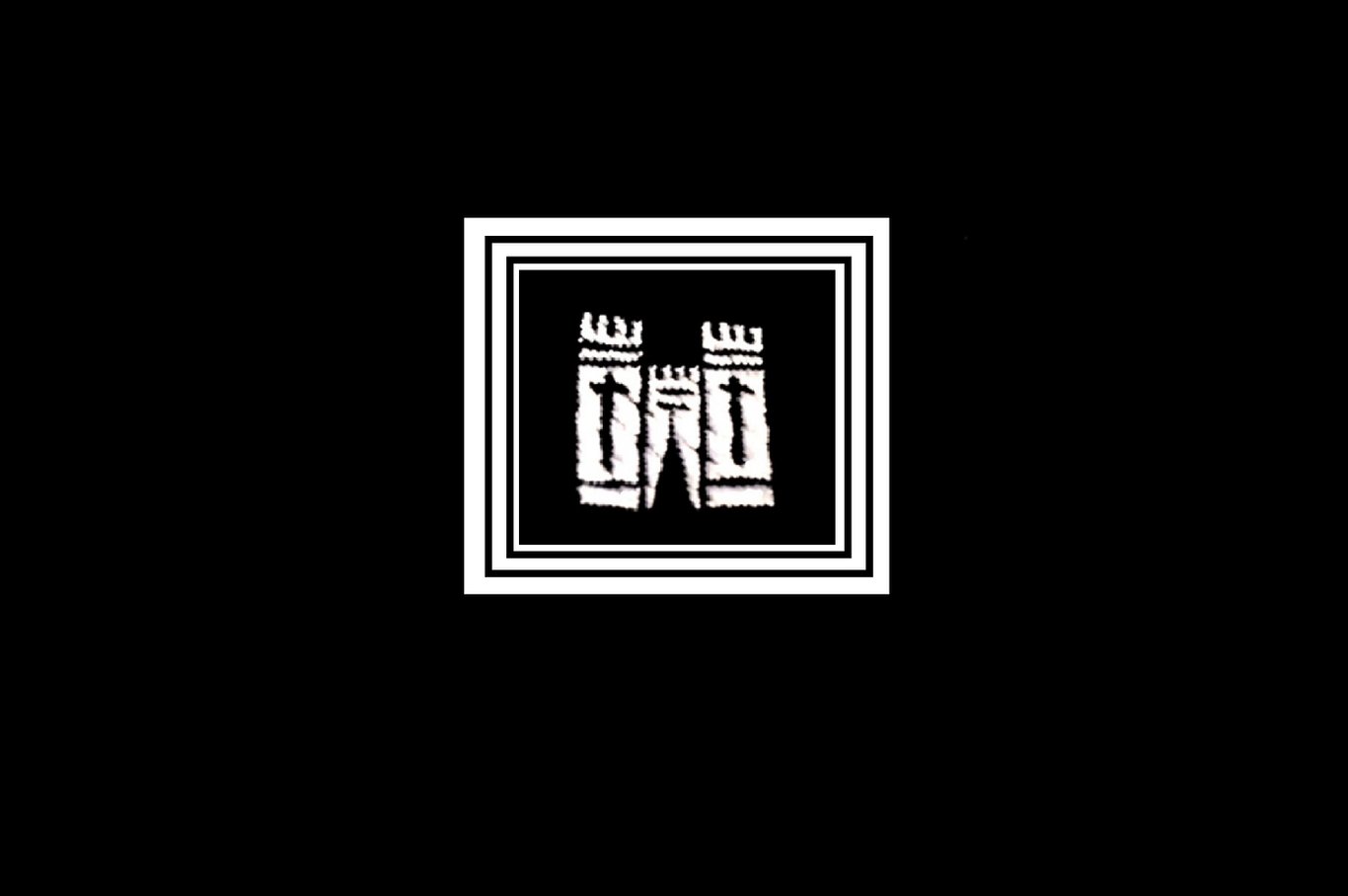受到诋毁的尼采遗志和现代人的道德危机
《容器的背叛》系列第一篇
机器轰鸣的十九世纪末尾,饱受多年梅毒折磨、即将丧失心智的尼采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人们不再信仰基督、不再遵循十多个世纪以来宗教为人类提出的道德和生命之意义,但却根本无力创造新的价值。他们不得不依附着旧的宗教道德活着,但心中却又充满着迷茫、卑鄙。在他看来,十九世纪的欧洲人是一群生命力减损的人类,不仅不配和古希腊“悲剧时代”能够直面生命之创造与毁灭的文化相提并论,还因为对过去积累起来的道德与文化的遵从走向了虚无和固步自封。
对此,他喊出“上帝已死”的口号,警醒人们脱离仍然支配着他们被动地生活的宗教道德。他不止步于此,而是发展出一套“强力意志”的理论,希望能够超越道德的藩篱,用生命本身的“力”(对强力的渴望、对弱力的征服)去指引人的生活与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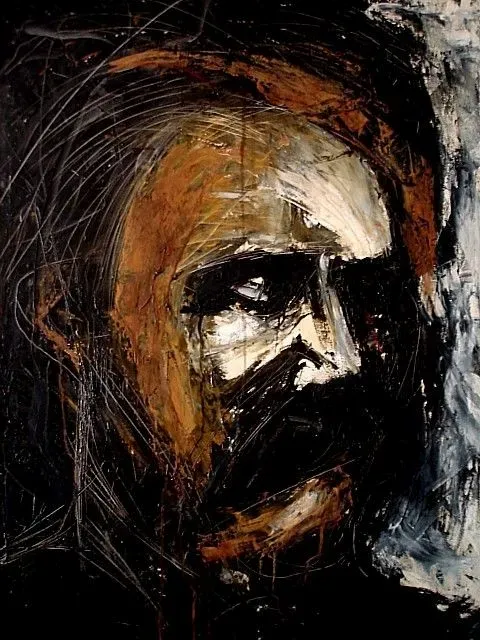
尼采之解决方案的对错优劣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他巨大的影响力也许不在于他激进的理论说服了多少人,而是他以自己的方式指出了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问题。一个被各个学科以各种方式和尺度指出的、只要谈到现代性、谈到我们引以为傲的理性和道德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似乎并没有在活自己的生命。
在欧洲人激烈地步入现代化的十九世纪,他们的道德观就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在清教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一套极度严苛、保守的道德体系被富裕的中上层阶级构建出来。沐浴在家庭权威、贞洁、虔诚和对任何罪恶都严刑以待的光辉中,人们或是被同化道德卫士和牺牲品,或是对道德采取虚伪的态度,过一种伪君子式的生活。在天主教的俄罗斯,人们同样为神所指示的道德生活而痛苦。我们可以在陀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塑造的二哥伊凡这个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中窥知一二。伊凡以自己的睿智的理性勇敢地推翻、驳斥天主教道德,但却在自己得出的“人因而可以做任何事”的结论中陷入犹疑痛苦——理性得出的结论却并不符合他的人性!他不可能仅仅通过拒绝一种道德,便能掌控自己心底的欲望和目的。在摇摆不定的念头中,他任凭(我不能够剧透的)悲剧发生。直到故事的结尾,他仍然在反思和成长着,仍未能取得对自己的胜利。
要么接纳道德,采取一种被动的生活;要么背叛道德,在虚无之中艰难地跋涉。尼采所指出的这一道德的危机贯穿了现代性的始终。或许今时今地的我们身上没有多少宗教的影子,但是许多道德与观念的作用简直和十九世纪宗教加诸于人的束缚如出一辙。
在此,为了使读者明确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危机,请容许我对主要方面做一番简单的列举:
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体系和观念:简单来说,我们工作至死,并在工作之后的疲惫中用消费建构起的符号和身份去定义我们自己。在道德上,人们赞美干电池一般的辛勤劳动和在消费主义中“创造性”地建立自身属性的方式,但对于整个体系的问题如阳痿的男人般无力应对。对于它我们有两种“背叛”的路径,要么有足够的资本摆脱打工人的属性并建立自由的生活和精神——如果是作为这一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而争取到这样的优越条件,那在精神上真的能够反叛得了吗?要么选择“断舍离”、“躺平”等等消极退出的方式,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是在作为弱者,以消极抵抗的方式定义我们自己。多数情况下,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力量去建构一种能够与之匹敌的生活范式。
文化上,我们有丰富道德的传统:我们的道德传统不是基督教式的,但对人的束缚并不较其更轻。基本上,上文所描述的十九世纪欧洲图景可以精准地套用在二十一世纪的许多国人身上。
知识上,科学之权威建构了我们对于科学主义之价值推论盲目过度的遵从。这方面可能是读者(甚至我自己)都最为不熟悉的方面,所以我稍微展开谈谈。我们有赖于神经科学告诉我们“人的天性”是什么,有赖于精神病和心理学告诉我们什么是“反常与变态”、哪些犯罪在心理上是应当被容忍的,有赖于现代的医学和运动科学等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方式……拥有专业资格和高深知识的专家在常人难以企及的方面为我们把关,这似乎不是件坏事?当然,一定有好的方面,但就像福柯不断向人们重复的那样,知识生产掌握了我们认识和解读现实的权威:什么是常态或者异常?什么是健康?什么是能够容忍的恶和发自本性的善?在无数的问题前面,我们自己的思想和判断被迫为专家们知识性的结论让步。而专家的结论常常是孤立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并不会为公众提供全部的知识与价值背景。
这至少造成了两方面的危险:其一,我们必须接受已经为我们设下结论的世界,没有探讨的余地——我们无法了解继而反驳那些专家权威背书的知识和标准背后站不住脚的观念和背景,所以只得生活在某些荒谬之中,只得在自我和那些标准与权威体系冲突的时候,将矛头对准我们自己。我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有关于短效避孕药普遍每21天停7天的服用周期。2019年一项专业机构的医学建议更新中阐明,这种停药周期其实完全无必要,甚至会有不必要的风险。之所以有这样的周期,也许是因为早期的药物发明者以为符合女性天然周期的流血形式更加自然健康,也许是这样的安排能在宗教上更为人所接受,总是就不是因为任何的科学证据。但是这样毫无必要的用药方式偏偏成为了绝对主流。
(一则相关报道:http://www.qdaily.com/articles/60603.html)

另一个例子关于各类精神疾病的争议。精神疾病的确诊与给药,必须由有专业资格的医师通过严格的标准判定,这似乎成为了一项不容置疑的严肃“病症”。无论确诊与否,患者常常经历痛苦的自我怀疑和否定,与来自外界的歧视。但换一个角度讲,许多精神疾病的因素或病症若是放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则是优越的、具有进化优势的特质。譬如,ADHD的兰花型人格和抑郁症的进化优势(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37366),或者曾经被认为是病症的同性恋的进化意义。只不过在特定的社会形态和道德规则里,这些特质被看成是异常、变态和有风险的,它们的携带者就不光要矫正它们的负面作用,还必须要经历自我怀疑和外部歧视的重重危机。这只是举出诸多问题中的两个例子了,说这种科学的权威体系“挑起了人和自己的战争”或许是一种过分夸张的形容,但是它毋庸置疑地加强了人与他自己关系的紊乱。
别忘了,科学主义还造成了另一方面的危险:我们其实不只是消极地接受它带给我们的影响,而是怀着与有荣焉的心态将科学主义的话语与逻辑当成是现代文明的珍宝,以及放逐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公允地讲,不光是因为科学主义和权威知识体系,更是因为后印刷时代的信息生产与分配方式,)许多人误以为知识的渊博就是对各种科学知识和标准的知晓与条分缕析的记忆。对这些知识点的巧妙罗列常被当成是伟大的思想,而审慎并富有洞见的论证却无人问津。这种以将人们的头脑用教条化的知识填满的方式所造成智识减损或许导致了难以言喻的公众生活与文化后果——洋溢着知识的愚昧犹如漂泊在海洋当中却缺乏淡水。我想,一些有知识精英和后现代性危机感的哲学家已经在他们少有人关心和读懂的著作中将对这个危机的绝望记录了下来。
或许一些读者也会在各色缺乏真正的思辨的公共讨论中,像我一样体会到那种让人心灰意懒的滋味,仅举一个和本文将要提到的话题高度相关的例子:关于同性恋合法性与社会认同的讨论。我不懂为什么好多人都花上几乎所有的篇幅通过论证它是“自然的、遗传的”来证明它是应该被接受。在我眼里,这明明和它在本质上被社会接纳没有任何关系。作为一个文明而言,我们明明接纳了那么多一点也不自然的社会规则,并且在那么多“自然”的行为上设置禁区,证明它“自然”与否又有何用呢!答案简单得让人头疼:对于整个公众讨论来说,同性恋被科学所承认和证明的价值的确是高过一切的,因为这些科学主义的论证想要说服的也都是科学主义者们。这种不容置疑的大众价值的主流,就像给预言家拿警徽的狼人杀玩法只是因为大家都接受这个逻辑所以才真的有了玩法上的约束力。
最后,在政治上,意识形态愈发鼓动人接受并非源自他自身真实的生活和思考而得来的理念,这不光让人们面对互相诋毁拆台的政治观念陷入迷茫和虚无,更瓦解了人们真实与可理解的生命体验,带来日常性的麻木。意识形态,或者说政治价值本身并不具备导致我们所谈到的这个人的危机的能力。当下人的危机来源于现代意识形态建构中两方面的倾向:
其一,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理论的论据和论证高度依赖于抽象的、脱离个人体验的对世界的结构化总结和数据分析。话语系统中从人的视角出发的评判愈发稀少,来自抽象概念的则愈发增多,无论是阶级、法律、国家利益、民族性,还是经济态势、生产关系、科技、全球化公司、政治化的历史……作为对比,前现代所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然法”等等一系列革新概念,或者干脆是那些尊崇君王和宗教领袖的理念,都和对人的直接认识紧密相关。这使得人难以通过切身体验和对自身生存处境的理解来接受政治价值,而必须让位于抽象的知识和结构的指引。
我时常在倾听旁人的议论时感到大为不解,当他们大谈中美力量和未来政策趋势如何时,其陶醉自得的语气就像是在谈论两个野心家争夺权位的故事,而完全忽略了这些超强力的政治实体让渺小的个体畏惧主体性的被剥夺和不能自决之命运的那一面;当他们饶有趣味地讲述某某政策可以带动经济发展(的指标)时,完全忽略了现实层面中处在不同位置的个体是会因此获利还是流离失所……这种惹人恼火的人文精神之淡薄并不完全怪这些说话的人,而是因为在现代意识型态系统所建立起来的话语体系里,个人的情思几乎已不再被体现。

其二,若分析政治价值背后的推动者,则会发现,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与政治诉求中,脱离人的面目的机构和力量赶走了那些尚存有人性特点的成分。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人面对的政治力量迫害,或许来自某位具体的村长、领主或者国王。无论那是怎样残酷的迫害,就算是宗教审判的火刑架,承担最终责任的上帝也以人的面孔示人。而步入现代,不仅我们的情感归属被“国家/民族”这样抽象的共同体支配着,而且正像卡夫卡试图通过寓言暗示的那样,我们需要与之对抗或者合作的对象变成了更加冷酷神秘的官僚式结构:堆积如山的官方文件、莫名其妙但麻烦非凡的规则、不知何故的审判……各种文化造物都循着更有效率,更能维护其本身利益的方式建立起了生命,而人在其影子下面显得十分渺小。
我不想一一详述这些因素背后推动力的来源,或分析那些宏大的历史之力量所带来的影响总和是否利好躲过弊端。通过上述列举,我们需要达成的唯一共识是:尼采所忧心的道德的危机在当代变得更加严重而瞩目了。虽然宗教传统早已不似当初那样火热,但是更加非人化的、高度渗透性的道德与思想说教已经覆盖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给当代人的主体性笼罩上了一层铁幕。
不仅如此,一个广泛的共同感受是,当下的世界变得更加不宽容了。这可能是因为新的信息传播手段极大促进了那些承载着道德和思想指令的讯息的流通。浅薄、极化的意见碎片被一遍遍重复,笼罩着整个互联网空间,真实而深沉的作品全盘落于下风;面对无孔不入的道德审判和意识型态的肆意侵入,个人尚且无力独善其身,更别说创造出什么崭新的价值、发展出强韧而个性鲜明的思考了。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们努力地希望建立自己,他们希望享有自由、逃离囚笼,但是他们手头的几乎所有材料和资源背后都潜藏着道德和意识型态的指令。如何才能给人以精神的力量去抵御这场无处不在的迷茫与危机?如何才能够重塑人作为人本身的尊严和主体性,不做愚妄而古旧的道德传统的奴隶?
继续在旧有的道德观念所铺下的道路上埋头分析已经不能带来颠覆性的成果。我们需要一个对于人的本质的重新诠释,去帮助我们重头理解和确立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而这个新的基础将会否定那些业已陷入危机的道德体系所援引的那个相对固定的对于人的常识性理解,继而为我们免除使人迷茫与痛苦的道德义务和作茧自缚的思想形态。
顺便说一句,尼采也选择了相似的道路。他把“强力意志”看成是一套他认为超越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更不用说各种道德的普遍生命规律。在道德家孜孜不倦地宣扬着陈词滥调,各色哲学和批评家也想在埋头厘清历史的线索中贡献微不足道的进步时,这个人忽然站起来大声疾呼:不对,你们这些理论所适用的对象并不是我,也并不该是任何人!你们关于人和生命的观点从本质上、从对生命假设的这个起点就是错的!可想而知,就算尼采自己精神没有出问题,很多人也会以看疯子的视角去看他:凭什么你可以说我们这么多人所默认的价值和理念都是错的呢?如果这些理念该被抛弃,那么建立在其上的文化大厦,岂不是都毫无价值,都要加以批判?
我的这一系列文章正是想继承尼采的这一个勇敢而伟大的遗志。但我不被想当成是疯子,我的关于人的崭新理论有一个更为精妙和严谨的基础:一套试图在新条件下将科学与哲学作以联合的新体系。
如果你读过《容器的觉悟和自我修养》这篇文章,那么就提前预知了我一部分的论点。即在自有其新陈代谢的宏观思想体系面前,人并不该自诩为主人。我们的真正地位只是它们的容器和载体。但是我们的载体身份并不是凭空随着观念的兴起而出现。事实上,这个身份在冥冥中已经注定,早在人类社会孕育思想道德的亿万年前,甚至早于人类遥远的祖先第一次在陆地上留下足印之前便已注定。我们初始的载体身份同演化历史上生命体与它们的本性之间的基本关系紧密相关。毋庸置疑的是,本性对于生物的行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对于有发达智能和意识人来说,我们的本性它真的就是那个不二真主吗?“伟大的母职天性”、“生儿育女,天经地义”、“男人缺乏阳刚之气,女人不再温婉柔美”……教人严守本性的道德说教仍然占领着我们观念世界的战略要冲,我们应该对这些理念点头称是吗?
在随后一篇文章中,我将给出一个支持容器们反抗任意蹂躏驭驶他们的旧有观念和世界的激动人心的理论。这将是一场重新认识人的本质的严肃而激进的尝试。在这场思想革命中,容器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将是对他们自身似虚无一样自由之存在的全然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