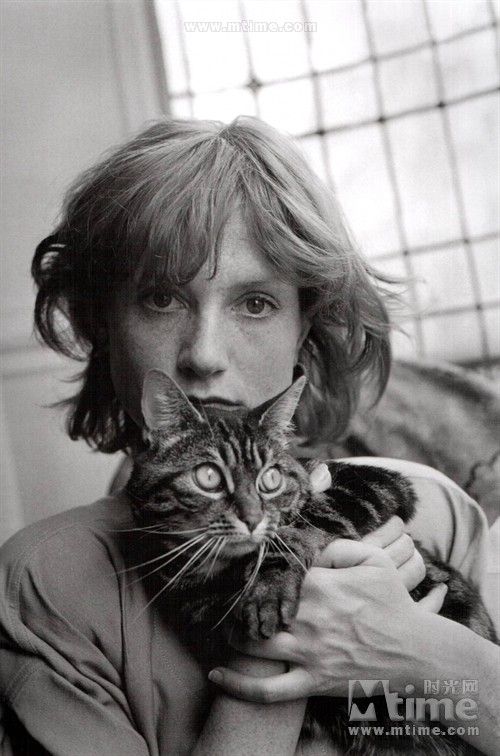在夢裏,我的手長出來了
(序)
2018年5月份在蘇州與樂行機構負責人見面時,他問我是否有意願寫壹寫工傷工友的故事,希望通過文字有更多人能關註、了解工傷工友群體。
6月份,我受其之邀,有了近距離與工傷工友相處的機會,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阿香。她在舞臺上開心地跳著她家鄉的舞蹈,她缺失的右手,對她的舞姿沒有任何影響。
離開佛山之前,征得阿香的同意,我留了她的手機號碼並加了她的微信。之前,我以為不戴義肢的阿香已接受缺失右手的事實,聊過之後,才知道,她多麽害怕見到老鄉和以前的熟人。
我曾壹度擔心自己的「不專業」會造成對她的二次傷害,所以每次聊天前,我都會跟她說,如果有些問題她不想聊就不聊。阿香很信任我,什麽都會跟我說。她會跟我說她現在頭發掉得厲害,臉上長了雀斑,她有每壹個女人的小煩惱。
(壹)
她搓熱的左手揉捏著右手截肢愈合處,她不記得自己什麽時候開始養成了這種習慣。或許是壹到變天的疼痛,或許是樓下的中醫告訴她要常常活動它,以促使血液的循環,手臂才不會萎縮。她可不想手臂萎縮到連自己都不想要了,畢竟,她已經失去了右手的掌心和五根手指。
受傷之後,阿香覺得自己殘缺的右手連帶著整個壹邊的身體都有問題,她的腦子也有問題,整個人都有問題。她的腦子裏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想法會冒出來。
有時候想,做壹天算壹天,拿著賠償金回老家算了。如果真的回老家,沒有工作,錢會花得很快。等老了,又殘了,更找不到工作,孩子們也會覺得自己是負累。如果可以的話,能在沃爾瑪工作15年,領到退休金也是好的。
有時候又想,賠償金不能亂花,要存起來。可是又想,存在那裏的幾十萬,等老了的那壹天,這筆錢是不是就不值錢了?就像以前的老人存了幾千塊錢,以為存了很多錢,結果現在幾千塊錢能幹嘛?
過壹天算壹天吧,她想。
我現在自己養活自己,啥也不要想。她這麽告訴自己。
可她看不到前面的路,因為眼前壹片黑。
有人安慰她:妳只是少了壹只手而已。
還有人說:現在妳有幾十萬的賠償金,妳打工多少年都掙不到!
他們不知道健康是多麽重要,受過傷的阿香知道,失去壹只手的痛苦和折磨,是多少錢也換不來的。
受傷後,阿香會更多的考慮到自己。她跟孩子們通電話的次數變少,好像沒有話對他們說了。有時候他們打電話找她有錢,她就用壹句「媽沒錢,找妳爸」來結束通話。
她覺得這樣對老公有些不公平,他壹個人要負責生活家庭方面所有的開支。可是,老天對她又何嘗公平呢?
在阿香看來,公婆若是嫌棄,也是人之常情,誰會想要壹個殘疾的兒媳婦?這個世界上,只有自己的爸媽永遠是自己的爸媽,不管自己變成什麽樣,他們都不會離開我的。想到年邁的父母,阿香流淚了。
失去了右手的體驗是,用左手做事比三歲小孩學走路學說話還要難。
綁頭發的時候,壹只左手怎麽也綁不好,即使有殘缺的右手幫忙。刷牙的時候,不能像以前那樣左手拿水杯,右手拿牙刷,只能嘴巴對著水龍頭漱口,左手刷牙。現在,她不買帶拉鏈的衣服,因為壹只手拉不上拉鏈,帶扣子的衣服相對來說方便些。有鞋帶的鞋子,保持它買過來時穿好鞋帶的樣子;需要洗鞋的時候,鞋帶不用抽出來直接洗就好了;走路的時候,如果鞋帶散了,只能多花些時間,蹲在路邊用殘缺的右手壓住壹邊,等待左手系好鞋帶。吃飯的時候,她會下意識地伸出右手拿筷子,殘缺的手出現在眼前,使她意識自己犯了錯誤——右手拿不了筷子。
2018年,阿香還沒回過老家。公家婆(婆婆)在電話裏跟她說,孫女問她,媽媽今年是不是不回來了。
「如果媽媽經常回家,被人知道了,那該怎麽辦?」孫女問。
「別人知道就知道了唄。」奶奶回答她。
阿香最怕回老家過年。受傷的那壹年春節,她並不想回去。但是父母的電話,還有壹年未見的兒女,她還是和老公壹起回去了。
(二)
回家的路上,阿香的右手藏在袖子裏,她怕自己殘缺的手會嚇到他們。
壹到家,家人圍著阿香,什麽話也沒說,除了哭。因為阿香的傷勢超過了他們的想象。
阿香忍住眼淚,沒哭,說「我這個沒什麽大不了,有的事情是做不了,有的事情還是能做的,只是做得慢壹點。」
在女兒和兒子們面前,阿香壹直戴著手套。有壹天烤火的時候,小兒子說「媽媽,烤火妳還戴著手套,怎麽不脫下來?」
「我怕冷唄。」阿香答道。
晚上,8歲的兒子們想跟媽媽壹起睡。阿香睡在中間,雙胞胎兒子壹邊壹個睡在她身旁。第二天早上,阿香戴著手套幫他們穿衣服。第三天早上給他們穿衣服時,兩個兒子盯著她看。阿香怔住了,望著自己勾住衣服的右手,才察覺到自己的手套不知半夜時丟到哪裏去了,回過神的她立刻把右手藏在背後。
「妳們不怕媽媽吧?」阿香問。
兩個兒子笑了,說「不怕不怕」。
「媽媽變成這個樣子,妳們不怕嗎?」阿香的鼻子發酸。
「我們早就知道妳沒有手了。」大兒子笑呵呵的。
「那妳們怎麽不問媽媽呢?」阿香聲音哽咽。
兒子們低著頭說不好意思問。
「我把手拿出來,妳們不要怕。」阿香調整好情緒。
「我們不怕。」兒子們大聲道。
其實,阿香並不想讓兒子們看到她受傷的手,但是她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媽媽很堅強。
第二天下午,村裏有鬥牛表演,所有的人都盛裝出席。家人也叫阿香去,她拒絕了。
妳去嘛。他們說,身著阿香做的衣服。
那是阿香受傷前做的。作為侗族的女孩,在她們懂事的時候,媽媽就會教她們怎麽做自己民族的服裝。
阿香脫掉手套,通過裝有彈簧的袖子,穿上自己親手縫制的衣服。看了壹會鬥牛表演,阿香覺得有點熱。她正準備脫衣服時,兩個兒子過來圍住她。
「妳們在幹嘛?」阿香不解。
「妳不是怕別人看見嗎?這樣別人就看不到了。」大兒子答道。他們用人形屏風擋住別人的眼光,讓他們的媽媽放心地脫下右邊的袖子。
大人們以為孩子年幼無知,其實孩子什麽都懂。
(三)
受傷在阿香看來是命中註定。
2016年五壹勞動節的第二天——5月2號壹大早,睡夢中的阿香被朋友的電話吵醒。
「阿香,妳今天上班嗎?不上班的話,我們去山裏玩。」那是上周阿香和朋友約好的。
阿香說不去了,她要上班。掛掉朋友的電話,她又睡了個回籠覺。
「妳別去上班了,壹起出去玩吧。」放假來看望阿香的老公也叫她出去。
「妳去玩吧,我要把貨壓完。」阿香想辭工,老板給了她壹批6萬個吊牌的訂單,說做完這批貨才有錢給她發工資。她已經壓了四天的吊牌,還剩兩萬的數量,她想早壹點壓完這批貨,拿到錢就可以走了。
阿香記得5月2號那天她很困,雖然平時上班也常犯困。他們早上8點開工,12點吃午飯,吃完飯就趕工(為了省去機器預熱的時間,吃飯時不停機),晚上8點下班。計件工資,做得多拿得多。模具有4、6、8、10、12、20的數值,根據吊牌的大小、厚度不同,選擇不同數值的模具。輸入20的數量,壓滿1萬個吊牌有25塊;輸入8、10、12的數量,1萬個吊牌是45塊;輸入6的數量,1萬個吊牌是75塊,輸入4的數量,1萬個吊牌是120塊。阿香每天的工資,大概是120塊。
上午車間有三個人開工,中午吃飯的時候,壹個大哥的老鄉來找他喝酒,大哥下午就沒來上班。
「我們倆也停工吧,今天所有人都停工,老板也不會說什麽的。」老鄉見車間只剩下他和永香,建議道。
阿香沒搭理他,心想妳要停工自己停好了,我把貨壓完就走了。
那天有那麽多人叫她走,她不走卻選擇了開工。阿香想,如果她聽從其中某壹個人的意見,是不是她就不會受傷。
阿香開了第5臺壓塑機。吊牌上的英文字要金色的,需要墊金。她到二樓包裝部叫老板娘(老板的老媽)擱金。
「我今天困死了,什麽時候才能壓夠,數量夠了嗎?」阿香壹屁股坐在包裝袋上。
「還沒有點數。時間太緊了,我們也做不過來。」對方無奈道。
阿香回到車間,繼續壓吊牌,不知道壓了多少,下午3點左右,她受傷了。從來沒有人告訴她怎麽註意安全,她不知道是機器的問題還是自己不小心。她弄不明白,她很想看受傷壹瞬間的視頻,但是老板說監控壞了。
她受傷那壹瞬間的記憶,似乎也被抹除了。當時她能想到的是,這只手沒了,這只手殘了,她感受不到任何疼痛。她回憶,那壹刻應該是很痛的,她也應該發出了大聲的慘叫。
同壹車間的老鄉、二樓包裝部的人、老板的爸媽圍到阿香的旁邊,換模具的師傅關掉了機器,阿香的手卡在機器裏,沒有人剛上前來幫忙。
「打電話叫醫生過來接……」似乎有人這麽說。
阿香冷靜了下來,從機器裏拿出自己的手——扁成壹塊的手,顏色發白,有沒有流血她也不記得了,能記得的是老板娘拿了壹卷紙巾,包住受傷的手。
不知道過了多久,救護車、醫生,都沒來。老板的表妹和表妹夫攙扶著阿香,說他們開車送她去醫院。阿香打電話告訴老公她受傷了,在去佛山中醫院的路上。
車裏的阿香,只有壹個祈求——老天爺,求求妳,把我的手接回來。
(四)
醫生打開包紮的紙巾——換上病服的阿香,這才註意到自己的手臂腫得像大腿那麽粗,都看不到自己的手。
阿香傷勢的嚴重程度超出了他老公的想象,他說「沒事,還能接回去」——這不僅是安慰老婆,更是他的希望。
他們不知道阿香的術前診斷為:右手嚴重壓榨毀損傷,右手多發掌指骨粉碎性骨折並骨缺損,右手多發神經血管肌腱斷裂損傷,右手皮膚軟組織嚴重挫裂傷。
蓋在手術布下的阿香什麽也看不到,局部麻醉的她聽見主治醫生說——「接不了」。
「我要接,要接。」阿香重復著。然後,聽見醫生走出去的腳步聲。醫生對阿香的老公和接到電話趕過來的老板宣判道:沒法接,只能截肢。他們只得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字。
阿香不想放棄,可連醫生都說沒有辦法,那她又能怎麽辦。
「我只能這樣殘了。」她絕望道,她才三十歲啊。
「妳這點不算什麽,妳只是右手沒了,比妳殘得多的人很多,等妳出手術室了,妳就能看見很多比妳更殘的人。」是壹個女人的聲音,應該是護士。
阿香不知道殘疾是可以比較的,她能想到的是以後怎麽生活下去。為了給人活下去的希望,人們不會把殘疾與健全做對比,就像不會把貧窮和富裕做對比壹樣,只能將更不幸者做不幸者的參照物。
「醫院裏有很多接不到活的律師,到時候可能會過來哄妳們,妳們千萬不要相信他們。像阿香這樣受傷的,不用經過律師,如果經過律師,到時候賠償費都到律師手上了,妳們什麽錢都落不到。放心好了,妳老婆受傷該怎麽賠我們就怎麽賠。」老板在走廊上叮囑阿香的老公,「千萬不要相信律師的話。」
「現在還痛嗎?」老板問已經推到病房的阿香。
或許是因為麻藥未退,或許是因為剛在手術室砍掉的右手,阿香連眼皮都懶得擡,她什麽也不想說,只搖了搖頭。
「明天我有事,可能來不了。」老板說著,從錢包裏抽出三張壹百塊人民幣,遞給阿香的老公,叫他拿去醫院食堂買張飯卡。臨走之前,老板叮囑阿香好好養傷,不用擔心錢的問題,他會承擔壹切醫療費用的。
吃飯的時候,老公叫阿香吃飯,可她什麽也不想吃,只想睡覺。
受傷的事情,他們夫妻倆意見壹致——隱瞞家人和朋友,說他們還在上班。阿香的老公跟廠裏請了假,在醫院照顧老婆,晚上趴在阿香左邊的床沿上睡著。
碰到幾個律師發名片,記著老板叮囑的話,不相信他們,不搭理他們就對了。
四天後,阿香的脖子終於解放了,不用再在頸部輸液了,同時,開始第二次手術。主治醫生問阿香是否要做皮瓣(由皮膚和皮下組織構成的組織塊,可以從身體的壹處向另壹處轉移),需要從她肚皮移植壹部分將裸露在外的骨頭包起來,重新長肉。手術有壹定的風險,有可能導致疤痕增生。
「不做皮瓣移植也可以,傷口做修復處理、縫合就行了。」主治醫生說。
阿香沈默著,不知道該怎麽辦。
「隨便妳啊,但是妳肚皮本來好好的,回頭肚皮也落疤了,不好看。」老板給出意見。
「是啊,妳肚子好好的,又要在肚皮上開壹刀……」阿香的老公也這麽說。
他們這麽壹說,阿香害怕了,「那就不用做了。」
阿香後悔過當時的決定,如果選擇了皮瓣移植,她的手是不是會比現在好壹些?為什麽那個時候她什麽也不懂?
(五)
「我的手沒了,以後怎麽過辦?」「我該怎麽告訴家裏人?」——這是住院時,阿香每天在想的問題。為了停止繼續想這些問題,她選擇睡覺。她多麽希望醒來之後,醫學奇跡能發生在她身上——她的手像割掉的韭菜壹樣重新長出來了。
睡覺的時候,受傷的手放在身體的壹側,不敢亂動。夢裏,她的手掌並沒有全部截去,只是截掉了幾根手指頭。夢裏,阿香看見自己受傷的右手,在抖動,像是要離開她的身體,手臂的抖動,吵醒了她。她的手臂從躺著的位置,變成了直立的位置。
「妳看——」阿香叫醒老公,「它真的要走了,它要去找另壹半了。」
「妳想太多了。」什麽也沒看到的老公答道。
住院第七天,家裏人打電話過來。只聽見老公說,我們現在沒錢,阿香受傷了,住院了。老公把電話給阿香——
「阿香,傷得嚴重嗎?」電話那頭的公家婆問。
「嚴重。」阿香忍住眼淚。
「壹根手指沒了還是兩根沒了?」公家公的聲音。
「整個壹只手都沒了…….」阿香的眼淚沒忍住,掉了下來,「右手…….」
他們在電話那頭哭,阿香在電話這頭哭。
與家人通了幾次電話,每壹次大家都是哭著掛斷電話。阿香不想跟他們通電話了,好像沒有話再跟他們說了,除了受傷的事。
11歲的孫女看見奶奶抹淚,問「我媽媽以後什麽也不能做了嗎」,孫女這麽壹問,奶奶哭得更傷心了。奶奶覺得孫子們還小,沒告訴他們媽媽受傷的事。
住院第八天,壹個老鄉打電話約他們吃飯。阿香聽見老公重復著昨天自己告訴家人的話,「嚴重,整個手掌都沒有了,右手」。
留在我身上的這部分手,好像要去找砍掉的那部分手掌。就像路邊砍成兩截的小蛇,互相遊動著,想要合成壹個整體。阿香對進來查房的主治醫生說道。
臨床醫學上,阿香的癥狀稱為「幻肢痛」,指患者感到被切斷的肢體仍在,且在該處發生疼痛。截肢後初期,患者從心理上難以接受業已存在的事實,無法擺脫傷肢所帶來的心理上的創傷。截肢使患者喪失了完整的自我,與常人有異。
「沒有。」醫生說。
「為什麽我的手會動得吵醒我?」阿香不解。
「那是神經在動。」醫生解釋道。
醫生的話使讓香擔心自己以後會神經。
「我說的是血管神經」,醫生指正道,「傷口愈合恢復好,就不會動了」。
阿香躺在病床上,轉過頭望了望另外兩個因交通事故摔斷了腿的病友。他們治療修養壹段時間後,就能恢復正常。而她呢?
她永遠地失去了她的右手。
(六)
「大姐,妳是不是工傷?」兩個女孩不知什麽時候進的病房。
「不是,是我自己不小心。」阿香看了她們壹眼,接過女孩遞過來的工傷資料,扔在桌子上,沒再理會她們。
兩個女孩見她緊閉雙眼,說了壹句「有需要聯系我們」,悻悻地離開了。
「吃飯了」——是老公的聲音。他們倆吃不慣醫院食堂的飯菜,每次都是阿香老公出去吃飯再打包壹份回來。
不久,吃飯的錢用完了,阿香的老公去食堂退了飯卡,用卡裏剩下的錢當夥食費。
她可以下床,出去走走了。透過玻璃窗,可以看到中午的藍天和陽光。大廳走廊裏,壹個女孩在跟壹個病人聊天,阿香走近壹點,聽見「工傷」兩個字,她站在旁邊聽了壹會。
「像我們這種受傷的,妳們做這壹行都懂,是吧?」阿香問女孩。
「是啊,我們都是專業的。」女孩說她手上沒有資料,另外壹個同事那裏有,等會拿給她。
阿香加了女孩的微信,女孩說她叫艾欣。
拿著艾欣給的工傷資料,阿香覺得很眼熟。回到病房,她到處找了找,在抽屜裏找到那兩個女孩留下的資料,原來都叫「樂行」,是同壹家機構。
艾欣常給阿香發語音,問她是否好壹些了,可不可以過來看望她。阿香拒絕了她的好意。
很快,醫藥費用完了,阿香掛的點滴也停了。她只好打電話給老板說「醫藥費沒了,夥食費也沒了」。
老板打了2300塊到阿香的銀行卡,這筆錢用完之後,老板又打了兩次2000塊給他們。對於醫療費,老板確實如他所承諾的那樣,並無任何怨言,阿香夫妻倆認為他們碰到了壹個好老板,他們也相信老板會像之前說的那樣「該怎麽賠就怎麽賠」。兩千塊沒多久又用完,這回阿香不好意思再找老板要錢了,只得把準備過年帶回家的錢取出來交醫藥費。
阿香不喜歡天天穿著病服,她想念衣櫥裏的連衣裙。打著石膏、紗布包著頭、各種受傷病人的藍色條紋病服,在她眼前晃來晃去,腦海裏不停地重復著「妳殘廢了」的聲音。她想走出病房,走出醫院的大樓。再不出去,她要瘋了!
「妳現在是不是可以出院了?」老板打來慰問電話,「妳問問醫生,什麽時候可以出院。」
主治醫生告訴阿香,拆線之後可以出院。
「25號床家屬,妳可以去領張床睡啊。」護士提醒趴在病床左側的阿香老公。他們倆這才知道床是要去領的,壹張床壹個晚上10塊錢。原本還以為別的陪床都是自己買的或者醫生發的,他們也沒有好意思問,現在想想鄉下人真是愚笨得很。可憐阿香的老公,熬了18個夜晚才睡上7個晚上的好覺。
「大姐,妳出院了嗎?出院了告訴我們啊。」是艾欣發來的語音,阿香沒回她。
住院第23天,阿香拆線了。
「現在,我可以出院了吧?」阿香問醫生,住院讓她心煩。
「妳那麽急著出院啊?妳想出院就出院吧。」醫生道。
得到醫生的準許,阿香高興地打電話轉告老板。
老板說後天開車來接她出院。
(七)
出院後,阿香覺得還是待在醫院好。以前穿得再靚,在別人眼裏,只是壹個陌生人。現在,不管走到哪,別人都會盯著她看,他們的眼光告訴阿香,他們看到的是壹個殘疾人。醫院裏沒有人會盯著她看。後來,她門也不敢出了,只待在廠裏。
偶爾去車間,跟同事聊聊天。同事看她傷勢嚴重,納悶受傷那天機器上沒有血跡。阿香哪裏知道呢,她根本沒有註意到這些。同事猜測是機器太熱,肉都烤熟了,哪裏會流血。
「妳是廠裏受傷的第三個人。」在廠裏做了9年換模具的師傅說,「每三年就會有壹個人受傷,妳是最嚴重的。」
師傅說,很多機器壞得沒法修理好,但老板還是讓他繼續修,他也無能為力。5號機可能就是其中壹臺有問題但仍在使用的機器。
看著本來好好的阿香,現在卻失去了右手,同事們露出了同情的目光。
「真可憐啊,以後怎麽辦哪。」他們說。
腫得老高的右手臂,阿香很擔心,她問老板是否要去醫院檢查壹下。老板說吃點消炎藥,消腫就好了,慢慢來。
「老板,我想回家了。」阿香說。
「那妳回去吧,等我有錢了會把錢打妳卡上的。」老板答道。
家裏人勸阿香暫時不要回來,到時候廠裏不認賬,可就不好了。阿香想想也是,她還是在廠裏的宿舍住著吧。
住了兩個月,老板來找她,說她待在廠裏,生意難做。
「本來昨天招了壹個人,看到妳受傷了,今天就不見人影。」老板嘆了口氣,「這樣吧,我在外面給妳租個房子,吃飯的話到廠裏來打飯打菜。」
「我受傷了,沒法搬家。」阿香囁嚅道。
「沒事,我幫妳搬。」老板說。
就這樣,阿香搬到了外面。
(八)
住在外面的阿香不踏實得很,心想老板是不是不認賬了,是不是不會給她任何賠償了,她越想越覺得事情不對勁。這才打電話給艾欣。
艾欣問她有沒有簽勞動合同,她說沒有;問她有沒有工資條,她說沒有,「都是發現金的」;問她有沒有工作牌或者印有公司名稱的工裝,她也沒有。
「讓妳們老板開個帶公章的勞動關系證明,」艾欣教她準備申請工傷資料,「或者其他同事的證言也行。」
阿香去工廠找老板,找了幾次都不在,打電話也沒人接。有壹次,老板的表妹對她說——
「我們問過律師了,按照國家的標準賠妳15萬,妳要就拿,不要的話壹分錢都沒有,不要就走人!他不會同意給妳蓋章的!妳要申請工傷的話,他就不理妳了!」
在此之前,阿香從來沒有想過要跟老板翻臉,畢竟老板待她不錯。可是現在,他不接她的電話不出面說句話,在他們眼裏她的壹只手這麽不值錢,實在令人寒心,鬧翻就鬧翻吧。
「我要搬回廠裏。」阿香說,他們當然不會讓她再搬回去。
阿香覺得自己被老板騙了,是房東叫她交第二個月房租的時候。她看到老板的「狠心」,是她去廠裏打飯,煮飯阿姨說沒有她的份的時候。
在房東的催搬聲中,阿香在老公工廠附近租了個單間,方便老公過來照顧她。
老板的電話無人接聽,人也找不著。老板的爸媽無奈的表示,他們也沒有辦法。阿香舉起右手臂,讓他們看截肢處——
「這兩個骨頭長得比手腕處的骨頭還大,碰到還會痛」,阿香說,「我之前還以為是沒消腫。」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麽。」兩個老人說。
阿香只得自己掏錢去醫院復查。主治醫生見到她,「讓妳出院壹個星期後過來復查,怎麽三個月後才來?」
阿香哪裏知道,根本沒有人告訴她。
「出院小結上寫得壹清二楚,妳都不看嗎?」醫生搖搖頭,給她開了壹瓶按摩油,叫她經常按摩,「剛長出來的骨頭是軟的,揉揉會消下去的。」
阿香根本不知道什麽是出院小結,因為出院手續是老板過來辦的,病歷資料都是他拿的。原來老板早就狠心了,她怎麽這麽傻。如果出院壹周後去醫院復查,做了康復治療,她的手就不會像現在萎縮得厲害,經常怕冷疼痛。
阿香去勞動局申請工傷,工作人員說「妳什麽資料都沒有,怎麽申請」。她沒有勞動關系證明,沒有病歷資料。她只得再次打電話給艾欣求助,艾欣看在電話裏溝通不清楚,叫她來樂行辦公室咨詢。
阿香給老公打電話,叫他和她壹起去樂行。老公問她真的要去嗎。
「去啊。如果真是騙子,就讓他們騙吧,我們只剩這條命讓人騙了。」阿香真的別無選擇了。
到了樂行辦公室,阿香看到了很多像她壹樣受傷的人在咨詢。艾欣過來招呼躲在老公背後的阿香,她膽怯的眼神讓艾欣心疼。
經過兩個多月的奔波,2017年1月13日,阿香的工傷鑒定下來了。根據《勞動能力鑒定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等級》國家標準,經鑒定,勞動功能障礙等級為五級。
接下來,又是壹輪開庭審理流程等待著阿香。
(九)
在樂行機構見到戴義肢的人,阿香會害怕,她不是害怕他們,她害怕的是義肢,摸上去涼涼的,沒有體溫,像是死人的手壹樣。
秋天的時候,阿香也戴上了義肢。她不喜歡戴著它,戴義肢的感覺像是下雨天赤腳穿了水桶鞋壹樣,厚重得透不過氣來。又像是手上綁了個什麽東西,做什麽都不方便。晚上睡覺的時候,阿香把脫下來的義肢放在床邊,如果半夜醒來,看見壹只手,會嚇死她的,她把義肢放進紙箱,塞到床底下。
老公來看阿香的時候,阿香把脫下的義肢放在壹旁,問他害不害怕。老公沒吭聲,她也不知道他害不害怕。
阿香想找份工作,不管多少錢,能有人要她就行。壹次在路邊看到工廠招工,她鼓足勇氣,怯生生地問了壹句「妳們還要人嗎」,對方看了她壹眼,說「不要」。那個人的眼神告訴她,是沒有地方會要她這樣的人的。
後來,她與在樂行結識的工傷工友結伴去了殘聯。有兩家通過殘聯介紹的面試,也沒應聘上。被拒絕的原因是:壹家說她文化水平不夠,小學三年級的學歷無法勝任文員的工作;另外壹家汽車生產公司說只要男性不要女性。
就在阿香準備放棄時,2017年6月份,阿香通過殘聯找到沃爾瑪的迎賓工作,每個月1600-1700塊的工資。
阿香不喜歡和「正常」的同事聊天,除了唐大哥。失去半條手臂的唐大哥,是和阿香壹樣的人,所以她喜歡和他聊天,願意與他成為朋友。
阿香在沃爾瑪工作三個月後,唐大哥因為受傷的手臂無法忍受超市的冷氣而辭工了。唐大哥說他在超市工作九個月瘦了20斤。阿香說,受傷的人受不了冷氣,別人覺得溫度剛剛好,他們覺得冷得要死。
2017年12月5日,阿香拿到了終審判決,判決工廠於十日內賠償53.8萬。阿香以為總算可以松壹口氣了,工廠卻以沒錢為由拒絕支付,她只得開始維權和新壹輪的等待。如果不是有艾欣的幫助,她都不知道該怎麽辦。
漫長的工傷賠償申請和維權過程,讓阿香害怕又無助,她害怕拿不到賠償,她不知道以後的生活怎麽辦,沃爾瑪的工作能做多久?她罵自己為何當初不相信艾欣,卻相信老板。如果真的拿不到賠償,她就用自己的命抵老板的壹條命。可是轉念壹想,要他的命容易,要他殘廢卻很難,那取他的命有什麽用?他完全不能體會自己殘廢的感覺。就算拿到了賠償又能怎麽樣,「我的手也長不回來了,我還是個殘疾人」。
(十)
2018年3月27日,阿香在《執行和解協議》上簽了字。她同意工廠賠償46萬(法院判決工廠當日支付20萬,剩余款每月支付1.5萬直至付清),她不想再為比法院判決少七萬多的賠償金堅持下去了。她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來維護自己的權益,這兩年她每天度日如年!她撐不下去了,她快要精神失常了!她好累,只想早點結束這壹切!
即使拿到了賠償,她的生活也不能像從前那樣了。
受傷之前,阿香下班後會和朋友壹起出去玩。受傷之後,朋友找她聊天,沒說兩句,阿香就懶得理人家了。她不喜歡別人問受傷的事,她不想讓他們知道太多,她怕朋友們心裏嫌棄她,看不起她。所以,她從不在朋友圈發任何關於受傷的事,她會選擇發微博,因為微博上沒有壹個老鄉。所以,家裏的親人和朋友們,聊得越來越少了。有什麽不開心的事情,她會去樂行機構找艾欣找工作人員,聊完就高興了,那裏變成了她的娘家。
前不久,阿香聽說唐大哥生了壹種不能走路的病,只能拄拐仗。
老天怎麽這麽不公平,讓他早早失去了手臂,現在又不能走路了。老天真的太不公平了,就不給人壹條活路了嗎?阿香想。
每天下班後,阿香回到出租屋會花兩三個小時做衣服,她花了300塊錢在網上買了壹個電動縫紉機。手受傷之後,衣服做得沒有以前好看,她想能穿就行。
現在的阿香不再害怕義肢,但是觸摸義肢的話,心裏仍會不舒服。她很少佩戴義肢,除了去老公的工廠那邊,因為那裏老鄉太多了。
現在阿香用筷子吃飯的左手,已經很熟練了。但是,如果突然來了壹個老鄉和她壹起吃飯,她夾菜的時候總會掉。她去老公那邊,如果老公的姐姐和他們壹起吃飯,她拿筷子的左手也會變得笨拙。
2019年的春節,阿香仍不想回老家。
晚上做夢,夢見回到家鄉,朋友們向她靠近,她緊張地把右手藏到背後,又拿了出來,她的右手——長出來了!她太開心了,她的右手長了出來!好像她的右手壹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