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專題之二】資本主義需要你失業!

編按:在反修例運動和疫情影響下,香港的失業率不斷上升。失業本身是一個社會產業轉型造成的結果,更為資本提供後備勞動力。但政府施政卻強逼個人承受,用綜援的污名和極低的金錢為失業人士「續命」,以並不能夠保就業的抗疫基金搪塞社會對恆常失業保障的需求。
文/洛石
隨著疫情在全球蔓延,病毒帶來的生產和消費停滯亦帶來了更廣泛的危機。
四月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表示,全球經濟「幾乎肯定已經進入了衰退」,伴隨著衰退而來的是破產和失業的大潮。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的報告指出,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了全球81%的工人,並將在2020年的第二季度減少6.7%的工作時數(相當於減少了1億9千5百萬個全職工作崗位)。
經歷「反修例風波」和肺炎疫情爆發,香港的失業率已經從2019年初的2.8%上升到2020年第一季度的4.2%。若考慮到大量被減少工作時數或被迫放無薪假等未被納入失業數據的情況,香港實際的就業狀況實則更加嚴峻。
雖然目前香港不算世界疫情最嚴重的地區,亦不是封鎖政策最嚴格的地區,但香港的打工者必然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當中最無助的一群:當美國領取失業保險金的人數一再突破新高(近2650萬人登記失業),香港的失業者只能指望綜援救濟(詳見蹲點關於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評論)。
失業:是資本主義的陰謀,不是個人問題
失業在香港一直被視為「個人問題」:如果被人炒多半是個人工作能力不足,如果搵唔到工亦應該是個人「不夠quali」,或是懶,或是眼高手低,「人人有工返,點解你冇?」既然失業是「個人問題」,那麼應對方式也想當然是個體化的:你應當勤力,要不斷提升自己,在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則應當接受現狀,不可好高騖遠。
但只要不面臨危機事件,失業就只是「個人問題」嗎?
事實上,即使在經濟騰飛的黃金年代,香港也不是「人人有工返」(香港在1989年錄得的最低失業率為1%)。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香港的產業結構調整,製造業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比例從80年代初的40%左右降到2019年的2.3%,而服務行業的就業人數則持續增長。一個長期存在的「產業後備軍」(reserve army of labour)服務於這樣的產業結構轉型,被排斥在就業市場之外的一批人被用作「蓄水池」,以保證永遠有勞動力可以被隨時調配到不同的行業位置。「失業」對個人生活而言也許是災難,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流暢運行而言卻是必須,換句話說無論個人是否甘願,「失業」總是無法避免。
在自動化和科技化的背景下,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沒有縮小反而是不斷擴充這個勞動力的「蓄水池」:一方面去技術化使大多數工人的可替代性越來越強,另一方面,零工經濟(gig gconomy)將越來越多的工人從穩定就業驅逐到零散就業。除了少部分的技術精英,越來越多的工人淪為可以被資本隨時取用亦可以被用完即棄的「剩餘勞動力」(surplus labour)。
疫情,或是其他社會或者經濟事件,並不是造成這些問題的罪魁,它們只不過是將原本就蘊藏在這套系統之中的危機暴露出來,讓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工人被剝奪的狀況。
以救濟支援失業:污名化失業勞動者
失業既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結構性問題,那麼就需要制度性的應對方式。然而,香港政府和商界一直極力反對建立恆常的失業保障制度,堅持剩餘型(residual)的福利模式,以救濟而非福利提供定位社會保障系統,認為政府只有在市場和家庭都未能發揮作用的情況下,才能介入並提供最低保障程度的「安全網」,「慷慨」的福利只會減弱基層的工作動機,浪費公共資源並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
政府的這種福利觀念亦進一步影響社會觀念,進而使「失業」在作為勞動力「蓄水池」發揮作用的同時,進一步污名化失業勞動者:配合嚴苛的入息審查制度和就業培訓計劃,大多數的救濟政策都帶有強烈的社會污名,而這樣的救濟政策在社會研究者看來是在製造一個「被遺棄」的階級,將一小部分人設為樣板以警示社會大眾,使工人甘於接受惡劣的工作條件和高強度的剝削,因為總有比艱辛的工作更糟糕的生活。
在香港,綜援就扮演著這樣的角色。樂施會在2009年開展「香港市民對綜援態度」意見調查發現,超過一半的受訪者(54.9%)認為大部分申領綜援的人士都是失業人士,有近七成受訪者(69.3%)認為「綜援會減低受助人的工作動力」。而事實上,失業綜援的申領人數僅佔整體申領綜援人數的5%左右,綜援的保障程度(單身健全人士每月2525港幣)亦遠不足以保證受助人的基本生活,削弱其就業動機。
疫情之下,失業率上升,政府先後出台兩輪「防疫抗疫」計劃都以「撐企業、保就業」為基調,無論民間呼聲如何高漲,政府仍一味拒絕推行失業援助計劃,將失業人士推給綜援。然而,無論政府官員如何虛偽地辯稱領取綜援的失業人士同樣「有手有腳、有骨氣,更是能屈能伸」,暫時放寬資產審查標準並不改變綜援作為一項救濟政策的本質。綜援提供的微薄資助以及其對失業人士連帶的所謂「自力更生支援計劃」本就暗含了對失業人士的歧視,政府不對綜援的制度設計反思,卻呼籲社會大眾應對綜援「去污名化」是何其偽善。
說到底,政府無論如何也不願意承認失業其實是一個「社會問題」,而不是「個人問題」,這背後不僅體現政府不願意突破「小政府」的作派,更反映它保持「港式新自由主義」,使「失業」持續發揮起「蓄水池」和「警世鐘」的作用,削弱工人面對資本的談判能力的意圖。
失業保障靠什麼建立?
失業率上升暴露出一系列社會問題,並引發廣泛的社會危機,這誠然為社會變革帶來契機,但就此坐等政府「紓困」,自動自覺出台有利勞工的政策,未免太過天真,尤其當這個政府是回歸後亦不改「殖民政府」作派的香港政府。
03年SARS和08年金融海嘯之後都曾有勞工團體呼籲建立恆常的失業保障制度。
近20年過去,特首換了幾輪,而政府對於這一制度的回應卻保持了令人驚嘆的一致:失業援助金涉及大量行政程序,政府需建立新的系統、招聘新的人員、建立新的機制方能處理,屆時事過境遷,「遠水救不了近火」,不如「罷就」。
二十年,高鐵建得起,跨海的大橋修得起,移山倒海的工程都做得,唯獨勞動保障的工程做不得,甚至連藉口都懶得換個新的!
兩輪「防疫抗疫」措施涉及2000多億公帑,香港政府儼然認為自己已經躋身「最進取」政府行列,然而「大市場」的施政邏輯不變,多少億公帑花下去也不過是「撐企業」,這樣的政府既無意願也無能力去解決最基礎的民生問題。
回頭看看,香港政府但凡出台影響民生的社會政策總是被動的。社會通常認為「六七暴動」是香港政府介入社會福利的轉捩點,當時的罷工和示威運動暴露出了社會不平等和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反抗運動進而迫使70年代的殖民政府推出一系列的民生措施,包括修改勞工法例改善基礎勞工保障,推行九年免費教育,甚至成立廉政公署等。亦有研究者指出,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當時的殖民政府本就有意有限度地推進福利政策,「六七暴動」只不過是為政府平息來自本港工商界的反對意見提供依據。而到七十年代,殖民政府之所以有動力增加開支、改善福利則是因為受到來自於英國工黨的壓力(香港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壓低了產品價格,提高了香港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而相對應的則是英國工業陷入低谷)。
無論原因為何,香港政府在這些政策的推行過程中都被認為是被動反應型的。
回到當下,既然寄希望於一個「進取」的政府是幾乎不可能的了,那麼改變的動力又可以來自哪裡?香港基層勞工組織化程度不高,雖然一直有爭取改善社會保障的社福團體和工會組織,但一方面工會有「去政治化」的取向,另一方面社會動員又面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強力挑戰,組織的動員力量始終有限,在政治上難以施加足夠的壓力。
2019年年尾以來,因支持「反修例運動」出現了一大批的新工會,2020年1至3月即有1578宗新工會登記。這場因政治運動而蓬勃起來的「工會運動」似乎讓我們看到了勞工運動的一線生機,2019年六月以來這場尚未結束的政治抗爭是否能通過這樣的「工會運動」找到新的抗爭領域,「海嘯式」成立起來的工會在爭取失業保障(以及其他勞動權益保障)的領域亦發揮出「海嘯式」的動員力?
關注我們:
獨立傳媒:https://www.inmediahk.net/user/532398/post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squatting2047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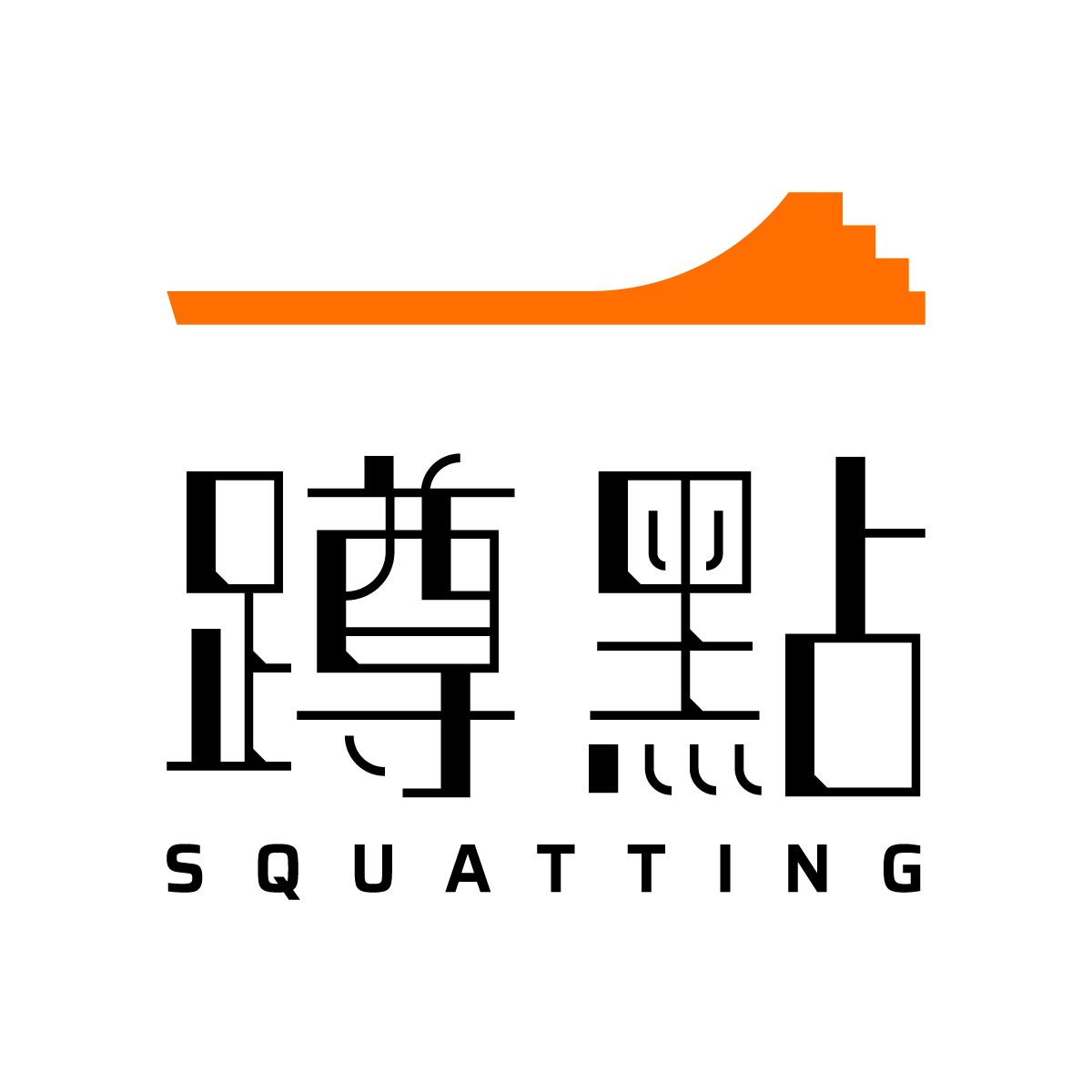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