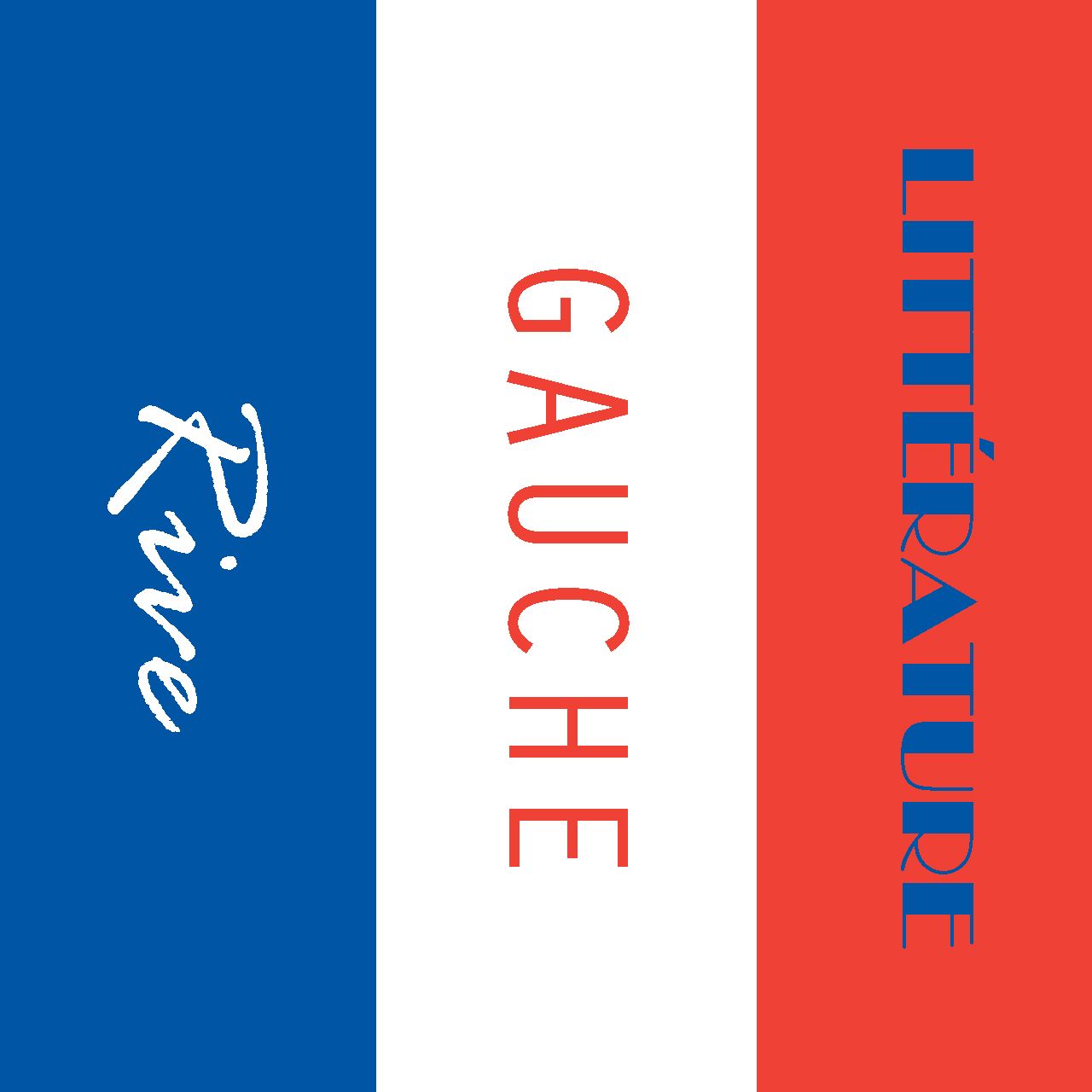随笔/一个左翼人士的自白:我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

一个左翼人士的自白:我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
文/林伯奇
图/"Film Socialisme", Jean- Luc Godard, 2010, Vega Film
全文 共计6114字/预计阅览时间 20分钟
在没有船的文明社会中,梦想枯竭了。侦查代替了冒险,警察代替了海盗。
米歇尔·福柯
在最近的很多谈话中,我常常地跟朋友说起一句话:我们的文明正在衰亡。
这样的话,很难不让人不想起那位写出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德语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他临终时的感言。茨威格的一生是属于维也纳与欧洲的一生,而当他踏足在巴西的土地的那一刻开始,他就相当于半条腿走进了自己的坟墓;一九四二年的他,会说出自己的母语与祖国已经被野蛮和残暴蹂躏至尽,自己的精神家园已经被毁灭,自己孤身一人流落异国他乡,为故乡的沉沦而痛心,会以完全的理智怀念那昨日的世界来服下药丸已经是一个被预见的事情。
这样的一篇文章,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写好,因为就如题目所言,二零二零年五月的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这篇文章里你完全不会见到上个世纪的理想者提出的革命乐观主义思想。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建立在完全的pessimism上。那么,我就以这一句话为本文开头吧:我对未来世界是感到悲观的。
这些年来,我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是非常迅速而无常的,用一位老友的话说,我如同一阵龙卷风一样;于我而言,这是一个人从少年成长到青年的过程,是一个慢慢揭开这个世界的面纱的过程,又或许是一个戳穿这个世界——我自己给我设下的谎言的经历。这个世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我不断学习的过程之中,这个世界的一切也在不断变化,最终在种种物质上的社会关系的变化造就了二零二零年的我。直到二零一六年,我还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会为对台进行网络出征摇旗呐喊,会和人一起谴责所谓青年领袖——我记得二零一六年的我还会认真地写入团申请书,然后把团徽别在自己的衣服上甚至是帽子上——万岁,英雄的民族!万岁,不朽的祖国!青年们!青年们!多么美好的青春时刻,愿借歌声欢度青春!说着我越来越想笑,如今的各位绝对不能想象这样受人排挤的我在若干年前受爱国主义的动员时的样子。到了二零一六年的年末,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与事情,直接促使我加入了自由主义的俱乐部,并维持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将近三年的时间,在这三年期间,我也只是在自由主义的各个流派之间徘徊,先是改良派的自由主义,后来是雅各宾派的自由主义,再然后民族解构思维下的新自由主义。在这个期间,我一度信仰了宗教甚至是为之狂热——那一段经历,如今在我与友人的谈话之间已经变成一段近乎是黑色幽默喜剧一样的经历存在了。
从自由主义者与宗教信徒到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与无神论者的转变过程是非常微妙的。脱离宗教的源头是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子的生活有什么意义么?神像并未移去,只是从物质上的神变成了心理上的神,这种靠反智主义与虚无主义建立的,通过消灭生活的战斗性与进步性所得到的幸福有意义么?就这样,我宣布了自己不再信仰任何神,但我仍然保持着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宣布自己成为社会主义者发生在二零一九年的夏天,在左翼的朋友的接触和影响下我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康慕尼斯特派对宣言》。吸引我的不是在于类似于八小时工作制或是提高工作待遇这样的口号,而是我在左翼人士身上看到了一股耀眼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宝贵的,是来自于一个光辉的时代的伟大精神,是“爱与死亡”的精神的延续。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我看见人类脱离抽象走向真实的希望;看到了人类可以完全走出父权制、神权制、资权制的曙光,看到了人类集体解放的可能。
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要谈什么方面呢?与茨威格的时代比起来,我们的世界变了太多,又好像什么都没变——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尽管极力否认,但事实上一直生活在一九六八年发生过的一切的影子之下。内卷化、威权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让大学与大学生不再拥有过去的神圣属性,大学不再是象牙塔,大学生也不再是拜伦笔下的Childe Harold;再也没有了工人以五人为一组行进的稳定秩序,军警宪兵报以友善微笑的游行,取而代之的是布满砖块、“鸡尾酒”和溴化二甲苯气体的大规模冲突;茨氏本人的欧洲一体化理想似乎已经实现,然而又要分崩离析。我们——作为经济全球化第一代青年,一出生就在泥潭里面爬行,然而如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要把我们曾经生活过的世界给撕碎了。我对朋友说:造反、瘟疫、饥荒与物价上涨、国家经济猛烈下滑与货币贬值、战争、流亡,如今我们已经把曾经一个家族三四代人的时间要经历的事情用一年时间都给经历了一遍。我们的时代的文明已经几近毁灭了。
或许一九九七年的人们,看着美俄共同建立的国际空间站计划发射升天时的心情,与第一次看见齐柏林伯爵的飞艇上天的茨威格的心情可能是一样的。如果要那些欧洲的传统文人们,那些在巴黎和维也纳受各种高雅文化熏陶成长的文人们来看我们今日的消费主义文化,不知他们会有多吃惊啊——可能还要指责我们今日的文化都是一堆狗屎呢。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贫瘠多年的国家与民族来说,消费主义带来的一切已经足够丰饶了,这就好像在西方世界被视为垃圾食品的快餐能够成为非洲饥民的美味佳肴一样——只是如今消费主义文化也在遭受沙文主义的污染。
或许,选择社会主义是我对这个世界进行的最后呼喊。我在这里要说明白的是,在上个世纪里,有两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人类命运的轨迹,并影响至今:一个是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另一个是美苏冷战。这两件事情使我们的世界一直在“罗生门的悖论”里循环往复;用直白一点的话语说就是天天在比烂。权威们在互相比烂,人们也在互相比烂,比谁更没底线。没有人愿意墨索里尼的鬼魂回归人间,于是所有人都竭尽全力地去围堵它——上个世纪里我们的世界里分别发生了越南战争、巴黎五月风暴、“布拉格之春”、苏联-阿富汗战争,时代的车轮没有停止旋转,在一种混乱当中世界得到一种巧妙的平衡;也许这是人们在用小的灾难来抵御大的灾难来临,毕竟“婴儿潮”族群本身就并不在一个文明的环境里出生,出生在黑暗当中,意识上先天失明,那么在他们未来与强权的对抗中毫无疑问地会肆意地乱挥自己手中的棍棒。在彻底砸烂了过往时代的文明的二十世纪过去,冷战结束之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全面发展,一切都看起来是欣欣向荣;又是一个太平盛世。我常常想象,未来的历史课本里会如何形容这太平盛世呢?是用“和平的三十年”(1990-2020)这样的话来形容吗?
又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这所谓的太平盛世,这不过只是我们这些享尽新自由主义红利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厢情愿罢了。苏联解体后不久,南斯拉夫就爆发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一,这场战争震惊了沉睡多年的欧洲;随后便是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而我们,这些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只是吸吮咀嚼着另一个世界的不幸,五大洲的野心家们肆意地满足自己的贪婪与财富欲望,我们这些普通人就像瘫在剧院座位里的观众一样,这一幕幕悲剧变成现实,我们还在放声大笑着,然后给予那点微不足道的怜悯,咀嚼他人的苦难来满足那名为“民族主义”的贪婪,直到我们自己变成了舞台上的存在(当难民危机席卷欧洲时,有谁真正关心人民?难道在二零一六年不正是中国的沙文主义者们担任了唐纳德·特朗普在亚洲的铁杆支持者,认为一个商人担任总统好过职业政客,通过一些经济上的贿赂就能换来他的和平保证吗?),种种灾难落在我们头上,而我们还在试图用宏大的叙事来安慰自己,告诉自己那个“太平盛世”还能天长地久——所以我说我们这代人是在泥沼里成长起来的,都是一群傻瓜,我也不例外,我也只是个试图亡羊补牢的傻瓜。也许,我们只是运气稍微比别人好一点,乘着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东风(苏联的尸体),在经济上完成了从吃不饱到想着怎么减肥的飞跃,同时享受一定程度上的开放风气;很多人凭吊那个所谓的“黄金时期”,其实一切根本没有什么变化,有的仅仅是满足野心的手段变多了,古董们掌握了新科技,新瓶装旧酒,学会了穿着西装皮鞋用刀叉吃人,他们全都没有什么差别。也许大家已经忘了砸日本车和抵制家乐福的行动——罗马并不是一天建成的,凯撒并不是一天掌权的。
我们这些人生长在北上广深的幻觉里,没有那些我们未曾谋面但又日日接触的人们有的底色,只能靠购买那点可怜和怜悯来满足自己的虚荣与需求。
这一年来我已见过了无数变化,再发生什么,我或许都不会吃惊了。基督教等抽象事物的虚伪、自由主义理论的可悲软弱、波拿巴主义的日益强大与扩散、或是我同辈人的无聊趣味,这些我都见识过了。宗教是愚蠢的,那个所谓上帝带来的“平安喜乐”建立在把人变蠢的基础上,我完全不认为那个把塞尔维特烧死在火刑架上,不准人们唱歌跳舞的让·加尔文会带来什么新鲜玩意,这些宗教能做的只有拿起刀叉继续吃人,它的反智、反人性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封建君王。那个关怀穷人,同情弱者,代表公正的耶稣被父权制和封建制度的卫道士们掩盖,取而代之的只有类似“妻子必须顺服丈夫”“同性恋是可憎的”这类冰冷而抽象的教条,对教权思想的鼓吹更是可怕,这简直是让人类文明回归到极其低级的孩童模式——这尚是温情脉脉的语言,在现行秩序下这种孩童模式与奴隶制没有区别。而自由主义——如今我们的世界在发生的所有危机,都是传统自由主义崩溃的迹象,那个旧的,蓝色与黄色相间的“自由民主”旗帜与神话已经破灭——我并不是否认这个概念,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个概念恰恰不可或缺,它是避免走向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的必要之物——但传统自由派,那些被沙文主义者整天攻击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过去三十年内做了些什么么?有什么改变么?恰恰相反,既然路易·波拿巴和他的盟友们尚能为这些人留下一些话语权,那就说明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他们也什么都做不了。他们只是打打擦边球,替工厂主扭紧他们松懈的螺丝,而明天机器会照常运转,机器并没有因为几个自由主义者而崩塌,相反它运转的更好。但这与人民无关——列宁早就说过我们要的不是从尼古拉·罗曼诺夫那里得到什么,而是要从中彻底解放。自由主义带给不了人民更多的东西,包括免费全民医疗、失业补助与低价住房,带来不了人类从精神到物质的解放——甚至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他们为了那所谓的自由市场理论也可以毫不在乎。如今的社会里,即使是被视为“国家垄断”的国企也完成了市场化经营与私营化,这还不是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的理想社会么?
至于波拿巴主义和我同辈人的无聊趣味——我先前同人开玩笑说,若我那象征着封建思想的父母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确实是小资产阶级中的保守自由主义者),那恐怕现在的我早就是个铁杆法西斯主义分子。我对那所谓的当代人的“情怀”(实则疯狂的,嘴角上带着唾沫的虚无主义麻醉狂潮)没有任何兴趣,尽管我同样对那些张口就是“WG重来”表现出对我们青年不信任的父辈们感到不满,但我绝对不会低级到用世界上最愚蠢的谎言,用这所谓的共同体来充实那些真正值得憎恨与鄙夷的人的欲望。我并不想自我标榜高级——沙文主义几乎是人类文明的毒瘤,它从精神到肉体上摧残着人类,这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里发明的最狡猾而恶劣的谎言,然而荒谬的是我们的社会竟然把他当成一种高贵的品质,一种必要的品质——见鬼去吧!我的敌人有三个:父权制、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与白色恐怖,而那所谓的,来源于陈旧的封建制度好像一个坐在阴森城堡里的怪异老头般的“情怀”与我想要的完全不搭边。荒谬的是我们当代青年竟然甘愿被如此陈旧的规训所支配着并乐在其中。而比起沙文主义的狂热者,更令我感到厌烦的是那些整天鼓吹精英主义的,热衷于玩文字游戏、和稀泥和道德过家家的我的同辈人。我实在难以想象,为什么有人能一边支持女权主义,一边鼓吹“孝敬爸妈”这种充满了封建等级制色彩的父权概念;为什么有人一边支持文字的创作自由,一边从道德角度上批判游戏产品里有的明嘲暗讽(你要知道伏尔泰曾经在他为谋生而写的小黄文里暗讽了当时的社会权贵)。我们的社会能够允许妻子向她的丈夫提出离婚,却对separatism抱有绝对的零包容,这难道还不离谱荒谬吗?我的同辈人们他们还不忘记通过批判文革的混乱与暴力来论证自己的客观理性与光荣正确——而我早已厌倦了他们对文字游戏的热衷,再没有比幻想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开明专制,让一个主子诚心诚意地带领他的奴仆们成为高素质的自由人更离谱,更充满空想的事情了。改良主义在如今何止是没用,它几乎是愚蠢的,它无法砸烂神像和宝石座椅,只能维修一下沙皇的官僚机器上脱落的螺丝。就是这样,我的同辈人里坐满了诈骗犯,我也早已不打算与这样一群人谋事——或许有一天他们会被突如其来的灾难震醒,到那时也许他们还要指责我幸灾乐祸呢。如今他们自称要进行“结构性的分析与反思、变革”,无一都是发发牢骚,若我在上面提到的三座大山不被彻底毁灭,谈何结构性与系统性?当然,这群低能儿还会为下岗潮的灾难辩护,拿那丰盈的数字来论证毁灭性的“产业升级”的合理性。指望一群靠着现有体制机器飞黄腾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是我的天真。
我见证了一场又一场的绝交与离别,一次又一次的重聚与团结——对我而言,这都无所谓了。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时代选择了我成为文明的见证者。如今我们的社会里再也没有过去“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取而代之的是两拨人互相认定对方是活在梦里被洗脑的蠢货和疯子,而自己掌握了天地真理,代表着新时代的理性与光辉,为此双方要打得头破血流,又或是要把傲慢与轻蔑写在自己的脸上并坚称对方狂妄自大(若轻蔑事实存在,那敬畏有何意义?),又或是要像对待麻风病患者、女巫和异教徒一样对待异己;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但或许这已经不重要了,我只是时间的过客,并见证了这一切,见证了温和的毁灭与崩塌。我是个失败者么?或许吧。我是个狂人么?或许吧。我是个懦夫么?或许吧。但不论如何,在经历了这一切,我那玫瑰色的旧日梦想彻底被时代的车轮所碾碎,罗曼蒂克彻底被众人抛弃;尽管我们已经得知,革命并不像德拉克洛瓦的油画那般理想而浪漫,但我别无他法,将我的视线投放在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文稿上。茨威格服毒自尽时已有六十岁,而我尚年轻,我尚有力气与这个世界上的荒谬搏斗,去与它决一死战,在没有选择的同时我尚有最后的选择;而这条名为“自由主义”的大道上已是萧条破败,“此路不通”的招牌摆在我们面前,旁边写着“德莫克拉西社会主义”的小径微微地传递着生机,指引了我们对待现代文明应当以怎样的方法与态度去面对,而非就此遁入虚无,我们——人民——人类仍然有办法与出路,从黑暗中重新站起,坦然面对我们经受的苦难并实现未曾有过的崛起,去实现幸福——这是人类的崛起。我要寻求的是:人类的终极解放,没有神与官僚的,从精神到物质的彻底解放。我想要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向众神发出挑战,而我所反抗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命运与僵化的秩序,更是悬挂在人类集体之上的枷锁,去如火山喷发一般地崛起。
或许,这部小小的杂谈也是时候收尾了。相比起茨威格,我现在更想引用托马斯·曼的一句话: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我带着中国的文化。我与世界保持着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失败者。
Le vent se lève, il faut tenter de vivre.(风起了,人生还要继续。)
2020年6月20日
时岭南仲夏霞光淡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