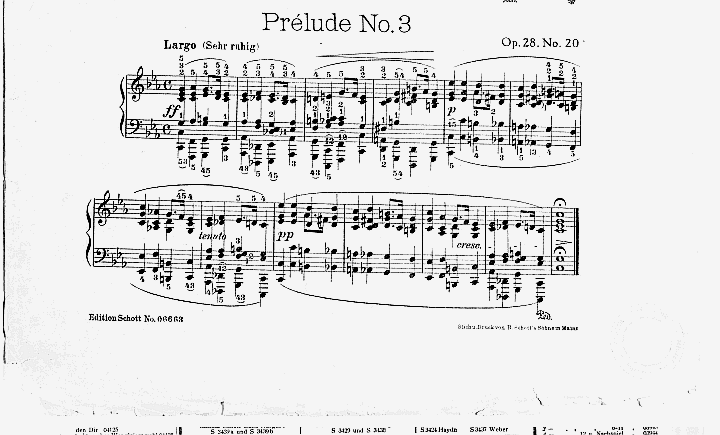色彩幻想
白,疏离,逐渐破碎的——
视线,清晰起来是卫生间白色的瓷砖背景。她嘴里咬着卷发,耳钉和汗珠闪闪发光。因为她的忙碌,因为两个人工作时间的偏差,他已经习惯了她在上厕所的时候打来视频。
“你有没有吃过鮟鱇鱼肝呀?”
“没有,那是什么东西啊。”
“他们说比鹅肝口感还好还便宜,我尝了一小口只是觉得好油。”
他喜欢这样看着她坐在厕所里享受短暂的放松时间。翘着嘴,语速很快,一会说这个一会说那个像小鸟在电线上跳来跳去。
他在大学城附近工作,住在二楼,晾衣服要到走廊那头挂在一堆雨棚上面。冬天早晨,白霜和青烟。躺在枕头上听摩托车发动机和人出发的喧嚣。路过小吃街,冬日清冷的街道拐角有小孩子追红气球。
她在蓝色的写字楼里面,颈椎疼的时候像玩弄火焰和针,下楼透透气看看街景,想起来小时候午睡醒来灰白的雨水坑,红房子和经过的滑板。
后来他们终于住到了一起,把情侣空间取名为邦妮和克莱德。她说不用每次下班都来接,有一次让他在外面等的时间有点长,他在便利店里浏览各种鲜艳的方便食品,突然感觉这种速度与混乱的现代生活也很不错,地铁到站的轰鸣能让人短暂体验失去意识的眩晕,她说地铁每一个窗口都闪动广告简直是强奸,他说靠在陌生的便利店座位上和陌生人一起吃乐吉士也很浪漫。有一次他们在商场三楼的咖啡店找到了一个可以俯瞰下面光线拱门的大落地窗,他突发奇想让她站在那个窗子中间,他跑到楼下去拍照就可以让恋人处于整个大楼面孔的中心,但是扶梯太复杂,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正对大厦的柱子,却发现建筑的反射彻底盖住了玻璃后面的幽光。两人花了半个小时才重新聚到一起,想起夜晚所剩无几都有些失落。
克莱德的第一个义体是邦妮送的,肾脏上的小组件,可以花里胡哨地监视自己的健康状况;她已经迷恋上漂亮小石头一样的的各种小改造了,手臂,闪光的脚踝,不断更新的脑机接口操作系统,但是他还是受不了她去做据说能改善抑郁的眼球手术:
“我以为你是那些数理学院毕业的弱智工程师呢。”
“亲爱的你可不必要这么批评自己~”
“但是你就是做社会学的啊,你知道那些论文都是怎么水出来,随便弄两个震撼的指标,然后剩余的所有部分就是玩弄统计学,这样那样,然后拿出来开发骗你们的钱。“
“你的意思是我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权力?”
“你知道我的意思……”
她把手里的包往沙发一甩,像是要摔门而出,走一半又回来了,一头扎进铺天盖地的网络流媒体中:
“你是斯蒂芬金的小说看多了。”
后来闹僵的时候克莱德坚决拒接她写的小作文,要求听她当面说
“可是本来两个人愿意坐到一起开放地交流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的嘛,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不想和你坐下来说了……”她终于抬起头,蓝盈盈的眼睛里的光让他不敢直视。
背靠城市喷泉,看自己的第二段故事,清冷的水花突然消失,快要天亮了。
他们都觉得两人分手又刚刚复合的那段时光最甜美,凌晨的时候两个人抱着此生不复相见的信念在公园的十字路口分开了,到黄昏的时候他从眼泪中醒来肚子饿了却错打了她的电话,于是太阳落下的时候两个人又重新抱在一起哭泣。在摩天楼顶空调外机的轰鸣中几乎听不见彼此的呼喊,她甩下披肩一遍挥舞一遍喊:
“你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对吧!“
而他却只能小声念叨,我爱你胜过一切,我爱你远胜过你爱我,然后扑上去把欢快的小鸟儿抱起来。
搬家的时候不得不早起,两个年轻人都像是很长时间没见过清晨的样子了。坐在车上,路过的街道都是这座城市夜晚浓妆褪下的残粉,垃圾堆中翻滚的床铺冲出一堆工人,像恋爱一样大口呼吸新鲜空气,酒吧和咖啡馆中毫无血色的底层程序员走出来昏倒在早餐铺前面。学生模样的闲散年轻人被政府组织起来,他们将在废弃街巷的垃圾中度过十个小时的工作,然后是宗教慈善组织的大喇叭和义务的课堂,外面的机器没有留给他们多少工作的机会,但是那些空气污浊的室内维持着十八世纪修道院的工作模式,只是城堡换成了大型电脑的机房。没洗脸就跑操,然后休息日用复合酒精饮料的狂欢换来持续几天的头痛,现在在街边列队用麻木的颜色看着他们。家具搬入空房间激起尘土抗议,邦妮放下包先去上厕所,他也跟了过去,笑,习惯了。
是冰水永远洗不干净的黏腻感,夏天都市的暴雨年复一年地刷新记录,雨水铸成海浪,把城市角落漂浮的恶心垃圾冲刷到大人物眼前。克莱德从来不放过浑身湿透回家的她,总是用亲吻盖满每件散发尸体遗憾气味的制服。邦妮又给他买了“风沙星辰”的个人定制套餐,他欣然接受个人意识和智能设备的融合——如果说有一天不得不这样,他很愿意用一副借来的身体去爱她的。
他缠着问工作上的事情,她吐出一堆脏话之后轻松的说:
“像我们俩这样的人完全不用烦恼这些蠢事。“
“你真的认为我们俩可以单独分割开来对抗全世界?“
“不然呢……别管白天的事情,现在只有我们俩,和热恋时没有任何两样”
我们在车上晃动身体,装出一副还在前进的样子。克莱德在等待室看杂志上的笑话消磨时光,逐渐变圆的身体摇动了一整排长椅。她容光焕发地走出来,完全置换的半个面孔和一只眼睛都美极了。她可以把嘴唇放到机器上涂口红了,他想着都感觉性欲高涨,邦妮踩上强化钽合金脚踝,好像回到了那个长袜校服的女孩子,膝盖都是光滑的。
即使是在两人冷战的间隙,他们还是会惊叹彼此一直走到现在的陪伴。城市啊城市,命运啊命运,第一次,梦见的不是牙齿而是头发脱落,沙漠中脱水的战士,长长的飘带在风中鲜艳,那里有一栋白石碉楼,有四个楼梯可以上去。他们出去散步,高架桥下,潮湿的黑糊糊的马路,她穿着裙子奔跑在上天桥的楼梯之间,凉鞋的鞋跟发出清脆的声音,因为兴奋跑来跑去。
他失业了,发烧躺在床上,女孩子端茶送水,昏沉的橘色光晕中看见她少女的脸庞。时常梦想邦妮才是那个拯救他的朋克少女,穿着黑靴子和紧身衣一脚踹开他昏聩的原生家庭……但是现在她再也不化哥特妆容了,棒球棍也丢在了那个有繁复美学的年代,打卡,打卡,穿上制服,打卡,刷脸坐电梯,宏大的公共交通系统,隔着车窗看梦幻公园的全息雕塑,最终还是无法躲避回家路上一百米的风雨,打卡,进门。他贪恋她的一切啊,奏鸣曲,应该把她被置换的血肉之躯捡回来的,他愿意到城市最肮脏恐怖的垃圾堆里面去翻找。咀嚼她锯下来的小腿的皮肉,把她的胫骨做成笛子,等她躺在沙发上的时候演奏爱者之歌。
自然,也走到尽头了,这个世界在变,完全不顾我的感受,所有的居所工作都遥远干净巨大的白色墙壁。遇到恶心的人就离他远点吧,每个讨厌的或者潜在危险的人都可以原谅,破产时那种要回到闷热恶臭的人群里的恐惧压倒了其他担忧。你要爱生活呀,但是在冷淡的街道冷淡的房间里,意识到我神圣的幻象居然建立在同样弱小的彼此身上,意识到拥抱在一起的人永远无法相互理解……
邦妮在洗澡,他冲进去要一起洗,要吻她的时候被推开。他弯下身子发出短促的声音,疯狂地自慰,她双手像鹰爪一样插入他的头发,冷漠和悲悯混合的眼神。他终于射在了地上,她像水蛇一样蜿蜒下去,舔掉了地上所有意乱情迷的精液,等到抬起头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
只有水声。
二
红,粘重,灼热的伤——
小指和半个手掌从焗饭铁盘边缘跳开,她低头咬住嘴唇才没有发出尖叫。她蜷起身子狠狠地咬牙忍住了第一波疼痛,没有给同桌的混蛋留下一点失控的表情,那些人还在讪笑着没有注意到一切——就像小学足球课上被皮球击中下体的男生,也是这样迈着章鱼一样的奇怪步子走几米,然后缩成一团慢慢落地的——
冰水冲不掉恶心的感觉——一想到自己刚才还忍着痛楚起身说抱歉然后直奔洗手间但是桌上的傻逼都没有注意到她刚才的烫伤。流水能产生麻痹疼痛的幻觉,她看着自己苍白浮肿的伤口有种在冲洗腐烂贝类的感觉,可以想象那些精致皮肤很快就会长出水泡,然后被耐不住性子的女人自己挑破,然后就能看到纱布底下流出褐色的腐烂液体。 她一点都不陌生,她十五岁的时候就是这样看着二哥手臂上一天天的变化,坏死的伤口逐渐和玫瑰纹身混在一起,坏疽和花瓣纠缠无法分别——
香精和腐臭的气味,傍晚墨西哥人焗饭的烟气,童年点点滴下的恐惧……
你爱力量吗?你见过资本巨大的盲目的力量吗?像台风或是一只抹香鲸一样不顾任何野蛮人的祈祷,挥挥手就可以让沼泽变成大楼或是山峦变成湖泊,然后又毫不在乎的游向下一片利润的海洋,完全弃之不顾。邦妮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资本巨人的玩具里长大的,楼房,以楼房作为景观的楼房。一个黄灰色的巨型建筑,从空中俯瞰呈U形的超级放大版苏联风格筒子楼,从成千上万的房间窗口望出去一大半的天空都被一模一样惊恐的公寓占据。楼宇圈出来的先是公园绿地然后是篮球场然后是停车场最后变成帮派管辖的介于黄土和市场之间的生物。未建成的现代化建筑中住着一群前现代的移民大家庭,小时候她天天在楼下玩耍,以至于第一次被哥哥带到海边直接哭了出来,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天空。
“怕啥,笑死了,走哥哥带你去吃好吃的。”
二哥说这是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画面之一,那时候大姐已经出嫁了,二姐周末发工资从工厂回家还要被奶奶搜身,大哥天天忙着帮派里的琐事,有时候一身伤回家,有时候又提着街上最昂贵的大蛋糕。她和二哥缩在衣柜里用一个做活动送的音响听第九交响曲,被弟弟哭声惊醒的妈妈进来笑着拽她的头发。
我的色彩,绿色露背的优雅裙子,她走出厕所的时候在想一些奇怪的东西,和木管乐器很配,都是弦乐暴风雨和巨浪之间俯冲的海燕。走出厕所,橙色的舞台上一个女孩在表演。
歌手蹦蹦跳跳唱起来,绿色的裙裾——她怎么可以那么可爱,是吃可爱长大的吗?
“噢那时我是一个法外少年,
忧愁从不曾爬上我的心头”
歌手洁白干燥的妆容能够给这个昂贵的宴会带来清凉,她想——看着她耳边的留置注射接口,为这个少女早早摆脱了愚蠢的生物技术游戏高兴。如今所谓的贵族学校都赤裸裸地标榜先天血液的纯洁,限制招收后天改造强化的孩子,那些中产阶级的子女只好忍受一次次奇异痛苦的非规范注射。
但是所谓的纯洁也就是我的救命稻草,从那个郊区大楼里居住的腐烂部落中逃出来的唯一绳索,学习,我的身体像出生时一样赤裸,而大学在招收特长生。鼓点,紫色,熬夜学习和荒淫的生活很配,父亲打二哥的时候说他自私没有出息一点都不为家里着想,二哥后来不回家了就打妈妈,后来被大哥和弟弟联手揍了一顿才老实。那时候他们搬到了大楼拐角的套间,有一间隔壁的房子是把墙打个洞进去的。她要穿过走廊在有机玻璃做的平台上晾衣服,旁边排气管里喷涌着不知道多少个楼下房间的恶臭,妈妈受不了这种发酵的有机胺味,非要往被子上洒花露水。她睡在这种恶臭和香精混合的被褥上总是祈祷,让我到城里去吧,到现代化一切都干干净净人们没有区别的礼貌的客厅里去吧,我受够了每一个藏污纳垢的角落开出来繁复的恶之花。二哥越来越瘦,纹身和身上打的孔那么多,总是穿着紧身的绚烂的衣服从酒吧出来,洗发水的月桂酸和恶心的硅油味道混在一起,让她的拥抱越来越迟疑。是的,就是你想的那种润滑油,还有用鼻子吸入的致幻松弛剂,他会得病的,小伤口溃疡脓肿,背上长出石子一样的硬块。她知道他会死,也许不能看到她上大学的一天,但是即使二哥活到了那个时候她也绝不可能回到这个地方对吧。兄妹两在黄昏的时候坐在屋顶斜坡分享一瓶烟草味鸡尾酒,她会想起来童年的蹦蹦跳跳,用粉笔在晾衣架之间写:
——Of what a path I choose to come back to you?
所以成长在她看来就是来自不同山谷的年轻河流汇到大都市的激流之中,彻底把坎坷的多样性抛在脑后。世界一直在变,人们越来越无聊,所有的人都进入同一个空旷的闷热的世界而无法回去,建筑只有在瓦砾中才得到和平与休憩。邦妮会羡慕怨恨那个失踪已久的前男友,他能够看着爱人在怀中安然入睡,而漫长的缺乏睡眠的女孩只能说着朦胧的梦话——衰弱,睡眠的奢侈是晚宴上这群中午才起的蠢货不知道的。
衰弱,放射性的疼痛,低头时裙子的吊带勒出红印,早晨起床的时候雾气蒙蒙,捡垃圾的人像老鼠一样躲避人影。那是她的青春时光——每次醒来都像吸毒的人一样,对阳光和鸟鸣和昨夜回忆全然麻木,而关节的每次摩擦,每一股香精和润滑油的气味,想象中人群推搡,连地铁上油亮的秃头全是刺痛肉体的针。我的城堡,我的一半残缺一半改造的肉体——她熟悉还留着的和已经被摘除的每一寸肉体,她能娴熟地控制每一束神经,然后去思考,奔跑,深恶痛绝的女足。她作为所谓的自然人特长生进入大学,然后理所当然地加入学校女足队以获得奖学金。她后来当了女足队长,是聚光灯对准的大姐姐,善于用凶狠的铲抢让对手胆寒,永远冷静看着对方痛苦的翻滚。但是一切都是傻逼,都他妈的是傻逼,她一秒钟都不想再忍受臭袜子味、屈辱和侵犯的检查,还有对手和自己身上的伤病。这群狗娘养的到底要花多少精力确认一个人是自然的正常的人,而所有解脱自然之身的同学们在看台上像古罗马贵族一样欣赏她肉体的献祭。
——但是她没有退路,没有奖学金就要一辈子困在这个原始的躯体里对不对?
——所以你还爱我吗?
在毕业舞会后凌乱的化妆间抽烟,看着蓝色角落浮动的肉体和荷尔蒙和橙汁汽水兴奋剂镇定剂美丽气体阿普唑仑也无法解释的美好睡眠那些猪一样生活的人从来不缺少睡眠对吧?
别睡,别睡,明早的头痛又算得上什么呢?当我拥抱爱人躺下的时候明天能不能醒来已经不重要了吧?当一切倒塌的时候也没有意义了吧,我发誓自己从来没有任何一瞬间嫌弃你的收入,我愿意养一个残破的卑微的你,可是为什么不辞而别,留下最后狂热迷幻的回忆和诅咒?如今我的睡梦像是翻倒的牛奶罐——幻痛,那些他亲吻过的脚趾早已化为灰尘的脚趾还在用腐烂的利爪研磨我的梦魇——打卡上班,遇见他之前租的那个浅绿的床铺,打卡。少年时赶在全家人醒来之前倒掉垃圾,只有自己房间的咖啡渣和茶叶渣甩进花盆,家人全部在热可可和氢化植物油的面包中开启又一天的昏睡,只有我独占的亢奋和眩晕。在绿茵上追着皮球狂奔时没有异样,但是静下来就会像墨鱼一样喷射悸动的心脏。只要闭上眼睛就会听到风声,眩晕一阵一阵袭来负鼠落入山谷瀑布。
——幻觉,关于时间和闹钟的幻觉(要依靠电手环才能从无边梦境中醒来赶去上班),我不知道,关于革故鼎新的幻觉,只有时刻触摸到更新和毁灭的脉搏才有安全感。所谓现代也只是空中移动的阴影,我只是抢在裂缝合拢之前跳过去才永远离开那个近代的不会变化的童年丛林。在地铁冲刺的巨响中她好像能看见每个人透明的回忆,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过去,每个人都可以在公司的冥想休息室里吐出来一辈子都写不完的童年啊奶奶的曲奇罐啊摩托车与牛肉面啊的回忆,但是要活下去就要和童年决裂,要长大就要和大学决裂,往过去看每个人纷乱的碎片都坠落下去,而此刻站在这里的都共享同一个梦……我不知道如何描述这种感觉,反正是过去都要死去都要决裂,自由就是,在一个平等的大市场中出卖自己。
——我们只是太节制地画了一条线,认定万物的衰老和我们无关,认定在爱情的王国中只要彼此就足够了。
——然后是全部沉浸在对方的呼吸中直到窒息,如果我也会更替呢?
——后来是我们两个人在不断破裂的冰海上蹦跳,还没有固定下来就已经衰老了,你在哪里,你还爱我吗?
路旁的草地上天然气火苗燃烧,比路灯浪漫奢侈多了。几个年轻女孩子簇拥着一个小男孩走向舞台,红——逐渐淡出,炫目的舞蹈,她们在给男孩子红酒喝,小孩子一饮而尽,脸蛋上逐渐淡入胭脂的模板。当她刚进入公司的时候依赖工位上的速食活命,在喝能量咖啡之前想些小孩子有的没的事情。为什么速食这么贵,因为要人包装好送过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家慢慢吃饭,因为要加班,为什么要加班,因为无数更加复杂谵妄的理由需要让外面那些穷鬼没有工作然后我们去养活他们让他们像狗一样跳起来争抢——的疯癫的少年在大风的露台上醒来然后全身金属装甲的骑士撞破墙壁前来营救。
不不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是你还在我身边做一个不死的鬼魂——
不,我不害怕,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的但是我真的受够了,受够了痛苦和多样性的痛苦,我的重伤后人造的十字韧带,我的肾和气管的监测装置,我的混乱的相互抵牾的辅助排泄和循环部件,我的不同款式的定制的小腿——这些都不是我的但是又能怎么样呢?亲爱的,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争取那个高级义体化实验的志愿名额,你知道的吧,你肯定知道而且愤怒而且哀伤可是我不会在乎一个脑中幻觉的早已离开的背叛者的声音了,我一天都等不下去了,秘书长就坐在那边我这就去再上个厕所然后鼓起勇气去找他……
然后同桌的先生和小姐们才注意到她再次站起来慌乱地走进厕所。
宴会被一声惨叫打断,人们冲进去,第一眼看见的是她的鲜血喷在天花板上。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