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不再恐同日的後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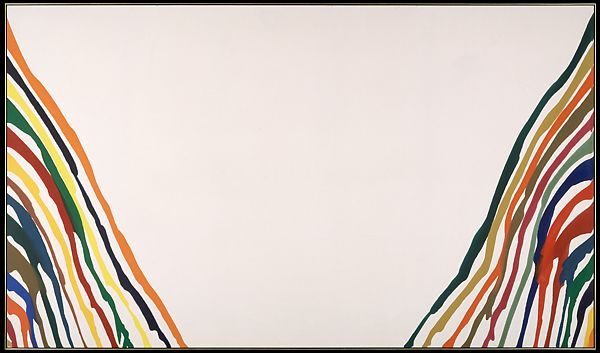
自從意識到自己雙性戀的身份後,每年到了這個日子就有很多話想說,但今年忽然覺得所有的話都是對第一年的發言一次又一次的重複,即使是有所改變的重複。
今年,朋友圈裡發聲的人肉眼可見地減少,我沒有失望。我了解ta們,這種發聲的減少並不來自於“不再認同”,而是來自於一種“常態化”。我的大部分朋友們已經把“性少數”這件事當成和吃飯喝水一樣正常的事,它本來也是。
忽然想到兩年前和朋友講,理想的狀態並不是每一個性少數都出櫃,而是根本無櫃可出。
可能和許多人不太一樣,我的出櫃來得一點都不撕裂,也不悲痛,那天就是所有無數平平常常一天當中的一個,我正在讀高中,我媽媽幾乎沒有花費任何力氣就理解了我,同學們也幾乎沒有用任何力氣就接納了我雙性戀的身份。
我曾短暫地將其歸因於父母和同學的寬容,直到後來多次和當年的朋友們聊起這件事才逐漸明白,ta們對我的寬容來自於對一種非常態化期待——我平日裡便常做ta們眼中不正常的事情,所以我的性取向是雙性在ta們看來反而是一件正常的、可接受的事了。
多麽可笑啊,我曾以為的尊重和寬容竟然來自於一種更複雜更深刻的異化。
那時我常常想,他們投射在我身上的期待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他們投射在性少數群體上的期待又是什麼樣的?而那些不如我幸運的人,他們的遭遇又是什麼?
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更加關注這個群體,去尋找和傾聽他們,去觸碰各種各樣的命運。我參加了許多關於性少數群體的活動,也自己做了許多性與性別的劇場。一開始,這完全出自於個人的身份認同和對與自己相似的人的好奇,後來慢慢地,我變得關注所有處在“少數”位置上的人,那些不被看到的、被忽視、被抹去、甚至被異化的人。
在這個過程中,「不再恐同」的意味對我來說也在逐漸變化,它在擴展,不止是不恐同,平等地對待性少數群體,也是不因不同而恐懼任何人,平等地對待任何少數群體,更是去努力營造一個對所有弱勢群體都更友好的環境。這個弱勢群體不只是性少數,還有殘疾人、痲瘋病人、抑鬱症患者、被拖欠薪金的工人們,甚至包括當下生活在疫區的等許許多多的人們。
它也意味著,所有人應該把所有人當成一個完整的生命個體來看待,不用“貼標籤”來簡化任何一個人,在那些“浪女”、“抑鬱症”、“渣男”、“同性戀”、“社畜”、“輟學”、“離異”、“爸爸”、“媽媽”等許許多多的標籤下,一個人還擁有著更廣袤更豐富的生活,我們應該抱著耐心和善意去理解ta們。
同樣地,所有人也不該因立場不同而去異化每個人,不可以把立場本身變成攻擊個體的武器,不可以僅僅因為他人一時一地的言語就將其貶低得一文不值,我們不應如此粗暴,而應該把每一個人當人看。人不是標籤,也不是立場,而是完整且豐富的個體。
還有,作為更加少數的“幸運”的人應該記得,不是每個人都有這份幸運,許多人甚至來不及發出自己的聲音,就已經在主流環境的圍攻下倒下了。當我覺得“性少數”已經是一種常態時,還有許多人在為此而苦苦掙扎,所以我不應停止說話,“無櫃可出”的那天還遠遠沒有到來。
希望有天,尤其是在我出生的那片土地上,不只是在性取向無櫃可出,政治立場也可以無櫃可出,我們可以擯棄被灌輸的先入為主的偏見,抱著耐心和好奇,去理解每一種不同,去看見每一個個體,也讓自己被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