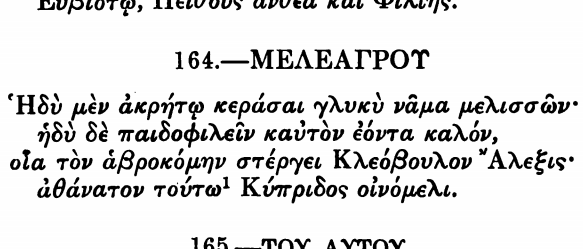新概念參賽文存檔-我曾夢想在十六歲時死去
我知道寫的很差........那年我十六,參加新概念作文大賽(忘了具體多少屆),作品是這篇。時間過去這麽久,我想也應該設法儲存下這段有點令人尷尬的回憶。非要我説什麽的話,就是前段時間寫下的一段話吧:
淺度壞詩人在深刻地咀嚼辣雞翅,就像聽al-Jazeera一樣又嚴肅又痛苦,忽然,整個餐廳裡的人一齊爽朗地喵喵叫了起來。
詩人驚慌失措,只好擺出了這世界上所有的最後的知識分子都非常擅長的笑容。
長大之前,少年們坐在圖書館的長椅上,如果視線抬起就會看到玻璃外牆上死水母一樣不輕盈的半透明污漬,從另一邊飄來廁所的氣味。
小心翼翼地帶著手稿見文學教授,後來聽到他家暴妻子的流言。
有全國第三的,廁所門壞掉關不上的圖書館的城市的少年,插著耳機聽一首女高中生一做夢就會成為魔法使的歌,在灰霾和人群中攥著要用來擦鼻涕的紙巾穿梭,想像自己可以像人魚一樣優美地游過地鐵線路。
少年期的好勝心和小聰明總是沒有好的結果,在夏天裡猶如要開記者會一樣正襟危坐,在白熾燈的下面。
疲劳的南京风景,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十六岁。
以下是正文:
我曾夢想在十六歲時死去
从小,我梦想能在十六岁时死去。
侏儒戴上滑稽的黑礼帽,吹着笛子跳过小镇所有的屋顶,路灯一齐喵喵叫了起来。天寒地冻的季节里,邻居家的猫打了一个呼噜。 拥有钢琴键一般眼睛的她,纵身投进黄海,嘴唇把整个冬天割成两半。 “夜晚是滚烫的,”她说,“我们做梦,就像长出水泡。” “透明的东西往往长久,因为灵巧地跳出了污秽的视野,越是不可见抑或不能被感知,离永恒越近。” “值得遗憾的是,梦不完全是那样的东西。梦更像是种混浊的赝品,因此,它只是徒有其表地坚固,仅此而已。为什么?正如没有向污水中投入足够的明矾,梦这条鱼栖在平缓的浅水里不肯向深处游去,它实在是太过单薄,以至于骨骼衰败得比一朵花还快,根本无法保护迅速凋谢的心脏,那些甘美的幻想的祖国,生产迷幻的工厂也不足以支撑梦的呼吸........” 奶奶冲上来一把拉走我,指甲嵌进我的手腕,“疯子!小心传染!”我悄悄回头看她,那双闪烁的眼睛好像海蜇。
小镇曾一度沦为它的乐园,心满意足地嬉戏玩闹后,它坐上每户人家的宴席。 省城的专家来了,绿军装的人来了,一个名字扩散起来,像糖块落进开水。 茶花落了,慢慢变成棕色。人们的皮肤发黑腐烂,活人开始流着烂苹果一般的汁液,哀嚎和咒骂声里老鼠咬着一截肠子逃之夭夭。 幸运儿们把自己关在卧室的床下,头戴饼干盒剪成的三角形纸板,绝不外出,甚至也几乎不说话,有时不顾一切地做爱,越发像一只只猫,似乎这样就能躲开老鼠指甲缝里的瘟疫。这多少有点可笑的哑剧没有取得多大成效,“老鼠病”仍然讽刺地登堂入室,摇响拨浪鼓,吹动纸风车。 瘟疫宛如野草莓结满了小镇。假装成猫的居民床下粘满头发和指纹,一些属于活人,一些属于逝者。一些人惊奇地发现,死人的数量和时间成一种模糊的函数关系,于是日历也被扯下来焚烧,用于验证人们是否活着,谁在黑烟里流下了眼泪,谁就将穿上浆得笔挺的丧服。剩下的人用天平称量骨灰,好像古代数学家拨动算盘,小心翼翼地算过去的日子。 事情平息的秋天她十岁。家已经成了一个烂橙子,男主人早在瘟疫伊始便逃去县里,隔天人们把他的尸体穿在线上拎回了小镇。黑色虽然从女主人的脖子上一跃而下,连日的高烧早已将头脑拆得七零八落。妈妈没日没夜在家里东翻西找,所有的钟表被凄惨地肢解,齿轮有的挂在她的睫毛上,另一些缠在阴毛里,阴森的门牙咯吱咀嚼着表盘,几根秒针刺进了手臂,血铁锈一般从黄灰的皮肤里长了出来。她浑身赤裸,蹲在角落里给钟表开膛,眼白织满红线,脚趾夹着一把螺丝刀,“找不到,找不到........”绝望的哭喊骤然响了起来,用头猛撞着一个被拆除了外壳的钟,钟血肉模糊的零件混着额头的鲜血沾满了头发。后来跳进了海里的女儿放学回家总是和她呆在一起,试图拼好钟表,这时母亲会揪着她的头发,笑嘻嘻地舔舐被疼痛呛出的眼泪。 后来女儿砸烂所有的钟,埋葬了妈妈塞满齿轮的胃,满脸怜悯地走进熟悉又陌生的村子。
六岁的我把大头针扎进胸口时,她浮在眼睑里就像只海蜇。 十六这个数字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即使我很久之后才知道它是第一个质数的第一个合数次幂。 茶缸里的樱桃只剩最后一颗,我还觉得没有感受到真正的鲜红味道。我要,求求您,给我吧,心这样恬不知耻地大喊大叫。汁液在口中爆裂带来的震颤让我情不自禁浑身发麻,在有些不合身的坚硬躯壳里像糖水一般瘫软下来,光亮攫住了我的神经,让它好像要动弹不得地静静融化,有什么东西在喉咙里挣扎欲出,绷紧的身体几乎要抽搐起来,随着景物再次涌进眼眶和退潮,心脏搁浅了,盐纷纷扬扬地从天上落下来。 当地面飞驰而来撞上我时,茶缸的温度弄凉了我那双成天和静脉留置针打交道的手,它们又软又黏,好像小孩玩厌了丢在一边的橡皮泥。这奇形怪状的蹩脚玩具倚着茶缸边,一面探进去,似乎想要捞上来那最后一颗樱桃,对于穷追不舍的蠢笨怪物,机敏的果实以虫子在苹果里挖洞的姿态穿梭在实在与空想之间,带着老妇人回忆少女时代会听见血液在脸颊下的毛细血管里呼啸而过的那种隔着镜面的悲哀的清晰,樱桃仿佛嘲笑着什么一样炫耀它完好无损的红色。即使焦灼的浓度爬升得叫人连眼睛都睁不开,蝴蝶一样栖息在指尖上的某种奇特的场也不会因此减弱一分,或许存在一种狡猾的平方反比,总之愈是想靠近,愈是近乎绝望地感到了透明的斥力。 我们都明白两物体间万有引力大小与两物体质量乘积成正比,不妨猜测这斥力也是类似的东西,倘若借助什么轻捷有力的武器,也许可以稍稍沾上樱桃的光晕。
在县医院里生着肺炎打吊针的我,盯着缠在左手上的边缘发黑的胶布,血管里涨着疼痛的悬浊液,那种凝滞好像一头瘫痪的猪。但是当针头在血肉里横冲直撞,铁链发出哗啦的响声,一种迫切蠢蠢欲动起来。正如蚕茧猛地被剪开,粘稠的满足涌出来,然后在顷刻间蒸发成一层冷漠的膜,这一切让我呆上半天,一言不发。对樱桃而言,这种伪接触带来的物质半衰期太短,以至于对它质量关于时间的函数求一个定积分,也就是历史上的总和,结果也小得惊人。
当人们开始尝试自渎时,往往并不清楚它的意义与性质,做梦的体会也类似。毋宁说,倘使梦境转化为自发的,它也将沦为一种自渎。在人工梦境中,令人佝偻起背的真实感从天而降,却闪过几乎每个组成我们身体的原子。如果那种真实碰巧遗落了一点粉末,我们就欣喜若狂地欺骗自己俘获了真实,那种喜感大概只有咬着苍蝇的捕蝇草的满足可以比拟吧。而真实漫不经心地穿越这个世界,和我们跨过一个蚁穴没什么两样,回到它的宫殿里呼呼大睡。
我已经谈论了那颗矜持的樱桃与种种徒劳,我想我可以说说其它的方面了。 假设一个袋子里盛了n个球,其中一个比其它的轻一些,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几次称量找出它,这个次数比n小的多。但让我们考察这“一茶缸的樱桃”,即使数目小到个位,你总找不出那唯一一个和其它不同的,原因在于总有n-1个普通樱桃,一个特殊的和一个无法被感知的“梦世界的樱桃”,而它们只要存在,就躲在时间的更衣室里玩双胞胎热爱的那种游戏。正因如此,我们只有一种模糊的概率,与向蒙德里安的白玫瑰上泼上一壶开水类似。 如果我能够,我在陈述一种假设,将“那颗樱桃”如愿以偿地攥在手里,我会如何残酷地侵犯以及亵渎“她”?我太想要脚下的防浪堤那样坚固实在的东西了。堆砌精致的劣质原料来摇摇晃晃地做梦只能让我贪婪的胃变得更加膨胀,永无止境地渴求更完全的满足。仿佛一个旧皮球,沿着星空里一条歪曲的道路一路滚落,直到撞上什么然后被自己的动能肢解。你要知道,没有什么比亵渎某种坚固更激动人心,搭建积木不正是为了让它倒塌的姿态够美丽吗?通过触摸和亵渎极致的真实,我们验证了自身的实在。病毒一般的真实传染到手上,在身体里遍地开花。通过这样不可能的假设,我们品尝完混着海洛因的压缩饼干,心满意足地打了一个饱嗝。
五岁的我挂着小灵通,走在防浪堤上,毛孔里还有医院床单的气味。我一面走,一面划着火柴,一点一点把小镇压得沉入火海。随着县城汽车站汽车发动机一块嚎叫了起来,小镇在被遗忘的痛苦中融化扭曲,我在粘满雾气的车窗外侧勾勒出那个柔软的临终微笑。
黄海在火焰奏响的迪斯科舞曲里翩翩起舞,挥舞着打弯的指甲竭力呼喊—— “同学们,定语从句是啥子?” 一口干巴巴的川普在教室里没完没了地奔跑,汇成一支金碧辉煌的交响曲。我摊开手,皮肤的褶皱流淌在上面,把我迟钝的头脑远远甩在后边。空空如也,没有任何有机质的存在或存在过的痕迹,只是塞满一团干涸,好像受虐狂嘴里塞着口球。 我闪烁银光的贫瘠的手紧紧钳着钢笔,或者说是种文雅的凶器,猛地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可是没有血,没有惊叫,只有叫人牙齿发酸的沉默和冻的发硬的微妙秩序。我想唱歌,喊叫,或为了某种不存在的牺牲举行盛大的祭典,然而什么都业已消失,抑或从未存在。我的子弹脱靶了,不,应该说干脆飞出了射击场。一方面,我又感到某种事实——我知道,对,知道,樱桃遭到了难以言喻的悲惨命运的袭击,果汁飞溅在墙上,储存这个世界的所有衰亡和消减的镜子上,下了雪的月亮的原野上。我知道这一切,如同神明懂得所有的数学定理。抱着一把凶器,爱丽丝抱着个猪孩子。世界平滑地向前推进,朝着遇难器宇轩昂地前进,这条铁轨上灾难的总和被放在某个未知的场所,其余的地方平滑而苍白,糊里糊涂前进的我们,根本无法辨别自己的运动状态。
我多么渴望不幸啊!鲜血淋漓的不幸为什么还不从我的指甲下面迸发出来呢?只有不祥的预兆,不幸的事情,有能力让我坠入一种戏剧化的真实,回到那间幽暗的有着一茶缸樱桃的堂屋啊!和真实相拥,同时灰飞烟灭,难道不是远远比无知无觉地溶化美妙吗? 肏你妈!我想如此嘶吼,所有摇曳的野花,青翠欲滴的草儿,操你妈啊!请击倒我,击倒这罪恶污秽之身,践踏它吧,肆意践踏它吧! 只有极致的明亮才能灼痛眼睛,只有借助到了虚无的极致,才能在真实的羊水里安眠。尽管远远不够这些,一时的麻醉足以让我吸食粗制滥造的糖水了。
我的头被按在地上,双手压在身后。疼痛腐蚀肋骨宛如氢氟酸破坏玻璃,我的脸颊在发热,好像一个电阻。巨大的屈辱感太过辛辣,鼻尖也变得湿漉,和一只野狗没什么两样。
诘问:这是你想要的吗? 一个有着值得被精神分析学家玩弄的童年的怪人,孤僻而寡言,被同学狠狠教训了一顿,不是这样的事吗?有什么复杂的极致和真实可言呢?我只想陈述我的愿望和渴求,拥有乃至于凌辱真实,正如
—— 我梦想在十六岁时死去。
後日談
從今以後,我並不覺得我會好好活下去,人生沒有什麽希望,一切東西都讓我感到惡俗無比。我快二十歲了,雖然沒在16時候死掉可能是挺好的吧。但是接下來的幾年,我一事無成,不太明白這個時代還能去幹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