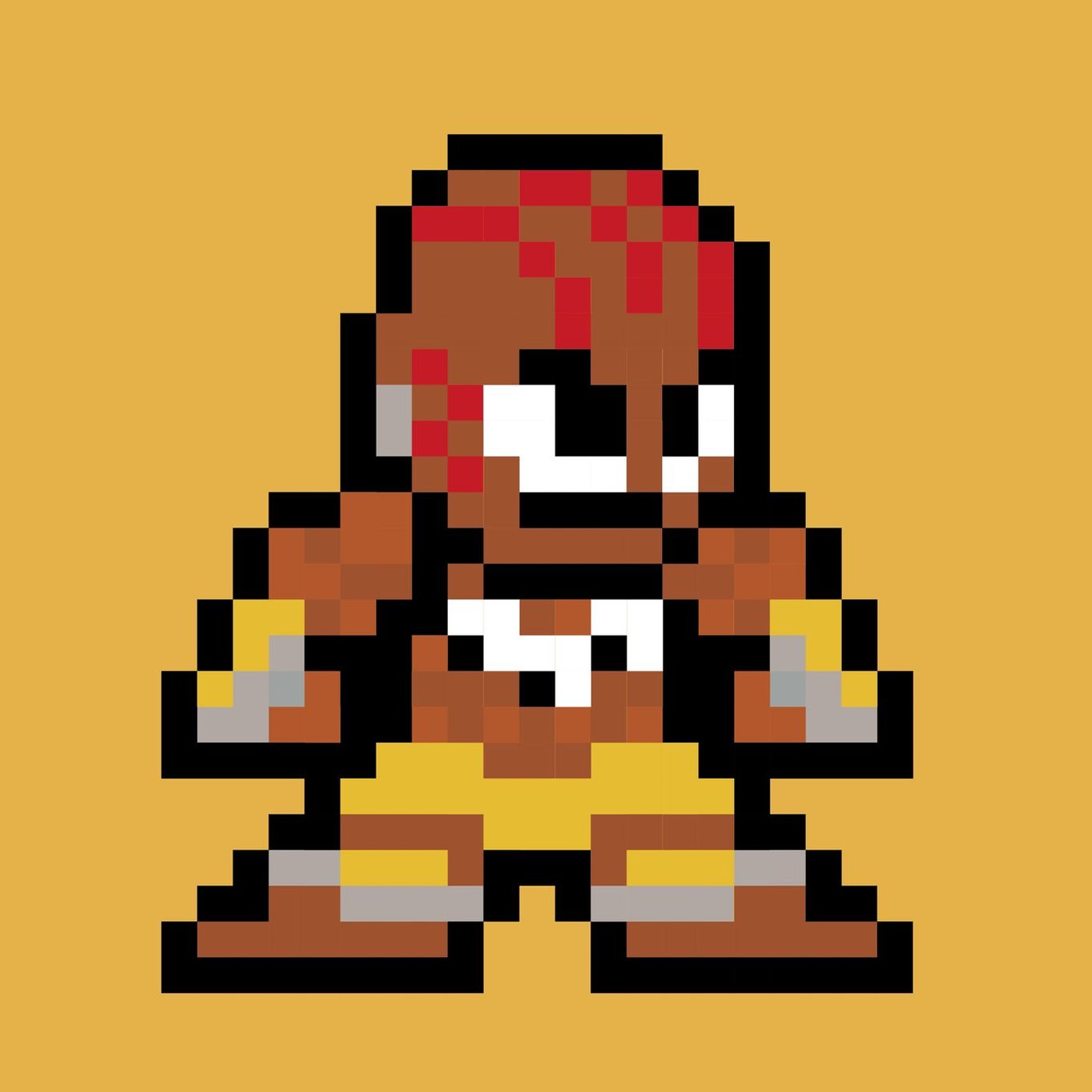一個上海小赤佬的魔都故事六部曲——PART 1 末代皇帝
1988年年初,甲肝病毒在上海爆發。當時剛懷上我不久的母親,自然成了家裡的重點保護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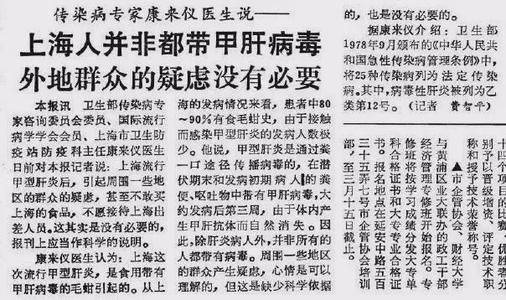
8月初,父親將快到預產期的母親,送進了虹口區第一人民醫院。
可是母親覺得待在病房裡太無聊了,肚子裡沒什麼大動靜啊,那時候也沒有能低頭看出頸椎病的智慧手機,連電視機都還沒在公共場所普及。恰好附近的電影院還在放1987年下半年上映的電影《末代皇帝》,於是父親趁病房醫生護士都不注意,將母親偷偷帶了出去,兩人看了一場《末代皇帝》。

上海話“王”、“黃”讀音不分,父親看完電影一衝動,講道,如果生個兒子,就叫他王帝,上海話念出來跟“皇帝”一模一樣,嗲伐?
我阿爺得知此事勃然大怒。年輕時思想進步的他老,為了“跟舊社會劃清界限”,主動將自己原本帶字輩的“封建姓名”都改了,豈能容許自己的孫子叫“皇帝”? 講來也怪,看完電影那天晚上,母親的肚皮開始有了動靜,第二天淩晨我便順利降生。當然,名字當然不叫“皇帝”,也不叫王富貴。
而我那愛看電影的父母一定沒有想到,他們生下我到現在,就只去過一次電影院,那是1998年年末,在安福路上的一家電影院看的戰爭片《拯救大兵瑞恩》。那部1997年成為“審核傳說”的一刀不剪版《泰坦尼克號》,兩口子反倒是沒去看。
令他們更沒想到的是,他們的兒子在若干年後,成了電影放映員。只不過放的不是商業電影,而是特種電影——IMAX的70毫米膠片電影,堪稱膠片電影界的“末代皇帝”。

說起放電影,跟我同齡的年輕人可能都不一定知道,曾經有一種職業,叫“跑片員”,直到上世紀90年代前,全國還普遍存在大量的跑片員。 雖說上海是中國電影的發源地,電影工業發達,電影院也不少,可在物質匱乏的年代,即便是上海的電影院,電影的膠片拷貝也常常是好幾家電影院一同共用。於是乎,穿梭於大街小巷,只為及時傳送膠片拷貝的跑片員,成了城市中不可或缺的職業。
舉個例子,好比前面提到的《末代皇帝》,這部電影的劇場版時長為163分鐘,而一本35毫米的電影膠片(通常裝在圓鐵盤裡),只能播放9-10分鐘的影像,放映間兩台放映機,通過時間碼的同步,按影片的順序,輪流交替播放著膠片,以保證畫面在視覺上沒有間斷。而播放完整部《末代皇帝》,則總共需要將近二十本35毫米的膠片。

而《末代皇帝》當時還被分為了“上下集”,也就是說,A影院正在播放上半部分的時候,可能B影院正在播放下半部分。而當B影院的《末代皇帝》下半部分放完之後,跑片員要從放映員那裡,將這些下半部分的圓鐵盤,放進他們的大挎包裡,急匆匆地沖到B電影院外的腳踏車或者摩托車上,儘快衝刺至A影院。
A影院此時可能《末代皇帝》的上半部分剛放完,銀幕上打出“正在跑片,請耐心等待”的字樣,底下一些觀眾習慣性地吹吹口哨、喝喝倒彩,叫駡兩聲“冊那”,便晃幾晃幾、篤篤定定走出影廳吃香煙、買冷飲、上廁所了。這期間跑片員必須抓緊沖到影院的傳送視窗前,將電影下半部分的所有膠片鐵盤,送交給電影放映員。
放映員也沒有閑著的時候。當時的放映員不僅僅是放電影這一樁事體,剛播放完的電影膠片,還需要放到倒片臺上進行“倒片”。(倒磁帶、倒錄影帶懂伐?)倒回來的膠片,才能交給跑片員,讓他送到其它附近即將要使用這些膠片的影院。

當時跑片員和電影放映員的忙碌程度,絕對不亞於現在的快遞員跟外賣小哥們。 如今全球還在放膠片電影的影院已寥寥無幾,而我卻很自豪地還在做著這項工作。明年3月,我們影院這套最後的IMAX帝王級膠片放映機就要被拆除了,一想到這點,便越發珍惜與這套已默默服役了20年的放映系統相處的時光。
機械雖說是男人的浪漫,作為“模擬設備愛好者”的我,就算再心有不甘,數位設備的洪流也早已無法阻擋。 放映間裡的“末代皇帝”,差不多也該鞠躬謝幕了。而那些曾經鮮活的歷史,若鮮有人關注和記錄,到了最後,都將成為不解的謎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