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遊民旅行日誌1《坐上車去Sama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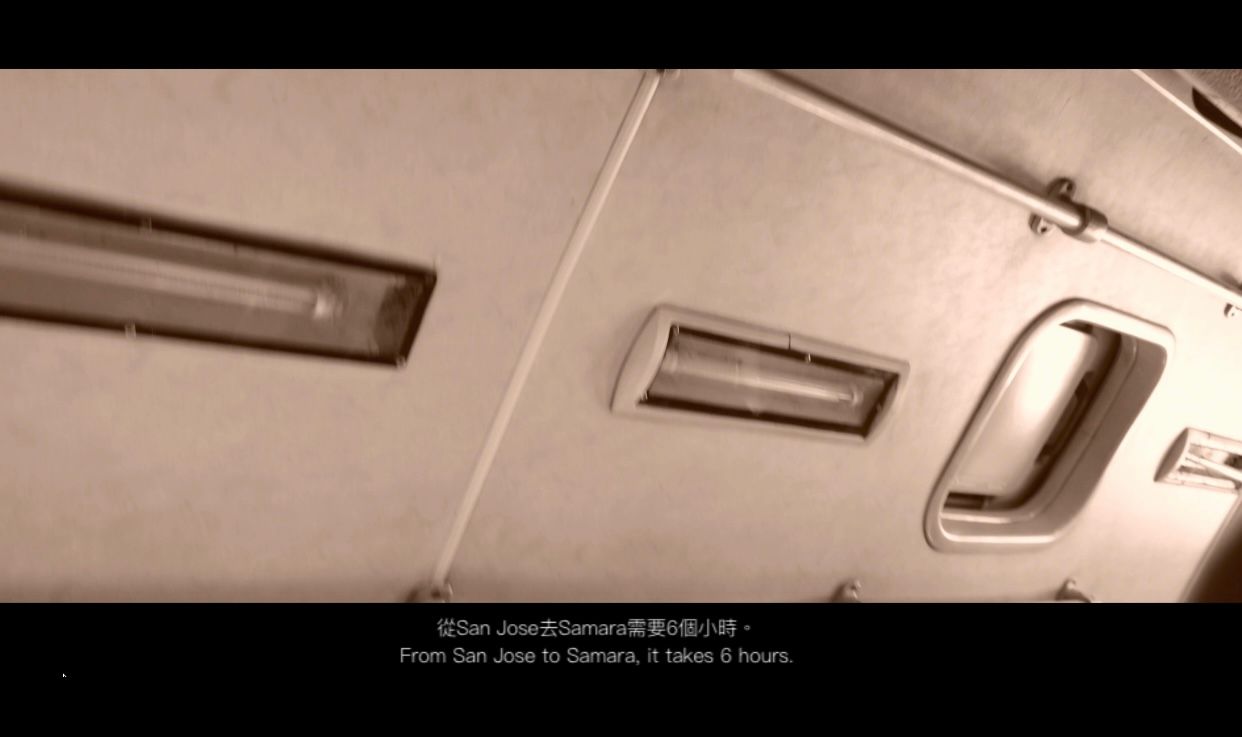
從San Jose去Samara需要6個小時。

車上潮濕且悶熱,熱帶獨有的慵懶讓人昏昏欲睡。
看到我拿著相機擺弄,同行的阿姨一遇到風景,便招呼我“快看快看”。
在大巴上我遇到了Viktoria, 來自瑞典. 她盤腿坐在大巴中間隔斷的狹小空地上,我索性加入了。
以下是部份談話紀錄:
當我們談到後疫情時代全世界普遍的國家控制加強,人們不再懷有期待。但有的地方更為甚至
她說到“最強的控制工具是恐懼,植入深處的恐懼讓人們相信他們無法辦成任何事。
多旅行感受不一樣的生存體驗吧,可以部分消解以前那些被環境強加的有毒思想。”
“我也不一定有身份認同啊。我說我來自瑞典是指我的出生地。
就像年齡只意味著你來到這個世界的時間一樣,很多事實被賦予了超過它本身的意義。
首先,你得明白大多數的“意義”都是人為建構出來的,而萬事萬物其本省是流動的。

這樣一來,你可以是任何人,無論你本來的出身,種族,文化。

當然你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本省是基於你原有的個人背景和集體記憶的。
在路上的意義就是妳能盡可能完全你對世界的認知,不偏頗於偏見
活著並不容易,你得充分的體驗而非壓制所有的情感,同時保證自己不被情感的洪流所淹沒。

在流動中,永恆和有意義的東西可能是妳對這個世界的信念,你知道你得在每一個時刻活到當下的極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