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個屋簷下,她和她的“解放與壓迫” | “文化研究”學什麼
我在香港的鄰居家裏請了外傭(外籍家庭傭工的簡稱),每天,我進出電梯,經過鄰居家門口時,總能看到他們家外傭那雙擺在角落裏的紅色塑膠拖鞋。我見過她幾次,有一次,她和我一起等電梯,她膚色很深,個子不高,紮著低馬尾,約三四十的年紀,一左一右牽著鄰居家兩個學齡前的女兒,還有一次,我出電梯,鄰居家的門打開了,我看到她蹲跪在客廳的櫥櫃旁,正從櫃子裏取東西,昨天,我拎著大包小包的菜出電梯,剛好看到她坐在打開的門前,正在整理鋪了一地的紙箱和垃圾,她抬頭看到我,露出了一個微笑,眼睛很亮。
我現在住在香港屯門的景峰,和兩個同校的女生合租了一套房子,房子不到三十五個平方米,卻規劃出了兩房兩廳一廚一衛。這套房子很小,房間裏只能放下一張1.2米的床、一張小書桌和一個布衣櫃,在衛生間洗澡或上廁所一不小心手臂就會撞到門或牆壁,廚房不能同時有兩個人作業。我常常在這個房子裏撞到,每當這個時候,我都會想:在與我的房子戶型大小差不多的鄰居家,他們一家四口加上外傭是怎麼住的呢?外傭會住在哪里呢?在狹小的家裏住進一個異國的陌生女人又是怎麼樣的一種生活體驗呢?
我第一次知道外傭,是很多年前,有一次在周日來香港。那天,我從中環往口岸趕,發現中環比之前幾次來都更加擁擠,馬路邊、天橋上、公園裏、地鐵口等幾乎所有的空地上都坐著人,他們多為膚色很深的女性,有著與我熟悉的中國人不同的面貌特徵。三五成群的圍坐著,中間鋪著報紙或野餐墊,上面擺著充滿異域風味的食物,有的吃著食物聊天,有的躺著睡覺,有的相互化妝打扮,有的唱歌跳舞,有的打電話,有的清理要寄回國的物品,非常熱鬧。

對當時的我來說,這是一種奇特的景觀:背景是代表著現代化香港的摩登大樓,而目之所及是正在悠閒聚會的來自異國的女性們,一時之間,摩登大樓仿佛變身成了一棵棵搖曳的棕櫚樹,而我也好似穿越時空,仿佛置身在另一個國度裏。這種“奇景”的感覺令我印象深刻,讓我開始對這個群體產生了興趣,好奇:她們是誰?她們從哪里來?她們在香港做什麼?她們為什麼坐在大街上?……
在這個學期《全球化與社會變革》(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的課程上,要求每個小組選一個與全球化相關的話題來進行分享,我所在的小組已經做完了分享,我們選擇的話題剛好是我一直感興趣的外傭。在準備這個分享的過程中,我算是第一次比較深入地瞭解了外傭的相關情況,接下來我將分享一些我印象深刻的點。
◆◆家務勞動的全球分工◆◆
何為家務勞動?在《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這本書中,列出來六項主要的家務勞動,包括:清潔、購物、做飯、洗碗、洗衣、熨燙,除了這六項家務勞動外,養育小孩和照顧老人(或需要照顧者,比如病人、殘疾人等等)也都屬於家務勞動的範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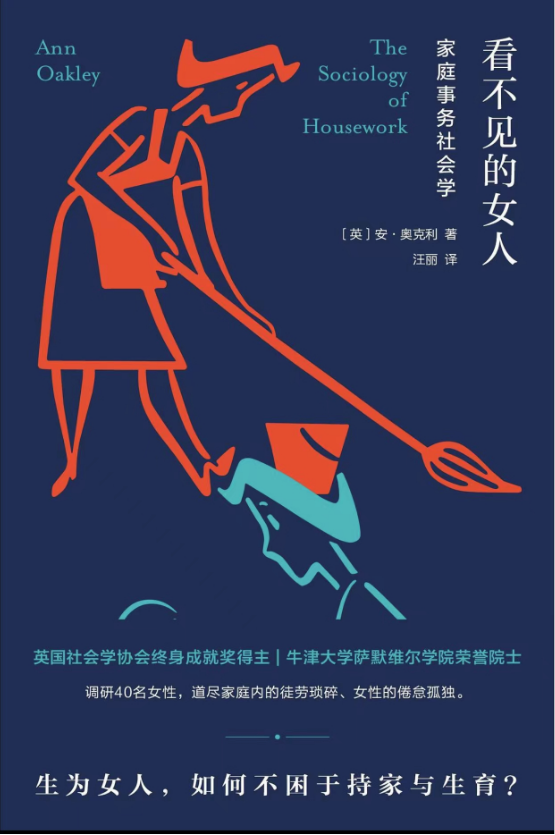
從中國這句“男主外,女主內”的老話可以看出,家務勞動一直被認為是女性的“分內事”。然而,當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婚後或者生育後繼續留在職場,女性面臨著一種“蠟燭兩頭燒”的困境,一邊是家庭,一邊是職場,很難兩全。這種“蠟燭兩頭燒”的困境帶來的後果包括,女性放棄職場,成為家庭主婦,或者從全職工作轉變成兼職工作。成為家庭主婦,每日從事重複性的家務勞動,在個人價值和社會參與上都有影響,另外從全職工作轉變成兼職工作,則會使得女性成為更容易被裁員的對象,在職業穩定和經濟收入上存在風險。
那怎麼辦呢?為了兼顧家庭和職場,女性開始選擇將家務勞動外包。對於這一點,我們不會陌生,在內地,對應的職業有保姆、家政服務、月嫂、育兒嫂、清潔阿姨等等,都是幫助女性分擔家務勞動的。而在香港,香港女性的選擇是外傭。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騰飛,政府鼓勵女性參與到就業市場中,以緩和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當本地的全職留宿家庭傭工供應不足時,香港政府自七十年代(1970年)准許輸入相對本地家庭傭工廉價很多的外籍家庭傭工來港工作。香港政府規定,由2022年10月1日起,外傭的最低工資每月4,730港元 [1],而據政府統計數據,2021年5月至6月,香港人每月工資中位數為18,700港元[2]。從懸殊的外傭工資和香港本地人工資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將家務勞動外包給外傭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
據統計,2021年,香港的外傭數量為339,451人[3],其中,56%的外傭來自菲律賓,41%的外傭來自印尼。2016年,菲律賓當地的工資水準為1,700港元。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下,人力成為了商品,開始了跨國流動,家務勞動也從家庭走向了市場,家務勞動也開始了在全球範圍內的分工。
◆◆她的“解放”與“壓迫”◆◆
對於香港的女性雇主來說,以較低的價格雇傭一個外傭來分包家務勞動,的確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自己。首先,有了外傭的幫助,女性雇主得以繼續留在職場;同時,女性雇主可以將自己的時間花在更容易產生價值感的家務勞動上,比如陪伴孩子;以及,因為不再困於重複性的家務勞動,女性雇主在家務勞動上與丈夫產生的衝突減少,家庭關係有機會變得更好。
而對於漂洋過海背井離鄉的外傭來說,在一個經濟發展水準優於自己母國的地方打工,也是一種解放。以我們小組研究的菲律賓籍外傭為例,首先,雖然外傭在香港的工資很低,但對比菲律賓國內的工資水準,外傭的賺取的工資屬於高薪,這種收入的差距,讓外傭取代母國的丈夫,成為了養家者,在家庭事務上有更大的話事權。同時,外傭在香港的工作經歷拓寬了她們的國際視野,使得她們有機會發展自我,而不用受到母國對女性發展的種種限制。
然而,在女性雇主和外傭的“解放”中,我們仍不可避免的是她們所受到的“壓迫”。香港的女性雇主真的得到瞭解放嗎?身為母親,當女性雇主看到自己年幼的孩子與外傭發展出類似母子之間的感情時,女性雇主會產生對自己身為“母親”一職的剝奪感和愧疚感;身為妻子,女性雇主會擔憂年輕的外傭對自己丈夫的“性吸引力”,而對外傭產生“雌競”和“提防”的心理;身為女性,如何去處理髮生在家庭中的工作關係,外傭是工人還是家人,還是又是工人又是家人呢?
而在外傭這邊,她遠離丈夫和孩子,她在香港帶大一個孩子,而自己的孩子則要在沒有母親的陪伴下長大,常年與丈夫分居,她可能面臨丈夫拿著她賺來的錢與他人另組家庭生活的情況,而她又由於宗教原因,無法同丈夫離婚。在狹小的香港雇主家裏,她總是住在條件最差的地方,好的能有一個小房間,最差可能要在廁所或廚房搭一個床,每天睡得最晚起得最早,基本處在24小時待命的狀態,一個禮拜只有一天休息,工作和生活的界限難以分清。最後,在隱私難以保證的情況下,還可能面臨著來自雇主的虐待和性侵害等等。
◆◆無解的“困境”◆◆
在查看資料時,我注意到兩個點。一是,外傭會在母國雇傭來自更貧窮地區的女性照顧自己的孩子和家庭;二是,外傭花費數年供自己的子女在母國接受高等教育,結果發現,自己的子女無法在母國找到工作,只能跟隨自己,跨國踏上做外傭的路。
這怎麼看都像是進入了一種“跳不出的迴圈”中。家務勞動的全球分工一層又一層,總有女性要離開家庭和子女去照顧另一個女性的家庭和子女。在這個全球鏈條上,看似處在鏈條上游的發達地區的女性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就如之前所說,這些發達地區的女性也仍舊是被壓迫者,是困在“家務勞動是女性分內事”、“女性的價值在於經營好家庭”、“女性是天生的母親”等枷鎖裏的受害者,而這個枷鎖的根源是“男性主導,女性壓迫”的父權社會。
在家務勞動上,男性是隱身的。比如,雇主大部分都是女性,雇傭外傭後,在家庭中與外傭溝通安排工作的也都是女性。在這個過程中,男性不參與,卻享受了雇傭外傭的好處,而又無需去面對和處理外傭和雇主之間的張力。男性不僅僅是一個享受者,同時還是一個評價者,當外傭沒有做好工作時,男性則會指責女性怎麼在有了外傭的幫忙下,還無法處理好自己身為妻子、母親和兒媳的責任。
在看資料的時候,有一個點打破了我的偏見,以前我總以為外傭是沒有很高教育水準的,是來自貧窮和落後地區的人。然而實際上,外傭的教育水準非常高,如菲律賓籍外傭,有很多擁有大學本科甚至以上的學歷,可以講非常流利的英語。她們選擇成為外傭的原因,一來是母國本身的經濟發展水準落後缺少之外,還有就是對女性就業的歧視,包括男女薪酬差異、年齡等等。這陷入一種很奇怪的迴圈中,外傭因為教育水準和英語在全球的家務分工市場受到歡迎,而母國依賴外傭的外匯收入但又沒有合適的機會讓外傭回國發展,於是就只能繼續做外傭,子女做外傭,一代又一代的傳承。外傭面對這樣的代際傳承,會失望嗎?
家務勞動的這種全球分工可以不要嗎?如果沒有這種全球分工,那外傭和女性雇主是不是就不會經歷“壓迫”呢?那天,分享結束後,班上一個香港本地的同學拉住我,她跟我說,她家裏是請了外傭的,但她自己是不想請的,但是,如果不請的話,她就沒有辦法做很多事情。我們倆個坐在教室裏面面相覷,互相問對方:那要怎麼辦?想來想去,最終我們一致得出的結論是:家務勞動不應該只屬於女性,不應該只屬於家庭,它需要從私人領域的事務轉變成公共領域的事務,需要全社會一同想辦法去解決,唯有如此,才能有真正的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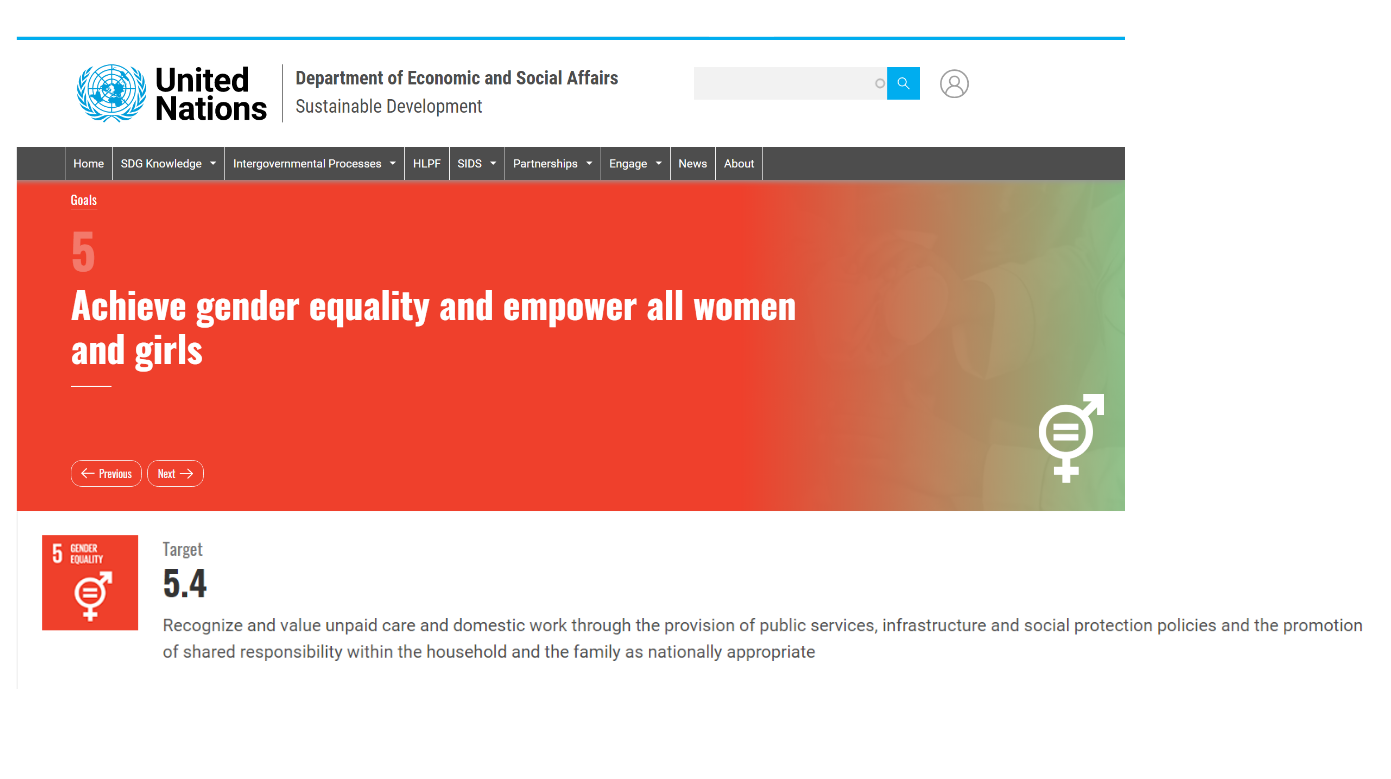
參考資料:
[1] https://www.fdh.labour.gov.hk/tc/general_policy.html
[2] https://www.censtatd.gov.hk/tc/scode210.html
蘇美智 & Godden, R. (2015). 外傭 : 住在家中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home (香港第1版 ed.).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藍佩嘉. (2010). 跨國灰姑娘 : 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 (5 版). 行人文化實驗室
[英] 安·奧克利.(2020).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南京大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