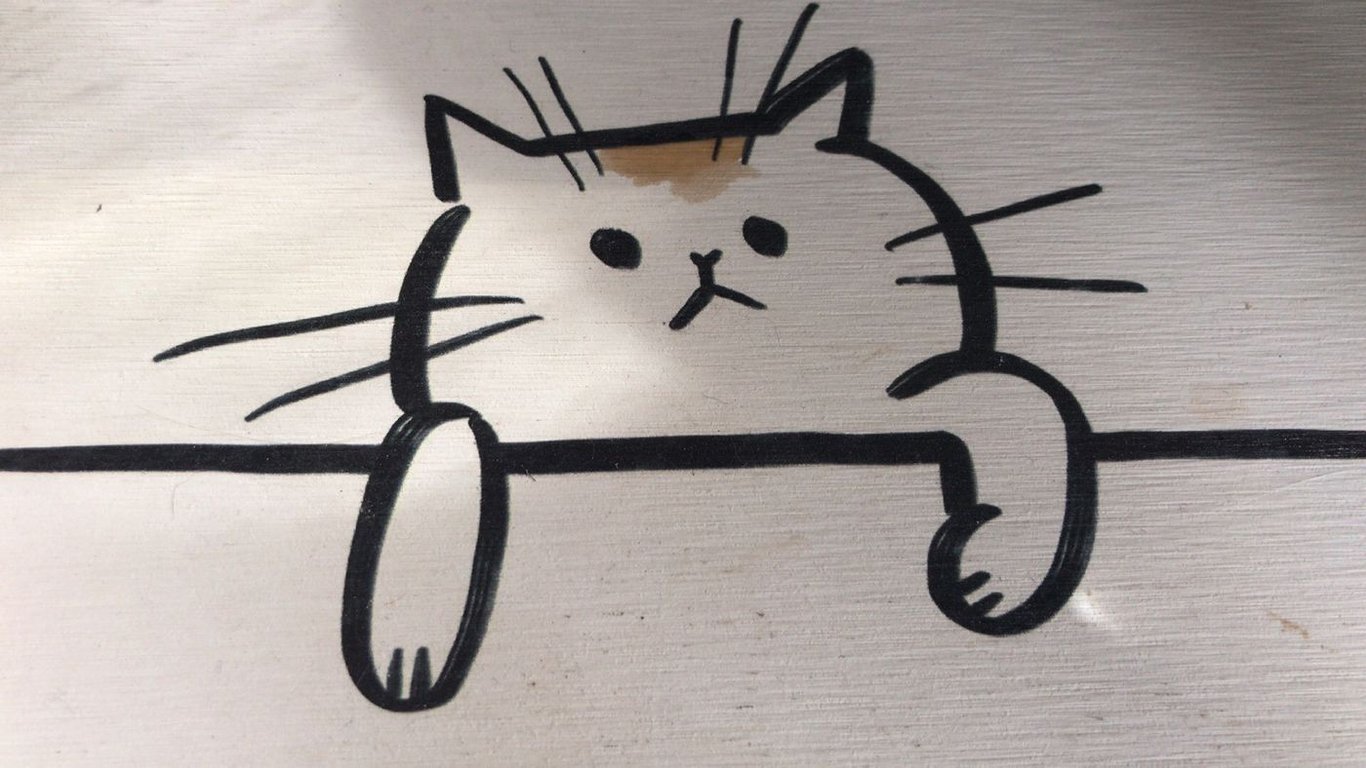战争的意义是什么?毫无意义。
近日重温美国小说家冯内古特的长篇《五号屠场》及其改编电影,不免想到这两年的战争片。投资更大、阵容更强、技术更好,叙事能力也似乎更专业了,但对人和战争的处理却趋于简单了,即便有鲜活人物,也常以某种精神或主义的化身出现。
过于掷地有声的战争片,往往缺少超出历史和战争观念的人性关照。
前年偶然参加某国产战争片媒体观影,有一场戏印象极深。老兵命新兵枪决俘虏,为亲人报仇。新兵不敢开枪,说这不是杀我叔的那人。老兵帮他端好枪,说他就是杀你叔的人。然后枪响,几分钟前大喊我不杀人的新兵完成了成为战士的仪式。
待到这片子精简版正式上映,已是一年之后。这场戏还在,但新兵那句疑问精简掉了,只留下老兵的回答。
省掉一句话对电影情节没什么影响,而我认为却极为关键。
合理的疑问是反思的开始,是不那么肯定的纠结。无论原因、动机如何,省去疑问,留下答案,结果就是关闭了可能的视角。
任何战争叙事都难免对战争本身做出某种解释,让你从中了解到:原来战争是这个样子。而一句疑问,就是一个提醒:好像不只是这么回事。
如果提醒不见了,情绪在血与火的视听轰炸中燃烧,那个响亮的答案不免让你觉得是唯一的,绝对的。至少一段时间内,你可能会忘记,除了感动的哭、愤怒的恨,英雄伟人和国族立场,还存在其他视角去理解一个士兵、一场战事、战争,乃至历史。
关于战争,有个老生常谈的观点: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谈论者常常忘记,政治总以在正义、民族、利益等“大局”的面貌出现。一旦涉及大局,就只有“大我”,具体的人最易被忽略。
战争是政治的手段,人是战争的手段。
如果剥离掉凌驾于人之上的种种目的和层层大论题,基于具体人的情感和体验去谈,战争的意义是什么?
一九六九年,冯内古特出版了《五号屠场》,用一个不同寻常的二战故事给出了回答:战争毫无意义。
《五号屠场》出版时,美国已陷身越战的泥淖近十年,可仍在高举“人类自由”的大旗用战略轰炸机对北越地毯式轰炸。台湾作家詹宏志评价《五号屠场》,认为正是这本书改变了美国年轻一代对战争的理解,促使了美国退出越战。
这句评价虽说得简单(至少还应算上同时代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却所言非虚。《五号屠场》完全站在一个普通的年轻人立场上,无论是美国士兵,还是德国士兵,他们在战场上,“没有方向、没有敌我、没有意义,只有死活”。
小说开篇,老冯讲了自己的创作经历。他去拜访老战友征求意见,却遭到战友妻子的白眼。这位妻子怒气冲冲地说:战争中你们只是些不懂事的娃娃!
老冯承认,战争中他们确实正处于“童年期的末端”。可这位妻子依然愤怒,认为老冯在小说中不会实话实说,她说:
你会假装你们不是些娃娃,而是男子汉,让弗兰克·辛纳屈、约翰·韦恩或者其他一些魅力十足、好战的、有一把年纪的无耻之徒在电影中表现你们的故事。战争看上去无比美好,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战争。送去当炮灰的是些娃娃,就像楼上的娃娃们。
成年人玩政治,小娃娃当炮灰。这是可以瓦解一切战争神话的常识。
老冯恍然大悟,举手发誓,担保故事里不会有弗兰克·辛纳屈和约翰·韦恩的用武之地。他说,这本书名叫《儿童圣战——与死神的义务之舞》。这正是《五号屠场》的副标题。
故事里几个主要角色都刚刚成年,甚至未成年。就像毕业后被分配了一份工作,他们被丢在战场上,怀里揣着两种恐惧:一种是怕自己被杀死,另一种是怕不得不杀人。
这就是剥离了“大我”的人之常情,却也常被忽略。
小说出版时,老冯将作品题献给了这位战友的妻子。我猜,这是因为老冯知道,她的提醒对愚蠢的人类长期适用。
单说故事,《五号屠场》情节很简单,且不太流畅,一些地方有胡扯淡的嫌疑。
二战快结束时,比利被送到欧洲战场,充当随军牧师。但他没找到自己军队,连军装都没摸到,就被德军俘虏送进了战俘营。随后他被闷罐车送往了德累斯顿——一个古老的德国文化名城,当时那里还聚集了来自各国的二十多万难民。
一天晚上,盟军轰炸机来了,比利和其他美军战俘及四名德军看守躲进了屠宰场的地下储藏库。轰炸结束后,他们从地下爬出来,发现城市没有了,不见一个活人。他们成了幸存者。
战后,比利得到了政府嘉奖,成为认证了的英雄。再后来他结婚生子,干起了生意。忽然有一天,他遭遇空难,再一次成为幸存者。伤愈出院之后,他开始向大家说起一件不为人知的往事:他曾遭外星人绑架,被送到一个叫特拉法玛多的星球上,关进了那里的动物园。
几乎没人相信他的故事,只有某些媒体感兴趣。因此他的余生就执着于此,要把他从外星人那里知道的真理讲给人类。
再后来,他就死了。事情就是这样。
若按传统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的叙述方法,或许不得不强调战争残酷,如何造成了终生创伤,把人逼成了疯子。但老冯觉得不够,那过于理性了——如一位评论家所说,不知不觉中会让恐怖的事“具有可阐释性”。
老冯写了至少五千页,又都撕掉,最终把故事讲成了碎片,“书不长,杂乱无章、胡言乱语”,因为“关于一场大屠杀没有什么顺乎理智的话可说。”
故事虽然涉及了比利的一生,但人物不多,也很多好戏剧冲突,因为“书中的大多数人病弱无助,成了难以抗拒的势力抛上抛下的玩物。”
这让《五号屠场》成为文学史上的“后现代”经典,是“元叙事”或“后设小说”的代表。不过,读故事不用被这些唬到。这其实是一本通俗科幻小说,只须把老冯当做个阴阳怪气的说书人即可。
他就坐在那儿,要给你讲一讲比利的故事,却不知从何说起,于是这儿讲一段,那儿说一段,有时候打断故事点评一二。
比如故事开头,老冯先来一句:听我说(Listen)……台湾麦田版的翻译更像说书人腔调——
诸位看官,毕勒·皮尔格林(即比利)已经无视于时间的存在了。
这句开场白是老冯的一个提醒,它打乱了惯常认知。所谓“杂乱无章”和“胡言乱语”的讲法造成了与现实的疏离,就像日常的我们,时刻身在社会角色和思维惯性的蒙蔽中,唯有抽身而出,方能离得够远,看得够清。
比如说,小说的科幻设定,给我们提供了高于自身的视角。
外星人绑架了比利和一位女明星,关在动物园里展览,不但吃喝拉撒,乃至性交都要直播。这一视角为说书人提供了自我审视的距离,就像人类观察蚂蚁。于是比利会站在人类的立场思考问题。
他对外星游客说:
——我来的星球上,有史以来一直纠缠在疯狂的屠杀中。我本人亲眼目睹过被我同胞放进水塔活活煮死的学校女生尸体,施暴者还为与纯粹的邪恶作斗争而感到自豪。
——晚上我在战俘营用来照明的蜡烛,是被那些死于沸水的学校女生的父兄残害的人类尸体脂肪做成的。地球仔一定是宇宙的恐怖生物。
——所以把和平秘诀告诉我,让我带回地球,拯救我们所有人:一个星球上怎样才能和平相处?
外星游客却表示,这个地球仔的问题非常愚蠢。
因为这个星球的人有着不同的时空观念,可以同时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和2016年上映的科幻片《降临》中外星人的时间观念很像,他们掌握了非线性语言,可以摆脱线性时间的束缚,从高于自身命运的层次审视自己。
比利掌握了这一时间的真理,认识到“事情就是这样”。
每个现在都是没有原因的,也不会成为任何未来的原因。所有的时刻并行存在,且永远存在。死去的永远死去,活着的也永远活着。
有了这样的时间观念,比利对命运的理解变得不同,他也学到了外星人的生活诀窍:忘却痛苦的时光,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好的日子。
不幸的是,比利学艺不精,无法控制时间跳跃,他不知道下一个瞬间自己会进入哪个时刻。我们渐渐明白,眼前的故事碎片是比利在不同人生时刻之间的随机跳跃。
尤其是在电影改编中,导演让我们看到老年比利躲在家里打字,讲述自己被绑架的经历,我们不免怀疑,这人可能脑子出了毛病。
一九七二年,电影《五号屠场》获得25届戛纳影展评审团奖。影片对巴赫音乐的使用和流畅的蒙太奇最为人所称道。这两个创意,可以说都是在表现比利的“精神错乱”。
比利告诉我们,早在被外星人绑架前,他就从时间链上脱开了。
一九四四年,他作为随军牧师助理参加战斗演习,为大家弹奏巴赫的圣歌。这时来了一名演习裁判,演习中谁活着谁死了都是他说了算。裁判说,从理论上讲,正在听巴赫的士兵理论上已经被敌军空军发现,他们理论上已经死了。
比利发现:
理论上的尸体们都乐了,然后美美吃了一顿午餐……这与特拉法玛多人遭遇死亡的经历是何等的相似,死了以后还可以吃饭。
这事发生之后,比利就被送往了欧洲战场,然后被俘,不久之后经历了德累斯顿大轰炸。我们可以认为,比利是在目睹人类不可救药的愚蠢暴行之后,只能以精神崩溃逃避创伤,虚构出外星人,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洞见,看清了人类的真相。
这让我想起一本家叫做《论杀戮》的书里说到,国家喜欢用金钱、生产力损失、或士兵死伤数量衡量战争成本。却很少以具体士兵所遭受的痛苦衡量战争成本。
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精神崩溃才是最昂贵的战争成本。
比利精神崩溃的无厘头人生,源自说书人老冯最深的绝望。
他的一生中,无时不刻活在蒙太奇的记忆穿梭中。“忘记痛苦,只想美好”大概是他幻想的安慰。其实各位看官,我们的脑内不也每天都在时光蒙太奇吗?只是我们一般不拿它当回事儿。
因为我们没有像老冯一样,于童年期的末尾在德累斯顿挨过轰炸,更没有挖过“尸矿”。
德累斯顿大轰炸的愚蠢,在于自始至终它都被当做“手段”。下令轰炸的政客视其为战略,执行轰炸的飞行员则高高在。没有人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到十五日,盟军动用800多架轰炸机,往德累斯顿扔了3900吨炸弹,毁掉了22.2万座住宅,72所学校,22家医院,19座教堂,5个影剧院,31家百货公司,等等。死亡人数难以统计,至今仍有争议——但数字早已经不重要,重要是人一个一个地死掉了。

轰炸是精心策划的,且良好运用了技术,先投高空炸弹,爆掉建筑物顶层,再投燃烧弹,确保所有东西烧起来,人们在火焰风暴中死去,很多还保留着死前的姿势。
电影用了很多镜头描写遭轰炸前的德累斯顿建筑风光,并展示了很多平民面部特写,看得令人十分难过。
和电影不同,小说中没有多少特写,比利在时光跳跃中看到:整个城市变成了月球。他和其他幸存者只能在滚烫的废墟里爬行。
谁也不讲话,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话好说。有一件事是没有问题的:城里所有的人,不管是谁,按理都活不成了。如果城里还有人在走动,就表示这次大轰炸的计划还有缺点:月球上是没有人的啊!
他们遇到了仍在侦查的美军飞机。飞机见都活人就扫射,试图斩草除根,确保更好地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对于这一行为,比利,或说书人老冯这样解释:事情就是这样——目的是为了加快战争的结束。
这确实是人类的惯用手法,打你是为了让你认输。人类很聪明,很少为了打你而打你。只是,他们总忘记挨打的滋味。死亡就更不用提了。
命令、麻木、正义感、仇恨上头,以及利用技术远距离操控,让他们故意失去了共情能力。
逃离死城后不久,比利和其他幸存战俘又被押回德累斯顿挖尸体。老冯称之为挖“尸矿”(corpse mine)。尸体太多挖不完,干脆用喷火枪就地烧掉。这项工作里有比利,有老冯的战友,还有老冯本人。
老冯就是比利,比利就是老冯。真实就是虚构,虚构就是真实。《五号屠场》是老冯和几十万次死亡共同写成的。
查资料时,我看到一个历史学家的评论:这座象征着德国巴洛克之最的城市曾美得让人惊叹。纳粹期间它却成为德国的地狱。就20世纪的战争恐怖而言,德累斯顿大轰炸是一个绝对带有惩戒意味的悲剧。
我想,他说的惩戒是指对纳粹的惩戒。
詹宏志的评价是,德累斯顿大轰炸更像圣经里索多玛遭天火焚城。这是人类堕落的报应。
老冯对此没有评价,他讲了个故事。
一个人穿越回过去见到了耶稣。耶稣正在跟父亲学木匠活。两个罗马兵走进来,拿出一张设计图,要求次日完工,要做一个十字架。耶稣父子很高兴接了这么一个订单,而那个蛊惑人心的煽动者将被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
事情就是这样。
不过老冯引用了一位退休的英国空军准的文章。在评价一本研究大轰炸的历史著作时,这位准将说,有人为战争里死掉的敌方百姓哭泣,却不同情我们英雄牺牲的飞行员,真让人无法理解。
……我想应该请欧文先生(作者)记住这样的事实,在他描绘德累斯顿平民被杀的图景时,V1和V2火箭正落在英格兰的土地上,杀死非武装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这种武器设计和发射的意图就是滥杀无辜。
最后他得出结论:盟军在德累斯顿杀死了十三万五千人,对此深表遗憾,但我记得是谁发起了战争,更痛心的是为了清除纳粹主义而丧生的五百万盟国人民。
老冯还引用了杜鲁门下令用原子弹炸日本之后发表的宣言,和这位准将意思差不多:敌人比我们坏,理应惩罚,上苍保佑拥有原子弹的是我们。
他们这些意思,究竟该如何解释呢?
老冯沉默不语,只是反复讲了另一个故事。
战争临近尾声的一天,比利和老冯在德累斯顿挖尸体,一个战友从废墟里捡了一把茶壶,于是看守抓住他,然后枪决了。
还能作何解释呢?
外星人的看法是:没什么好解释的,就你们地球人爱问为什么。
地球仔都是做解释的高手,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个事件是这样构成的,预言其他的事件是如何促成或者防止。我是个特拉法玛多人,看到的是整体时间,就像你们看到绵延的逻辑山脉一样。整体时间就是整体时间。它不会变化。
如果看到得到无限,意义也就消失了。这不难理解。可是人类从来没拥有过全知视角。
人类必须解释。行动之前解释理由,完事之后阐述意义。
解释是人类文明的动力,但也是自毁的动力。人解释世界,再对解释做出解释,解释解释再解释。最后难免满口都是自以为是的谎言。
德累斯顿大轰炸之后,交战双方动用了解释机器,指责对方不义。战后几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军事专家和政府都参与了这一行为。
大轰炸能叫大屠杀吗?大轰炸算是战争罪吗?吵得不可开交。
有人很理性,认为大轰炸是技术性杀人——这一点美国就比英国做的好,他们先发传单再轰炸,白天先做尝试性轰炸。真是体贴入微。
必须要说明,当时这些争论从未出圈,普通人甚至执行任务的飞行员都在鼓里蒙着。政府说,这属于国家机密——老冯问,这是跟谁保密呢?
任何试图通过战争叙事寻找因果逻辑的行为,都是人类在为自身的愚蠢和荒诞找借口。
战争结束后回家的路上。老冯问战友:这一场仗打下来,你有什么收获?战友想了想说:我再也不相信政府了。
事情就是这样。
一九九二年,《花花公子》杂志请两名小说家对谈。一个是冯内古特,另一个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者约瑟夫·海勒。两人年轻时都代表美国参加了二战,经历可谓“天上地下”——老冯在德国亲历大轰炸,而海勒在北非干的就是空军投弹手。
老冯说,德国党卫军训练士兵,会要求他们必须徒手勒死一只猫。而现在,大家只需要看电视,就能达到杀猫的效果。
海勒回答,我猜勒死第一只猫后,其余就容易了,接下来的纯属娱乐。
勒死猫的训练不一定真有,但这两人的谈话触及了人类存在的一个荒诞悖论:因为拥有共情能力发展出超越动物的文明,又不断设法抹杀共情能力,让自己变得原始野蛮。
战争离我们很远,但也总近在眼前。
殴打、性侵、羞辱,同类间的恶意攻击、掠夺和支配,是现代日常生活中的恐怖袭击。各项你黑我白的“军事训练”时刻都在发生,而你死我活的真实战争就是这种极端思维的最终表现。
一九八零年,冯内古特在访谈中说,人类是在以一种嗜酒者互诫协会的方式生活,相互劝诫,却不加克制。
......每一天都有更多的武器被制造出来,更多战争论被愉快地灌输,更多危险的弥天大谎被讲述,所以说是没有克制的。如果我们能像戒酒者那样,不好战地多过一天,就已经很美好了。但不是这样,我们绝对好战,迟早会出问题。
事情就是这样。该怎么办呢?
不知道。但至少不要主动蒙上眼睛堵上耳朵吧。
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像老冯在《五号屠场》里提到的那样去想——
上帝赐予我
接受我无法改变之事物的
平静,
改变可改变之事物的
勇气,
以及区分
这两者之不同的
永恒智慧。
注:未说明出处的小说引文,来自译林出版社《五号屠场》,虞建华翻译。
二零二一年九月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