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女孩之死》#02
我相信這些片段一定存在。而且是在許多地方。
我是宜君、是婉琳、是蕭子黥。
Day060_宜君
宜君身高一米七,身形說不上胖但也不會用纖瘦形容他,因為是家中的么女,所以經常聊天中不免出現幾句:我就是小公主吶。粉色系的衣著是基本配備,口罩也要用粉紅款做搭配,喜歡聽到人說他是個少女,但事實是已經三十六歲的少女,但在藝術圈還沒站上舞台的都算是少女吧。
宜君專打的招牌是學術研究,從第一天認識起,他就說了他對研究的熱愛,但只是說。從大學畢業之後他選擇前往台北,在面對工作的壓力下,他先到了畫廊擔任櫃檯工讀生,這一刻起,他的生活不只是凡俗的瑣事,而是多了「藝術」,一個可以解答生命的「藝術」。
床頭貼上法國作家馬塞爾 ‧ 普魯斯特的名言:「偉大的藝術品不像生活那樣令人失望,它們並不像生活那樣總是在一開始就把所有最好的東西都給了我們。」我們需要為了藝術犧牲,金錢並不重要,情愛只是一些小事。
宜君開始看展覽聽導覽,甚至遠赴國外參與雙年展,打卡證明,節錄藝術家的話變成是必要的發文方式,限時動態必須放上「#到了巴黎」、「#在咖啡館坐了一個下午」、「#懷念的聖母院」、「#如畫一般的萊茵河」,漸漸社群軟體充斥著與自己相似的女孩們,不免俗的是必要在網路世界中放上自己的出身,女孩們各來自不同美術館、畫廊、協會等等等,但工作岡位一欄是個空白,「不想給自己侷限。」宜君解釋道。在臉書強大的社交結構下,宜君一個一個點下藝術家的交友邀請,曾經我們都在同一個美術館工作,這是宜君的開場白,喜歡老師的作品,接著討論下去。
宜君知道藝術圈其實是個刷臉吃飯的行業,而學歷也是其中之一,代表了你的階級。宜君選擇用「藝術史」來包裝自己,選擇了南部的研究所,課程中學會了「研究」。積極跑著美術館看展覽,期望在展覽的角落會偶遇個誰,來討論一下藝術史,不用談論太核心的話題,話語中帶著文本、想像、認同、分析、論述、再社會化等等,大家都會心照不宣點到為止,用一些無法輕易定義清楚的名詞組構一個句子,已經足夠。
漸漸宜君渡過二十幾歲的青澀,時間沒有停緩,到了三十六歲,和第三任男朋友分手、沒完成論文、回到北部繼續工讀,眼看畫廊又進來了更多的年輕女孩,宜君知道自己該想著下一步,不問工作內容只要是正職就好,沒關係的,這裡離藝術夠近。
迎新餐會上同事問著之前是做什麼的,宜君回答道,我是做研究的。同事驚呼居然讓著做研究的人來收發公文,肯定是主管昏了頭大材小用,宜君笑笑地說,我研究所是念藝術史的呢!同事各個為宜君抱不平,這樣的資歷,怎麼會被放在這間小小的辦公室?沒錯,「研究」藝術是宜君一生的志業,宜君的生命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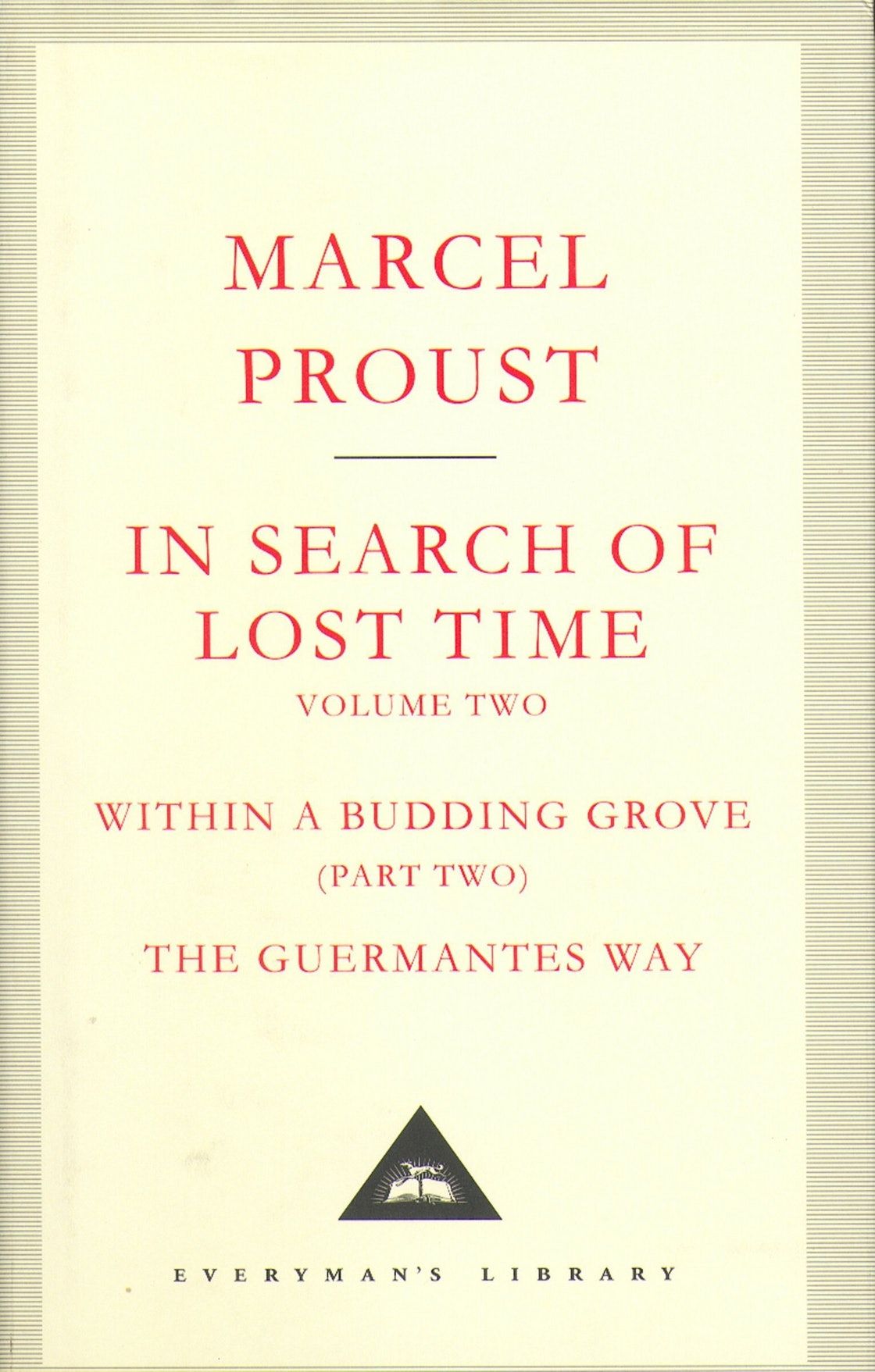
Day090_婉琳
回到今日的飯桌,婉琳有些不同。「除了講座,我終於有了其他工作!」容光煥發的原因是這個。接下來一個多月的午休時間都少了婉琳加入,我與宜君的對話,總是停頓在收發公文有多麼無聊,然後就轉向新聞報導,看著哪個藝人愛上了不該愛的人。吃完了每日不變的炸醬麵,沒有冷氣的小店顯得有些悶熱,電風扇轉動發出依依歪歪的聲響,摸透午休模式的我與宜君都不急著離開,喝著老闆娘免費提供的冰涼紅茶,只有甜味沒有別的。
「叮咚!」「叮咚!」…
「叮咚!」「叮咚!」「叮咚!」「叮咚!」
兩個人手機的震動聲同時LINE起,我和宜君對看了一眼,婉琳由遠端加入我們倆的沉默飯桌了,「其他工作」像是個爛攤子般讓婉琳由愛生恨。
從小麵攤回到辦公室有一小段路,我和宜君有一搭沒一搭的開了幾個話題,但兩人其實都沒有心情,宜君時不時發出些無意義的嘆息,街道沒什麼變化,跟一個小時前差不多。修馬路的三角錐依舊擋住我們的人行道,走進行政區前的草皮依舊沒一片遮蔭,原本只是稍微炎熱的午餐時間,手機延燒了婉琳的憤怒,平淡的風景,讓人看得好膩。
婉琳出生於彰化小鎮,大學時期脫離了家鄉到了北部念書,畢業後不顧一切留在了台北,與宜君一樣,選擇了到畫廊打工,不同的是婉琳在台北唸了研究所,閒暇時刻還在美術館擔任志工,每每說到那個時期的婉琳總是眼神一亮;偶爾休假婉琳會告訴我們他這禮拜要「回」去美術館看展覽,對於婉琳來說美術館可能更像是他的家鄉。
身高一六四,身形纖瘦,第一眼見到他的人都會用漂亮氣質來形容,不負眾望的,婉琳也曾擔任過藝術家的模特。衣著的選擇總是寬鬆的飄飄然,灰色駝色白色,仙女類的材質都適用於婉琳的身上。
婉琳是個積極的人,開口閉口希望主管增加工作內容,教育講座不是他的志向,婉琳的主動讓主管指派了新的任務,並且讓坐在我前面的如芳姐指導。那時那刻,我羨慕著婉琳的坦率。
「其他工作」在婉琳由愛生恨的前一個月都還是有趣的案子,婉琳見到了藝術大師,又參觀了工作室,「我還拿了那個獎盃呢,沉甸甸的很有手感!」婉琳開啟照片分享道,畫面中的婉琳擺出了各種姿勢與表情,獎盃在他手上看起來再自然不過。
新工作內容在經過走訪踏查後,馬上就要開始執行,婉琳興奮的等待著如芳姐的指示。再一次講述工作流程,如芳姐決定要婉琳為自己負責,公文、採購、發包、核銷,對婉琳而言都是新的事物,一個錯誤就要重頭來過,在如芳姐離開婉琳身邊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事與願違。
「這跟我想的做展覽不一樣。」婉琳抱怨道。
茶水間,患難姊妹群接續著中午飯局,婉琳繼續講著,行政的繁忙如何讓他失去了策展的熱情,「那個藝術家一堆單據交給我,要我想辦法去報帳。這到底關我什麼事?」這是體制壓迫,這是諸多的不合理,「只是想要做展覽,為何最後成了這樣?」婉琳下著結論,插曲聚會解散,我們各自帶著婉琳的怒氣在辦公室的一角,但依舊,無聲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