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基雅維利到馬克龍(中):為保衞共和而「衞生獨裁」?
前情提要:《從馬基雅維利到馬克龍(上):「出言不遜」背後的選戰考量》
如何防止公民德性滑向朽敗?
對馬克龍這種選戰手法的揣測(參見《從馬基雅維利到馬克龍(上):「出言不遜」背後的選戰考量》),無疑符合一種厚黑學式「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認知。但馬基雅維利在思想史上的真正意義,一直是個聚訟紛紜的話題。保守主義、共和主義、民主主義等不同流派,各自提出對馬基雅維利的解讀和闡釋。其中尤其以《君主論》和《論李維》為二元框架,形成了闡釋馬基雅維利的某種內部張力,前者顯然更汲汲於意大利城邦間的爭鬥權謀,後者則似乎更傾心於羅馬式共和的理想圖景。
嚴格來說,馬基雅維利既不是精英主義者(如大部分傳統觀點所言),也不是民主主義者(如麥考米克所言),他所真正看重的是民眾和貴族之間的衝突而對共和國造成的好處——「平民和羅馬元老院之間的不和,促成了共和國的自由與強大」(論李維,第4章)。他對民眾本身的「美德」並不抱期望,甚至不乏鄙夷之詞:人遠不是天使,他們忘恩負義、容易變心,是「偽裝者」和「冒牌貨」、逃避危難、追逐利益,他們會更容易忘記父親之死,卻不容易忘記奪財之恨。在他看來,民眾有兩個致命弱點:一是缺乏足夠的理解和判斷能力,容易為外表和眼前狀況所欺騙——「庸眾(vulgo)總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結果所吸引,而這個世界裏盡是庸眾」(君主論,第18章);二是缺乏統治和領導能力,容易變得一盤散沙。
劍橋學派代表人物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指出:馬基雅維利式的共和主義,其本質可以用兩個相關命題來概括:一、除非支持一種自由的生活方式,否則任何城邦都不能實現偉大;二、除非堅持一種共和的憲政,否則任何城邦都不能支持一種自由的生活方式。但斯金納同樣承認,馬基雅維利的困境可以歸結為:「如何才能在天然缺乏德行的公民群體中培育出德行?如何防止他們滑向朽敗?如何強迫他們在足夠長的時期內保持對公共福祉的關心,以實現城邦的強盛?」事實上,這不僅是馬基雅維利面臨的困境,也是古今一切自由體制所面臨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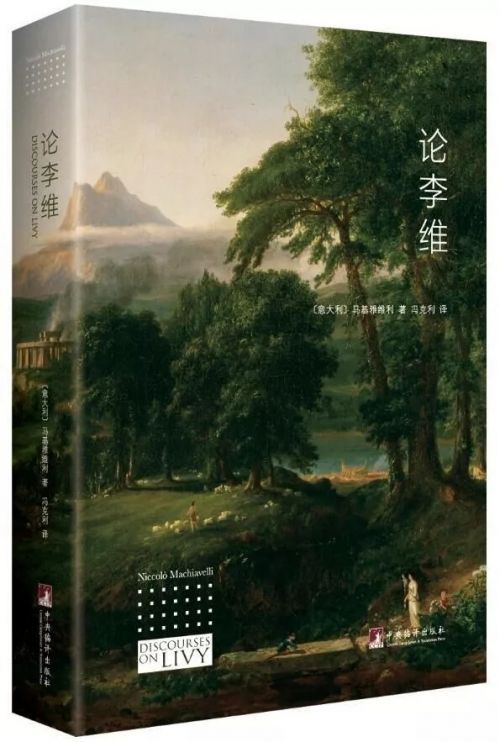
在馬克龍的發言風波中,媒體普遍都將注意力放在emmerder這個用詞、以及挑釁性的語氣上,卻往往忽視了另一句話——「一個不負責任的人,就不再是公民了」,這句話已經顯得如此老生常談,甚至被庸俗化誤讀為「不打疫苗就不是法國人」。但顯而易見,這裏的「公民」不是指所有具有國籍的國民,而具有明顯的共和主義意涵,意指對維護和發展共同體負有責任、必要時作出貢獻和犧牲的成員。
從馬克龍的角度出發,他無疑希望將「支持政府防疫」和「展現公民精神」二者綁定在一起,畢竟這最有利於他的施政;但對於反對者來說,要論證「反對政府防疫」和「展現公民精神」二者可以並行不悖,也同樣困難——尤其是當未接種者大量佔據重症病房床位、迫使醫院推遲甚至取消常規手術的時候。對此,部分法國醫護工作者憤而投書媒體,認為抗拒疫苗群體當然可以珍愛自己「免於接種疫苗」的自由,但同時也應簽下一份聲明,放棄同已接種疫苗、但仍被感染的患者爭奪救助機會的權利。
在同一次發言中,馬克龍還發出另一句警示:「在民主體制下,最糟糕的敵人是謊言和愚蠢。」反對者無疑可以從「愚蠢」中解讀出又一重傲慢和蔑視。但顯而易見,此次新冠疫情成為「謊言」——假消息和陰謀論——大行其道的教科書式範本(甚至迫使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正式發聲明闢謠,稱並未製造新冠病毒、並未在武漢投毒)。但和網絡霸凌言論不同,圍繞疫情的假消息雖然同樣可以起到殺人的效果,因為在法國極易進入「言論治罪」的雷區,難以採取強硬懲處手段。但對於馬基雅維利來說,謠言對共和極有害處,必須嚴懲造謠者,而且這種對謠言的打擊,應當同公民保有指控權(放在當代法國背景下,例如在共和國法庭起訴總理和衞生部長防疫不力)形成平衡手段,共同維護共和體制下的自由。

為保衞共和而「衞生獨裁」?
自2017年上台以來,馬克龍經常被批評是第五共和歷史上最年輕、卻最有威權氣質的「朱庇特式」總統。在強力推進退休制度等領域的各項改革、並激起黃馬甲運動之後,新冠疫情又迫使當局採取封城禁足、健康通行證、醫護人員強制接種疫苗等措施,更加劇了對於「專權」的質疑聲。在蔓延歐美多國的反疫苗、反防疫抗議浪潮中,「衞生獨裁」(dictature sanitaire)成為似乎尤其適合法國的應景口號。
在古典語境中,「獨裁」並不是一個全然貶義的名稱。馬基雅維利為之進行了強有力的辯護。在這一點上(正如施特勞斯學派的曼斯菲爾德所指出的),他甚至突破了王政和共和的體制界限,將二者等量齊觀,所謂「君主」事實上是王政和共和制下的共同產物(因此《君主論》和《論李維》也並沒有看上去那麼強的對立性)。馬基雅維高度讚賞古羅馬獨裁官制度,認為這是應對緊急事態所絕對必須的機制——「我敢斷言,共和國在危難之際,若不能託庇於獨裁官或類似的權力之下以求自保,必毀於嚴重的事端。」而即便在一般意義上,「任何共和國或王國的創建,或拋開舊制的全盤改造,只能是一人所為,要不然它絕無可能秩序井然……因此,共和國的精明締造者,意欲增進共同福祉而非一己私利,不計個人存廢而為大家的祖國着想,就應當儘量大權獨攬。」(論李維,第1卷第9章)
一個看上去弔詭的悖論是,以「獨裁」應對非常危機,乃是為了保衞共和作為穩定體制存續下去。正如馬基雅維利在描述一個面臨圍攻局勢的城邦時所指出的:「一個強有力的果敢的君主,此時一方面要使臣民感到有希望,相信禍患不會長久下去,另一方面又要使他們對於敵人的殘酷感到恐懼,同時把自己認為過於莽撞的人們巧妙地控制起來」(君主論,第10章)。而新冠疫情作為一場圍城戰,事實上也不脱這三方面的框架:一要讓民眾保有希望,不至於因疫情導致士氣一蹶不振;二要反覆強調疫情的嚴重性,不可掉以輕心;三要將那些「過於莽撞的人們」——抗拒接種者——以新冠通行證或疫苗通行證方式「巧妙地控制」起來。

在《君主論》關於「殘忍」與「仁慈」的討論中,馬基雅維利駁斥了道德論者的立論。後者鼓吹,仁慈的君主應當竭力避免懲罰措施,只有當罪行「一犯再犯、超出忍耐極限」時,而且在慎重和遲延之後,才會出此下策。但馬基雅維利認為,倘若君主一開始以仁慈自詡,其實是在放任混亂滋長,等到局勢不可收拾才訴諸於嚴刑峻法,這和一開始就雷厲風行地懲治首惡相比,究竟哪一種做法才算是對人民仁慈?正是在這一點上,馬基雅維利引出了他最著名的論題之一:君主應當受人愛戴,還是被人畏懼?他認為,如果無法二者兼得的話,那麼君主寧可被人畏懼,也要好過受人愛戴。
在現代意義上的「民有、民治、民享」政體中,真正意義上「被人畏懼的君主」宛如昨日絕響。但即便是民選領導人,個人氣質和執政風格仍然明顯分殊。以法國為例,右翼的戴高樂無疑屬於最具有君主氣質的民選領袖,威嚴而有擔當的形象,直接「召喚人民」的全民公決,都成為最具標誌性的治理風格。相比之下,左翼的奧朗德則是典型地以「仁慈」形象示人,結果卻導致陣營內亂頻頻,空有雄心壯志,卻憋屈到連二度出馬競選都做不到,功未成而身已退,以碌碌無為的「宋襄公式」總統形象進入選民回憶。
馬基雅維利指出,君主在履行自己基本義務的過程中,反對者對其所謂「惡德」的批評,乃是不可避免的代價。「君主為着使自己的臣民團結一致和同心同德,對於殘酷這個惡名就不應有所介意,因為除了極少數的事例之外,他比起那個由於過分仁慈,坐視發生混亂、兇殺、劫掠隨之而起的人說來,是仁慈得多了。」(君主論,第17章)而且「人民的性情是容易變化的;關於某件事要說服人們是容易的,可是要他們對於說服的意見堅定不移,那就困難了……當人們不再信仰的時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們就範。」(君主論,第6章)

「衞生獨裁」的界限
然而,馬基雅維利畢竟不是專制主義者,他只將「獨裁」作為一項臨時的非常手段予以接受:「獨裁官只是臨時之職,並非常設,僅僅是為了消除使他得到任命的事由而採取的手段。他的權力得到擴張,使其能夠為克服危機而獨自做出決斷……但是他不能做損害國家的事,例如剝奪元老院或人民的權力,對城市的制度廢舊立新。」(論李維,第1卷34章)
在馬基雅維利看來,在國家的危急關頭,將權力授予一人,有時是非常必要的,但正確的做法是通過合適的制度,確保這項權力不被濫用。而要實現這種目的,有兩種方式:一是為這種絕對權力設定期限,不允許無限期行使;二是確保該權力的行使僅限於最初需要應對的事由。
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以法德為代表的法治國家,在疫情防控問題上並未突破法治框架。儘管政府以「緊急狀態」為名頒布封城等嚴格限制措施,但前提仍然是議會針對緊急狀態法進行明確的法定授權。在德國,隨着新政府換屆,緊急狀態法不再延長,但同樣有新法取而代之。而在法國,緊急狀態雖然已經多次延長,但在每次延長時,其具體截止時間和政府由此獲得的行事範圍,仍然是議會「討價還價」、藉以節制政府的手段。
此外,法國的司法體系扮演了在緊急狀態下進行權力制約和權利保障的角色,例如行政法院此前否決了封城期間在巴黎大區超大型商場查驗健康通行證的措施,今年年初又否決了巴黎重新實施戶外強制口罩令的措施,認為這是對個人自由的「過當侵犯」,更不必說憲法委員會和共和國法庭也在各自職權範圍內,對政府施政行為起到相應制約。
反防疫、乃至反體制的激進人士或許對此仍憤憤不平,認為這些機制都是「一丘之貉」,根本無法保障他們鍾愛的「自由」,但從疫情兩年來的博弈進程來看,雖然行政當局為應對疫情而獲得了平時狀態下無法想像的權力,但這種權力並非絕對性質,按照馬基雅維利的標準,它既不是無限期行使,也並未突破最初需要應對的事由、變成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管治的工具——正如在世界其它某些地方所展示趨向的那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