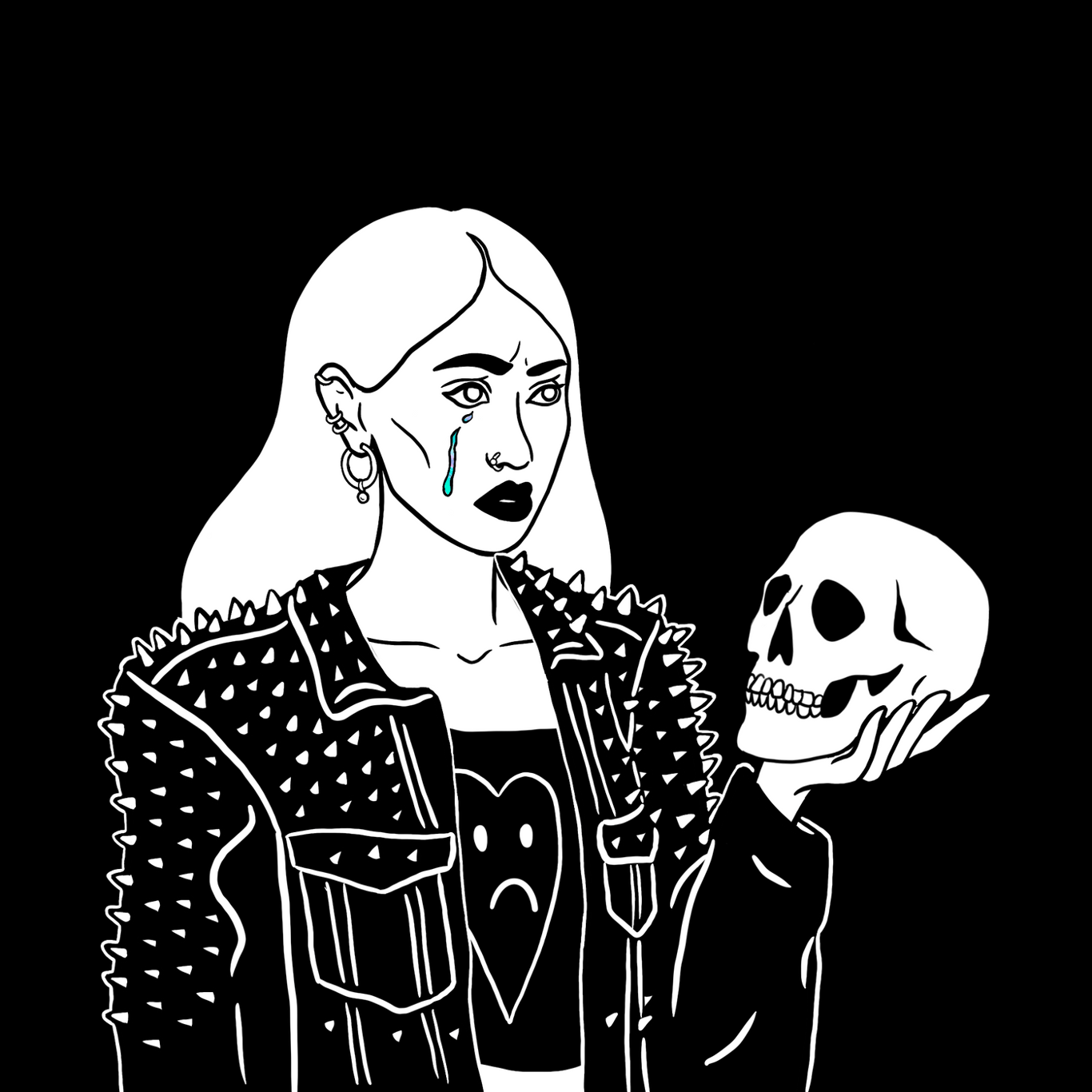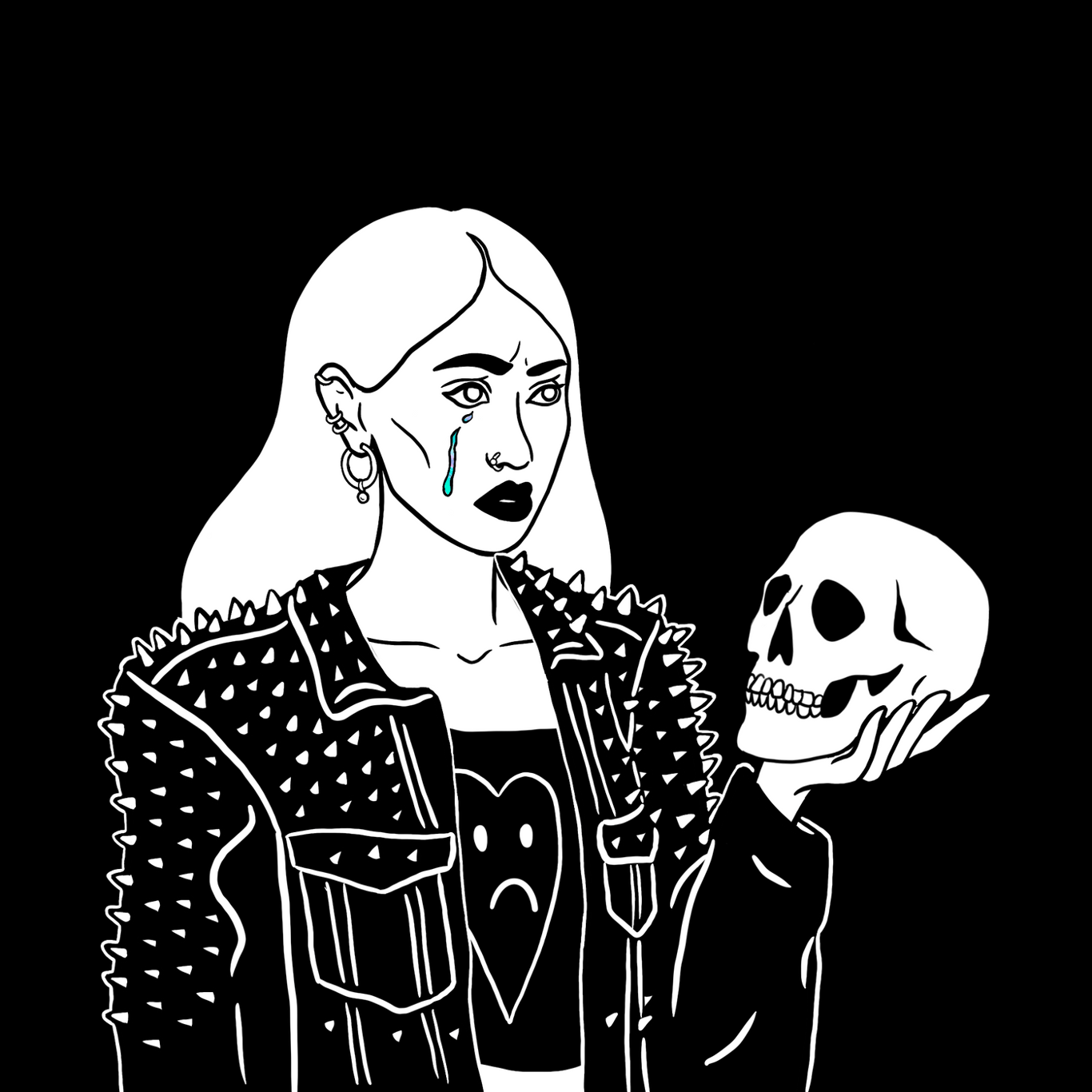循環的夜
時隔五個月與黃巴士再會於香港。一早已經在思索難得重遇要一起做些什麼事。我們同時想到要一起去bc睇戲。於是兩個同時擁有見面熱情、時間,以及離譜時間觀念的人,約定電影開場前三小時於電影中心碰面。繼在柏林看的那場沒有英字的德語紀錄片之後,『烈日餘盡』是我們一起睇的第二套戲。其實這部在弗羅茨瓦夫時我已與lyu一齊看過,但我又十分願意在電影中心看多一次夜間場,以抵抗jet lag之名。其次,regardless of 『紅色天空』使我想起菲的『回憶是紅色的天空』以外,我其實更喜歡港譯名『烈日餘盡』,亦覺得它十分符合這城市這分鐘的氣候和狀態。
電影散場已經凌晨十二點,黃巴士問我有否在這時間到過果欄,我不記得有,於是我們就這樣即興決定於午夜夜遊果欄。行走在檔口之間,我發覺夜晚燈光下的生果尤其鮮亮市聲也格外動聽。一路散步到了地鐵站,我提出不如再將黃巴士送回家樓下。就這樣將這晚稍稍拖延了一點,我們終於站在樓角告別。當擁抱使我們之間距離最近時,黃巴士笑笑著說: 噯不要這麽難捨難分! 語氣輕輕帶過。
第二日一起去吃炳記,只因前一晚在bc看到本雜誌的封面是炳記的插畫——『即興』彷彿伴隨我們每次會面。埋單時老闆壓低音量略帶神秘地問我是否認出了對面著黑色衫的男子。但當時男子背對著我,使我難以辨認。『大明星咩?』,我問。『你再睇睇,睇實d』,檔主答。黑衫男子不知是否感受到我們的熱烈目光,突然間轉過頭來,我定睛一看,噢,原是陳山聰。那一刻我的心理活動是,還好我的確叫得出對方的名字,不然怕會令檔主感到些許失望。
從炳記出來下了小雨,我們決定去附近的咖啡廳坐坐。在路上黃巴士透露她已收到我從柏林寄的明信片。我感到些許驚詫。從過往寄給ta的信件判斷,從歐洲到香港通常耗時兩個禮拜,我大概也已在心裏悄悄計算過明信片會在我離港後才抵達: 再會——分別——收到明信片——再次見面——而後再度分開,這是我自以為恰當的不至於令誰驚怕的聯絡密度。在咖啡廳坐下後,我情不自禁回想著明信片的內容,於是開口問可否將它借給我再讀一次,藉口是,讓『記憶復甦』。結果讀了兩行字我竟然有些不好意思再讀落去。而黃巴士也說,見你讀我也感到不好意思。於是我將話題轉移至——我發覺明信片的郵票不見了,興許是途中掉落了,總之右上角如今只剩被切割整齊的半枚郵戳。但我的信仍然送達了。作為總是盼望憑藉信件交心的人,我慶幸信件丟失這種大概率事件今次沒有發生在我身上。對了,明信片的背面是珍寶金的插畫,我自然是因為聯想到『美孚根斯堡與白田珍寶金』才選的。
在上環的古董店,我和黃巴士留意到一張幼兒園畢業證。正唏噓於這張證明流落到這的神奇,發出不知主人如今過著怎樣的生活之類的感慨,我們這才留意到數字: 生於1993年。我們竟發出了失落的噓聲: 彷彿主人公(at least和我)差不太多的年紀使這個物件的魅力大大折損。而後,我們又花了較多時間凝望一張手寫的結婚紙,紙張抬頭的印花裝飾如同獎狀——婚姻像是某種勳章。已是上個世紀的婚姻證明,我先是發現簽紙時女方已經四十余歲,說著這在那個時代應該算是晚婚之中的晚婚。黃巴士又接著留意到新娘比新郎大整整十歲,這在當時應該也並不多見。我其實很喜歡這百無聊賴的對話。一如在大坑散步見到『lonely』字樣的塗鴉,我說這lonely,看起來真的好lonely啊,黃巴士就會不假思索地接: 它旁邊甚至都沒有別的塗鴉。有人能立即明了你的離題實在是很好的一件事。
受邀去小王小包家做客的傍晚恰好有一小段空閒,我於是在黃巴士的家稍作停留。黃巴士提議不如彈吉他給我聽? 我心中狂喜。唱『介乎旺角與法國的詩意』時,我感到我們之間眼神接觸的timing和歌詞似乎形成了微妙的對偶。我不免情緒氾濫、過度思索,但隨即提醒自己切勿overinterpret這密密的eye contact的用意。滿心飄蕩聽著『浪漫九龍塘』,心裏想著,對著我唱我的歌,這是無與倫比的待客之道。而後我又『得寸進尺』點了『馬田的心事』和『你的微笑像朵花』,因這兩首是我最希望能在此次演唱會親耳聽到的。大概因為所處空間以及歌詞氣氛的關係罷,到後來我們各自都有些不好意思,於是決定提前出門到電影中心煲菸。那天的後半段黃巴士突然回過神說,怎麼不記得要給你彈黃耀明的歌了,我會彈『身外情』。我說那留待下次好了。
那晚從朋友溫馨的家離開,我們需在油麻地站分手。很快到站,閘門打開,我們在座位上匆匆講了再見,黃巴士快步離開,跑到門邊突然又記起什麼似的,迅速折返,我尚未回過神來已接收到一個適度的擁抱。黃巴士再次快速跑跳出閘門,門隨即關上,地鐵啟程。精密得幾乎令我痴迷的卡點,沒有一秒鐘是空白的。隔著車窗,黃巴士一邊朝著車行駛的方向在月臺行走,一邊回頭對住我笑。我恍恍惚惚間朝ta揮手,突然一句my little airport的歌詞就潛入我的腦中。
更多細小的事不知如何記載。例如我們剛剛入座,餐廳就開始播『石頭記』。我在心裏想這種事像是只有跟黃巴士一起時候才會發生,尤其是當這間店根本不像是會放這種歌的。在界限書店,書架上貼了很多我們過分熟悉的廣東歌詞,黃巴士也輕輕留低了幾句,引用自『下一站天國』。問我要不要留言時,我搖搖頭。我寫下任何字以前都免不了內心交戰,信手拈來對我很難。所以『天然』才會是我尤其欣賞黃巴士的特質之一。在信和,我低頭無目的地尋覓著,驚覺黃耀明的一輯號外封面原是在致敬德國樂隊kraftwerk,於是我立即興奮地在店的另一端找到黃巴士。而後,就像開啟了某個神奇按鈕,我們進入的每一家CD店,目光掃到的每個角落,都是不斷地再遇kraftwerk那張唱片。以及,在媽不在家傾談時,因我過分發達的淚腺和感同身受的能力,我竟然聽黃巴士的故事聽到淚流。事後也反復領略著對方所說的,『不男不女,不彎不直,不順不跨』。這『宣言』使我深深感到人的遼闊和無垠。但,即使我們都不喜標籤不想將自己放置於小盒子裏,我們都承認詞彙的重要性。沒有詞彙,我們怎知『自己』是甚麽。
總而言之,過了四年重回這裏,聽了一直想再聽的樂隊,見了一直盼望再見的人。同時以一種新態度體會著與『人』的親近感。我的身體被純粹地用來感受不可明說的狀態和情緒,以及細微的動作,譬如聽show時不時與隔離輕輕觸碰的肩膊、點菸時怕風將火吹滅於是貼於一起的手、不覺意用了同一隻飲管… 諸如此類的。失真幻醉已分不清metropol和九展,香港和柏林也相差無幾。但我已決心將my little airport的「微妙」實踐。欣賞有生命力的人、柔軟的事物、與人關係的多種樣態,喺呢一刻是最緊要呢。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