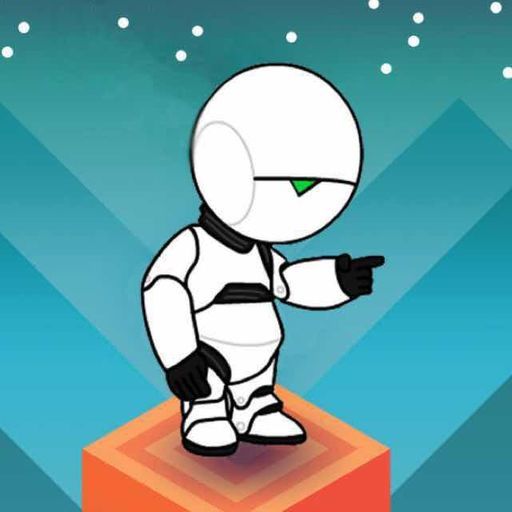书评 | 《为了活下去的思想》上野千鹤子的理想与现实之重

因为很敬重上野千鹤子,也认为有必要更认真地对待她这部作品,好听的赞美就尽量少说了,毕竟夸得天花乱坠的书评豆瓣上根本不缺,短评 里我也夸完了。这篇书评就仔细讲讲这本书中上野的大概思考过程,以及让我感到困惑和遗憾的地方。我相信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提出质疑,也是上野希望她的读者们去做的事,正如她在本书第四部第一章那篇访谈中所谈到的——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再给我一些反应会更好呢?没想到几乎没有反响。感觉这种沉默仿佛绵里藏针(笑),有一种说不出来但一定不对劲的寂静感。
这段话是她在谈及本书第一部第三章“对抗暴力与性别”(以《女性革命战士的一系列问题》为名发表于2004年,见P287“初出预览”)时的感慨。这也是 我认为书中尤其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理解上野“活下去的思想”的基础,在当下的中国也非常有现实意义。
表面上看,这部分是上野在回答“女性能成为革命战士吗”的问题,实际上在谈的却是“弱势方以暴力形式反抗强势方无罪吗” 这个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
上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清晰有力:“不存在正义的暴力” “所有暴力都是犯罪”。而且为了更进一步解释自己的观点,她在后文(第二部分战争的犯罪化 第三章 9 在战争罪与名为战争的罪行之间),很完整地讲到了为什么在女性主义的角度下,需要有如此明确的观点——
女性主义就是一种少数群体的思想。少数群体指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吃亏、受到歧视、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女性主义并不是一种要求“女性也要和男性一样变为强者”的思想,而应该是“弱者以弱者的姿态受到尊重”的思想。
(更完整上下文请参考我的 读书笔记)
而我们要理解上野为何如此强调女性主义需要有为弱势者发声、捍卫弱势者尊严的立场,就需要回到本书第一部分的第一第二章,去看看上野是怎样分析“公民权”概念的源起和后果的。
在作为理论基础的这两章里,上野敏锐地指出:传统父权制结构下“兵役”制度往往与“公民权”深度绑定,服兵役成为了一个人具备“公民权”的必要条件。而看清二者之间的关联,也能让我们认识到 传统的“公民权”实际上就是以个体参与公领域的暴力(战争)为条件,去交换在私领域行使暴力的“许可”。公民权所承诺给公民的特权之一,是对私人财产的所有权和处置权。然而,传统父权制结构下,女性、孩子、老人等家庭成员中的弱势者,是不具备公民权的,他们同样被认为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所以后果就是——当一个人(往往是男性)以服兵役的形式,参与了战争等公领域的“正义”暴力,换得了公民身份后,他在私领域(家庭、亲密关系)内也就可以按照同样的逻辑,对其财产任意处置,并被父权制国家认定为“无罪”了——因为这是他的隐私。不幸的是,对所谓“财产”的处置中当然也包括了使用暴力,结果便是女性、孩子、老人等弱势方常常沦为受害者,实施家暴、性侵、虐待等等行为的加害者,却往往被社会纵容和包庇。
所以,如果女性主义的诉求是平等分配这样的“公民权”,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而且这样一种为强势方量身定制的“公民权”,也必然是稀缺的,不可能实现平等分配。即使如第二章所着重分析的那样,女性中的一部分人通过服兵役获得了这样的“公民权”,其结果也不是女性改变了军队,稀释了其中的暴力性和残酷性,而是反过来,女性被军队所改变,同样成为了施行暴力者,甚至可能也成了私领域(家庭)中新的暴君,变成了另一个父权制结构下的“男人”。而这显然违背了女性主义的初衷。上野在分析这种转变时对本质主义女性叙事的批判,非常犀利精彩。
因此,在第一章 10 公民权与社会的公正分配(P33) 中,上野才引述了野村浩也的这样一段话,并如此总结——
“在性别框架之中 , 男性首先是歧视 ( 女性 )者:变得像男性一样 ,就意味着成为歧视者(对女性而言,她们自己要成为歧视女性的人)。然而 ,要想成为歧视者,就一定需要被歧视的一方:不存在没有被歧视者,而所有人都是歧视者的社会。”
对女性而言,公民权的性别平等并非要求性别之间分配正义的思想——女性也享有男性所享有的公民权利。换句话说,“女权”的要求,即女性对“公民权”正义分配的要求,是要通过揭露公民权概念的破绽,使其从根本上脱男性化。
为了实现公民权概念的脱男性化(我更倾向于称之为“脱父权制”),就需要我们审视暴力这一传统男性气质的核心特质,拆解围绕着暴力的种种矫饰。比如,对于“比生命更重要的价值”的信奉。
上野认为,人之所以会选择将暴力行为正义化、无罪化,就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假设,既世间可能存在着某个目标,比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更重要,因此“值得”牺牲生命去交换。一旦接受了这样的想法,哪怕是女性、老人、孩子等等弱势者,也同样有可能成为暴力的实施者,这也就是“弱势方以暴力形式反抗强势方”。当这样的转变发生时,弱势方便“被军队改变”,成为了新的施暴者。
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性循环,上野才认为需要从根本上否认暴力有“正义”“无罪”的可能性。尤其是,如果我们要消除那些发生在私领域(家庭、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伤害,那么我们也必须同时明确地反对公领域那些被洗白为正义的暴力,战争或作为弱势者反抗方式的暴力革命都得包含在内。
可以说,上野是一位非常彻底且观点明确地坚持“非暴力”的女性主义者。为此她甚至坦言(P147-148)——
我的回答很清楚,暴力不存在“好”与“坏”,暴力就是暴力,我无法认可暴力。这就是我所给出的唯一答案。女性主义所给出的回答只有这一种。……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将私领域暴力全部铲除,为什么就不能一并铲除公领域暴力呢? 我认为, 在我们的目标里,私领域暴力的犯罪化和公领域暴力的犯罪化是可以并存的,并且都是可以实现的。
可是,如果“所有暴力都是犯罪”,那么作为要坚持实践非暴力的女性主义者,又该如何应对暴力的恐吓和伤害呢?上野的解决方案是“逃出去、活下去”,而这,便是上野所说的“活下去的思想”。
所谓“活下去”,是和“比生命更重要”正相反的一种态度,意味着无论如何也不能牺牲生命的观点。而且上野解释了为什么与拼死一搏相比,这并不是一种懦弱(P74)——
对抗暴力(以牙还牙的想法)不过是具有行使暴力能力的人所拥有的一种手段罢了。 倘若弱者想要试着对抗,只会遭到彻底的反击,并且遭遇比以前更为严苛的打压。暴力中所谓“压倒性的不对称性”指的正是这种情况。
(更完整上下文请参考我的 读书笔记)
的确,现实中人们之所以会对弱势方“反杀”强势方津津乐道,正是因为这是一种“反常”,是特例。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弱势方的暴力反抗都会失败。“压倒性的不对称性”决定了强弱,也决定了挑战不对称性的结果——前者是浪漫主义,往往歌颂例外、鼓吹为例外奋不顾身,现实主义却要求我们直面残酷,甚至要安于自己的“弱”。
现实主义似乎很窝囊,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表面上不窝囊的浪漫主义是危险的,毕竟从神风特攻队到法西斯旗帜下热泪盈眶的德国青年,他们都曾经是那同一种浪漫主义的信徒。
不仅如此,为了强调“逃出去”作为实践方案的重要性,上野还提出了“海啸来临各自逃命”的具体指导意见(P284)——
“海啸来临各自逃命”其实是一种对对方的信赖和期待——我相信,家人和朋友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活下去。所以,我仅需考虑我自己,赶紧逃命。我们一定、一定可以再活着相见……
然而不得不说,当上野完成了她对“公民权”和公私领域暴力关系的精彩分析,发出了要让“弱者以弱者的姿态受到尊重”的呼吁后,她对于“如何实践”所提供的这个解决方案,却是 非常脱离现实,也缺乏可行性的。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她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比如在第五部那篇谈及3·11的演讲词中,她也在提出“海啸来临各自逃命”这句话的同时,不得不承认(P272)——
灾区也有一些人是灾难中的弱者。只有强者才能靠着“海啸来临各自逃命”逃出来……当这些人没办法自己逃走时,那些叫上他们或拉起他们的手一起逃走的人,以及为此而受灾的人,他们的故事同样会留在我们的心里。
“他们的故事同样会留在我们的心里”——这啥意思?这就完了吗??
我不知道如果有人当真耐心地读到这里(我怀疑没多少🙃),会不会理解我看到这句话时的困惑。因为很明显,她用了这样一句话回避了自己倡导的解决方案中存在的那个明显的矛盾——灾难当头时照护无法独自逃命的弱势者,就 需要冒生命危险。也就是说,在“海啸来临”时,选择了去照护弱势者的人,是一定程度上将他人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而这不是恰恰违背了上野“无论如何也不能牺牲生命”的观点吗?一句“他们的故事同样会留在我们的心里”,这能算什么回答?
更不要说,海啸来临或者其他重大的灾害事件,即使有人为因素掺杂,呈现的形式也是压倒性的,而且也不是通过人去推动的。所以,它的性质与由人类策划、执行的暴力完全不同。我们能够把应对海啸的经验,套用到人类社会强势方对弱势方的暴力伤害中吗?要知道现实中人类强弱双方力量的差距和较量,是往往比灾害和人类间的复杂得多的。有时强势方可能比弱势方强大百倍,但也有时候,确实存在一些虚张声势的强势方,那么是不是也可能弱势方没有无可挽回地弱,暴力反抗成功的概率也不至于低到微乎其微?
这一点我不相信上野没有想到。因为哪怕只是凭人人皆有的“常识”,我们也可以提出明确的反例。比如,就拿法律领域的“正当防卫”概念来说吧——我们知道有可能出现某些特定情况,弱势方会通过“以暴易暴”把自己从危险处境中解救出来。遭遇严重家暴时反击却不慎失手杀死施暴者的受害人就是如此,难道我们也要按照上野的逻辑说Ta(往往是她)是“有罪”的吗?如果她还是要保护孩子、老人免于被害呢?这时候,是不是她就是那个灾难当头为照护弱势者,冒着生命危险放弃独自逃命的人?那么上野老师,您真的会对这样的人也说一句:她的故事会留在我们的心里,然后仍然宣判她有罪吗?
更进一步,我们甚至还是可以回到上野自己也曾提出来的那个问题:
如果我这样说,可能会立刻招来反对的声音:这也太不现实了,你连警察的暴力也不认可吗?你要对侯赛因这样的独裁者入侵科威特的行径视而不见吗?你要对17岁少年劫持公交车事件坐视不管吗?
我知道上野的回答(参见这里),我在上文讲了那么多,就是在呈现上野的回答。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她的回答仅仅做到了在逻辑上足够自圆其说,但在实践中完全脱离了现实。她提出的其实是一种纯粹的理念,我们无法以逻辑去证明这种理念是假的,然而我们都知道这一理念从经验的角度去看,实现的可能基本为零。因为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人类。存在不使用暴力的人类吗?扪心自问,我们都知道答案。即使是对于彻底的弱者,我们也都知道暴力是印刻在Ta的人性之中的(或许只有婴儿和完全失能的老人、病人能例外)。
我这样提出质疑,不是因为想彻底否定上野的所有观点。事实上我非常喜欢她这部作品,我甚至认为这是上野“思想史”中堪称承上启下的一部代表作(原因见短评)。只不过这部作品做得够精彩够深刻的部分,主要还是分析和个人观点的表述,但在涉及到现实的解决方案时,就过于语焉不详,甚至明显回避矛盾了。
如果女性学如上野所说,是与女性主义的实践密切相关,理论也应该来自于实践经验。那么像她这样止于理念的表达,就是在实践中难以立住的了。也是这本书让我感到最遗憾的地方。
至于更现实的解决方案可以是怎样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需要其他学者再写一部作品才行。我只能试着讲讲自己的大概想法——
我们需要承认,以暴易暴,是我们能够考虑的所有应对暴力伤害的解决方案中最最糟糕的一种。我们承认它,是因为它不可能彻底消除,在某些情况下,也确实可能是合理的,甚至是无罪的。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暴力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无罪”,便将暴力“正义化”,对其进行歌颂,鼓动人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暴力。比如在自己和利益相关者的生命并未受到死亡威胁时,主动去投入战争,或在普通人明明还能维持生存时,胁迫或洗脑人们为了某种政治诉求参与武力行动——女性主义者(或广义上的弱势者尊严的捍卫者),必须态度明确坚决地反对这类做法。
上野本人对于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划分,其实也可以用在帮助我们划定何时使用暴力才“合理”的那个底线:一切公领域的暴力因其施暴目标的不明确,都是不合理的,而私领域的暴力仅在弱势方面对强势方的暴力伤害时,由弱势方为了自我保护或保护照护者而做出,才可以算合理——当然,更现实地去看,我们肯定还需要把这个标准进一步放宽。比如,警察为维护治安而行使的暴力,也可能是我们现阶段不得不接受其存在的部分“合理”,甚至也许在某些时候,一些弱势群体为保护群体中的某些人生命财产安全,做出暴力了反抗的行为,也可能是部分“合理”的。我很难像上野那样斩钉截铁地说“这些都不对、都有罪”,我甚至感到,正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女性,有身为女性在当下这样的环境里“幸存”的经验,才更让我难以对一些情况下的暴力直言“这不对”。
我不知道上野千鹤子老师有没有和那些生活在比较动荡、混乱社会环境下的女性,有过关于“暴力”问题的讨论。说真的,我其实更期待看到她与这样背景女性进行对谈,而不是仅仅与那些同样属于知识阶层的女性交流。
(最后,其实这本书里还有一些点同样非常值得讲,比如难民视角,或者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复杂互动,但是限于篇幅和主题,我无法继续展开谈,也许以后会补充上来吧)
想不到写了这么长,但确实这个问题也算是困扰我多年了,能借着上野这本书仔细梳理一遍,也算是给自己做一个交代。如果有人当真看完了,非常感谢。也期待跟大家继续讨论,欢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