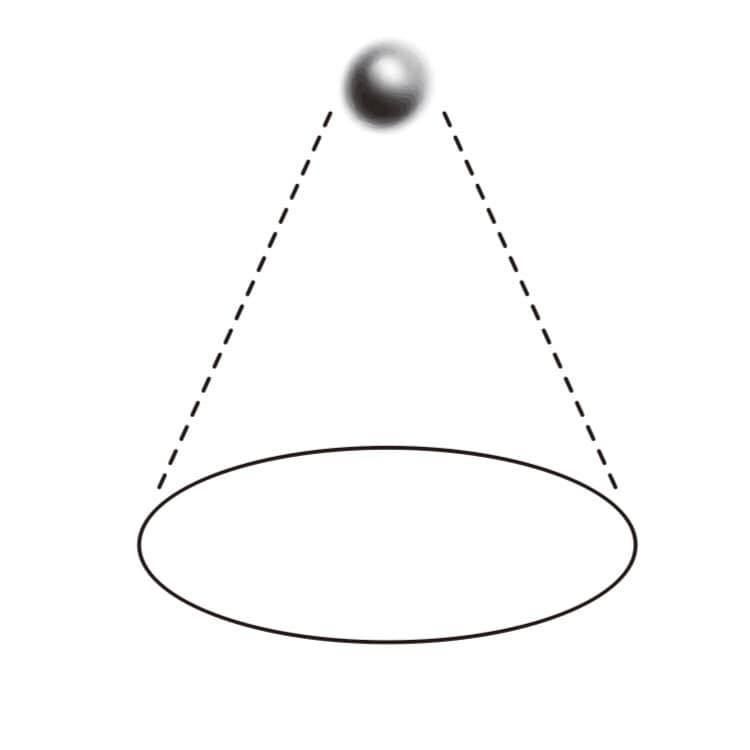【講座側記】艾未未X張潔平|《艾未未:千年悲歡》新書分享會
原文發佈於2022年10月9日,首發於端傳媒《艾未未對談張潔平:記憶完成了我,記憶就是自由本身》。

寫在前面
文 / 張潔平
如果知道自己將失去自由,可能有長達十年的時間,你會從你的父母、孩子、親人朋友、乃至所有人的視線裡消失。如果你的生命並未停止,只是不再能與其他人互動,你們看不見彼此,可能會淡忘彼此,而你必須眼睜睜看著這一切發生—— 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在你身上,你會做什麼?有什麼事,是你覺得就算與全世界隔離,就算剩下自己孤絕一人,也應該做,不做會留下遺憾的?
艾未未的選擇是寫回憶錄。但與許多人不同,他的回憶錄不是追溯自己的創作歷程,也沒有由頭至尾詳盡記錄自己經歷的種種大事,而是先花了一半篇幅寫自己兒時陪著父親艾青,從反右到文革期間,被流放新疆的遭遇,再花了一半篇幅,寫自己後來在中國所做的社會行動,以及與國家政權之間的互動——時隔半生,與父親艾青面對相似處境的互動。
讀這本發願於獄中,最終在自由世界完成的回憶錄時,才知道他這樣選材的原因。他也很清楚地在書中寫出了:
「徐警官總結:『你將用你的生命為你的每句話付出代價。依你的這些言論在文革期間,可以槍斃你一百次。』⋯⋯那天晚上,時間在我腦海中往回延伸,我不由得想到父親,意識到我對他的了解是多麼不完整。徐預審的話並不誇張,我是否會為活在不同的時代而感到慶幸呢?父親經歷的年代要更艱難,有太多人為他們說過的話付出了生命代價。而我從來沒有問過他是怎麼想的,甚至沒想過,他用一隻眼看到的世界是怎樣的。現在,我為自己與父親間無法逾越的那一道溝壑感到遺憾,這讓我徹夜難眠。這之後,我萌生了寫一本書的念頭,為的是不讓艾老有同樣的遺憾。」
2011年,艾未未因發起四川地震公民調查以及此後一系列的批評言論與行動,一度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為名被關押。他曾被威脅可能判刑十年,最終失去自由了81天。在這81天裡,他決定寫一本書,記錄「我父親1910年出生之後直到2009年我兒子出生之間共99年的歷史」,「給我的兒子留下一個紀錄。」
「秘密拘留期間,在我內心的恐懼不是無法見到我的兒子,而是失去機會讓他了解我曾存在。我要用我的理解和信念架起一座橋樑,它可以被看到和感受到。如果,有一天他想知道更多,我的故事就在這裡。」艾未未說。
「艾老」是艾未未的兒子。他也讀了父親的這本書,並以英文寫了書評。
艾未未用了父親的詩作為回憶錄的書名《千年悲歡》。
「我父親經歷的流亡,塑造了我和我的孩子,如影隨形,儘管我們身處不同的時代。⋯⋯只有將我、我父親和我兒子三代人的命運,與那些素不相識的人的命運連為一體,我才有一個合適的理由,說出心裡要說的話。」
在這本書中,他述說的,正是「意識形態像一道強光,個人記憶就像是無影燈下的影子一樣不存在」時,那些殘缺的、同時代人的記憶。

不留下這本書,就非常的失職
以下為對談紀錄。張=張潔平;艾=艾未未
張:想先問問未未,在你被監禁時起心動念寫這樣一本書之前,作為一個藝術家,你想過要寫自己的回憶錄嗎?你讀其他藝術家的回憶錄嗎?如果你想過寫自己的回憶錄,你曾經想要怎麼定位它?
艾:我是2011年被秘密關押81天,時間很短,我現在也覺得有點遺憾,他們應該多關我一些時間。當時他們告訴我。我可能會被判十年以上。我當然認為他們不是在詐,而是確有這個可能,因為我認識的、聯繫的一些人至今還在服刑的或消失了再沒出現的都很多。
所以當時有個簡單的念頭,就是我這一生過得怎麼樣?我覺得確實要被判,因為我的活動確實有影響力,影響了一個政權、影響了對它的評價。但我有兩件遺憾的事兒,一個是對我父親的了解是非常不確定跟不詳盡的。不確定是因為在那樣的時代我父親並不會去講自己的事,我也不會去問,雖然一起生活,但我們都相敬如賓,雖然我所有的遭遇都源自於他的遭遇,但實際上我對他非常不了解,我從來沒有正面地問過他一個問題——這是我非常遺憾的:你怎麼會跟人生活幾十年,但對他身上發生的從來沒有關心過。
這可能是我個人的問題,也可能不是。因為我和許多朋友聊過天,我經常會問,你們祖上的爺爺奶奶是什麼人呢?他們都知道自己爺爺奶奶有很複雜的故事,有的是地主、有的是資本家,還有很多是跟著國民黨去了台灣的。我說那你能知道更多嗎?幾乎每個人都說他們從來沒有問過、家裡從來沒有說過,這個遺憾當然沒有辦法彌補,因為我父親1996年就過世了。
第二個遺憾對我來說更大一點,就是如果我會被判刑十幾年,公安人員告訴過我,我出來以後母親肯定不在了,兒子也不認識我(因為我被關的時候兒子才剛過2歲)。這個話對我打擊比較大,如果我不在他們身邊十幾年,基本上那個血緣關係都會被切斷了。所以我想寫一本書,既能把我跟我父親的書講清楚,又能為我兒子留下記錄,儘管我兒子未來生活的時代跟我是完全不同的,甚至他可能完全沒有興趣讀這樣的書,但這是我的責任:如果我不留下這本書,就非常的失職吧。所以我就留下了這本書。
張:你寫這本書的時候你父親已經去世了,而你寫的是兩代人的經歷,你已經來不及做很多細緻的口述歷史,那在這種狀況下,你要找回父親的歷史、重溯自己的經歷時你做了哪些準備?這些素材和史料你要如何確保是可信的?
艾:這個事情比較有趣,因為根據我的經驗,在中國市面上存在的、關於現在的史料絕大多數是不準確的,甚至是歪曲的,這顯然不是我可以依靠的資料。比較有幸的是我父親在20歲左右就開始寫詩,詩是一個沒有任何障礙與遮掩地表露了他的心情與感受的載體,而且他又是一個用白話寫詩、非常激情、天真的一個詩人。所以我有幸讀了父親在1930年以後(那時候在國民黨監獄)到1957年之前,這二十多年的自述詩。之後又有二十多年的流放、沉默期,而那時候又剛好我跟他生活在一起。
現在關於他的生活資料有很多,是作為一種「愛國主義」宣傳的文學資料,比如哪一天到了馬賽、巴黎,研究者記錄的非常準確。甚至不是關於我父親的事,是關於從清末(因為他是1910年生)、到民國、到延安、到中共建國、到政治運動、反右與文革,再續上了之後跟我的生活。我必須尊重中國發生過什麼,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解釋他的情形,這個問題必須要釐清楚。這整個過程我們大概做了100萬字的第一版,就把中國歷次的政治運動、社會變化記錄下來,後來又壓縮到最後的20萬字。
張:你剛剛說父親留下了大量的詩作作為可依賴的素材,那想問有日記嗎?因為書中有提到很多第一人稱的很小的細節,那些我也很好奇:是來自於什麼樣的檔案?
艾:他沒有日記,不過也有很少去南美洲旅行的筆記,但很少,因為是在流亡,很多手稿已經不存在了。但他有對自己早年的回憶,這個回憶也是我的(資料)基礎。
不被允許看到的檔案
張:整理父子兩代人的歷史,你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是史料的殘缺,還是什麼?
艾:史料的殘缺當然是不可迴避的問題,我父親是作家協會的頭,我就讓我母親跟作家協會說父親死了,那他一定有一份檔案,是每個中共高級幹部都有的(甚至普通國家公職人員都有的)。既然他死去這麼多年了,國家也對他很敬重,那我希望能看到這份檔案,因為裡面有歷次中央政府對他做出的評價,比如被批判為右派,一定有很多人對他揭發、甚至是自己交代的材料。
所以這份檔案應該是非常厚重的,有詳實的資料可以了解中共文藝界以及我父親的經歷。但我母親被正告說,「你是永遠不可能看到這份檔案的」,這份檔案是一個高度機密的材料。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我還是得試一下。是很大的缺陷,但其實也沒有,因為我了解當時很多跟他同代的人的經歷,我是生長在那裡的,所以我對那個氣息非常了解。
張:所以官方檔案是不是就完全沒有看到過?
艾:嗯,那是不允許看到的。
張:那你剛剛說官方檔案裡寫過的一些思想檢討,是有一個神秘的空間保存著的是嗎?
艾:那是當然的,因為我在二手市場經常買到其他人的檔案,很吃驚其他人很重要的檔案是被當做廢紙賣掉的,我看到一個醫生的檔案,在西北,清楚地說了他如何從東北到了西北做了醫生,哪一次在他那很小的診所裡說了哪一句話,說這句話的時候同時有幾個病人對他揭發都表示了他說那句話時候的情形,如果檔案上有一個錯字,都會看到有更改,還有畫押,「這個更改是依據揭發者本身做的」。非常嚴謹。
我想這份檔案是從蘇聯或者日本學習的,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人,西北農村的一個大夫,說的哪句話,都做了很細緻的檔案記錄。我相信我父親的檔案應該豐富一百倍,我想看,但也不想看,因為我覺得裡面有很多東西是我根本不願意看到的。
張:你在德國一定去過史塔西檔案館(Stasi Records Archive)對不對?
艾:我沒有去過,但我知道。檔案館會揭示很多歷史中的東西。我覺得中共檔案是永遠不可能公開的。因為他們會定期地銷毀很多檔案。

我們比孤立的個體更加孤立
張:明白,因為這個書裡涉及到了很多你跟父親的經歷,你在這個整理的過程中,對父親艾青的認識,經歷了怎樣的過程?與以往的認識有沒有變化?
艾:兩點,一是整理本身就是發現的過程,甚至你整理一個自己存放的東西,一間抽屜、一個屋子,都會發現很多意想不到的東西。那整理他人的時候,還是有所發現。但是實際上,這個整理只是把語序、語境整理得更加合理,我不願意用我的方法來重新解釋他的生活,因為究竟我不是他,我不是生活在那個年代,我不在這個位置上所以不能這麼做。我只能將他和我的聯繫梳理出來。
張:那在做完這百萬字的整理、寫完回憶錄後,你會怎樣評價你的父親艾青?
艾:每個人都要想這個問題吧,因為每個人都生活在時代的框架中,我的評價必須是以他的方式完成對他的評價,他所處的時代、語境、遇到了什麼。今天我們面臨的危險是今天以我們的道德標準來評價前人,我們也可以管這個叫「cancel culture」,就是把以前的雕像、史實重新以今天的價值觀整理,甚至是清肅,這是很危險的。因為我們要時刻認識到我們生活的現在也是暫時的空間與階段,實際上我們沒有任何權力對任何事情做出結論的。
至於怎麼評價艾青,我在書裡寫了幾點,我很難用一句話來評價。
張:是的,您非常少下直接的評價,但為讀者展開了很多脈絡,可以讓讀者來評價。我自己看這個書的時候有個好奇的地方是,你跟你父親的角色在書裡是非常突出的,但是整個家庭包括家族(家庭裡的其他人),很少在你的回憶錄中出現,這是一個敘事的安排,還是真實生活裡就是這麼isolated?如果是後者,這與人們對中國傳統生活的認知很不同,你怎麼理解這件事呢?
艾:這樣說吧,我們比孤立的個體更加孤立。現在我在西方很常被問,對家的認識是什麼。我父親是在流亡之中去了延安,然後莫名其妙他們取得了政權,然後他又成了政權的異見分子。在我出生那年我們已經被送到了新疆,接受再教育。你想現在很多人談到新疆,對維吾爾人的處置的方式,其實很多人忽略了中共不止對維吾爾族人,還有對自己的漢人,甚至是高官,在取得政權之前就是用同一種方法訓練、控制,這是他的立國之本,從來沒有改變過,只是到現在才被提出來。
所以我⋯⋯不知道什麼叫家,因為家這個概念是與私有財產、記憶有關,但在中共控制的這幾年,其實沒有人有私有財產,都是公有的一部分;你也沒有隱私,沒有可以區分你和另一個人關係的記憶,你沒有屬於你個人的記憶。當這個範疇都不存在的時候,不管你在新疆還是河北、江西,每個人的生活都像部隊里的生活一樣,是非常具有統一化的。
家?一個籃子裡的幾顆洋蔥
張:您剛剛說的對家的感受在過去幾十年有變化嗎?
艾:沒有,到今天也沒有。因為我很早就離開了北京,去了紐約待了12年,但也不能稱之為家,雖然我是上了「賊船」的人,但「認賊作父」我也沒做到。然後回了中國,又是一個和中國毫無關係的人,我跟中國所有價值,不論是傳統還是現代的,我都不認同。我再次了解中國的時候是做一些古董的收藏,可以讓我理解遠久的歷史。然後我又開始做建築,讓我再次了解到現實政治的情形。由於互聯網可以給我一個發表觀點的機會,所以我又成了今天的艾未未。
張:您這麼重視父子三代人,比如在意把自己跟父親的歷史留給兒子,讓自己兒子明白這個血緣的歷史曾經這麼存在過;但你又不會用家的框架來理解對嗎?
艾:這樣說吧,我們就是放在一個籃子裡的幾顆洋蔥,或者土豆,家不家的不重要。比如我父親並不知道我上學幾年級,我也不知道他的生日是什麼,我兒子到今天也不會叫我父親,只叫我名字艾未未。所以我們的關係很近但又相對陌生。
張:那你去到歐洲之後,包括在中國、歐洲各地,你會認識到這個狀態是很特殊的嗎?
艾:我不覺得這是特殊的,就像你現在在台灣,之前在香港,去香港前在中國,但你還是有一種中國文化的依託吧?包括開書店也是。但我走得比較extreme,反差比較大,從新疆到了北京以後去了紐約,然後又回到北京,不得已的情形下去了歐洲,在德國落了腳,但不適應,又去了英國,兒子在那裡讀書。
那又不是我理想的地方,我就搬去了葡萄牙,開始種地跟蓋房子。這讓我感覺好一點。我在葡萄牙的菜市場裡,一個女士走來問我:未未,你去了那麼多地方,為什麼最後搬到這個小鎮子上。我想這就是我搬過來的理由吧,我想弄清楚我為什麼搬過來。實際上我們通常知道做事情的理由並不是真的有,而是要做了以後或過程中才會發現的。這是我對我人生的一個很好的經驗吧,我必須要在那兒創造一些困難和障礙,當我應對時我才會發現我存在的價值。
張:因為你在歐洲待了這麼長的時間,至少在「家」這個小集體的概念裡,應該很多地方都有家的傳承,你會對跟你非常不同的人與家的形態感到好奇、並去研究為何如此不一樣嗎?
艾:我覺得這是明顯的現象,在歐洲所有人都會有自己的祖父祖母,會三代人甚至四代人一起去海邊、去生長的小村子小鎮子裡,一起去餐廳。這個不難了解,也很容易認識到這個社會雖然經歷巨大的動蕩與革命,仍然還保持一些這個社會固有的一些東西。
在中國大陸是不一樣的,可以說已經在過去三十年完成了城市化的運動,即每個人都不止一次的搬了家;以及沒有人有私產的,即沒有人是有房子的,每個房子都是不同的城市和小區,是一樣的,只是有貧富價錢的差距。這個東西經過那麼多次的篩選與漂白之後,家的原始含義是完全不存在的。所以我到一個城市、即使是歐洲,也很喜歡去自由市場,因為可以看到過去五十年、一百年是什麼樣的,人們為什麼設計了這個工具?這個工具怎麼用?到今天已經沒有用途了所以作為舊貨賣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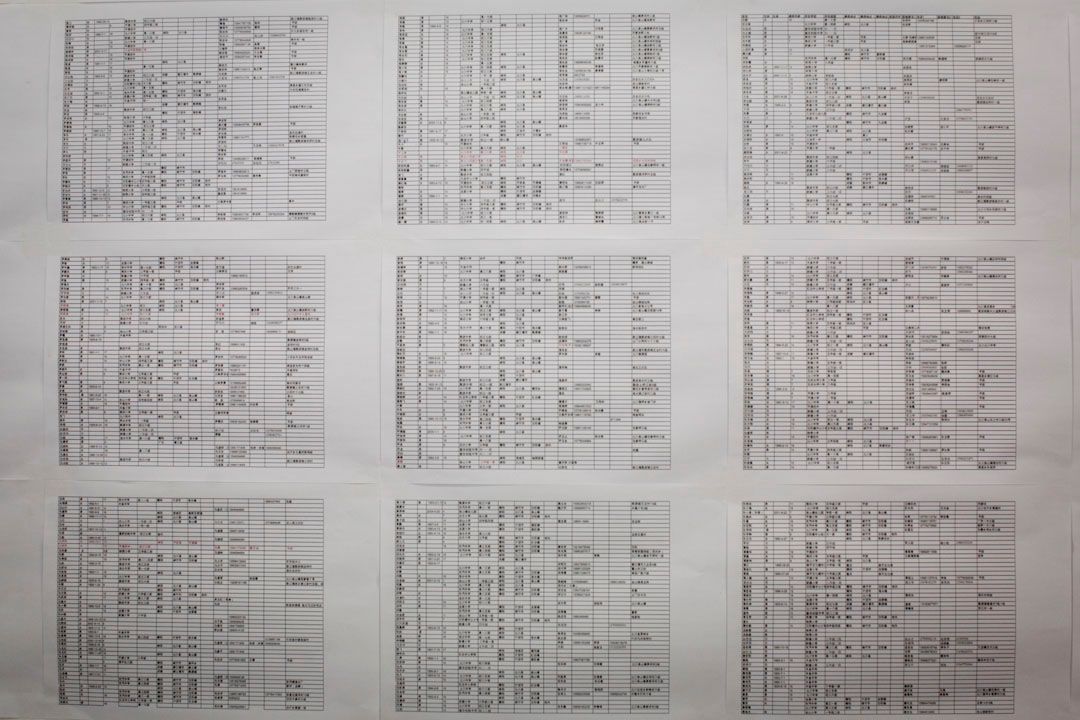
落筆那一刻,所在的位置
張:我看這本書的時候可以感覺到作者很自覺地把父子三代人的命運跟共和國的命運連在一起,但又很難感受到這是家族回憶錄,因為就像剛剛說的籃子裡的土豆一樣,是相對獨立的。我覺得這本書對於至少幾代人的回憶錄來說是蠻特別的事情。還有一個點是,艾未未這個名字,你的許多藝術作品、社會行動被中國以及世界很多人都知道,是從07以及08年你真的開始做很多公共參與與行動開始的。
我們會發現行動裡「記憶」與「真相」是非常核心的主題。比如要恢復四川汶川地震中遇難學生的名單,看起來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在中國重重的體制障礙下你卻要花巨大的精力、要付出巨大的犧牲才能恢復那些人的名字。記憶作為一種使命,記憶之忘卻。這是你的一個母題嗎?它源自哪裡?
艾:這樣說吧,這實際上談的是因果關係。可以說「我是創作的靈感,創作也是我的靈感」——由於我這樣做了,才出現了我;並不是有了我,我才這樣做了。所以說這些記憶是我在爭取我個人成為個體的一個基本的、本質性的手段。如果沒有這些通常稱為正義、真實的追求的話,我是不存在的。實際上每個個體也是一樣的,他在不同程度上,只有追求真實,可能包括愛與恨,在這樣的過程中才會一次次認識到自己的存在。或者說魂不守舍,怎樣才能招魂?
張:那你覺得這本書對你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它有把這件事往前推一步嗎?
艾:它沒有往前推一步,但至少找到了寫這本書落點的那一刻所在的位置。很多時候可能不是往前推一步而是往後退一步,我找到了某一刻我實在的位置。這個位置實際上是說,我們都想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是什麼,比如你的飛地書店,你會想到書店的緣起、會吸引哪一類的人來;出版社,他們可能也在想要尊重哪一類的文字;每次這個行動都再一次表述了我們個人存在的價值觀,表示我們的認同之處,甚至是批判性的、自我否定的一種可能,這種可能才構成了每一個個體、國家或社會的可能,沒有這些我們就看不到這些特征。
張:你剛剛說透過這本書確定了落筆那一刻的位置,那倒推回一點,你曾經站過哪些不同的位置?
艾:如果看生命的過程,我其實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被動的,比如我出生就必須跟我父親去了新疆,在那裡經歷了我的童年和青年時代。然後莫名其妙地我們又回到了北京,進入了電影學院,這也是非常莫名其妙的,我對藝術本身沒有太大的興趣,只是因為我的家庭、我的父親是詩人,這對我有一定的引導。
假設他是個農民,可能對我的引導就少一點,因為我不會想去看人民怎麼種棉花,我自己早期就在做這件事。在青春期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在中國會很危險,因為我比較反骨,所以我找了機會去了美國。但去了美國之後我又不認同美國的價值觀,不認同美國夢之類的,所以我在那兒做了個流浪漢,讀了三四所大學都沒有畢業。我很容易拿到畢業證,但我看不起那個價值觀,所以我就在社會上晃著比較好。
但這個其實很悲苦的,沒有生活來源、語言不同、生活習慣不一樣,但我晃著還行的,因為可以街頭畫像、街頭做點工,只要能交房費就行了,結果一晃十二年過去了。在我父親去世之前,我在美國沒事幹,又不屑於回到中國,但我父親住院可能就是我最後一個藉口回中國。但回到中國又沒事幹,我就只能去古玩市場看古玩,用六年時間研究,過去這塊土地上發生什麼,也收藏了一些東西。當時我父親已經去世了,我母親很不高興,這孩子就跟沒去過美國一樣,沒有畢業證,沒有身份,身無分文,十二年真是跟沒去過一樣,覺得我是很沒出息的孩子。
我確實沒事做,因為我不想也沒興趣捲入中國的發展大潮。一怒之下我就說我搬出去,但屬於三無人員,沒地兒搬,所以我找了一個農村,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幹一些違法的事情,比如我蓋了一個違法的建築,村長說你願意蓋就蓋,我們不管,但是這是違法的。我想說這太好了,這樣的違法太快樂了,就蓋了這個房子。我想的是我蓋了就算你拆了我也高興過了,至少滿足我想蓋房子的可能。所有人都說艾未未你太傻了,蓋了拆了不就沒了嗎?我說沒了之前不還有嗎。到今天還沒有拆,公安對我還比較寬容,說你這房子就留著吧,所以這個房子到現在還在,叫草場地,258號。
這個地方沒想到就成為了中國現代藝術的算是發源地吧。在那兒也有很多的工作室搬過去。大概是這些情形,包括我來了歐洲,也是被動的,我的理由是我兒子在外面讀書,我必須讓他安全,所以我來到了歐洲。要不然我可能還是在北京。
爭取自由的手段
張:書裡印象很深一句,你說「被動塑造了主動性」,你剛剛說表面上看起來是隨波逐流,想問這些主動性在之前的隨波逐流裡會體現在哪裡?
艾:體現在你始終考慮這個被動性能寄在哪兒。如果我沒有想寫這本書,我的主動性就不存在;只有我寫出這本書當年在新疆如何和我父親生活,我的主動性才存在。我覺得大多數人都有他們的資源,但只想著主動,而沒有想被動性是具有必然性的,包括我們人類如何出現在地球上、如何消失,這些事情實際上都是被動的,沒有由人類自己做主的。
現在很多人能看到他們事業有成、或推崇某種價值觀,看起來很主動,但主要都是被動性在裡面起到了作用。而如何能在被動性中、逆境中發現存在的可能,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爭取自由的手段。
因為我是一個人,我很不滿意我是一個藝術家,全世界都認為我是最活躍的藝術家,我很不滿意這個位置。我覺得文字仍然是我非常在意的一種人類技巧,將思想用白紙黑字寫下來,每句話都是清楚表示了你認可的狀態,這東西是沒法掩飾的。可能是受我父親的影響吧,跟文字、文學有關的活動,仍然是人類最重要的活動。
張:而且在你寫下來的這一刻,是你透過對被動性邏輯的分析掌握了主動。
艾:我覺得人類的思考是被動的,人類之所以能成為有智慧的人,是因為我們的處境和要面臨的問題。文學本身,並不是你生下來會成為一個文學家,而是說你不斷地將感受的能力和願望,透過非常艱難的方式,一種書寫的敘事的方式記錄下來,這顯然不是一個非常自然的行為。
張:你剛剛講到了自由,我一直想問這個問題,人類因為這個經驗引發思考是被動發生的,其實如果把這個記憶刻畫出來,似乎會獲得你存在的主動位置;你剛剛又講到自由,所以我想問你覺得記憶與自由的關係是什麼?
艾:我覺得記憶是人們的一種活動,這個活動並不一定是準確的,但這個努力是一種可以明確表述出來的,無論是對自我的、情感的、歷史的記憶,實際上只是包含了你個人理解能力的一種記錄,而這個記錄能力是因人而異、因時而異的,會有變化的,如果沒有變化就是一種教條。所以我覺得記憶本身就是自由,是爭取自由的手段。
如果我們不能完整表述、或追溯到底發生了什麼,不能批判性思考、甚至反復地去談同一個問題的話,實際上我們稱之爲自由的是完全沒有意義的。這個意義完全體現在我們對自我的認識,以及在認識當中取得行動的能力。
張:那你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創作,除了寫作之外,也會體現這個事情嗎?
艾:那是當然。無論是做一頓飯,或是我跟你做一次談話,我覺得都是具有挑戰性的,都是可以別開生面,因為在這個過程中,都有相對拓展的空間。

只有專制社會交流成本才越來越高
張::未未我想插一個問,為什麼這麼喜歡談話?因為我第一次認識艾未未、採訪艾未未的時候,就是很多年前去他的草場地258號的家裡採訪,那時候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幾乎不會拒絕任何採訪,任何人想要採訪他,理論上在那個時候都可以,所以你會接受大量大量的採訪。你也不介意重複。
艾:迄今為止我做了有將近2000個採訪。我說採訪不是說簡單的採訪,是屬於西方媒體的專訪,昨天時代在頭版第一條寫的就是「艾未未與他的藝術與生命將會同歸於盡」,他已經不需要說誰是艾未未了,中國人還是藝術家,而是直接說艾未未。這也就是說,這個人是不需要介紹的,已經變成公眾的符號了;但這唯一被證明的只是已經被採訪得太多了。
我為什麼喜歡採訪,因為我剛跟我父親去新疆的時候,我十歲,我發現農村裡的這些人,二三十歲、四五十歲,都很喜歡問我問題,你父親多大了、母親去哪兒了、你想不想她啊?他們都願意把生活裡一些不願意跟人說的事情跟我說,所以我最早時候就是一個傾聽者,直到有一天我上了互聯網之後,我發現很多人喜歡我的一些事,可能因為我口無遮攔,不太在意問題是不是有深度,或是不是比較幼稚的問題。
但我認為沒有幼稚的問題,只有幼稚的回答。我覺得交流是成本最低的事情,只用腦子,一張紙都沒浪費;今天我又遇到了最好的時代,我隨時可以跟任何人交流。
張:交流會帶給你智識上的刺激嗎?
艾:交流是人或者文明最重要的一個手段,雖然貓之間的交流也很多,他們都有自己的交流方式,而且非常美妙。作為人,我們都比較自戀,認為我們的交流更複雜一些,可以透過寫碼、文字、電影,或透過互聯網上的推特、Instagram⋯⋯可以看出交流的豐富性是將個人的智慧或人類文明不斷打造。只有專制社會交流成本才越來越高,像香港交流成本越來越高,中國的交流則基本是不可能了。
其實我喜歡交流的很大程度是我發現為什麼專制社會這麼害怕交流,比如我的一句話、一個態度、一個表情或者一張裸體照片,在中國簡直是大逆不道,他們覺得這太恐怖了,恐怖的連思想也不是,而是一種態度:我們是自由的,沒有人能戰勝我們自由的慾望。
父親與兒子:一起穿過的黑洞
張:艾老怎麼看這本書?
艾:實際上我寫這本書我覺得他愛讀不讀,只是我作為責任必須要寫下來;我做現在這個採訪他還必須要下到樓下餐廳裡去,他剛才已經很埋怨了就說,要在餐廳裡待兩個小時。我說你隨時可以回來啊。因為他已經非常反感我要說這麼多話。他是第一個讀完的,他寫了一段話,大概意思是我記錄了一段生活,這段生活將會影響到他對中國的認識。一代有一代人的事,所以我也很感謝我父親沒有告訴過我什麼。
張:在書的最後,你說自己在歐洲的難民危機裡,意識到只有將父子三代人的命運與素不相識的人的命運連為一體,才有一個合適的理由去表達。在寫完這本書、你在歐洲又生活了新的七年之後,回頭來看,這種命運連結你如何讓它發生,你怎麼去看自己後半生與艾老將會展開的歐洲經驗呢?
艾:我先前說過我來歐洲是被動的,那個被動就像我們經常看到一盆熱帶雨林巴西的植物在歐洲市場上,當然我們可以盆栽它、放在家裡,但我發現他們很難長好,空氣、濕度、土壤品質都發生了變化。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生物特強,把原生植物都殺掉,但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移植的植物都不能生長的;還有我發現把他們從盆栽放到土地裡的時候,會好一些,風啊、水啊之類的可能性都有了,這些條件在屋子內是都沒有的。
我覺得我在歐洲就是在一個巨大的不自在當中,首先我必須理解歐洲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他們的歷史是什麼?經過了怎樣的掙扎演變至今。這也是我去到任何地方都會想到的問題,因為你不可能不想這樣的問題。然後也不可能不去跟中國的文化有對應,因為我對中國應該算是了解吧——就算不了解也沒時間了解了——我在中國生活過四十多年,由於我有美國的經驗與歐洲的經驗,所以對中國的了解都更深一些,包括我父母那代的經驗,還有今天的一些事情,每天都在不斷認證我的一些觀點。
但是對歐洲,我只有在15年出國以後,我覺得我才希望了解它:因為我一時回不去中國了。紐約是我沒法不了解的,24歲到36歲都在。我了解歐洲是剛好在面臨一些難民潮,幫助我了解了中東社會和難民社會,以及歐洲的文化。為了拍一部電影《human flow》,我們去了23個國家,訪問了世界上40個最大的難民營,我個人採訪了600多個難民,透過這種方法強制地讓我了解歐洲或者中東的一些問題。說起來話比較長,總體來說是這樣的。
張:這個過程艾老有參與嗎?
艾:很不幸我必須帶著他。他跟著我去了很多地方,黎巴嫩、巴西、墨西哥,他去的地方非常多,儘管他都不知道他去了哪裡,但都是跟著我。有很多危險的地方,比如難民營、ASIS、還有墨西哥販毒集團的地方,我們都一起去了。
張:所以這有點像當年你跟著你父親去新疆?
艾:差不多,但當時我們都在一個地方,地下一個坑住了五年,是一個黑洞裡。但他這是在非常多個黑洞裡,穿來穿去。

註:本文轉載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歡迎關注端 Plus 會員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