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爾斯與中國自由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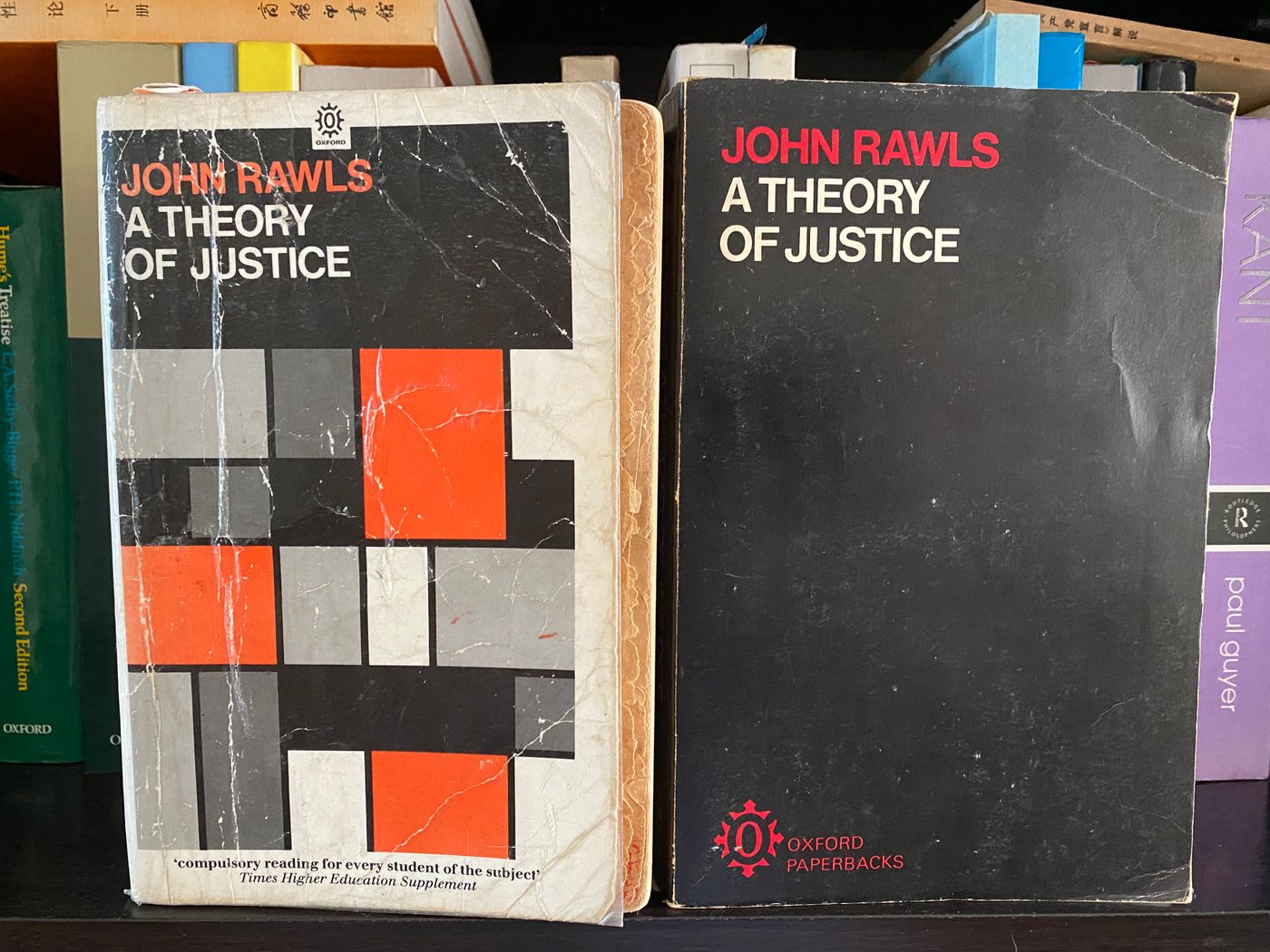

值得留意的是,轉型問題雖然重要,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卻幾乎沒有討論,因為他覺得處理這個問題的前提,是我們須先知道在一種理想狀態下,怎樣的正義原則才最值得我們追求。只有當我們對此有所把握後,才可以用這個正義標準去處理不義制度產生的各種問題。(註12)可是這樣一來,人們難免會質疑,既然那些理論前提(例如每個人都有充足的正義感、源於民主社會的基本理念等)在今天中國極為欠缺,那麼最後得出的結論,無論多麼理想,似乎也與我們沒有太大關係。
再者,羅爾斯並不認為有所謂永恆的、普遍的哲學問題,反而覺得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各有自己需要處理的迫切議題。(註13)羅爾斯的理論關懷,不是如何從專制社會轉型到自由社會,而是如何令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變得更加公平和更有正當性。他思考的出發點、動用的道德資源,以及提出的制度安排,都和西方民主傳統密不可分。既然如此,從促進中國轉型的角度出發,羅爾斯的理論可以給我們什麼啟示?我認為最少有三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特別關注。
一、建構轉型時期的自由主義理論
首先,我們要論證自由主義的方案為什麼是中國社會轉型應該走的路。這需要我們從政治道德的層面,指出相較其他理論,自由主義為什麼能夠建構出一個既正義又可行,因而值得我們追求的理想社會。我們需要這樣一套政治道德論述,一方面讓我們對現實政治做出評價,另一方面也為社會改革提供方向。這其實正是羅爾斯所做的工作,只是在中國當前語境下,自由主義缺乏羅爾斯可以援用的歐美自由主義思想與制度的歷史傳統,思想上的對手也不再是上世紀中葉在西方學界居於主流的效益主義,而是政治保守主義、威權主義、菁英主義、民族主義,還有打着「中國特殊論」、「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等旗號的種種反自由主義論述。
自由主義要在中國發生影響並產生認同,就要用公眾能夠理解的語言,將自由主義的理念和制度做出系統性的建構和論證,並將之應用到社會不同領域,令人們明白自由民主制到底在什麼意義上,可以更充分地保障每個人的權利,更合理地回應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和穩定性問題,更公平地讓人民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以及建設一個更能教國人自豪的文明社會。自由主義要有生命力,就需要知識人共同努力,對它的吸引力和進步性作出有力論證。
因此,我們不能只滿足於翻譯和引介西方理論,也不宜將所有精力花在西方社會才須迫切面對的議題,亦應避免在學院使用艱澀語言生產一些「與世無爭」的學術成果,而應有志於發展出有思想創見、能切實回應社會現實的政治哲學。我們不要忘記,《正義論》之所以能產生那麼大的影響力,正是因為它能在當時極為低沉的學術環境中,直面美國社會迫切的政治議題與激烈的社會衝突,提出極富原創性的思考。
我明白,在目前的政治氣候和學術環境中,當最低限度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都受到各種限制的時候,從事這樣的理論思考已變得相當不易。 可是,我依然認為,這是我們應行的路。回望歷史,自由的理念實踐於人類社會,幾乎毫無例外地要經歷許多考驗。今天的處境並不是特例,我們不宜過分悲觀喪志。
西方自由主義傳統,如果從洛克算起,已有三百多年歷史,其中有無數思想家為這個傳統作出偉大貢獻,包括盧梭、休謨(David Hume)、斯密(Adam Smith)、康德、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黑格爾(Georg W. F. Hegel)、馬克思、穆勒(John S. Mill)、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伯林(Isaiah Berlin)、德沃金(Ronald Dworkin)、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拉茲(Joseph Raz)等。(註14)羅爾斯自己說得明白:沒有這個傳統所提供的思想資源,就不可能有《正義論》,也不可能有民主社會成熟的公共政治文化。他甚至聲稱:「政治哲學只能是指政治哲學家形成的傳統。在民主政體,這個傳統總是由思想家和他們的讀者共同合力創造的成果。」(註15)
自由主義傳入中國已有百年,我們形成自身的傳統了嗎?我們有足以傳世的經典著作了嗎?老實說,仍然未有。可是沒有這樣的傳統,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我們的公共文化就不能提供太多有用的道德資源,而當自由主義面對其他意識形態挑戰時,也就不會有什麼有分量的學術著作可供憑藉。當然, 我們總是可以向西方思想家求助,但我們應知道這樣遠遠不夠。
有人或會回應說,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只有傻瓜才會做。如果著眼於當下政治現實和個人利益,這種選擇確實不是很明智。事實上,不少曾經自認是自由派或同情自由主義的朋友,近年已紛紛沉默或轉向。羅爾斯晚年曾很感慨地提及,威瑪共和之所以會失敗並最後導致希特勒(Adolf Hitler)上臺,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當時的德國知識菁英在關鍵時刻,沒有人願意站出來支持《威瑪憲法》(Weimarer Verfassung),其中包括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曼(Thomas Mann)。羅爾斯提醒我們,知識菁英的立場和態度,對一個社會的公共文化和政治行為會有莫大影響。(註16)我們能為下一代留下什麼樣的道德資源,歷史日後如何評價我們今天的作為,都是難以迴避的問題。
全文見: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710-opinion-note-john-rawls-chowpoch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