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ve与commitment之间——我的两段relationship
写在最前面:
我感到这篇东西有点傻。
我想像新浪潮电影的主人公那么洒脱,坦然面对自己的爱与恨。可真写出来发表了,我更担心被人道德谴责,或者被人嘲讽,“怎么刚分手一个月不到,又谈了个新的,还是白男(if Hispanic is counted as white),是不是离开男人活不下去了”。
于是安慰自己,退一万步讲,我才20出头,说点傻话、做点傻事也是可以被原谅的!
另外请原谅贯穿全文的中英夹杂,这似乎成了直觉,我不知如何只用一种语言准确表达自己。
2021年7月24日,断断续续使用tinder一年后,我在上面捞到了个男朋友。
2022年8月11日,和男朋友一起坐飞机,从上海出发,在哥本哈根告别,我来纽约交换,他去都柏林读研。
2022年8月23日,在一系列drama后,他(以下称“前男友”)向我提出分手。这完全是我的错,但为了避免陷入被读者道德审判的位置,个中细节将被省略。
周年纪念文一拖再拖,成了分手文。
刚分手时可谓鸡飞狗跳。那时还没开学,我在这里举目无亲,每天不得不逼自己出门社交,否则只会对着空房间大哭;后来状态混乱到无法面对自己,多次向学校的心理咨询求助。这是一段我今天都无法笑着谈论的灰暗日子。
可是命运和我开了不止一个玩笑。
无法抗衡孤身在异乡的虚无与孤独,我又下回了dating app。使用一天后,我戏虐地统计了match/chat/深入了解的概率,并且决定在第三天就和唯一一个继续聊天的男生(以下称“Drew”)线下见面(主要是劳动节假期太无聊的原因)。此后的每一天我基本都是和他一起度过的,他带我去了他在这座城市的secret spots,我们聊了哲学和数学、宗教和生活,总的相处模式很像话痨的《爱在》三部曲。
认识两周的时候我就见了他的家人们,这使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恐怖的事实:我们成了彼此生活的一部分——我始终感觉我在纽约的生存状态是悬浮着的,我在这里没有根、没有什么connection,任何苦乐于我而言都是暂时的;因而当我目前的快乐回忆大多都和他相关,我失去了安全感。刚走出一段亲密关系又阴差阳错进入新的一段,我怎么能不害怕自我在他人中消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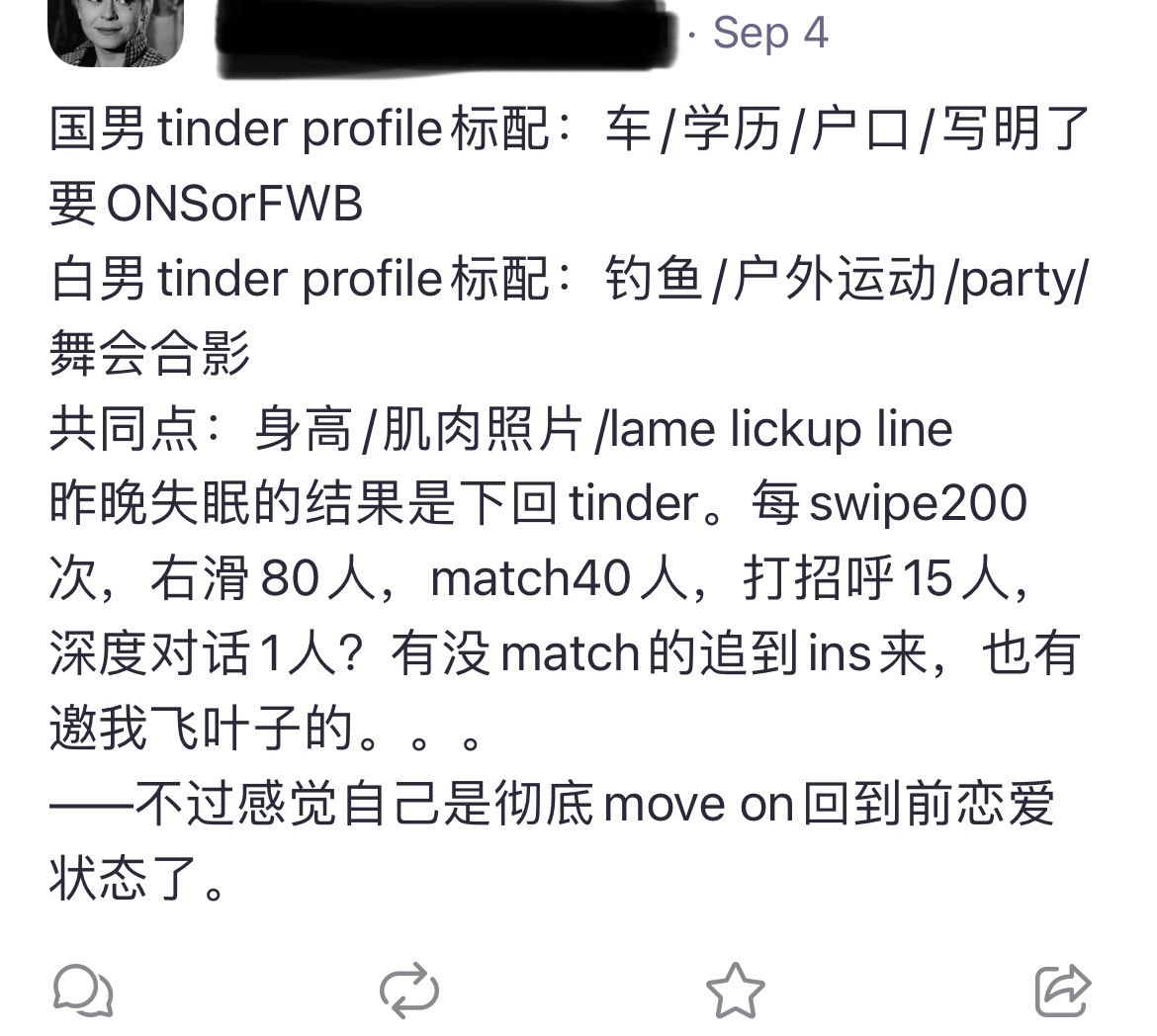
他用中文对我说“我爱你”,却告诉我我不必作出任何回应;就连我们决定一起注销tinder账号,他也对我说feel free to hook up as long as you keep yourself clean。纵然我更愿意将这段关系视为幻影,我忍不住在他身上寻找前男友的影子。相似的对话在一年前已经发生过一次,只是前男友实际上并不这么想。
我发现,前男友和Drew和我,我们对于love和commitment之间关系的理解大相径庭。然而他俩的逻辑都能自我融贯,而我的价值体系却是自相矛盾的,可以说,我就是个伪君子。我希望为我的挣扎寻找答案。
在进入正文前,我有必要解释为何标题和文章中多次出现英文。
直觉告诉我一些词在中英文语境中的内涵不同,另外我对恋爱的认知很大程度上被sitcom建构。即使现实生活不会像电视剧呈现得那样,主人公轰轰烈烈地说出I love you以推进关系,不可否认commitment都应该是严肃的。似乎中文对于“恋爱”一词的使用相对模糊,可以同时指代“就是玩玩”和“认真谈谈”两种状态 ,而我倾向于用dating和relationship加以区分。直接使用英文能更准确地表达我的意思。
三个男人,三种love
在遇到前男友之前,我从未进入过relationship,也不知“爱”为何物;看似高扬性解放大旗,却羞于承认自己“喜欢”上谁。我想这种缺乏勇气的懦弱心态大概可以追溯到被校园霸凌的中学时代,那时我吃尽了荡妇羞辱的苦。今天我还无法摆脱权衡利弊的心态:如果我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那我会不会太傻了点?
总之,爱之于我,正如千边形之于笛卡尔。笛卡尔可以「领会」千边形是由一千个边组成的形状,却不能像「想象」三角形一样直观在脑海中呈现出千边形的模样;我可以「理解」爱作为两情相悦的自然情感,但不知道爱与被爱究竟是什么「感受」。
前男友
——love = commitment (also tied to the validity of THE ONE)
前男友给我定义了什么是“爱”,爱是唯一,love = commitment。
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对我说“我爱你”,我被突如其来的告白吓坏了,在微博小号表达对爱的迷思。当时的我写下这段话,“‘我爱你’,这三个字好像一句魔咒,每说一遍都在心中加强一遍这个观念,我们都是爱的虔诚教徒。睡前说、临别和重逢说、做爱到高潮时说,到最后我们都不知道说出口的爱与最初的爱是否一样。爱成了习惯,爱成了肌肉记忆,爱成了生命的一部分,爱对方别无选择,那还是爱吗?”
我渐渐发现探寻爱的本质毫无意义,转而相信直观感知。日记里记录下出国前我们的这段对话:我说,我们open relationship吧,但你不能跟一个人睡超过五次//我说,即使我跟别人睡了,也不代表我不爱你//我又说,至少此时此刻我是爱你的,我们在一起也是开心的,only perception is real!
那都不是爱,我全都错了。
我意识到分手后的崩溃像戒毒,我无可救药地染上了对亲密感的瘾,我爱上了被绝对化了的爱的幻影。我从对爱的恐惧到对承诺的依恋,以至于最后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我依靠着他对我的爱活着,因而当他说他不再爱我,我就好像是坠入了虚无的深渊,痛苦、迷失,那种被爱加以我的独一无二的光环永远消失了,连带着我存在的全部意义。
我的问题在于,永远被动等待被爱,羞于承认对别人的爱,除非完全确认了对方爱自己。这大概是由于我太爱自己吧!一个极度自私的人,怎么可能主动将爱托付给别人,赋予他珍惜或蹂躏的权利呢?选择不爱没什么了不起的,选择去爱才需要勇气。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与此同时,深知我的好友向我指出,不论是我过去的casual date,还是我投入过多的这段relationship,都是一体两面的,我或享受操纵他人的权力感、或沉迷于被他人的爱主导,本质上我都将自己的价值依托于人——多么可笑,这与我自爱的目的相违背,归根结底是不够强大的灵魂导致了一系列宿命般的悲剧。我在这段感情中丢掉了主动权,也丢掉了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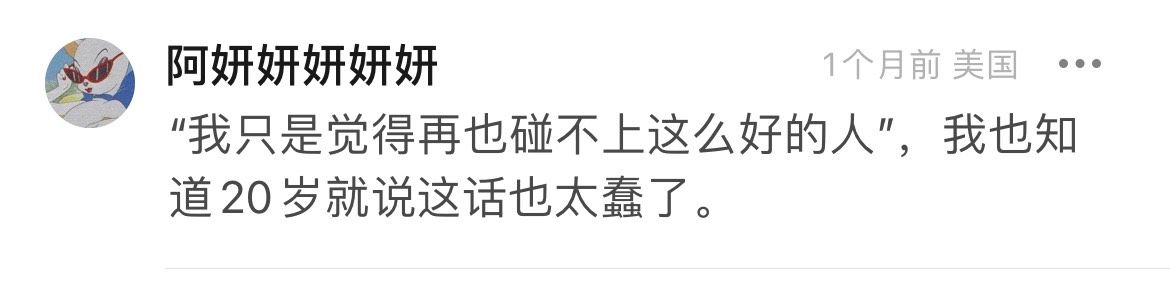
匈牙利大叔
——just a fling of love, no commitment involved
我怎么也没想到,分手后的第二天,我就遇到了第二个说“爱我”的男人。
几乎哭了一整晚后,我逼自己去大都会博物馆散心,扛三脚架的我看到同样举相机的匈牙利大叔,便请他给我拍几张照,当时我并没有察觉到他的热情过了头。直到第二周他约我作他的模特、去时代广场拍照,他用夸张的语调对我说”you are my angel, my muse, my goddess”,用油腻中年男人那套假意肢体接触,我才认清形势、赶紧拒绝。如果我还是缺爱没有安全感的年纪,我可能会稀罕一下这份“爱”,现在我只想快跑。这种不值钱的爱,不要也罢。

DREW
——love >> commitment and there are many ONES, it’s all about your choice.
遇见Drew之后,我的「THE ONE理论」有所改观。
在sitcom《how I met your mother》中,主人公Ted总是报以“她就是我人生独一无二的the one”的心态面对每一任date与女友。长期以来,我也相信我的人生中存在着一位真命天子,需要我耐心等待他降临,这大概是没什么恋爱经验的人们对于爱情的普遍的朴素美好期望罢。
因此当我和前男友first date聊到人生规划,发现彼此都痛恨国内大环境想run、以及厌恶孩子计划丁克,我们以为自己遇到了THE ONE,这为日后的争吵与挣扎埋下了阴影。每每因为他不及时回复我的消息 我发脾气/他受不了我的情绪 我说的“疯话”会给他留下永久的心理阴影/他讨厌用相机给我拍照 然后看我不满意的脸色/他也讨厌陪我city walk走很多路/他讨厌我对他的利用,我们都好像被困在这个循环中;他说这些矛盾根植于我们天性根本的差异,是无解的问题。换而言之,我和他之间的矛盾永远存在着,我们长期像朝鲜和韩国一样处于暂时休战而非永久和平的状态,维持休战状态取决于他出于爱的对我的“忍受”。有两次他不愿再“忍受”我,提出分手,可THE ONE的唯一性和lifetime commitment的神圣性让我依旧坚信,我们的关系值得继续,也许我应该多反思自己吧。
在和Drew的第一周相处中,我们也聊到了移民和丁克。随着深入了解,我发现虽然我们的本体论(关于道德绝对主义还是相对主义的立场,对我而言只是哲学家的文字游戏,他却把对与错的绝对性看得很重要)不同,但在实践层面都得出相似的结论。更让我惊讶的是,他主动向我分享他的生活/我的情绪得到justified 而不被男权叙事污名化为不理智/虽然我们吵架吵得更凶 但是和解后很快move on不会记仇/我们都痴迷于漫步纽约/他并不介意我对他别有所图,我和前男友的“根本矛盾”在他这边似乎都不成问题。
可我是在分手后不到两周就遇到的他,未免太巧了吧!这让我怀疑the one概念的合法性。因为人生目标类似而被我视为the one的前任,他的种种行为未免有PUA(或gaslight,也即“你有很多缺点,但因为我爱你,我愿意包容你,且只有我愿意”,潜在地让我自我贬损)之嫌,我的老师和挚友曾经提醒过我,当时我并没有相信,好在现在醒悟还不算太晚。
Love&commitment应当被珍视,但不该被捧上神坛,the one的概念更应当被祛魅与解构。与Drew的相遇让我相信,世界上本没有the one,相反有许许多多的the ones。In other words, it’s all about choice, and if this ONE doesn’t work, there will always be better ONES. It is worth adjusting in a relationship, but you should never ever get stuck in ONE if he makes you painfu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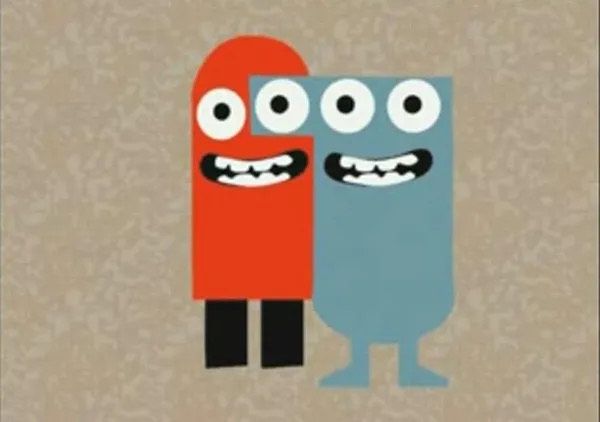
我的出现也让他重新相信,他尚未失去真正爱与关心一个人的能力,他的上一段感情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我还记得相识半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他第一次对我说“我爱你”,用的还是有些蹩脚的中文。我对这突如其来的表白的第一反应是失语,下意识地说I’m sorry I can’t say it back。毕竟“爱”是严肃的,这点不容置疑。他告诉我没关系,他对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那种广泛意义上的、对待家人般的“want her to thrive”的美好祝福,而这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他进一步解释道,他的爱的具体逻辑是,he wants what I want。也就是说,如果我想要跟他“在一起”(dating or relationship),他很开心;即使我不想,他也会尽其所能帮助我;他唯一的要求是我的诚实,如果选择前者,需要出于真心而非settle down的本意,至少我要快乐。根据我的理解,对他来说love >> commitment,又或者这种commitment是他对我单向度的,我不需要尽相同的义务;his offering is guaranteed, but I should never abuse his generosity.
(我始终感觉这个段落不流畅,因为我所做的工作是翻译他对我说过的话,甚至我脑海中还可以还原原句的从句结构)
关于commitment,我的答案
前男友问过我,说他没什么好的,我为什么愿意跟他在一起?我的回答是,他是我「当下所有选择中最好的一个」(很像莱布尼茨对上帝存在的论证,也即:即使世界不够完美,但这不足以威胁上帝存在的论断,因为我们如今所生活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
Drew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he said he doesn’t deserve me, why I’m willing to be committed to him instead of exploring all types of men in this city, which is an understandable goal when studying abroad?我给出了同样的回答。
但这两次的commitment有着本质区别。
在上一段感情中,我时常觉得我的主观欲望与道德的客观规范相冲突。一方面,我有时会怀疑他并不是我最好的选择,会有种出轨的天然冲动;另一方面,我又敬畏commitment的道德法则。我最终选择恪守后者,可道德规范无法内化为我的行为倾向(本人对元伦理学了解不多,不知我所说的这种「内化」是否真的可能,以及是否应当借助科技手段帮助实现,而这又引申到科技伦理的范畴),而带来的结果是我无尽的痛苦与挣扎。因为让我不出轨的唯一合理解释便是,前男友是我人生唯一的THE ONE;面对种种不愉快,我只能给自己洗脑,让自己必须爱他,对其他念头进行自我道德谴责(可以说,内化的是那种gaslighting而非morality)。
我对Drew就不存在这种挣扎。这恰恰验证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不是迎头赶上,而是不把它当作问题,像禅宗那样“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我们达成共识:maybe I can find better, but I am happy about where I am and how things are----it is my CHOICE, it is FALLIBLE, but I am willing t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all the possible outcomes.我愿意快乐地活在当下,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正是其魅力所在。
这就是我对于love与commitment的矛盾的解答。
最后的最后。
如果前男友还在看我的matters,你大可以骂我虚伪,hypocrisy is embedded into the human nature。
但是时至今日,我终于能够真心说出,我祝你一切都好。
恩恩怨怨,旧情难续;
世事沉浮,何叹今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