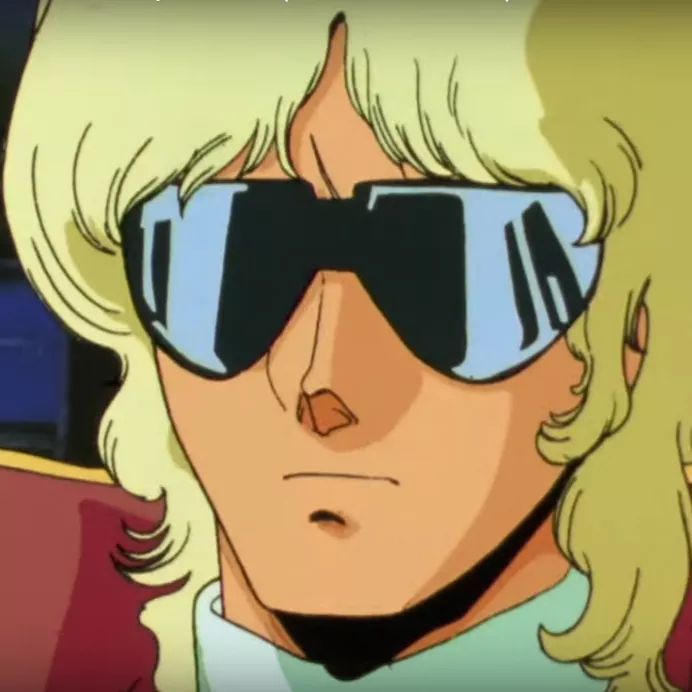憤怒新一代:《忿怒的一代》三十年後的書評

《忿怒的一代》寫於九十年代初,建道神學院榮休院長梁家麟博士問香港人能否免於恐懼。三十年後,香港人能否真正做到?
香港地少人多競爭大,人們本身已經容易燥動。加上當年先有中英談判後有八九六四,表面平靜的香港人有不少人選擇移民他方,內裡十分忿怒。作者承認在討論國事家事之時感情比認知先行,所以產生忿怒作回應為人之常情。作者並不否定忿怒,認定那是良知對不公義的即時反應,也證明了並未對現實麻木。不過,他亦指出發怒其實並不理性和持平,指出別人不義容易做成自義。而最直接結果就使人陷入對一切事也只有二元的看法:逃避還是接受現實,實現理想還是同流合污。作者指責這既有違人性又抹去面向上帝的向導。
再者,忿怒消磨生存勇氣,令人長期處張力和絕望。作者指忿怒過後仍要面生活的絕望,只有憑信心重尋理想才能克服負面情緒。作者認為社會畢竟需要中堅,忿怒只能間歇地發揮化悲憤為力量的作用,不能長期只逞一夫之勇(即係今日的攬炒),也要咬實牙關朝向理想。信心不否定世上困難的真實性,也不妄想上帝會很快介入,以為上帝只在緊急才出現。信心教人在承擔中付出自己,成為意志和勇氣的根源。人們不應因現實可愛或理想可實現而去愛,卻因所在的群體和身份堅持理想和愛,才能免於忿怒。
今日的處境與三十年前不同,香港人的本土意識達到了前所未有幅度。當年主張離開的人都漸漸移民,沒有繼續做成太大分裂。如今社會卻因著政見而分為黃藍二營,且在黃營中也分裂出幾個門派。始自北京對實現雙普選和高度自治的諾言落空,連民間學者(亦即「和理非」)最後温柔的嘗試 — 佔領中環及衍生出來的雨傘運動 — 也功敗垂成。走得更前更激進的指責對較保守的泛民有政治潔癖使運動失敗,但他們也因內部分裂失去組織力,變得無力改變現實。這情況使整個民主一翼也充滿著忿怒、灰心和無力感。令本來就算不主動的香港人也累積了忿怒。此外,近年由左北方傳入的「留島不留人」的喊話在香港人的眼中,這種態度比他們被殖民經驗更差,與國內一家親的想像也幻滅。凡此種種累聚積更大的忿怒。
上文作者對忿怒的神學分析提醒人們應當心二元的思考,仍然對今日的情況有啟發。佔中以降門派分裂便是這種思考的結果,到了反送中才催生武勇和理非的和解。可是也生出不少引起爭議的二元思維,包括割蓆和人血饅頭等,其中「攬炒」可算是最具代表性。既是源於絕望和忿怒,也希望懲罰壓迫的政權及其為虎作悵的權貴。作者指出這快意恩仇失去了使運動持續的韌力,容易回到夢想爆破的失望和灰心。 至今運動已經持續超過一年,加上疫情拖累,單靠忿怒和仇恨不能維持下去,需要為抗爭尋找出路。雖然不少抗爭者已經轉移至兩次選舉和「黃色經濟圈」,以保持與政府的張力之餘又可以維繫抗爭一方的團結和生計,但長久而又能免於忿怒的生活上抗爭提案仍然缺如。
另一方面,三十年前香港因移民而出現的是群體問題。在社會上,有人曾經為夢想奮鬥,相濡以沫。由於港英政府六七暴動後主動改善施政減輕社會問題,加上六四以降中國夢的瓦解,使不少理想主義者好夢落空。現實的去留問題而產生存在問題。有人因此放棄理想,有人遠走他方,少數留下的也相當灰心。作者觀察到,一些人為了自證其決定正確而以屬靈理由包裝移民,同時貶抑選擇留下的人。使本來只屬個人意願的選擇提昇為存在主義危機。別人的決定成為自我的威脅,為留下的人產生壓力。更甚者使人們要爭相證明自己的選擇合理,引致群體的解體。 即使再相聚也無法再如以前一樣交心同行不再開倘自己,破壞群體中的互信及影響團結,也變得忿怒。
三十年後,縱使反送中運動在重建群體上開出了新的可能性,香港人仍需在此繼續努力。反送中運動開始不久便在討論區出現「不篤灰不割蓆」的方法以解決漸漸分化的情況,在運動的中間也發揮著口號和檢討的作用。可是,這種方法只能保持政治性群眾的團結,而不能組成互相交通之一「體」。這種群而不體的做法就是梁家麟上文開始時所述失落了的群體。一如他對群體的分析,與其只高舉一己的立場和理想而視異己者為敵人,更應要接受群體的不完美和「落水」一同參予改變。
書中最後部份,作者著力重尋群體的新基礎。他引用潘霍華的神學否定個人主義,力陳他者不是自己的伸延。無論教會還是社會,只有「我與你」這種互為主體的框架下,才能承認他者的主體性,人類社群才能開展。個人也能認識自己的界限,在群體中才能認識自己。同樣,人在與上帝的關係中才能認識自己,故上帝不能是人的延伸,卻反而是人性保衛者。要放棄聖化自己的理想,才能謙虛地活出使命和接納他人的不同,這不單是教會也是群體和社會的基礎。教會裡信徒一體而非齊一,不單彼此照顧也包容差異,教會應可發揮孵化公民社會的作用和典範,也是在「誰也不能代表我」的網絡生態所急需的。從佔中到今日逆權運動和疫情,教會都發揮著調停、支援甚至是分配物資的作用。雖然在教內這個位置引起不少爭議,但縱觀二戰後的民主化及社運,由南非東歐到南韓,教會也從不缺席,香港教會也不應例外。
或許,要香港人止息忿怒仍然困難,唯有放棄二元的思考和「落水」擁抱不完美的群體,才能促成個人和社群的改變,能讓香港重拾笑臉。
原刊於時代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