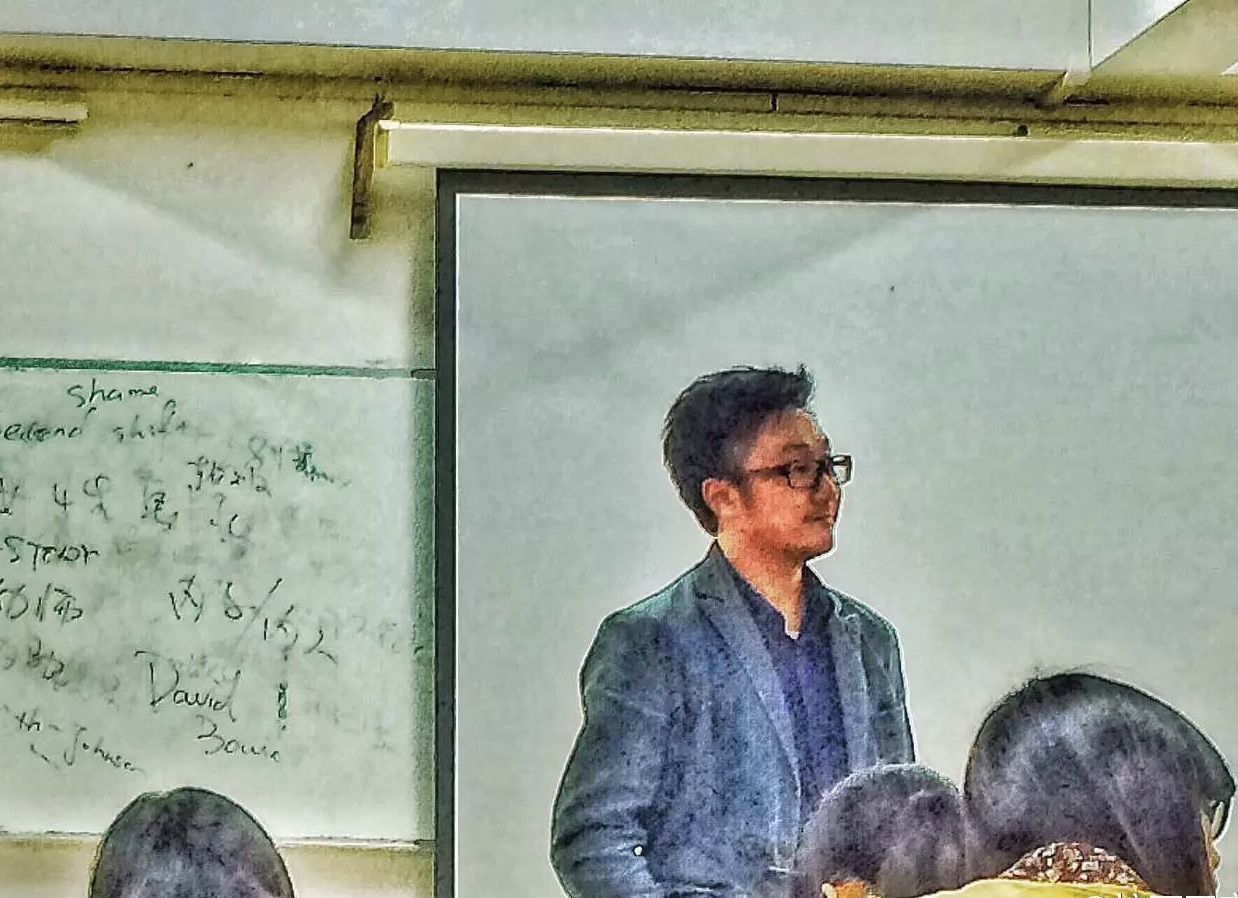我是清醒的厌女者吗?团结、身份与责任(三)
4. 团结
既然受益者悖论并不成立,据此而排除受益者参与到运动之中的结论也颇有问题,这时我们似乎有必要也反思一下,女性主义运动应该让谁参与的问题。特别是,当面对制度性系统性的性别不平等不断的压迫,女性主义者常常需要动员和争取需要的力量,此时最常见的口号便是女性主义者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然而,什么才是团结?什么人才能加入团结的行列?“团结”这个概念本身似乎也需要反思。
在反思团结这个概念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既然受益者悖论不成立,那么政治运动中加入受益者是可允许的(permissible),进一步,受益者加入到运动中,能不能为运动带来什么好处呢?这方面的考察或者也会为我们反思什么是团结提供帮助。
4.1 受益者加入的好处
首先,受益者加入运动去反对和终结压迫,可以帮助改变运动中可能存在的偏见。上文提及的Nian Hu说,“这些男性女权者没有意识到的是,作为男人,他们永远都会是压迫者。”这种对男性女权者的看法,背后预设了一种男性的本质,男性本质上就是坏人。如果一个人是男人,他就是压迫者。这种关于性别与人的品格或行动的关系的本质主义描述,恰恰应该是女性主义需要反击和改变的观念。当受益者加入到运动中,这些偏见便可以有机会去改变,通过那些认真投身运动的受益者的行动和品格进行修正。除此之外,这些偏见的修正还可以帮助女性主义者修正其他可能的偏见和歧视,比如关于种族的偏见,关于宗教的偏见,关于国籍身份认同的偏见等等。
另外,允许受益者参与到运动之中,可以为运动和团体带来多元视角。这些视角可以是关于运动的性质的不同看法,可以是关于性别不平等的不同理论解释,可以是关于行动策略的不同理解等等等等。女性主义以及女性主义运动本身就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论,参与者的多元视角对运动的增益自然不少。比如,受益者/男性加入女性主义运动,可以为运动和团体带来新的内容,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其他受益者/男性拒绝承认和认可历史上以及当下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状态,使这些男性经验得以容易理解(demystify),进一步可以帮助提供对抗压迫和不正义的新理解和新策略。
再者,根据Sally Scholz的说法,不同参与者带来的多元视角可以帮助群体和运动避免暴力或者反向压迫。Scholz引用Nancy Frazer,另一位著名的女性主义哲学家,“没有任何一个受压迫群体可以仅凭一己之力作出重要的结构性改变,[我们]也不可能相信任何一个群体能够保证照顾到其他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社会转型要求我们与我们的反对者接触(engagement with one’s opponents)而努力。”即便是来自受益者的声音,多元声音能够对终结压迫提供贡献。
最后,受益者参与行动会对个体的行动者也带来好处,其中表现在受益者参与可以帮助解决行动者在运动中所受的“不幸难题”(the wretchedness problem)。Sandra Bartky在她的文章“Sympathy and Solidarity”提到了这么一个行动者可能遇到的难题。Bartky问到,“在政治行动者在认知上完全了解和情感上体会到(attuned to)世界上不幸者的不幸时,我们如何能够将我们从绝望中或者心理上的麻痹中拯救出来,做出有效的成果?”行动者面对种种让人窒息的不正义压迫下的人,需要各种帮助来应对这种感同身受的绝望。Bartky认为我们需要培养我们的同情能力的同时,也要学会在行动中保持情感上的距离,否则行动无法实现。Scholz进一步认为,要完成这种保持距离,我们可以通过面对压迫的不同视角的统合来实现。受益者的视角或者可以带来这种稍微分离(detached)的视角。
4.2 团结的基础:承诺而非身份
如果这些好处是真实的,并且这些好处对于运动而言是可欲的(desirable),如何让其实现自然会对我们如何理解运动提供新的线索,特别是,当我们需要在运动中强调团结时,如何理解团结,似乎需要新的反思。
不少女性主义者,比如上文提及的两位,会认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团结对象应该限定于经验着压迫的女性,背后的基础正好就是立场理论。在她们看来,团结的基础应该是被压迫的经验:仅当她具有被压迫的经验,她才能真正地加入到运动团体中形成团结。这种从知识论来的立场优势同时也为受压迫者在运动中赋予一种道德上的优势(moral privilege/moral superiority)。Sally Scholz认为,这种道德优势就是,因为受压迫者正在受到这些不正义和压迫的伤害,所以她们更有权(more entitled to)去制定应对这种不正义的策略方案。这种“更有权”或者“道德优势”可以奠基于比如自我防卫的辩护之上。
然而,这样理解的道德优势是有问题的。首先就是上文提及的,受压迫的经验本身对于行动而言既不必要也不充分,尽管受压迫经验对于理解和明白压迫的事实非常重要。具有受压迫经验不能必然蕴含受压迫者就会真正行动起来,受压迫者本身也需要经历重要的认知、慎思、决定等过程,这一点跟没有经验压迫的人似乎并没有实质区别。
更进一步是,这种道德优势的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force)也是可疑的。一个人受到不正义的压迫,因而反抗去终结这种压迫的道德理由,与另一个人知道其他人受到不正义的压迫,因而反抗去终结这种压迫的道德理由,有什么会带来不同道德效果的区别吗?
假设甲受到了某种制度性性别歧视的伤害,在运动中结果E能够终结这种性别歧视。这时候,甲经历了这种压迫,她做了行动带来结果E。另一方面,没有受到这种性别歧视伤害的乙知道甲受到伤害,她也做了行动带来结果E。根据这种道德优势的说法,因为甲在性别歧视上受更大的伤害,所以甲行动的理由,比如出于自我保护或者自我保全,是更有力的理由,甲更有权利做出或指导做出行动。然而问题是,乙做出行动带来结果E的理由客观上与甲的理由有道德上的分别吗?甲和乙的行动都是基于有人(甲)受到了性别歧视,因而要结束这种性别歧视,两人都是出于同样的情景而做出行动带来结果E,区别在哪里呢?
其中一种可能做出的区分是援引行动者相关理由(agent-relative reasons)和行动者中立理由(agent-neutral reasons)的区别。所谓行动者相关理由,就是一个行动者所具有的行动理由(reasons for action)并不必然成为其他人的行动理由,这时候,这个理由就是行动者相关理由。而行动者中立理由便是不管行动者是谁,此理由都是其行动的理由。(Parfit 1984,Reasons and Persons)
假定,如果我在家里播放周杰伦的音乐,某人会非常高兴。这时候,我或许有理由在家里播放周杰伦的音乐了。这时候,根据Nagel的形式化处理,我播放周杰伦音乐的理由可以改写为:
R1:如果结果E「播放周杰伦音乐」能使某人感到高兴,我有理由行动带来结果E。
再假定,这个某人其实是我的妹妹,如果我根据R1来行动,我的妹妹从中感到高兴其实是很偶然的,因为就算是一个陌生人感到快乐,我同样会有理由这样做,并且,其他人也同样有理由这样做,假定这样做得到某种规范伦理学理论的证成或辩护。然而,情况会有所不同,如果我行动的理由改写成这样:
R2:如果结果E「播放周杰伦音乐」能使我的妹妹感到高兴,我有理由行动带来结果E。
这时候,我的妹妹感到高兴不再是我行动的偶然结果了,而是我的行动理由的目标。我的行动理由与我使得陌生人快乐的理由在这里便截然不同了,并且其他人未必同样有理由这么做了。
这两个例子似乎能够说明行动者相关理由和行动者中立理由的区别。如果将此区别应用到受压迫者和非受压迫者参与运动的理由上面,或者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假定参与行动是为了实现结果E,来结束甲受到的性别歧视。首先,非受压迫者参与运动的行动理由便是:
R3:对于所有E,对于所有p,如果E能够结束某人受到的性别歧视,那么p有理由行动来实现E。
而受压迫者行动的理由便是:
R4:对于所有E,对于所有p,如果E能结束p自己受到的性别歧视,那么p有理由行动来实现E。
如果这样的分析和改写是正确的,讨论R3和R4是不是同一个理由,就是讨论是否真正存在行动者中立理由和行动者相关理由的区别。这个问题当然无法在这里探讨,并且是当下伦理学一直在讨论的大问题。假定这个区别是真实的。R3和R4自然是不同的理由,按照Nagel的说法,因为R3和R4两个理由的前件并不一样,R4的前件出现了对行动者自己的指称,但是R3并没有。
然而,如果R3和R4的这种区分就是非受压迫者和受压迫者参与行动的理由的不同,那么受压迫者的理由在女性主义者的眼里就更加不可能具有更高的道德优势或者优越了。因为,受压迫者行动的理由R4恰恰是女性主义者经常批评的一类理由,即仅因为自己或者身边人受伤害而反对性别歧视。当出现性骚扰性侵犯事件时,很多男性公开表示谴责,不过他们常常使用的理由是“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太太/母亲受到同样的对待”。女性主义者强调,这样的理由并不足够。我们不需要因为身边人或者自己会受到伤害才谴责性骚扰,仅仅性侵犯本身就足以对这些伤害进行反对。仅仅从个人或身边人的利益出发来反对性骚扰,似乎会预设,这些不正义和压迫不过是利益与利益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对正义或公平的侵害。如果女性主义要保持对普遍价值的追求,我们似乎就不应该强调反对性别不平等是一种利益与利益的冲突和斗争。
如果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女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就不应该是受压迫经验。那团结的基础应该是什么呢?bell hooks对姐妹情谊的论述,可以为答案提供一个方向。
上文提到bell hooks认为,将姐妹情谊(Sisterhood)建立在共同受压迫经验之上,会导致女性的受害者化,造成的结果会是,首先,继续顺从于性别主义对女性的想象塑造:真正的女性就是柔弱的受害者;其次,女性主义运动排斥那些自我肯定的、强势的女性;最后,推卸性别主义责任,并且遮盖女性之间,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差异与分歧。
既然这样,bell hooks设想了另一种团结的基础:
“女性并不需要通过消灭差异来获得团结。我们不需要通过共同压迫来平等地为终结压迫而斗争。我们不需要通过反男性情绪来凝聚起来。我们有如此丰富的经验、文化和观念等财富可以互相分享。我们就是姐妹,因共享的利益和信念而联合,在向往多元中联合,在终结性别压迫的斗争中联合,在政治团结中联合。”(bell hooks,ibid)
bell hooks提出的姐妹情谊的团结是一种政治团结,而政治团结的基础,就是不同参与者互相做出的政治承诺(political commitment)。(commitment这个词根据语境,有时对应的是汉语的“承诺”,有时对应的是“投身”。)政治承诺不同于其他的承诺,比如因为出身于中国而投身到中国的建设;因为我是广州人,我承诺热爱广州。政治承诺的重要特点是资源选择一个事业的承诺,好比投身到一段关系或一段友谊。按照Sally Scholz的理解,政治团结作为一种团结的方式,就是在于这种自愿选择的承诺。承诺的内涵很多,但至少应该包含两方面,承诺的目标以及承诺的责任。bell hooks认为,姐妹情谊,女性主义者承诺的目标当然就是投身于旨在终结性别主义压迫的女性主义运动。要完成这一目标,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和策略,这些毫无疑问会成为持有不同意见的成员之间长期讨论的问题,但是讨论也恰好是女性主义者分享经验与资源的最直接的方法。
另一方面,政治承诺蕴含着责任,这些责任可以看作是真正做出承诺或者投身的要求。姐妹情谊形成团结的责任,在bell hooks看来包括,除了终结性别主义压迫之外,姐妹们还需要“合作起来,去指出,去检查,去消除我们之间的性别主义观念”;抵制姐妹间“互相猜忌、防御、竞争的行为”;姐妹们要“懂得承担责任去反抗那些可能并不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个人的其他压迫。”(Women must learn to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fighting oppressions that may not directly affect us as individuals.)
bell hooks认为,只有这样,姐妹们才能形成真正的姐妹情谊,才能真正团结。事实上,按照她的看法,女性主义的团结的真正基础实质上与性别身份是没有关系的。如果只考虑女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的承诺,那么我们似乎并不需要将团结限制于姐妹,而是只要愿意投身于运动,个体就可以加入到政治团结之中。一个扩展版的姐妹情谊就可以成为包容不同性别的女性主义者的政治团结。
这个女性主义者的团结的基础不再是身份,而是个体的承诺。这意味着,就算是前压迫者,未受过压迫者,只要做出对女性主义运动的承诺,都可以形成女性主义者的团结。个体承诺的目标依然是终结性别主义压迫,而承诺的责任,Scholz总结的更好:合作,交流,相互性(cooperation, communication, mutuality)。
前两者很好理解,合作和交流都在bell hooks提到的几个责任之中贯穿。什么相互性?Scholz认为,“相互性强调每一位团结中的参与者的独特性,同时又强调所有参与者之间的互相依存和互惠(reciprocity)”。我的理解就是,所谓相互性就是,凡是在政治团结中可以应用于一个个体参与者的对待方式,都必须可以应用于其他个体参与者。所以,每个个体参与者都是独特的,不可以完全被另一位替代,不然就不存在团结了;同时,每一位参与者需要通过依靠其他的参与者的帮助来完成运动的目标。
如此理解的相互性,意味着个体不能仅仅通过主张自己就是参与者便加入了女性主义团结之中。个体要真正成为参与者,就必须明白运动的整体责任,并且要做出个人的改变,成为运动中能够被依靠,能够参与到合作的参与者。
同时,这也意味着,在女性主义运动中,个体参与者之间必须存在责任的平等(equality of responsibility)。所谓责任的平等,并不是说每个参与者在运动中拥有同样的责任。女性主义运动会不停变化,团体里面不同的位置当然会有不同的责任和要求。责任的平等指的是,个体参与者只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坚持投身在运动之中,个体参与者就应该被承认尽到责任。这种责任只与个人能力和个人坚持相关,因而都是平等地重要的。因为,相互性要求每个参与者被平等对待,个体参与者的能力都有独特的价值。女性主义运动中不同的位置可能有不同的功能作用,对于任何的社会运动,包括女性主义运动,总会有些时候,行动者的坚持抵制会比理解澄清不平等的形成机制更重要;但总会有另外一些时候,理解澄清比行动更能带来运动的成功;有时某一部分人能够比整体带来更大的社会改变,有时又是反过来。(Scholz, ibid.)所以,每一个个体参与者根据其能力为女性主义运动带来的贡献都应该是独立而平等的。这是承认上的平等。
只要满足了这些责任,做出诚恳的承诺,不同性别的个体都能够并被允许成为女性主义者,并形成团结的女性主义运动。
这样来理解团结,女性主义者就可以更加好地组成团体,形成团结的女性主义运动。即便面对可能会出现清醒的厌女者的情况,女性主义运动也并不需要限制和排除性别主义受益者。
5. 我是清醒的厌女者吗?
用了以上这么长的篇幅讨论女性主义运动应该如何团结可团结的人,仿佛为我自己辩解,我们最后回到第二个问题,我是清醒的厌女者吗?就我个人而言,我最诚实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并且我或许很可能就是。
如果我们要问自己是否清醒的厌女者,稍微一般性的回答当然是可以存在的。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和反思自己是不是厌女者。这可以从我们是否在言行或意识中表现出比如上述提到的各种厌女者的症状。
然后,我们反思自己是不是清醒的厌女者,事实上就是在问自己,是否真正投身到性别平等。这跟反思自己是不是厌女者是不同的问题,尽管两者涉及很多相同之处,比如反思自己是否真正愿意聆听女性表达她的感受和观点,真正愿意平等对待女性等等等等。除了这些之外,成为真正女性主义者,还需要承担上述提到的承诺的责任:合作,交流,相互性;或者像bell hooks所说,“合作起来,去指出,去检查,去消除我们之间的性别主义观念”,抵制“互相猜忌、防御、竞争的行为”,“懂得承担责任去反抗那些可能并不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个人的其他压迫。”按照Scholz的总结,简单来说,受益者成为真正女性主义者,而非清醒的厌女者,有三个要求:
第一:是否愿意放弃自身的特权和优势,不管是社会地位上还是知识论上的特权和优势;
第二,是否能够真正去尝试理解受压迫者的状况和经验;
第三,是否参与反对性别主义的行动。
根据这些要求,我们可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者。
但就我自己而言,我似乎只能最多回答,我不知道。或者我很可能就是清醒的厌女者。所以,经常反问自己是否清醒的厌女者,每次看到任何女性批评男性如何如何时,总会觉得就是在针对自己。有时这样的不断反问的确会让人神经衰弱,不过这种提问也是一种反思和警觉,自己是否做得足够好。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的这个问题,“我是清醒的厌女者吗?”可能本身并不需要回答,只需要提问就足够了。女性主义运动也好,其他为了改善受害者或弱者的运动也好,参与这些事业最首要要回答的问题是,她们的生活和处境是否得以改善?借用钱永祥先生的话,不要把自己的道德成就当成道德事业的首要要求。社会议题的焦点在于改善受害者的处境,不在于我们自身的道德完善。
最后,我再为自己做了一次辩解,我是清醒的厌女者吗?这个问题不用回答。或许更应该问,女性的处境有所改善吗?我帮得上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