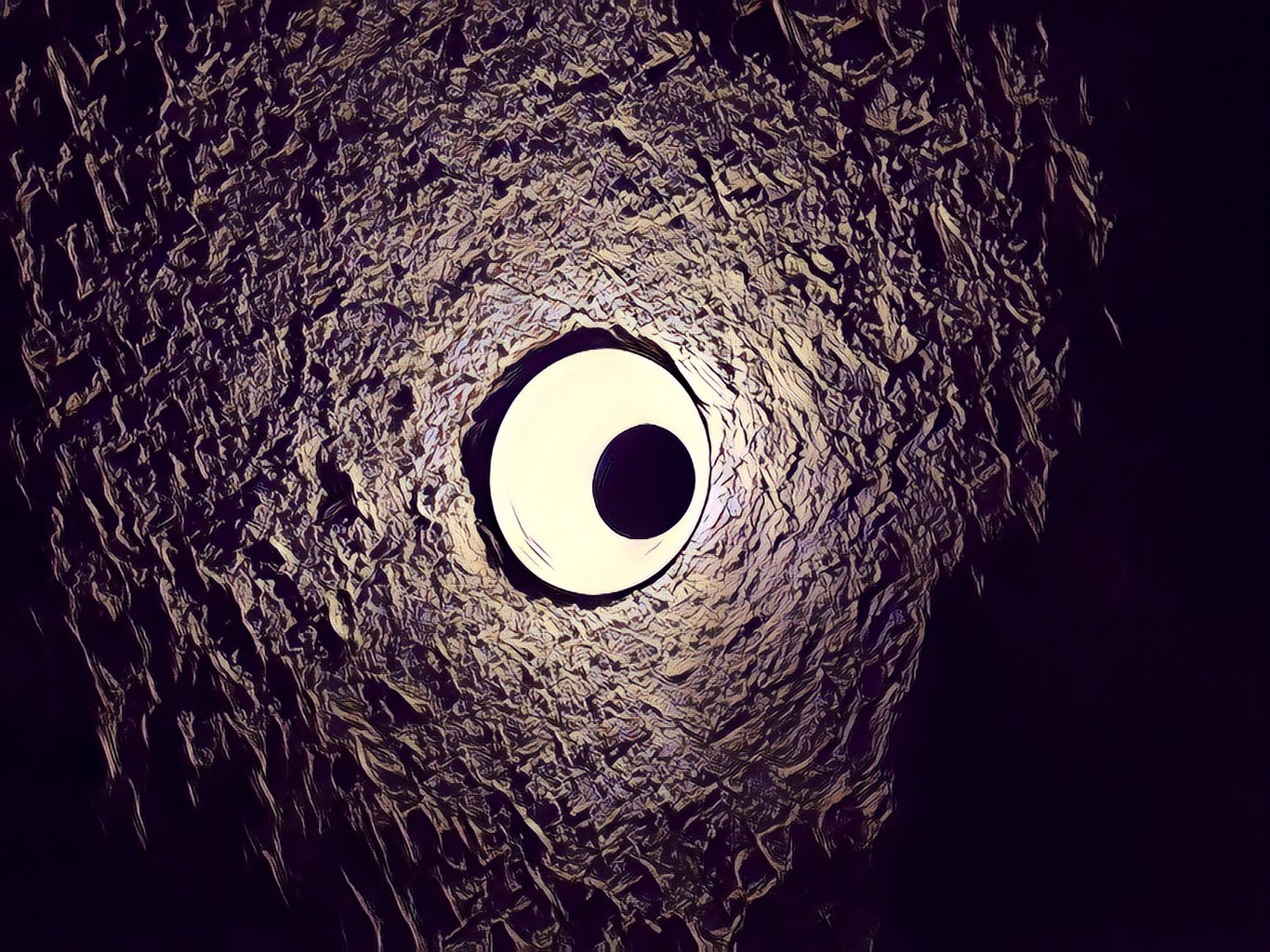泥娃娃|1|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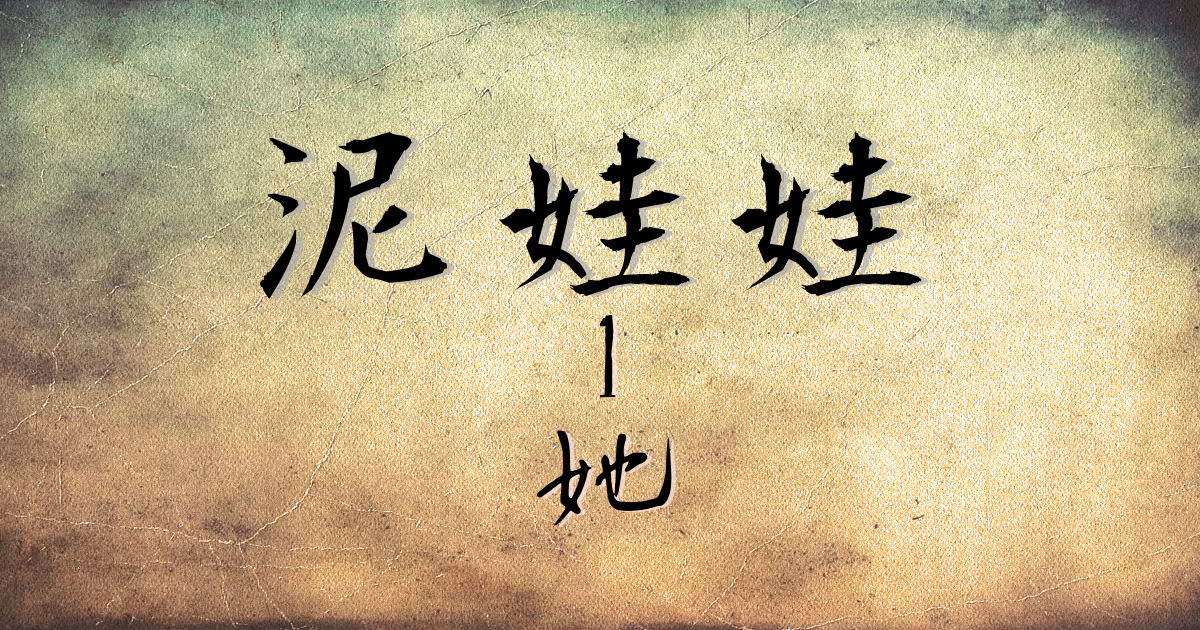
冬天常常在時間軸上延遲,拜人類所賜,我們早快習慣逐漸失衡的生態變化。當夏天、秋天不再壁壘分明的時候,這一切反映在少女的穿搭上。我望著捷運上的人們,正低頭默默吸收著來自這時代的片段資訊。而讓我在車廂裡發呆的原因,只是因為我太過疲憊。寧願虛度人生的十三分鐘,也不願再讓腦筋打轉。
正當我凝視窗外的黑暗至出神之時,熟悉的進站鈴聲使我暫時恢復精神。當車廂門敞開時,冷風滲透到腿邊時,我不免打了哆嗦地望了望車廂門。警示聲與進車廂的人群像是交響樂的指揮與各專業音樂家,大家各自戴上耳機,站在可以逕自恣意徜徉的小世界框框中,打開屬於這世紀的通俗資訊設備。
我無趣地回頭看向前方,正想準備靜謐地進入夢鄉時,眼前的光景似乎將我的神經凍結。
不。
我想是大多數人可能與我反應相差不遠。
一名披頭散髮的少女站在我前方,她在最後響鈴的嗶嗶聲衝進車廂,可能因為長時間的奔跑,她不停低頭喘氣,穿著單薄的褪色長洋裝,她的雙眼被那髮質奇差無比的長髮擋住,不過即便如此,但從我坐的位子的角度,卻可以隱約看見她的眼神。
我周圍的人已經開始議論紛紛,也許是過去在捷運上發生的隨機殺人事件,車廂裡的人們慢慢將目光轉移到這少女的身上。她那充滿暴戾之氣與不知所措的衝突表情,根本不像是正常人,反而比較像是『野獸』。正當我們開始默默觀察她時,她也正以一種狩獵的眼神攫著我們。
她就像是靜止的狩獵者,思考自己的下一步,
因此我雙手開始不禁發抖。這個少女的下一步會是什麼?
她沒有說話。她會說話嗎?
這個疑問不僅只有我在思考,或許車廂內的人也是。
但眼前的景象對於這個世代的人們來說,已經是太過前衛的存在。
她似乎低語喃喃什麼,活像是電影裡頭中邪的人們。
於是整個車廂的氛圍就像是表面張力一樣,
每個人試圖在最小維度下保持平衡,
就像是液體自始自終都會試圖走到能量最低點。
我們保持一種微妙的默契,等待下一站的來臨。
但我腦中不停翻騰的疑問及不由自主地衝動,
就像是從天空落下的雨滴,讓水面產生了漣漪。
「妹妹,妳還好吧?」我對她說。當我說完這句話時,自己也愣了一下。我還在思考這句話是我說的嗎?當我正想確認時,我已經發現車廂內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朝我看來。
「妳還好吧?」我的神經、我的反應、我的腦中決策都像是自動化機台一樣,並且試著填補這中間的空白。
當第二句話漂浮在空中近乎三秒之後,我的腎上腺素似乎被啟動了,我得說這是一種我無法預期的直覺。彷彿我知道她會做些什麼。那種微妙的壓力巨大地打在我的心頭上,當我這麼反應的時候,她已經往我衝過來。緊接而來的是難以言喻的疼痛與灼熱感受。
尖叫聲從我的四面八方從來,每個人不知所措地望向我,
她像是野獸般地啃著我的左臂。
霎時,刺痛從左臂一路爬升到後頸。
幾個身旁默默不語的成年男人終於卸下了冷漠,
想試著從我身上將她拉走。
但每一次的拉扯,我都感受到手臂自己發出哀嚎一樣,宛如待在鳥巢之中的幼鳥受到天敵欺壓發出既稚嫩又真實的叫聲。而當我咬著牙恢復理智時,才發現那個哀嚎是卻是從自己的喉頭發出的。車廂裡頓時從都市冷漠環境,進入了上古的殺戮戰場。
那些我身旁使盡了全力的男性們幾乎無法撼動這個少女。我看見她那獸性的啃咬之下,那冷峻的眼神與超乎常理的蠻力成為詭譎的衝突。
眼前吵雜、混亂、荒唐的樂曲伴隨著從未有過的疼痛幾乎讓我昏厥。我不清楚是不是要昏倒,只發現自己的力氣與反抗正慢慢在流逝。也許是因為每一次的掙扎只會換來更為紮實的啃咬,於是我揮起了右手示意讓那些幫助我的男性暫時停手。
我知道任何語言應該都無法與她溝通,
我試著用肢體語言對她示好,
當我正嘗試釋出善意的微笑時,
內心某個自己似乎在低喃自己的愚蠢。
不然能怎麼辦?
眼前幾乎沒有人敢再靠近我。
因為沒人可以有把握全身而退,大家在那剛剛的混亂局面中,都見識到了少女那近乎不能以科學解釋的蠻力。我們這樣的都市人竟然只在這微妙的咬合動作中,就成為了食物鏈中的供給者。
於是,我伸出手,忍著那幾乎超越疼痛的感觸,試著要彌補我們之間的隔閡。那種鴻溝不像是人種、宗教、政治立場、性向、性別等等,而是必須跨越物種之間的那種交流。
而當我的手輕輕地碰觸到她的臉龐時,
我感受到她的遲疑,
她的世界及宇宙似乎產生了巨大的矛盾與混沌,
就像是個新世界的開端一樣。
我很訝異自己竟只是透過這樣的觸覺,
就產生了這種感受。
我很確定這並非只是我單方面的理解,
我正看見她的眼神正微妙的質變當中。
她的戒心與混亂似乎打亂了生為狩獵者該有的自尊與冷靜。
她究竟有怎樣的過去?
我的好奇心是使我不要昏厥的原動力。
剎時,嗶嗶聲從我耳邊劃過,
接著我聽見眾人的吆喝與混雜的聲音。
那是少女與上車民眾推擠所引發的,
包括好心的民眾衝上前去要揪住她。
不過我已無心去一一辨認一切,
世界的聲音似乎離我好遠,
我靜靜地握著自己的左臂,
鮮血像是少女留給我的紀念一樣。
接著就是一陣昏沈的黑暗包覆我,
但是在我閉上雙眼以前,
我彷彿又看見她那充滿未知與衝突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