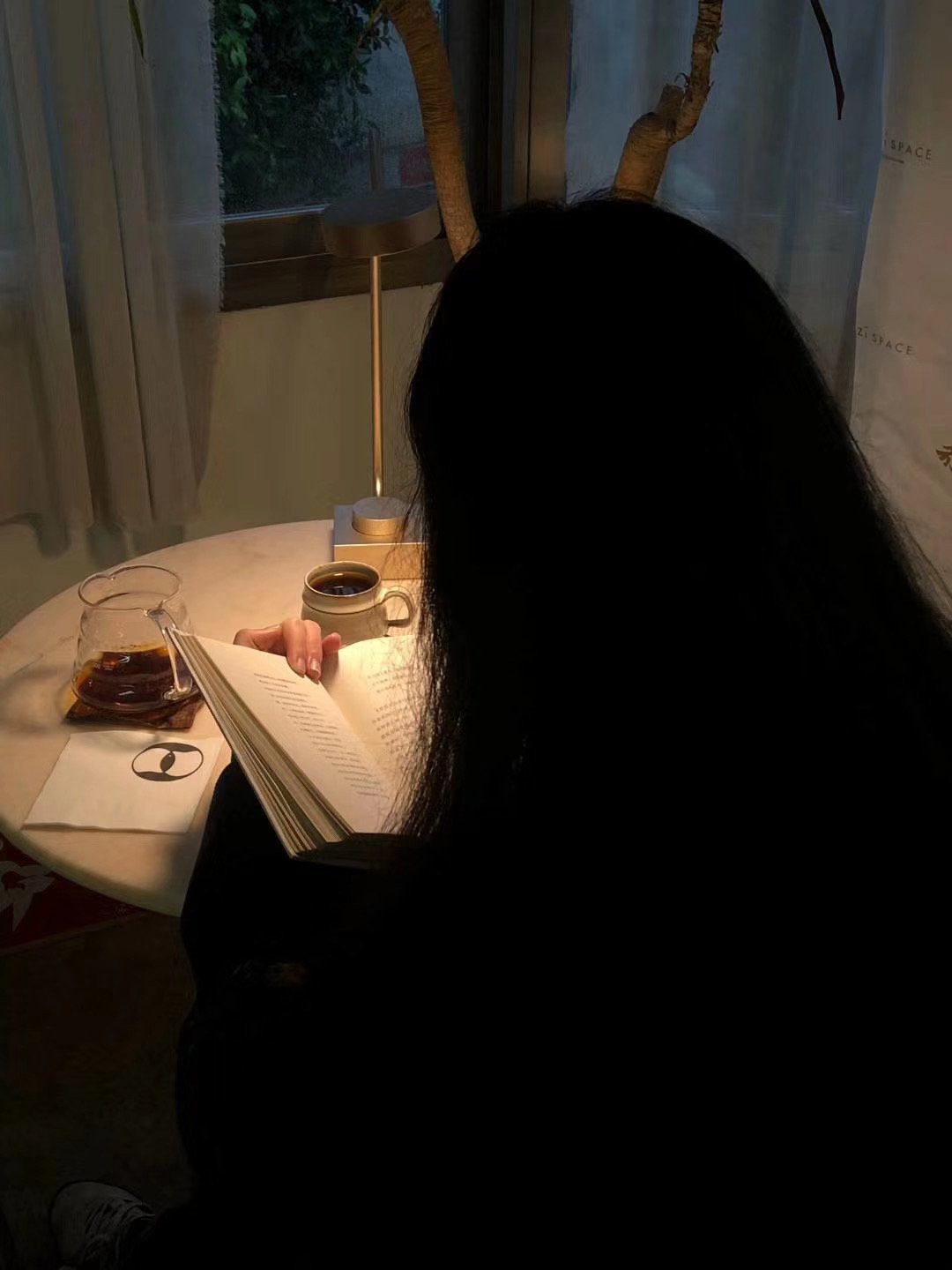七日书第四期|第六天-赤子空间和巴浪鱼咖啡
今天看来,巴浪鱼咖啡和赤子空间是我的第一个庇护所。
在从县城考进市区上学的六年青春期里,为了应付复杂的家庭状况,和因高压而裂变出最原始幽微的傲慢、妒忌与陷害的青春期社交,我似一根被来回拉扯的弹簧一般,并未彻底断裂,却松松垮垮地失去弹性。失去一切热情,机械一般地顶着偏头疼与胃疼写那些永远写不完的理科卷子,常常痛得睁不开眼睛,于是只得眯起一只眼,睁着另一只眼,继续写。胃病,有时甚至为此感到庆幸,至少疼痛限制我以去卫生间为借口,离开窄小的教室座位,在走廊到处走动拖延时间。然这于我而言并不足为道,我惧怕的是市区同学那包藏在礼貌下的嘲笑。各种莫名其妙的罪名,随着他们不堪承受的压力一起倾倒在我身上。
在这所掐走全市最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学,在造成了本市教育断层严重的超级中学,无处落脚。优渥的市区,我本是个没有家的人。于是,从早上七点持续到晚上十点半的在校时间里,屈辱不堪,只得长久地将头埋进王后雄与教材全解里。而晚上回家,我便要安慰刚到市区谋生,在工作上同样遭受霸凌与污蔑的父亲,分担他的孤独与辛劳。父亲睡下后,我接着掏出卷子,解那些还未解完的题,直至凌晨两三点,疲累地倒在床上,却常常睁眼到天亮,无论如何都睡不着。为了逃避家庭,我去往学校,又为了逃避丛林法则一样的青春期社交,我躲进家里,似在两个牢笼间往复,无宁日。便是在那时,为了支撑自己完成每天的任务,自残成瘾,并延续至今。在一夜无眠却仍该往早已处处断裂的大脑倾倒数理公式的早晨,我偷偷用美术刀熟练地滑开肚子与大腿的皮肤,随着血液流出而起床,穿好衣服盖住仍在渗血的伤口,一分钟喝完牛奶麦片,失魂地骑上电瓶车去学校。
住在学校附近的公寓楼,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听说同校的xx学生在小区里跳楼的消息。然后便是校方无休无止地封口、压消息,大家齐聚时喟叹一阵,便再也不愿谈论。我止不住想起那些从天台一跃而下的同学。压力大时,同学间流传着一些 “邱季端大楼,一跃解千愁” 之类的玩笑,我却无法笑出来,因为真的认真思考过是否要去那座以捐款人命名的办公楼自杀。
在某个周四的晚自习,我彻底崩溃,将试卷习题册胡乱塞进书包,扶墙走出校园。本想回家休息,却鬼使神差骑着电瓶车去往与家方向相反的市中心老城区,在当时还未成为旅游城市、排水系统乱七八糟的小巷里,带着无尽的委屈、怨怼、愤怒,以及自戕的强烈愿望,蟑螂一样乱窜。便是在那个晚上,我发现了承天巷深处的赤子空间与巴浪鱼咖啡。
赤子空间和巴浪鱼咖啡其实是同一家店,占据了一栋三层小楼。一楼的赤子空间售卖一些艺术摄影类独立出版物,也售卖店主阿梅自己淘来的衣物。二楼的巴浪鱼是一家咖啡馆。那年,承天巷还未被好好地修缮,周边也还未林立如今精致的小店,地面坑坑洼洼,常年积水,到了晚间,大多店门紧闭,往里走,便看到赤子空间亮着暖黄色的光。推门进去,顺着狭窄的木楼梯上二楼,楼梯左侧是吧台和一个木质书架,摆满了店主自选的书籍杂志。吧台后的柜子,摆着店主喜欢的一些唱片、cd、磁带。当时不知道,日后这些书籍与音乐会如何陪我走过低谷期。
店里装潢温馨之余不失其表达与活力。花盆里插着海边的植物,木麻黄,墙上挂着港口运来的船木,书架旁摆着一把有年头的理发椅。悄悄在角落的位子坐下,随手找了本杂志读。至今仍记得,是《联合文学》出版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25周年复刻纪念。当时每日为扭曲却无法宣之于口的家庭关系撕扯,又如无根浮萍般飘来飘去,因饮食失调造成的肥胖在学校受尽冷眼,我自卑、讨好、懦弱,把自己带入影片中的小明,感慨着无法逃脱这一切桎梏,无可奈何地成为一个被杀死的失德者,却完完全全自作自受,不配得到一丝同情。
后来,我常常逃课,骑车穿过长长的坪山隧道,躲进巴浪鱼咖啡,先是埋头读数理化教参,王后雄荣德基,写卷子,背琵琶行背行路难,将英语课本末页的单词仔细抄默数遍,然后进行那时我最喜欢的活动:站在书架前挑选当天的读物,偷出时间阅读。博尔赫斯、苏珊·桑塔格、帕蒂·史密斯,只知埋头做题的我谁也不认识,纯属乱读一气。某一天,偶然在书架上找到马世芳的《地下乡愁蓝调》,读得入迷,才知那段民歌历史,知道原来 “唱自己的歌” 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中学时,因为喜欢说闽南语,而被当时唯一的朋友不断讽刺为 “乡巴佬” 。那是 “做文明人,说普通话” 的最后几年,闽南语仍是上不得台面的乡下人语言。而后来,随着文旅的兴起,闽南语又被当时嘲笑我的市区同学当作自己的culture identity,想来真是讽刺。在这来之不易的阅读间隙,我第一次在店里听到交工乐队的《菊花夜行军》。后来,在无数被母亲入骨的羞辱刺激得夺门而出的日子里,我骑车听着《风神125》泪流满面。
现今, “县城文学” 已成为社交媒体上被浪漫化、奇观化、随意赏玩的文化符号,可在这一标签成文前,巴浪鱼咖啡与赤子空间便以其对县城、小镇、农村叙事的珍视和关怀,将我从青春期的慌乱里打捞起,安置认同。直至去年,与店主阿梅聊天时,我才知道他们那几年其实也过得艰难,在那个 “老土” 仍被唾弃的年代,他们却在坚持发掘属于边缘青年自己的叙事。那时,他们曾办过一些基于闽南村庄的小摄影展览,在其中一个展览上,我看到过一张展示葬礼上的二十四拜化着浓妆、骑在电瓶车上、载着孩子的照片。于是,被复杂的情感击中,这便是我记忆中的生活,却因羞耻而深埋心底,原来这些事情是值得被记录、被讲述的啊。
现在想想,赤子空间与巴浪鱼咖啡或许在无意中影响了我的志业选择。和友人讨论作为留学生和新移民的身份挣扎时,发现自己早已在成年前经历并完成了这一过程。在这北美洲的城市,我坐在一家波斯咖啡馆里敲下这些文字。如今,我已无需再四处躲藏,寻求避难所,我已拥有属于自己的叙事,不再畏惧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