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工人主义:技术,平台和工人挣扎的循环
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十年间,一些寻找能帮助理解当下劳工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起源于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工人主义(Workerism)重新产生了兴趣。同时,工人调查(Workers’ Inquiry)这一被工人主义用来理解阶级斗争的工具,也再次进入左翼的视线。多数派曾在工人和学生联盟主题下,详细介绍过意大利工人主义。受工人主义影响的刊物《自下而上的笔记》(Notes from Below),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去理解工作场所,再通过阶级构成(class composition)理论来解释调查后的结果,即:
“首先是将劳动力组织成工人阶级(技术构成);其次是工人阶级组织成一个阶级社会(社会构成);再者是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成为阶级斗争的力量(政治构成)。”
文章作者主张建立一种“数字工人主义” (digital workerism),将工人的观点和行动放在首位,从而对工作场所如何成为数字社会主义的斗争场所形成批判性的理解。只有在理解和支持工人的斗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赢得数字社会主义(digital socialism)。

文|Sai Englert, Jamie Woodcock and Callum Cant
翻译|丁冬
原文链接:Cant, C., Woodcock, J., & Englert, S. (2020). Digital Workerism: Technology, Platform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Workers’ Struggles.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18(1), 132-145. http://oro.open.ac.uk/70417/
零工经济和平台工作的快速增长为数字工人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落脚点。但很多时候研究的重点不是放在讨论阶级构成的新类型,而只是狭隘地关注技术和算法。现有关于Uber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讨论上,如算法监视和平台控制,包括数据的使用和客户的评级等。不可否认,这是理解平台工作不断变化的关键,但这些被视为总体控制的讨论存在着局限性,即它们几乎没有为工人提供竞争或瓦解这控制的可能性。但随着“工人调查”方法(The workers’ inquiry method)逐渐被利用于理解伦敦的零工经济发展,如Aslam和Woodcock就采用了这种共同写作的方法,通过与工人进行询问,将他/她们的劳动过程展开:为Uber开车的历史、如何组织的故事、以及与公司、监管机构和法院的斗争等,以了解工人在实践中的工作方式。
现在,我们将使用伦敦Uber的案例详细地讨论技术如何被利用来规训工人,同时技术如何以各种方式被工人重新利用。通过对平台上发生的技术、社会和政治重组的分析,我们将超越技术决定论,将各种技术放置在正出现的社会关系中加以分析。
首先,在伦敦,大多数汽车都是丰田普锐斯(Prius)混合动力汽车租赁,通过将驾驶员与特定汽车捆绑在一起,并利用每周高昂的车费支出,有效地限制了Uber司机较为便宜的选择。此外,Uber司机还必须持有由TfL(Transport for London)颁发的私人租赁执照。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司机唯有通过全职做Uber才能支付高昂的费用并以此谋生。这与美国部分地区可以允许驾驶员没有驾驶执照、可使用种类繁多的车辆,因此大部分人都是兼职做Uber司机的情况很不同。
另外,Uber司机的社会构成是由出租车行业内既定的关系所决定的,尤其是黑色出租车和小型出租车之间的两级区分。黑色出租车司机必须通过地理和路线的“知识”测试,并驾驶与众不同的黑色出租车;而小型出租车司机的进入门槛要低得多,他/她们不需要通过测试,但需要拥有私人租赁许可证。许多小型出租车司机都是从移民群体中招募。于是,Uber司机的种族组成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以白人为主体的黑色出租车司机和以移民为主体的小型出租车司机。在Uber成立时,它的目标是招募这些小型的出租车司机。这意味着,很多事先就已经存在的关系和网络,如移民组织和友缘团体等“无形的组织”(invisible organization)被嵌入到Uber司机这一更为正式的组织中。
伦敦的Uber有持续多年的斗争历史:从2013年的WhatsApp小组开始,Uber司机希望可以与平台相关负责人讨论为Uber工作的问题;到2014年,司机们开始组织会议,并成立了LPHADA (London Private Hire App Based Drivers Association);次年,司机们加入GMB工会(GMB,英国总工会Britain’s General Union,LPHADA被折叠),支持针对Uber的就业法庭案;后由于司机对GMB的方法不满意,另成立了一个名为UPHD(United Private Hire Drivers)的司机网络……在每个阶段,司机们都尝试过不同形式的组织(政治重组)以及将针对目标从Uber扩大到监管者和伦敦市长等。整个斗争过程也不断从网络上联络转移到线下罢工和抗议。Aslam提及到:“在我们刚开始组织司机时,所有人都说我们永远不会成功,包括我们原以为会站在我们这边的工会组织者、学者和记者”。因此,司机们必须要学习如何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成为组织者。这注定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从开始寻找方法到成功抵抗(平台的剥削)。最近,司机们开始进行国际间的联动以抗议Uber上市。政治重组正跨越国界。
Uber的案例分析所强调的,不仅是平台工作的技术重组是由资本主导的,同时,Uber还涵括了之前的工作类型、社会关系和组织架构。因此,它不仅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同时,它也被资本主义内部的现有压力所调节。虽然平台利用了假自雇的身份,但它依旧需要实际驾驶汽车的工人,而这将使得工人的主体性重新得到关注。

建立“数字工人主义”?
因此,透过对工人斗争新形式的关注,我们主张建立一种“数字工人主义”,对工作场所如何成为数字社会主义(digital socialism)斗争的关键场所形成批判性的理解。意大利工人主义者(Italian workerists)对工人自我活动及其政治主体性的关注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长期承诺。恩格斯在他对共产主义宣言的介绍中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工人阶级本身的行为”。在此过程中,他改写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和他俩联合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规则(General Rules)的干预方措施。这个基本思想是他们通过下层斗争和工人自发组织来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伟大愿景的基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使得我们从旧秩序中脱离出来的关键是确定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只有通过与资本及其代表的不断斗争才有实现的可能。尽管这种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传统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不幸的是,从列宁和卢森堡等开始,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以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主导,这两种方法都屈从于技术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而放弃了工人作为社会变革驱动力和通往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道路的可能。Draper将这些传统定义为“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因为他/她相信,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可以经由社会主义政府占领国家统治后,自上而下地实施。而这与始终强调与资本和国家对立的工人的斗争和自发组织,实现“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类似的问题依旧困难着今天的社会运动。无论是在欧洲兴起的自我宣称的社会主义选举项目还是乌托邦技术中心主义者兴起,当代激进主义者和理论家所提出的摆脱资本主义的路线都绕过了工人的自我组织、斗争和对生产的集体民主控制等关键。
UBER司机的挣扎与数字社会主义
从技术构成(工人阶级的形成)到政治构成(工人的自发组织)的飞跃一直是工人主义面对的挑战之一。在Uber的案例中,我们需要思考的便是如何从技术构成结合到政治领域中的构成。在讨论如何将Uber司机的挣扎斗争与数字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之前,对现有平台工人运动中的两种介入方法进行分析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借此可以看出在工人运动的传统中,工人的自主性并没有被重视。
第一种方法是理论结合实践,尝试以影响为导向的研究:公平工作基金会(Fairwork Foundation)。该项目的基本目标是通过认证流程改善平台工人的工作条件。公平工作项目的核心是在10分总分中,根据公平工作的五大原则(薪酬,条件,合同,治理和代表制)对平台进行评分(五项原则中的每项都有两分)。该项目在拒绝遵从平台将工人看作自雇人士的操作上取得初步的成功,同时并鼓励南非的一个平台同意建立工会。但这些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自愿参加,例如针对咖啡和巧克力等大宗商品的公平贸易认证持续瓦解,并且公司在决定退出时,从未将工人权利作为首要考虑事项。像其他认证方法一样,Fairwork也需要资金支援才能继续运营,并需要与已认证组织保持联系以获取数据等。在Fairwork中每一个持份者每年都可以通过得分来获得发言权(比如通过提高报酬获得1分),这意味着不仅工人,平台、学者、政策制定者等都有话事权,而不是将工人放在首位。
第二种方法是平台合作社或合作者。乍一看,平台合作社似乎是当代阶级斗争令人兴奋的捷径。毕竟,社会主义被认为是 “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生产资料不再是私有的,而是社区和合作地持有的。平台合作社或类似的说法很简单。出租车合作社不需要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而仅需要一个合作应用程序即可,因为驾驶员已经拥有了资本(以汽车和智能手机等形式)。这种论点被认为是技术解决方案和通向公平工作的捷径——甚至不需要与现有的资本主义企业发生冲突。平台合作社显然受到FLOSS(Free,Libr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自由,自由和开源软件)运动的影响,并受到一些技术决定论的支持者和自由主义乐观主义的影响。平台合作版Uber的问题在于出租车的实际成本比向用户宣传的价格要高得多,甚至比向驾驶员支付的价格还要高。鉴于伦敦对Uber战略部署的重要性,Uber已投入了大量的风险资本来作为补贴,以维持运营。所以说,尽管与Uber这样的公司相比,平台合作社在道德上占有优势,但因前者拥有高额的营销预算且庞大的用户群,并且充足的风险资本能够应对亏损以确保垄断(或接近垄断)的地位,也即掌握着成为恶性竞争对手的资源,除非监管机构或法律变更明确禁止资本的替代方法,不然平台合作社很难成功运营。

上述两种用于更公平工作的方法都是“自上而下”设计和实施的。他/她们从学者而不是工人那里汲取专业知识。如Draper解释,“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是通过统治精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馈赠到大众手上;“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则是强调“只有在斗争中,自下而上地动员群众,群众在运动中解放自我,用自己的双手去争取自由,作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实现”。与其陷入用“Uber for X”来构建数字社会主义的陷阱中,即平台模型可以且应该被应用到所有事物上,我们更应该自下而上地确定数字社会主义建立的位置、方法和条件。
卡勒姆(Callum)认为,自下而上实现数字社会主义的策略是进行“平台没收”。该策略假设,通过不断升级的政治斗争,实现资本所有权从老板到平台工人的转移,这将是防止市场竞争破坏不同形式工人合作运营平台的最佳方法。但如果仅有所有权转移,即仅仅转换成在工人的控制下进行商品生产,便只能算是在资本主义下的对所有权分配的一种奇怪的形式。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于对资本主义的去商品化。比方说,人们共享的Deliveroo的市场定位不再是为相对富裕的城市白领提供食物,而是透过积极的重组,设计出服务于集体的服务计划,以产生最大的社会使用价值。原被剥削的平台工人可以逐渐成为一个去商品化城市食物系统的共同生产者,而该系统的前提便是社会再生产关系和集体化的社会主义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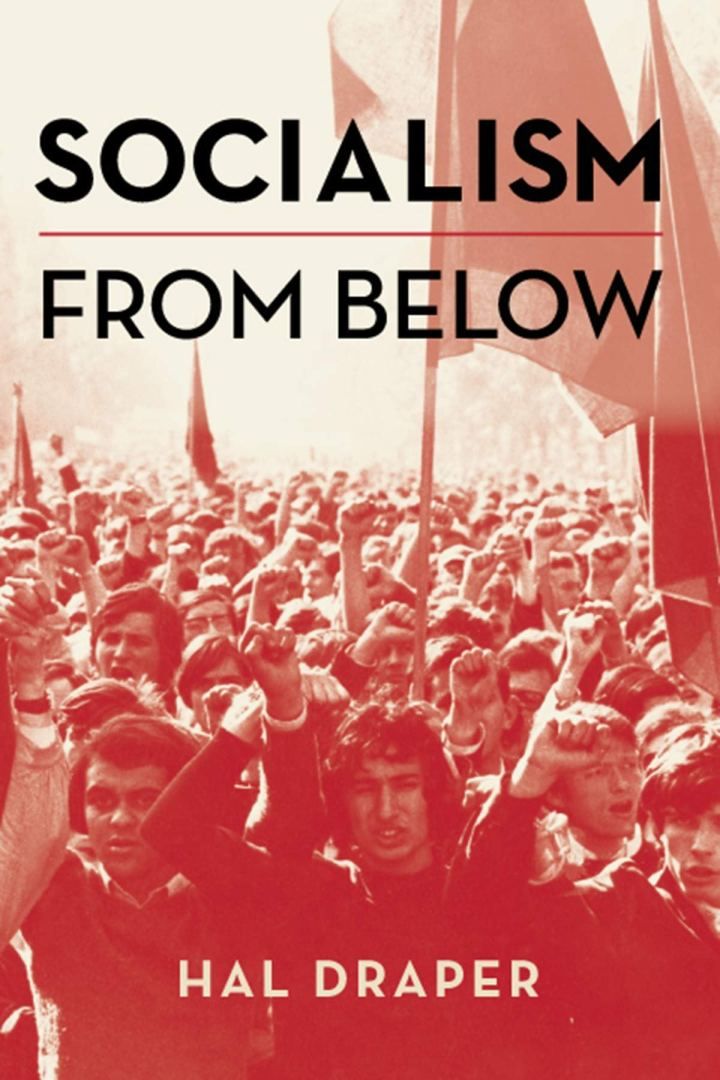
上述这些深远的变化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数字社会主义”才能赢得。随着工人在平台工作中的挣扎不断加深,以及跨国层面上的联系日益紧密,如伦敦、班加罗尔、圣保罗、开普敦和旧金山的Uber司机开始凝聚和开展抗争,未来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平台工人的抗争与反对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更广泛地联系起来。因此,数字工人主义不仅限于数字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析,更要涉及到平台工人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正如当年马克思从邮政调查表等传统方法入手,其目的不只是收集数据,更重要的是与工人建立联系,力图将研究过程作为组织工作的起点。同样,数字工人主义也可以从研究开始,但它必须涉及会议、纠察队、WhatsApp小组和Facebook的研究。它还必须将工人的观点和行动放在首位,支持平台工人的抗争。只有以此为基础,数字社会主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今天,社会主义常常被误会为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通过选举投票给某人来实现。毫无疑问,“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的确优于现有的数字资本主义,但如果我们想要赢得的未来,是一个将技术发展的成果从资本的需要中解放出来并由整个社会共享的未来,则需“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的力量来实现。无论工作是否以数字媒介为媒介,我们仍需坚守从工人主义出发,因为只有理解和支持工人斗争才是我们建立替代方案的关键。
关注我们:
Twitter:https://twitter.com/masses2020
Telegram:https://t.me/masses2020
Facebook:https://facebook.com/masses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