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前两天,小江过来问我:“你致谢写了啥,还记得不?”我回复道:“早他妈忘了,感谢了一下导师没怎么插手吧。”
一晃,竟是5年前的事了,模糊到我都不确认自己是否写过“致谢”这东西。只记得前一年,中文系刚摇身一变,成了文学与传媒学院。而我,向来鸡贼,自知写传统题目将遭老师“毒打”,便利用自己那时正好做自媒体账号的经验,起了一篇论文。况老师得知后,确没就内容过多插手,每一笔下去,深也好,浅也罢,都是自己的。3年后,我再用俄语写硕士论文,已没有致谢这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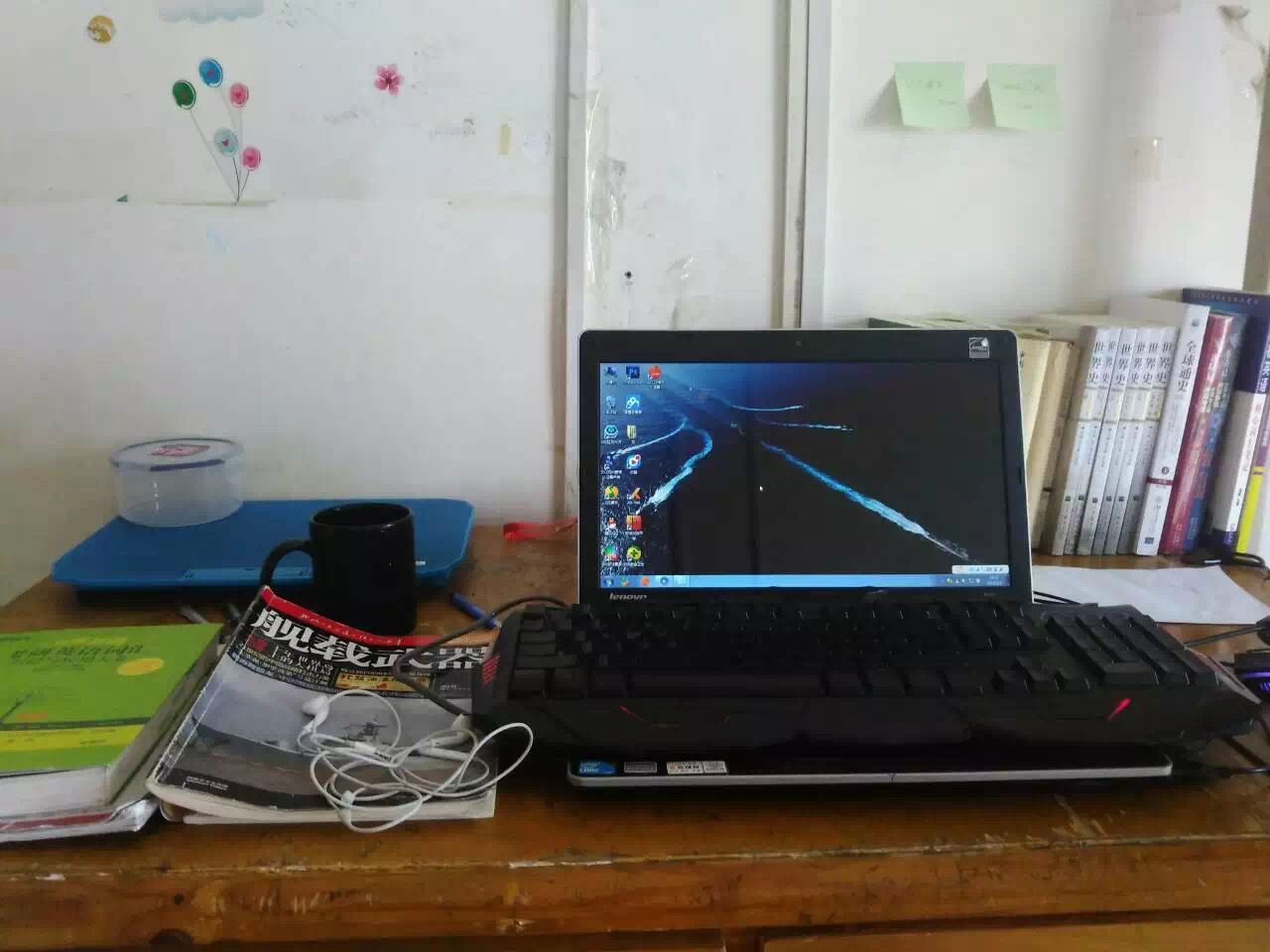
我应该是感谢过她的,而且真心。
昨天,薇刚刚离校,结束毕业旅行并回到家乡。夜里,和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四年里同室友一直友好、但有分寸,许也正因为这种界限而友好。临了的时候,突然有人提出吃个散伙饭,四人尽数出动。坐在那里,相互说了一些祝福的话,心有戚戚,不知所往。她给我细细复述那些熟悉的祝福语,难掩伤感,熟悉的话因真情而特别,回荡在沙沙的电流声中。
我说:“也还是有机会再见的。”
她沉吟了一下,复:“我们的关系,应该是不会见了。”
但又为什么那么伤感呢?大概这些话,站在此四年——而且是18到22岁而非70到74岁的四年——的末尾,有一种力量,穿透并带领四年中的所有他乡之路,艰难起飞,心有戚戚而不知所往。
于是我回忆起彼时的我。离校很早,5月中下旬的时候,419的兄弟一起在汉江边吃饭,心里暗暗知道这是散伙饭,但少有人明说。大家讲话突然变得特别诚恳、认真,侧耳听、娓娓讲,酒过三巡后又特别疯狂,什么玩笑都开,被开什么玩笑都笑,专注、豁达、神旺。我们没有说什么毕业祝福,但我记得路灯下都涨红了脸,老马走两步停下来,扶着路边的冬青哇哇地吐,抬起脸哈哈地笑。

我走那天,6月的第一天,时候很早,天光还在渐渐变浅。潇潇在靠近门口的下铺上熟睡,我键盘磕到桌子上时,他翻了个身。我看已经吵到了他,拖箱出门的时候低声告诉他:
“潇哥,那我走了哦。”
他半眯着眼睛,模糊但又急切地喊:“那我把你送一下么。”像是从睡梦里发出的声音。
我连忙俯身“嘘”了一声,说:“么事么事,你快睡你的,这么早呢。”
他轻轻地“嗯——”,似乎不舍又如释重负,复又开始有节奏的气息。
我满意离开。这就是我的离校。
我记得《士兵突击》里,老兵离开的时候都挑在清晨,静静地走,但宿舍里其它人其实在假寐,都在他开门的瞬间转过头来,他惊讶并释然一笑,摆手,让他们不要起身,并轻轻掩门离去,他们转头,枕巾上滴下泪水。我懂那种心情,那些节点经常是那样,日后被人认真问起来,沉沉地想,轻声说:“那真是平常的一天。”
重来一次,我也决不会让潇潇起身相送,这是我的习惯,一方面是男人羞于表达情感的顽疾,另一方面大概料定只有这样轻放才给足了自己日后回味的力量。正如扎加耶夫斯基用“学生毕业离去后学校里一次长长的间息”形容写诗,他是对的,我理解他。
我们再次回到致谢,这当然是强命题的写作,里面有我惯常厌恶并讥讽的客套、煽情,于是我漫待它,模糊它,戏谑它,复又回味回望它。我真是一个嬗变又自私的人,我用惯常地轻挑态度,让大多数人不在我跟前提及它,但又在四下无人的时候,独自回味、咂吧出许多味来,皆因心有戚戚,不知所往。
在不知所往的夜路上,我突然双脚驻地,刹车回望,我回望的,仅仅是“致谢”吗?哈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