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2 武汉是西风东渐之下中华帝国的孽子|余杰
野兽按:今天在油管上观看纪录片:中国解密:禁书时刻,里面采访了余杰。
于是想起了余杰的这篇书评。
余杰:武汉是西风东渐之下中华帝国的孽子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一七九六至一八九五)》

武汉的苦难与反抗
从清末到民国一直到毛泽东时代,在经济规模和工业化程度上,武汉在中国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心城市。二十世纪末中国搭上全球化顺风车,东南和华南的经济和国际贸易崛起,武汉才逐渐失去“中国次子”的地位和“九省通衢”的光环。
二零二零年初,武汉肺炎肆虐全球,又让武汉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为全世界瞩目。台湾历史学者陈弱水在脸书上发文说:“武汉处于长江和汉江(汉水)的交口,是由武昌(古名江夏)、汉口、汉阳三个城市所组成的,在世界上,这样的‘三子城’,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一定非常稀罕。而且,这三个城市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段都曾扮演重要的角色。作为中国史的研究者,我对这样一个大都会蒙此命运,还是有着特殊的感受。”
武汉被封城,近千万人宛如监狱中的囚徒,在武汉的历史上没有过,在世界史上除了战争期间被围城的华沙、斯大林格勒、长春以及几乎被原子弹抹去的广岛和长崎以外,和平时代绝无仅有。武汉女作家方方在日记中写道:“武汉人好难,先度过了初期的紧张和恐慌阶段,紧跟着,是史上未有过的悲愤、痛苦和无助的日子。及至今天,虽然不再恐慌,也没那么多悲愤,但是人们迎来的却是难言的郁闷和焦躁,是遥遥无期的等待。”那些此前沉迷在“岁月静好”之中的大人们未必无辜,孩子却是无辜的,方方说:“最惨的是那个爷爷去世几日,自己不敢出门,说是外面有病毒,靠着吃饼干过了几天的孩子。还有,更多更多,关在家里不能出门的小孩,你能想得到大人是怎么吓唬他们的。病毒!病毒!病毒在他们心里,必然是魔鬼般的存在。我不知道,当有一天,他们可以出门时,他们中会不会有人不敢出来;更不知道这道阴影,会在他们的心里留存多久。这些弱小者从未对这个世界犯过任何错误,他们却要陪着所有大人承受这个苦难。”

2020年3月10日,习近平在武汉市火神山医院指挥中心通过远程会诊平台,同正在病区工作的医务人员代表视频连线。(法新社)
习近平一直不敢踏入武汉一步,大概他知道这座城市民风彪悍,即便天不怕、地不怕的毛泽东也险些在此马前失蹄。一九六七年夏,毛泽东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来到武汉,试图解决当地造反派与保守派对峙的僵局。谁知,七月二十日,由军方和公检法部门支持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涌入东湖宾馆,突破保卫线,绑架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将其带到武汉军区大院批斗。反叛民众离毛泽东居住的房间仅数十米之遥。毛泽东仓皇撤离武汉,周恩来不得不化装进入与离开市区。两天后,周恩来在中央讲话说:“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武汉简直成了“敌占区”。多年后,“百万雄师”一号人物俞文斌坚持说:「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有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许久不敢视察武汉疫区,就是害怕重蹈毛泽东之覆辙——“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又当如何?所以,习近平在武汉肺炎爆发两个多月后才君临武汉,武汉的方舱医院全部关闭,数以万计的患者被转移,习近平所经过的住宅社区,每户人家的阳台上都有两名全副武装的安全人员入驻,比希特勒视察德国占领的巴黎还要紧张。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中写道:“大概是明末的王思行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句话也可移用到武汉身上:武汉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受够了中共之谎言与暴政的武汉人,或在沉默中灭亡,或在沉默中爆发。武汉这座城市,原本就是西风东渐之下诞生的中华帝国的“孽子”。美国学者罗威廉在《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一书中,以武汉三镇中最西化的汉口为主人公,为之作了一部绝无仅有的传记。深受武汉肺炎所苦的武汉人,所有心系武汉安危的人们,此时此刻,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
管理这座城市的不是官府,而是“公共”部门
集中研究专制权力如何支配社会这一问题的学者历史刘泽华指出,中国城市的发展道路与欧洲城市完全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是工商业中心,是相对独立于国王、领主直接控制之外的自由市。中国的城市则不是独立、自治的团体,而是帝国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先秦到明清时代,不论是中央的首都,还是四方的州府,首先都是统治者的驻在地;交织在整个统治机构之中的全国上下每一个郡城和县城,都是帝国秩序的一部分,都是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单位。中国古代城市的性质,主要是政治的、军事的,其次才是经济贸易的。
清朝晚期,依清政府与外国政府缔结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汉口被辟为长江沿岸最早的三个通商口岸(镇江、九江、汉口)之一。汉口开埠虽略晚于“五口通商”(南京、上海、厦门、宁波、福州),却后来居上,贸易量很快超过传统国际贸易商埠广州,而仅次于上海。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英、德、俄、法、日等五个国家先后在汉口开辟租界,使得汉口外国租界的数目在通商口岸中仅次于天津。十余个国家均选择汉口作为在中国中西部省份开设领事馆的首选地,驻汉口的外国领事馆的辖区包括中西部的八、九个省份,占中国本部十八行省的将近半数。至二十世纪初,汉口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超大型城市,被称为「东方芝加哥」。
外国人的到来和西方思想的进入,为城市建设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罗威廉发现,城市工商阶层的兴起和外国人的示范,使城市自治的观念出现。比如,英租界沿江一带的杰出建筑给中国商人留下深刻印象,使他们于一八七六年促成了一次迟到的街区整修。他们采取了一种策略,即请求代理汉江关税务司的美国人拉伯利(Rubery)帮忙,拉伯利很高兴地承担起这项使命,设计了一份蓝图,建议将街道垫高在洪水线之上,用石头铺设路面,挖掘排水沟,并用煤油灯作照明。按照拉伯利的建议,中国商人转而去恳求美国领事在发起募捐与获取中国地方官府的批准方面给予帮助。美国副领事将此事照会汉口道李道台。李虽然拒绝用政府的钱维修街道,但为了表示善意,提供了一百两的个人捐款,以此带动地方士绅和商人捐款。这项工程在四个月内就完成了,得到广泛的赞扬。
在外国人的影响力增强、新型绅商地位崛起的同时,朝廷对汉口这样的新兴城市的管理和控制却在削弱,一升一降,对照明显。罗威廉写道:“在清代大部分时间里,城市的重要建设,与社会福利一样,并非国家直接积极主动介入的事务;在很大程度上,这应当归因于国家机器特别是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日益衰弱与困乏。其结果是公共建设工程一般严重不足,其建设与维修只能留给地方菁英零零散散地去做。这样,就使得社会上对城市基础建设的热情越来越高。主动创议的大部分来自地方社区——来自‘公共’部门,而不是‘官方’部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的不作为,反倒为民间的大有作为提供了空间和机会。
当然,中国长久形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观念并未崩解,朝廷也非彻底退出城市、让城市自行发展。罗威廉指出:“地方官府放弃了大部分地方活动的主动权,将它们交给地方社会自身,但它仍保留了对这些活动的监督权,在一定范围内提供城市社会活动本身无法提供的协调与统筹。”可是,随着城市日渐自成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城市需要朝廷的时刻迅速减少。“随着这些社会服务功能或明或暗地不断归入非官方的‘公共领域’之中,清政府越来越显得无足轻重了。”因此,城市市民不再对朝廷顶礼膜拜。
城市市民的身份认同,高于帝国臣民的身份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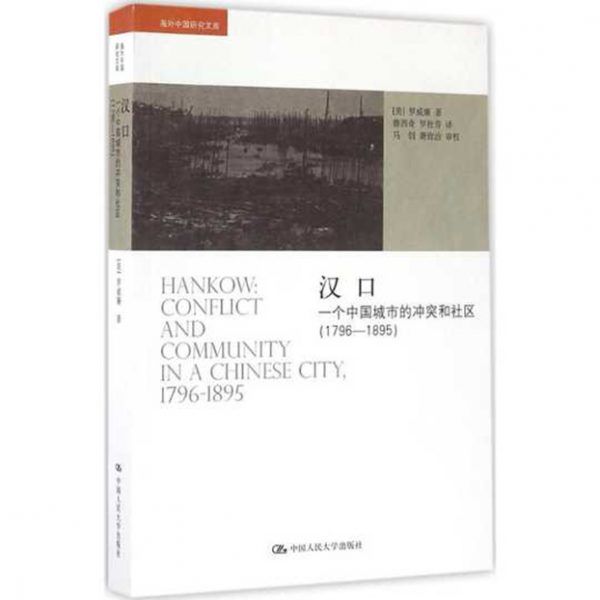
中国人不是没有自治的能力,而是长期被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所奴役、所凌虐,被剥夺了自治的能力。久而久之,就对“自愿为奴”的状态甘之如饴。但是,一旦有“出头天”的机会,中国人也会跟欧美人一样拥抱自由、追求独立,像石头缝隙中的小草一样顽强地向上生长。
汉口的发展和城市市民新身份的认同就是如此。当汉口居民发现,原来自己的城市可以自己建设和治理,他们便全身心投入其中,正如罗威廉所说:“与现代早期的欧洲城市相比,汉口的公共建设更注重实用(其规划目的就是增强汉口作为经济单元的功能),甚至是更民主化(工程项目通常要得到街区居民联合会的同意,并由他们提供经费支持)。这里可能存在着这样一个原因,即汉口能够比较好地维持一种公共舆论环境。”这种公共舆论环境的萌芽,从晚明就出现了。台湾历史学者巫仁恕在《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一书中指出,明代中叶以后,印刷技术的进步带动了出版事业及新闻传播工具的多元化,城市的通俗信仰也盛行起来。这不只是代表了城市文化的进步,而且对明清的城市集体行动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零二零年春,在瘟疫的阴影下,一首名为《武汉伢》的歌曲让人动容,有几句歌词这样说:“热干面糊汤,一样的吃相。海角天涯,流淌唇齿香。汉路的雨,淋过你几回。二厂汽水,换成了酒杯。只准自己骂,只许别人夸。这是我的家,在这里长大。”正是这种共同的经验与记忆,锻造出比国族身份认同更真实、更鲜活的市民身份认同,这种在地身份认同成为民国初年地方自治政治实践的前提。罗威廉从史料中发现,从清末开始,“里人”、“街市人”、“镇人”等词语就出现了,汉口有特殊的地方性度量衡,可以明确区分的汉口方言,以及大量的方言词汇,还有自建的城墙,这一切都进一步强化、巩固了社区和城市的认同感,尽管还不足以形成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即便在张之洞这位能臣担任湖广总督、大兴土木且加强政府对社会控制的时代,汉口的城市社区仍在循序渐进地建立机构(并非是预先设计的),并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行会联盟、善堂与消防网络、‘冬防’以及一八八三年的城市团练等组织与工作项目越来越制度化和系统化。”尽管儒家的影响还在,汉口却形成了灵活圆融、兼容并包的社会共识,汉口独特的都会性强化了这种共识,使它成为包括几乎全部人口(不管他来自何方,在汉口居住了多久,也不管他的职业与经济阶层)的共同理念——鸦片贩子、妓院老鸨和传统文人,打短工的、乞丐和富甲一方的商人、店铺老板,都会认同这些社会共识。这种情形符合哈耶克强调的“市场经济”和“自发秩序”原理。
“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是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来的。哈贝马斯认为,近代的公共领域源自十七世纪的英国,于十八至十九世纪传到法国与德国等地,具体的例子是国家与政府以外的俱乐部、咖啡厅、文化沙龙与文学期刊等场域。在“公共领域”之中,人们可以不分彼此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地位(包括性别、阶级),平等地就大家都关注的议题讨论,当中不涉及利益考虑。正是在“公共领域”之中,人实践了自由、平等与团结等价值。用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说法,在近代化过程中,“公”这个词逐渐远离“官方”的内涵,转变为更接近“集体”或“社会”的内涵。在此意义上,汉口拥有了自己的“公共领域”——如茶馆、庙会、龙舟赛、善堂、会馆、书院等。没有朝廷的地方,就是生机勃勃的地方。
武昌起义的枪声,既是偶然,又是必然
具有现代意识的城市,从来就被专制统治者视为“眼中的梁木”。历史学者巫仁恕认为,明代后期以降,城市内的社会结构随着城市化以及社会分工的需要而渐趋多元化。城市社会出现了复杂的阶层分化,新兴的城市社团组织也随之而生。这些城市社团组织并不受朝廷的掌控。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汉口这个“水路码头”城市的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差异,社会关系极度紧张,人们的怨愤日积月累,逐渐增加,暴力成了家常便饭。“暴力倾向几乎是出自每个人的天性,个人间的冲突甚至影响了直系亲属之间关系的和谐。”汉口、重庆、长沙这些长江边的城市都有此种特点,汉口尤甚。不同利益取向的群体形成了自己的社团和组织,彼此争夺资源和权力。
武昌起义之前三十多年,武汉发生过多次反叛,主要是由秘密宗教组织和会党推动。比如,一八八三年,发生了白莲教起义,白莲教是信奉千禧年主义的佛教的异端分支。汉口传教士戴维·希尔在写给伦敦总会的信中描述说:“目前,中国的这个心脏正处在巨大的动荡之中……一场从这个城市发动的、可能会广泛蔓延的反政府起义,虽因密谋泄露,而在千钧一发之际得以消弭,但却在全省引发了巨大震荡……他们明确表示要推翻现存的清王朝。……按其常规揣测,一定还会爆发。”一八九一年,汉口再一次成为反清运动的神经中枢,更世俗化的、以民族主义为第一要旨的哥老会充当了反叛的主力。
一位汉口海关工作的外国官员曾试图解释汉口何以会在辛亥革命中采取那种令人吃惊的反清立场。他认为,原因在于,事实上,“汉口的人口构成中,本地人还没有来自附近或遥远故乡、得到允许在本城居住的人多。汉口居民既多种多样,又一直不断发展;他们理所当然地经常对抗政府,因为官府往往阻碍他们的发展。”也就是说,市民身份跟帝国统治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了。
清廷靠传统的军事力量很难处理汉口这样的新兴城市的叛乱,它被迫采取新的动员方式,而在罗威廉看来,这种新的动员方式本身就是一场豪赌。首先,这种社会负责的公共安全机构的创立,以及在此之前就高度制度化与系统化的公益与福利事业,使汉口在外形和实质上都形成了高度的城市自治。并非官衙的沈家庙看起来像是自治城市的“市政厅”。更重要的是,同意城市精英掌握准军事力量,不仅要冒激化阶级矛盾的危险,还把王朝的安危交给了对朝廷并不忠诚的城市菁英们手上。一八九一年,代表商团的汉口“八大行”的商董们得到地方官府授权,筹集一笔资金,创立一支有一百艘船的水师,让其巡逻汉口及其周围地区的水道。后来,消防队改为保安队,成为一支常备武装,并入城市公共安全系统。罗威廉在此敏锐地指出,接下来,“反叛者的反满和社会革命意识,与其菁英对手的社会基础和组织能力,两者之间发生新的交汇融合。这种交汇融合一旦发生,清王朝这个老朽政权,就成孤家寡人了”。
于是,革命从城市爆发了。湖北的新军、哥老会、立宪派士绅、地方商会、城市警察、团练等各种力量都因反朝廷而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拉枯摧朽的力量。当武昌的枪响起,王朝很快就覆灭了。
来源: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