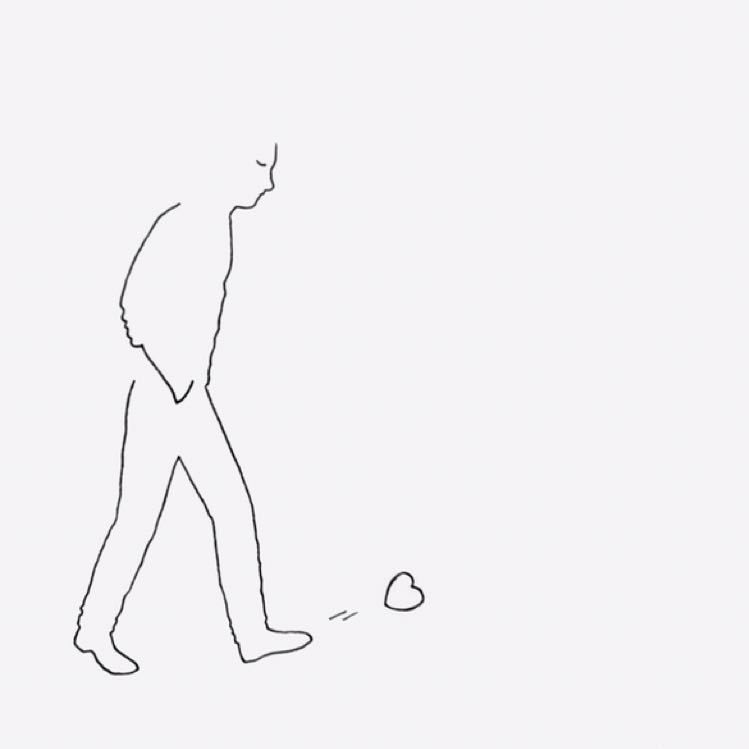从深井到灯笼 ——《大红灯笼高高掛》改编过程中女性意识的消隐
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发表於1989年,对于苏童而言,《妻妾成群》绝不仅仅是一个“旧时代女性故事”,或“一夫多妻的故事”,而是一个有关“痛苦和恐惧”的故事。痛苦和恐惧,自然是源自《妻妾成群》中“像狗、像猫、像金鱼、像老鼠,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的女人们,而这一女性意识,自始至终贯穿於整部小说。1991年,张艺谋将其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掛》,并在角色、意象、情节等方面有所创造。颂莲女学生身分的淡化、从深井到灯笼的意象变化,皆削弱了《妻妾成群》中的女性意识,并增强了影像中的男性凝视。
一、颂莲形象的转变:从女学生到小妾
在《妻妾成群》中,颂莲以留着“齐耳的短发”的女学生形象出场,一度被下人们误认为“在北平读书的大小姐”。而在电影中,颂莲扎著两束麻花辫,从角色形象上已然失去了“短发”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进步意涵。作为一名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小说中的颂莲在旧式封建家庭中始终保持著格格不入的疏离感,有別於封建伦理的新思想也影响了她的语言、行动与选择。但在电影中,颂莲的学生身分成为了空洞的符号,只存在于视觉形象与人物的语言之中。
小说中颂莲身为女学生的女性主体意识,在与陈佐千的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面对陈佐千这一父权家庭权力掌控者,颂莲始终试图在反抗中保持自己自尊,也在一次次行动与选择中逐渐确认自我位置。二人初次见面时,颂莲将地点定在“西餐社”,并在陈佐千面前提前度过自己的十九岁生日。在封建社会中,女子十五至二十岁可行笄礼,《仪礼·士婚礼》记载:“女子许嫁,笄而礼之,称字。”及笄之年的生日是女性社会化过程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笄礼后,女性便可婚配,并通过婚姻步入作为父权机器的家庭,在父权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此处颂莲过生日举动,则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体意识。对她来说,这一次提前过的生日,意味着“十九岁过完了”,也意味着她对从前作为女儿/女学生身分的告別与悼念。面对颂莲的这一举动,陈佐千则感觉“颂莲的话里有回味之处”“颂莲身上某种微妙而迷人的力量”。颂莲的女性主体意识,也体现在对自我情慾的肯认与探索中。初次见面,陈佐千便看见了颂莲身上的“销魂种种”,颂莲在性关系中的“热情与机敏”也令他著迷。在封建社会的婚姻关系中,女性的性欲望往往隐而不现,甚至被视作不洁。但在小说中,颂莲的欲望被明白地叙述与揭露。“从高处往一个黑暗的深谷坠落,疼痛、晕眩伴随着轻松的感觉”是颂莲女性欲望的初次显露,她对自己的欲望并未抗拒或压抑,而是选择探索与追寻,她“每逢阴雨天就会想念床笫之事”甚至让陈佐千有点“招架不住的窘态”。颂莲的女性主体意识,在陈佐千试图将其的主体性抹煞之时,成为了“痛苦与恐惧”的根源。在陈佐千壽宴上献吻被拒,和被陈佐千要求用特殊方式释放其性慾,使颂莲彻底认清了女性在这一封建家庭中非人的位置。一边反抗,一边悲哀地认识到无法反抗,正是在这一不可调解的矛盾中,颂莲走向了最后的疯狂。
而电影中的颂莲,则失去了对自我主体的肯认,不再是小说中清醒的女学生,而彻底成为了封建婚姻中小妾这一角色。在面对“灯笼”“锤脚”等赤裸裸的父权欲望时,颂莲并没有关于自我主体的反思,其所表现出的毫不在意的态度,在其举动的映衬下,也成为了流於表面的虚伪。小说中的颂莲,对陈家众人始终保持著若即若离的距离,时而对其他女性之间的权力斗争冷眼旁观。而电影中的颂莲则彻底投入了家庭权力的争夺之中,不仅设计了假怀孕的戏码,在面对其他三位太太和丫鬟雁儿时,甚至不时表露出趾高气扬、小人得志的蛮横之姿。在小说中,颂莲因发现雁儿对自己的诅咒而逼迫其吞下草纸,最终导致了雁儿的死亡。而电影中颂莲则在众人面前扯下雁儿房里的红灯笼,并要求大太太对其进行处置,因为雁儿“坏了规矩”,而“太太就是太太,丫鬟就是丫鬟”。她不仅彻底认同了封建家庭中的父权逻辑,并且试图运用这一权力逻辑来维护自身的地位。此时的颂莲已然失去了作为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而被权力结构所同化,成为了旧式家庭中最典型的小妾形象。
二、符号与意象的变迁:从深井到灯笼
在《妻妾成群》中,最令人瞩目的意象便是院子里的那口深井。井从一开始的神秘、奇怪逐渐显露出阴郁、可怖,也象征者封建家庭撕下虚伪的伦理道德,而展现出残忍、血腥的一面。《大红灯笼高高掛》则以小说中极少出现的红灯笼作为主要符号,同时设计了“点灯”、“灭灯”、“封灯”等伪民俗,灯笼成为陈家权力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就连女仆雁儿也在自己的房间偷偷掛起了红灯笼。
封建家庭中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以及在这一阴影之下女人的痛苦与死亡是小说与电影共同的主题,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选择用更多的笔墨展现女人的痛苦与死亡,而电影则着重不同人物在权力斗争下的表现。小说中处理偷情女人的“死人井”,在电影中则改为一间吊死女人的“死人屋”。电影对死人屋的直接展现只有两处镜头,而在空间上,死人屋的位置高于陈家日常生活区域,同时也意味着它与日常生活的隔离。然而小说中的深井位于陈家院子中,与日常生活区域不可割裂,颂莲与梅珊也曾坐在井边谈话。深井这一符号所象征的死亡与恐惧的在小说文本中占据重要地位,陈家内部的权力流动则隐藏在人物的行动与言语背后。电影则通过点灯、灭灯、封灯,包括多个镜头的重点描绘,将权力的变化暴露无遗。每天入夜前各房太太站在院子门口等待点灯的场景,简单而明了地揭露了人物之间权力关系的分配。
弗洛伊德曾认为,女人是一块“黑暗的大陆”,这一观点多次被女性主义者诟病其性別盲视,然而这也从另一侧面揭露出了女性的处境:被压抑、被忽视、从未被了解。陈家院子中的那口幽深而不可测的井,也象征著这个封建家庭中的女人。她们是不可言说的禁忌之物,“陈家上下忌讳这些事,大家都守口如瓶”,死去的女人是不能提的,她们无法拥有自己的身分,也无法拥有自己的话语,一如一眼望不到底的黑暗的水井。然而,尽管这口废井被视作禁忌,颂莲始终被它所吸引,并时刻感受到井以及井中死去的女人与自己的联系。井中的亡灵呼唤她“颂莲,你下来”,井中死去的女人就象征著她自己,“井里泛出冰冷的瘴气,湮没了她的灵魂和肌肤”,她已然被那口井湮没,成为井中死去的女人,“我走到那口井边,一眼就看见两个女人浮在井底里,一个像我,另一个还是像我”。显然,这是在封建父权家庭逻辑中缺失的女性意识与经验。从初次踏入陈家,到最后的精神失常,颂莲始终被深井所吸引、呼唤,她的生活与命运乃是围绕这口井,围绕那些自始至终存在而又缺席的死去的女人,而这便是《妻妾成群》中贯穿始终的女性经验与话语的体现。
而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掛》中,张艺谋将红灯笼作为最主要的视觉符号,其颜色与意涵都极具冲击力,成为贯穿电影文本的重要象征。伊希伽黑指出,阳刚欲望透过视觉隐喻表达自己,视觉在所有感官中最能产生距离感,也因而得以达成主体与客体的分离。红灯笼在电影中象征著陈家的权力,谁点了灯,谁就可以点菜,只要多点几次灯,“在陈家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然而这一权力必须通过陈佐千的性欲望给予,女性在此成为了承载男性欲望的客体,不再拥有女性主体的自我意识。在父权逻辑的运作下,女性不再是女性,而成为了一个个社会角色: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四太太。四人之间的互动也几乎成为封建家庭结构的展现,即藉助陈佐千的权力来提升自己家庭内部的地位。连陈佐千自己也不可避免地被结构裹挟,被颂莲的假怀孕所欺骗。红灯笼作为父权家庭中权力的象征在视觉上是暴力且赤裸的,点灯时的红色在电影阴沉的画面中尤为突出,给观众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如在颂莲宣称自己怀孕后四院点起的长明灯,用明亮的大红色几乎占据了全部画面。而象征著颂莲被剥夺家庭权力竞争机会的封灯,则通过黑色的灯笼套来加深画面色彩,与点灯时的明亮形成鲜明对比。相较之下,《妻妾成群》中对深井的描写则运用了多种知觉,如视觉“井水是蓝黑色的,水面上也浮着陈年的落叶,颂莲看见自己的脸在水中闪烁不定”,听觉“听见自己的喘息声被吸入井中放大了”“那口井仍然向她隐晦地呼唤著”,触觉“颂莲这时感到一种坚硬的凉意、像石头一样慢慢敲她的身体”“井里泛出冰冷的瘴气,湮没了她的灵魂和肌肤”。通过运用多种知觉,小说文本通过对读者感受的召唤,邀请其进入故事中女性的经验。但在电影中,具有冲击性的视觉符号将观众与人物拉开距离,令故事与人物完全成为被观看的对象。情节上,除了颂莲与梅珊几处对话外,女性的经验与话语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被赤裸裸视觉化的父权逻辑,以及女性角色在这一逻辑中的同化。
三、结语
作为苏童的代表作品,《妻妾成群》中对不同女性角色,尤其是女主角颂莲的刻画,向来得到较高的评价。通过对人物经验的描绘,以及种种象征意象的运用,《妻妾成群》所揭露的,是封建社会父权家庭中隐而不现的女性话语。对于苏童来说,“小说人物首先是人、是人物,其次才有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通过对女性作为人之主体性的肯认,《妻妾成群》中的女性意识才会如此真实并具有独特意义。
在《大红灯笼高高掛》对原作的改编过程中,张艺谋对电影美学的追求压过了原作中女性意识的展现,阴森的北方大院与鲜艷明亮的红灯笼,通过冷暖色调的强烈对比,带给观众极强的视觉冲击,充分发挥了电影艺术的视觉性。但电影文本的变造,使得原作中无处不在地女性意识消失在种种视觉符号后,女主角颂莲人物形象也由复杂趋向简单,可谓是一大遗憾。
《华语电影与文学》课程论文
写于2019/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