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在地獄就無法感覺天堂的蒼白(四之四及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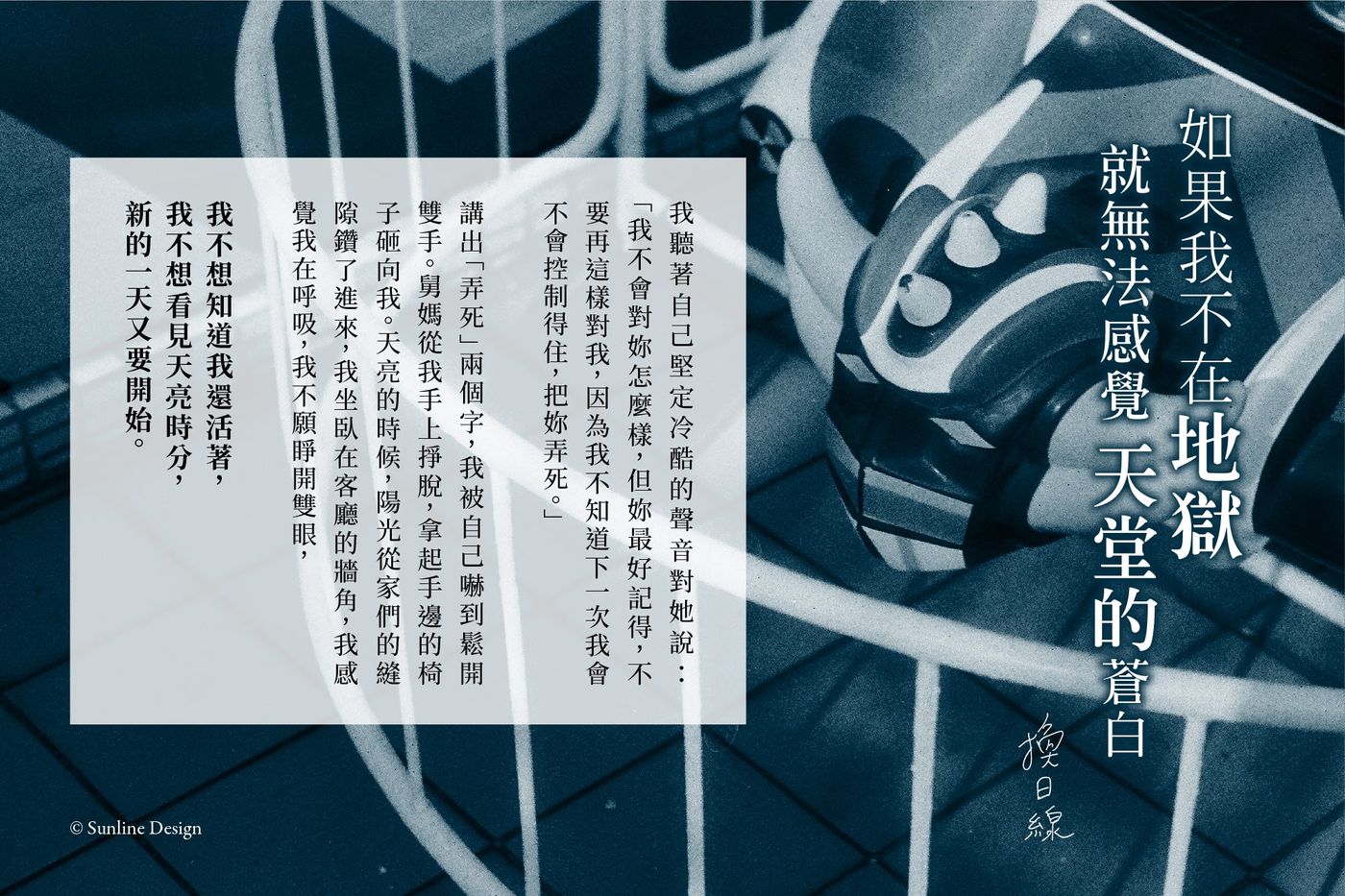
「男男,媽媽說她找到爸爸了。」阿虎走後,姊姊走進病房對著我說。
明明是正中午的時間,從病房看出窗外,竟已是一片陰暗。病房裡的光線也有點微弱,我沒帶眼鏡,看不太清楚姊姊的表情。她的語氣是高興的?期待的嗎?
我撐坐起身問姊姊:「那他會來嗎?」
姊姊掀起我的被子,看著我腳上的傷口,喃喃地說:「應該會來吧!你先專心養傷啊,把傷養好,不然爸爸來看到,會很難過的。」
我滿足的點點頭。窗外的黑影裡一道光閃過,雷聲伴著大雨滂沱而下,我戴起眼鏡,望著窗外的雨。
*
一樣是閃電、雷聲、大雨的中午,我站在姊姊的教室外和小符僵持著。姊姊的同學、我的同學將我和小符圍在一個圈圈裡,像拳擊擂台那樣,看誰可以撂倒誰。
姊姊班上有幾個男同學起鬨,叫囂著:「小符衝啊,把男男打敗啊!看他會不會哭。」阿虎沒作聲的在一旁看著這場擂台開打。
小符殺紅著眼拿著手中的掃把朝我步步逼進。我的手掌心在冒汗、我的眼淚已經漲滿眼眶。我沒有哭。我只是努力地握著拳頭,讓指甲戳進掌心,好忍住眼淚。
「男男,你在這裡做什麼?」姊姊的聲音從人群的一端傳來。
小符往後退了幾步,阿虎往場邊姊姊的方向看過去,那幾個起鬨的男同學和場邊所有的人都安靜了下來。我鬆開拳頭,心想終於得到解救,可以鬆一口氣。
我帶著發抖的聲音說:「小符他⋯⋯他說爸爸不要我們了,他一直笑一直笑,笑著說要來問妳,我好生氣就追上來⋯⋯」我忍不住眼淚,我哭出來了。
原來跟小符一夥的那些人,開始像在巷口那樣笑我大叫:「男男是女生」、「男男愛哭鬼」、「男男愛爸爸」,那些聲響越來越大,越來越大,我的眼淚越掉越快,越掉越快。
直到姊姊搶過小符手上的掃把,我以為一切都可以停止了。但她卻朝我身上打來,我的眼淚停住了,身邊所有的聲音、吵鬧也全部靜止了。
姊姊揮動著掃把說:「不是叫你安分點,講不聽、講不聽」掃把重重的朝我揮過來,我沒有閃。她的手完全沒有停下來的意思,不停揮動著自己手中的掃把,繼續說:「講不聽,叫你不要鬧事,你講不聽,爸爸不在了要講幾次,不要哭、不准哭,聽不懂是不是?」
姊姊瘋狂地不知道揮打了幾下,我閉著眼感覺她的憤怒和悲傷和身上的痛。我希望如果可以,她就把我這樣打死,我不會再看見天明的景色。
*
「媽,姊姊說妳找到爸爸了,是真的嗎?」在我醒來看著母親走進病房的進進出出後,我終於決定問她這個問題。
母親放下手中大包小包的東西,摸摸我的頭說:「今天頭還會不會痛?」眼睛散發著我好久沒有見到的溫暖。
「舅媽說舅舅以前有一個同事,現在跟爸爸在同一間公司。前幾天遇到才聊起來的。」
「那他會來嗎?」我急著問。
「媽媽會去幫你找他來的。你不要擔心。好好養病。」
我開心的笑著點點頭說:「謝謝媽。」
我的頭有點痛,不知道為什麼出了個車禍,世界就變得美好了起來,心裡還想著:「那不,怎麼不早點出車禍呢?」
*
那天夜裡雨也這樣伴著雷電下著,我沒有被喝醉酒的舅媽打死。但我終於在她一而再、再而三的猥褻下,做出反擊。
我使盡全身的力氣抓著舅媽的雙手,將她壓制在牆邊,她像是終於清醒了盯著我看,問我:「鄭天男,你現在是想做什麼?我是你舅媽,不要忘記是你爸害我們變成這樣!」雨聲和雷聲很大,我沒有理會舅媽,只是更用力地緊握她的雙手,不讓她有任何可以回擊我的可能,然後我用我也害怕的吼叫聲,對著她大吼:「這樣很有趣嗎?這樣欺負我很有趣嗎?妳整天喝得爛醉,舅舅就會回來嗎?我爸就會回來嗎?」
我看著舅媽扭動的身體掙扎著,她已經清醒的眼中泛出求饒的訊號。我感覺我心裡長出的怪物正逐漸的壯大起,我更貼近她的臉,她那一身酒氣和菸與檳榔味讓我想吐,我聽著自己堅定冷酷的聲音對她說:「我不會對妳怎麼樣,但妳最好記得,不要再這樣對我,因為我不知道下一次我會不會控制得住,把妳弄死。」
講出「弄死」兩個字,我被自己嚇到鬆開雙手。舅媽從我手上掙脫,拿起手邊的椅子砸向我。雨聲、雷聲都太大,像在學校那樣,沒有人發現我的異狀。天亮的時候,陽光從家們的縫隙鑽了進來,我坐臥在客廳的牆角,我感覺我在呼吸,我不願睜開雙眼,我不想知道我還活著,我不想看見天亮時分,新的一天又要開始。
*
「男男,你父親說今天要來看你喔!」舅媽從姊姊和母親的身後冒出頭說。
再醒來時,病房又是一片明亮了。我的頭疼痛加劇,但看著她們仨的笑容,我也笑了。
我傻氣地問著母親:「媽,爸爸會不會不記得我的樣子?他走的時候我才九歲啊!」
母親笑著輕撫我的臉說:「不要擔心啊,男男跟爸爸年輕的時候長得很像喔!」
姊姊也在一旁附和,像那些夜裡她在我身後幫我拍背時,用著照顧弟弟的疼愛對我說:「而且你還是小時候的笨蛋愛哭樣喔!」
我不好意思的抓抓頭說:「可是我今天頭有點痛。可不可以問一下醫生怎麼回事?」
還沒人答話,父親已經走進病房,他的頭髮已經有點花白,身材好像沒有小時候感覺的那樣高大,他走向病床開口喚我:「男男!」
我頭更痛了,痛到我眼淚直流。父親笑著說:「是看到爸爸太開心了嗎?怎麼會哭了。」
我帶著眼淚擠出一點笑容看著他說:「不曉得為什麼頭那麼痛。」我摸摸我的頭,父親繞過母親、舅媽、姊姊,站到我的枕邊,我又跟他說:「看到你我好開心,可是頭痛到眼淚一直流。」
父親看著我,摸摸我的頭說:「怎麼騎車那麼不小心?以後要小心一點,不要讓我們擔心,好不好?」我看著他,點點頭。
母親和舅媽靠在一起,姊姊站在父親旁邊握著我的手說:「男男要快點好喔!我們都在等你一起回家。」我頭痛到閉上雙眼,腦中一幕又一幕從小到大的影像不停地播放,我伸手拍打著頭,希望停住那陣巨痛,更像是想停住腦中那些畫面,卻聽見父親說:「那你好好休息,我再來看你喲!」
我揉揉眼睛,想再睜開眼看父親和母親、姊姊、舅媽的身影,卻被熾白的光線給蓋過,眼前是極蒼白的景象。
*
如果我不在地獄就無法感覺天堂的蒼白。
。後記。
多年前朋友送我一本《職場冷暴力》。我沒看,我想她知道我經歷過所以送我。
「冷暴力」大概是我從小至今最常經歷的事(任誰都可以跟我冷戰把我當空氣)。你很清楚知道「你被漠視了」或者你被用任何方式被排擠在外,但沒有被欺負或是被攻擊。
舉個例來說,同事之間交辦事項都不直接說,你明明在同一個空間裡(甚至在旁邊),但同事會這麼說話:「那個誰到底什麼時候把稿子交來啊?」(誰=你)。
面對職場冷暴力,我的方式是:不干擾我做事的,我完全不理會,我把事情做好就是。干擾了我的工作進度,我可能直接越級找可以處理的人問:「現在是還要不要做事?」再不就什麼都不說,直接離職。
如果是網路的冷暴力,我可能找幾個對我還算友善的人搞清楚狀況免得誤觸地雷被冷到。但有一種冷暴力是最難處理的:家人的、親人的、愛人的。這是〈如果我不在地獄就無法感覺天堂的蒼白〉要說的事。
故事裡面,所有的肢體暴力是我刻意加入的,大部分的人都只關心「肢體暴力」對人的影響,但有非常大一部分的心理創傷都來自於「冷暴力」的漠視。
這篇小說寫在2016年。本來是投稿文學獎的,原稿寫得很糟,大概就是如同當時的心境。(心境總是左右了自己的文字,這是絕對不用質疑的。所有的慌亂焦躁,文字都會幫你說話。)
一直沒敢拿出來看,就別說修了。我很怕回到寫這個小說時自己的心境,那不是孤獨,而是一種「即使你都已經開口向世界求助,但每個人還是認為你不需要幫忙」的狀態,就算是在那以前你真的穩健的從來沒有麻煩過別人,卻發現自己連稍微軟弱都不行。
有點像「父親如山」的感覺,就像所有的人對母親套上「一定會有母愛」一樣。
我把心情都寫到故事裡,這個故事當時的確有療癒我那些需要被安撫的心情。寫完後我就把它擱在我的硬碟裡,再沒拿出來讀過,直到今年(2021)開始寫起其他的故事後,才回頭把它找出來,從完全不敢看到可以把它讀完,然後發現缺漏了非常多的細節,然後一一補上,雖然仍不稱得上完整,但也算是我重頭梳理這個故事的起頭,以及面對寫這個故時的時候,那個非常不安的自己。
我從小的確會有這一個儀式:在睡前我會假裝自己快要死去了,然後身邊有人很在意的希望我快點活過來。(不過,父母給我挺強健的體魄,除了前幾年被壓力壓迫到頭暈、胃痛外,我都是個健康的孩子。)
小說就是小說,它本來就有很多部分是屬於作者的生命經驗,即便是寫別人的故事,也一定有作者的角度。
我每一個小說都有「我」在裡面,但可能不是你知道的那個我,或者其實每一個主角都是我。
謝謝你讀完這篇沒有得獎而且加了6000字的小說。不是什麼太好的作品,但算是對2016年及那些渴望死去的我,在生命裡畫上一個句點。
之後,繼續往前!
圖:2010高雄大立兒童樂園,Canon AE-1,黑白底片。另外拍了彩色底片和彩色數位的,但就決定以黑白來搭這個故事。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