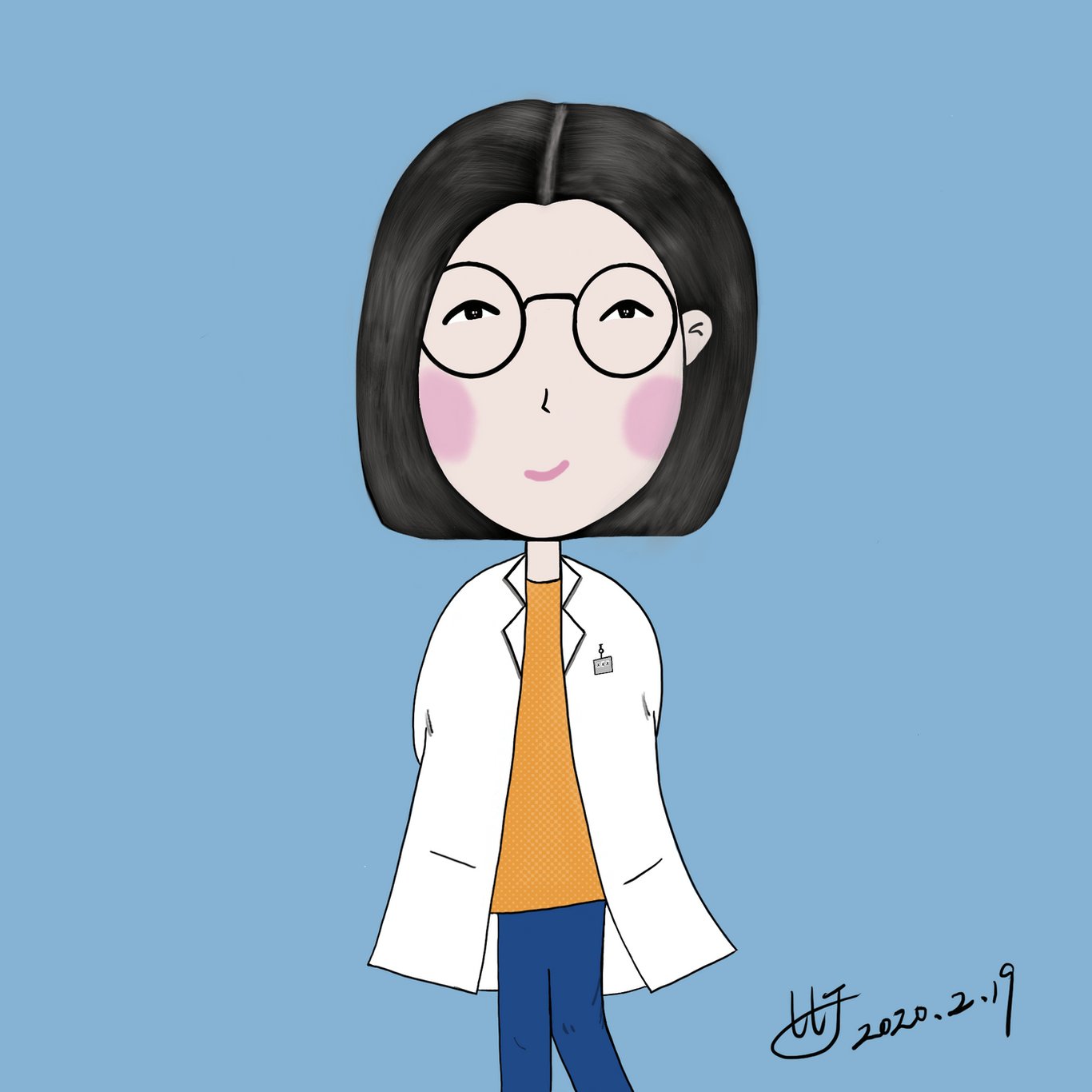十年,穿行在躁郁症的风暴中
注:躁郁症目前的诊断名词为:双相障碍(双相情感障碍)
说明:访谈前由主管医生向橙子说明本次访谈的目的和形式,橙子表示非常愿意接受采访。为了便于记录,我们征求了橙子的同意对访谈进行了录音,为避免曲解橙子的原意,将修改后的文字稿交由橙子校对,是为此文。本文内容已获得患者书面知情同意公开发表。
本文图片来源:unsplash.com
受访者:橙子(化名)
访谈者:刘丽君医生 黄昀医生
访谈时长:60分钟
访谈时间:2018年3月
———————————
橙子是一个年轻女孩儿,时年二十八,看似十八,常以“三十岁的老女人”自居,自诩“有一套完整的护肤方法”。
访谈者:今天不是查房,而是以访谈的形式,希望更多地听你说说关于这个病的感受和理解,目的是为了科普,不仅是给患者和大众,也给像我一样年轻的医生,让大家更好地去了解这个病和这个人群。所有涉及到你个人的信息均会做相应的修改和匿名处理。
橙子:没问题。请问您能不能说重点啊!节约一个人的时间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尊重。有没有采访提纲?提高咱们的效率。而且我现在是一个轻躁狂的状态,一会儿肯定会跑偏,你们一定要提醒我。甚至最好的方法是直接以命令的语气说“闭嘴”。
访谈者:哈哈,好。(递给橙子采访提纲,上面罗列了十来个问题。)
橙子:OK,没问题。首先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是社会边缘人物。我在简书上写自己的经历,希望自己走过的弯路,别人不要再走。但是投稿首页一直失败,关注我的人也都是同病相怜的病友,彼此鼓励。
访谈者:你可以大概说一下自己的情况吗?就是你得这个病有多长时间了?
橙子:十年,2008年的时候开始。如果说潜伏期的话,从小跟父母之间的互动便种下种子。高中最为明显。作为文科生不希望在理科见长的学校学习,但父母会认为我总是活在过去,试图挣扎。直到18岁,离家求学,才敢以“生病”的方式来回应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东西。
访谈者:第一次发病是什么状态?
橙子:大一的时候躁狂,积极参加各种活动,表现得很出色。持续一年。后期混合,本来学校是派我参加省主持人大赛,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depression。大二直接开始depression,然后是半年,三个月,一个月,半个月,甚至2017年4月的一周(抑郁发作、躁狂发作)。
访谈者:第一次确诊这个病是什么时候?
橙子:大二的时候男朋友陪我去看医生,当时不是去专科医院,就是普通综合医院的心理科,医生跟我聊了会儿天,就诊断我是躁郁症了。他给我开药,但是我逃走了。后来大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很亢奋。我去找学校心理科的医生,他认为我很正常。有一次遇到一位“元老”级别的医生,他认为我生病了,但是没说是什么病。从那以后,就开始了十年鏖战、求医问药的征程。去过A省的中医院、B省的安定医院,差不多找了七年多才找到北大六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从我个人的角度,十年颠簸,我真的觉得精神科疾病啊,好的医院、大夫、药物和药量,这四个因素才是最最具有决定性的。我跑遍了全中国,甚至跑到澳大利亚,一切都是为了找寻那个最适合医院里的医生开出的适合自己药量的药物。
访谈者:你刚刚提到了花了很长时间,包括你自己能够回忆到自己生病的时候是08年,到你听到躁郁症这三个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快两年。
橙子: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你不开心的时候,你才会去看病,但是你开心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去看病。
访谈者:很多患者是以抑郁首次就诊的,但是之前的躁的表现,他们不认为是病。
橙子:对啊,所以才说那个第一次看的那个医生厉害啊,我是抑郁去看的,他居然能给我诊断躁郁症。但是我当时也没听,直接就逃走了。
访谈者:什么时候开始吃药的?
橙子:关于吃药,我也走了很多弯路。一开始被当成抑郁症治,后来寻找中医西医偏方大仙,全部试过。整整六年,直到2014年3月3日,妈妈担心这样下去,这孩子就废了。为了治病,专程来到北京,才真正开始打这一场硬战了。
访谈者:那从08年开始算就过了六年了。
橙子:这六年间我就不停的找医院、医生,药物,药量。但是我已经是很幸运了,有些人是从小学初中就开始的,那真的是很恐怖,我看他们的掌纹真的是那种把世间的苦都吃遍的掌纹。
访谈者:你的经历确实能代表很大一部分人,因为你也是吃过很多苦。
橙子:我明白。所以一直觉得自己非常荣幸和幸运。能够有这样的一次机会,作为不能且不敢发声的我们这样一个社会边缘群体中的一名,以这样的方式被看见,同时也作为一个桥梁,起到连接作用。
访谈者:你第一次确诊时,你爸妈是什么反应?
橙子:我个人感觉,可能一直到现在,父母都没有接受我生病,我妈常讲一句话:为什么是你生病,我能不能替你生病?是妈妈不好,把你养成这样。我爸甚至跟我妈说“不要管她,她就是故意这个样子的”。
虽然现在看起来,我可以和你们嘻嘻哈哈,甚至自黑,但是这十年之间我不敢和男生很认真的交往,因为你要对他、对他的家族负责,即使他们都跟我说你可以不生孩子啊,但是我不行,我必须负责。两年前我由教育行业转行健康领域,在行业会议上遇到一名前辈,他治疗好了几名躁郁症的小姑娘,都结婚生宝宝了,我当时觉得生命又燃起了希望。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健康领域里摸爬滚打,深知郎中不可自用。近三年的学习:中医,西药药理,健康生活习惯,瑜伽,营养学,走罐,推拿按摩,愉悦心情,适量运动,合理膳食。以上种种,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
作为一名十年的精神疾病患者,在此,以我个人经历,想强调一下:我们要用科学和知识来保护我们自己,而不单单用经验和习惯。

访谈者:你可以描述一下你躁狂时候的样子吗?
橙子:我可以讲一下轻躁和躁狂,轻躁就是我虽然想讲话,但是可控,我累的时候,我可以停下,这是一个加号+,有本书叫《双相情感障碍你和你的家人必须知道的》,有非常确切的躁狂量表,一个加号、两个加号、三个加号(+ ++ +++),然后我两个加号(++)的时候就是,cannot help doing something,不停地做事情,必须别人很严厉地跟我说stop,我才会停下来。
三个加号(+++)就是我在墨尔本的时候,5天睡17个小时,剩下所有的时间就是工作,我工作的状态就是不停地讲话,大哭大笑,所有都是浓度非常强烈的那种。甚至为了不让浓烈情绪影响自身,我会扔东西,甚至捶墙,把墙捶穿,当然那是因为国外的墙质量不好,我在国内就没有捶破过(笑),导致楼下奶奶神经衰弱,直接报警了。
访谈者:抑郁的时候什么样子?
橙子:我抑郁轻一点时候能出门,跟安全范围内的人,未婚夫啊、爸爸妈妈啊,包括team里跟我关系比较好一点的人都没问题,他们都看不出我有什么异常。
最大的感觉就是麻木,我觉得用“麻木”形容depression是最贴切的词,所谓大脑迟缓没有办法判断,对情感的感知能力下降,甚至全部消失,就是麻木,最严重的时候,那种麻木真的很可怕就是对这个世界毫无感知,就是我眼睛看到就只!是!看到。那个时候母亲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很伤心在哭,我知道我妈妈很伤心在哭,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上去,我感!受!不!到!!让抑郁时候的自己双重的难过。
相对应的,躁狂时,任何一点小触碰就大哭大闹,大喊大叫。其实中和后就正常了啊。
生病十年,带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balance”——我一个朋友说,你为什么会抑郁,因为你躁狂太high,你是大悲大喜,这样的(手比划起伏大的曲线),你就永远得这样子。但如果你是一条直线,或者小幅波动,那不就正常了吗?

访谈者:你现在会觉得这是一个病么?有时候我们会对患者这样说:这个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必须要治疗的。
橙子:这个类比没毛病。首先,是病就得治,药不能停;其次,生病后大部分人,尤其是女孩子会问能生宝宝么?尤其是在这种需要长期服用药物的情况下。我们会有很多的顾虑和担心,常常不知道怎么办,就自己停药。
访谈者:这个病对你的生活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有什么影响吗?
橙子:从08年开始,也算是生病的时候,被全班同学排挤,我大二的时候都没有人愿意跟我住同一个宿舍。我那个时候躁狂,学校的社团啊,组织加了很多,活动很多,那个时候所有的话,我都是当着人的面讲的,好话坏话,导致不停换宿舍,换到最后都没有人愿意和我同宿舍。
访谈者:这个病给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橙子:痛苦就是我不想经历这些,就像《天才向左,疯子向右》,我只想做个普通小老百姓。做一个接地气的人,暖一颗过日子的心。我不想拥有那么多老天给我的天赋。
访谈者:这个病本身也会给你带来好处?比如说创作、灵感之类的?
橙子:会啊,语言天赋。没有生这个病以前我是很害羞的,初一上台讲话,我就站在那站五分钟,一个字都讲不出来。
后来为什么语言有天赋,那是因为躁狂的时候见到人就聊天,就问一个路都能聊几十分钟,我这口语就这么天天练。
还有一点,轻躁狂的时候,你就是想讲话,can’t help doing it ,你就是忍不住想说话,随便逮着一个人就能聊到老死不相往来。
访谈者:所以轻躁狂似乎给你打开了一扇门,锻炼了你语言的技能,包括你后来教书能力、培训能力很好,是这样吗?
橙子:是啊,如果我像过去一样,上个台都紧张的要命,没有学生愿意选我,尤其我是做一对一教学的,我必须第一节课就让学生喜欢我,因为只有喜欢我,他/她才愿意听我的所有课,所以我不得不open,招人喜欢,活泼开朗。其实“为人需藏”,我是不喜欢笑的,虽然初中就被说为什么只有笑这一种表情,因为哭并不能解决问题啊。
反正问题都是要解决的,为什么不选择嬉皮笑脸,去面对人生的难。

访谈者:你看过那本《我与躁郁症共处的三十年》,在尾声部分,作者问自己如果有选择,会不会选择“拥有”躁郁症。假设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不会要这个病?
橙子:如果这辈子我已经活过了,那下辈子我不要。
访谈者:那这辈子呢,比如这辈子你还没有活过,从头有个选择的话?
橙子:那我就要。
访谈者:这个回答还挺让我意外的。
橙子:因为在我的价值列表上,“体验”是我非常看重的一块。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 have a try,因为安稳是他看重的一个点。
访谈者:我会有点担心,这个回答会让大家产生一些误解,会认为那既然这个体验那么好,那我就不用看病了。
橙子:人生是有舍有得,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任何东西你不要光想着它给你的利益是什么,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平白无故的,你要得到这个好处,你就必须去承受另外一层(代价)。
上一次住院我直接跟马大夫说,你把我调成轻躁好不好,我喜欢这种状态。马大夫很认真的回答我这个问题,她说如果你变成轻躁,你会怎么怎么样。想拥有这种体验的人,请时刻记住:任何所得,你一定会付出同等甚至更严酷的代价的。
一定要补充一点,有时候看起来你现在活得很轻松,是因为有别人替你承担了属于你的责任。这才是我生病十年的原因,如果第一年自己扛了自己的那部分责任,就可能不会有后面这九年了,但是一直我的父母,爱我的人一直替我扛着的,才会鏖战十年。

访谈者:可以聊聊你的住院经历吗?第一次住院是什么状况?
橙子:我第一次住院是被强行送到B省那边的。当时我以为就是去玩儿呢。我妈也没和我说要去住院,我以为参观一下就走,结果一下子门就在我后面“啪”地关上了。我直接拿头撞墙了,很认真的撞墙,绝不马虎的那种。然后我在里面闹,就给我打了一针。我还特别客气,(对护士说)谢谢小姐姐,后来才发现“被骗”了。
任何一个人住院,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都有个心理过程。你是人嘛,不可能一下子强行扭过来。
我发现生这个病,大部分都是父母包办太多。比如我妈就是,觉得我孩子生病了,所有事情我都得扛着。所以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管,完全只顾着撒欢了,还不知道自己的病,还以为自己在玩儿,北上广深,不知道自己是在找大夫(治病)。
那个时候我就没有扛起自己的(责任),然莫名其妙就进去(医院)了,撑死了扛了三天,我男朋友来了,我闹得更厉害了,没几天就出院了。
真的不希望大家走我走过的弯路。北大六院是全球性价比最高的,我在墨尔本6小时花了4500人民币。那也都是辛苦钱啊!(笑)
我第一次来这边住院的时候,特别矫情,饭也吃不惯啊,确实也吃不惯,北方人吃馒头,我得吃面啊。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看到病房的一些细节,比如水壶上贴着提醒的字条这些细节让我很感动。

访谈者:住院期间你也被保护过,能谈谈你的感受吗?
橙子:我被保护过,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好的认识。但是,确实有一些问题,去年我住院的时候,有个小妹妹就抱着我一直哭,我就问她你怎么了,她说我就坐在那里好好的,他们就突然上来把我绑起来。我就特别难过。
我被保护的原因特别简单,我吃药有点副反应,大舌头,主管大夫就把水煮蛋换成蛋羹,但是连续说了三天厨房都没有换,我TM每天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吃鸡蛋。后来我就敲窗口,不被搭理,一下子犯病,感觉血压蹭上脑子,我把塑料碗扔到了地上,护士就判定我是发作了,一下子两个人上来绑我。当时本能的挣扎,直接给我绑到小黑屋里去了。我还边说:加油加油一定要齐心协力,才能把我绑起来啊。
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医生和患者之间,其实是一个合作的关系,疾病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不要把我们的医患关系变成一个对立的关系好吗?我很揪心啊!
我现在学会的一点是,所有的事情一定要和主管大夫和盘托出。
我们病人有这种现象:比如我这几天一定要好好表现,不能特别暴躁,不能哭,哭也不能让他看见,这样我才能早点出院,这样子来掩盖实际的病情。
那为什么要住院呢?这不是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钱财吗?我看到这样的情况我是不会去劝的,劝不动。主管医生需要用心而不仅仅是眼睛去观察,确认哪些病人有这样的现象,一定要让他们有安全感之后,是一个全然接纳的状态后再沟通——毕竟我为什么对你close,因为你(对我来说)是不安全的。
或许可以这样子和病人说:突然的住院,肯定会有不舒服,我也不相信有“感同身受”这种事情 ,因为谁都无法体会到你的痛楚,但是我知道的是,你一定是希望快快出院,尽早康复。所以现在开始,面对疾病这个敌人,我们一起努力,统一战线,打好配合。好吗?我知道一开始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有充分的信任度是非常难的,咱们都不着急,一点点来,你愿意说多少,我就听多少,但是请你记住,只要你需要我就一定会在你身边。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这样作为病人其实更能接受一些。

访谈者:我记得查房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你说:你们这些没得过这个病的人给我们治病,凭什么呀?
橙子:我没有说凭什么。我的原话是:你们一群人靠着想象力给我们治病。你们就是靠想象力的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原来有个住院的妹妹,她总尿床,每天都尿床,有个护士说:你是故意的吧。大概是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好难过,谁愿意这样子,我TM尿的是自己的裤子。我的意思是,我们有时候就是病态,大家知道你打喷嚏、流鼻涕,这叫感冒,但大家不知道你哭闹、尿床这可能是疾病。甚至很多人自己抑郁躁狂很多年,自己不自知。最可怕的不是他不承认,而是不自知。
访谈者:其实我还挺想申辩一下的,关于“我们在靠想象力治病”(笑)
橙子:我讲得过激了一点,我看《我与躁郁症共处的三十年》那本书。国内没有人替我们发声,没有人精准、妥帖、细腻地去传达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是可以胜任的。我也没有奢求要改变什么。我写的东西也基本是患者和家属看,我觉得即使公众看不到,那我们就抱团取暖好了。这就是我的动力。为什么我说你们靠想象力治病,因为没有人站出来,去充当这个角色,你们也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去翻文献,什么都要看,是因为这一块没有人(去做宣传,关于这个疾病)。
这也不是你们的问题。
访谈者:还替我们说话(笑)。
橙子:本来嘛,就是这种疾病,我躁狂的时候讲的话,你们也不能全信。我现在轻躁会好一点,躁狂的时候,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当时我跟我朋友说我一年能挣1.4个亿,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说:你可以的。我去,这也信,你干脆跟我一起治病得了。(笑)
所以说,能够在一个状态比较OK的时候,谈这些,因为我走过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弯路的,有一种使命感。

访谈者:我不知道你看了前阵子奇葩大会的一个节目没有,分享躁郁症的?
橙子:看了。
访谈者:她特别勇敢地说了自己的故事。这一点特别棒。但是其中有一些信息,在我们精神科医生看来是有一些误导性的,比如自己把药停了等等,你怎么看?
橙子:我只看了一点片段。我觉得她很幸福,她能够站在那个平台上,影响到整个圈子。
但是停药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太可怕了。是病得治,药不能停。这就是她靠想象力给自己治病。你看她讲这句话,她没有以科学和知识来保护自己,你还用影响力这么大的一个平台说这样的话,影响力这么大,你有考虑过这些病患,完全有可能有一批病患就走向歧途了。
因为我断过药,一旦断药一个月,立马病情就会突变,只会越来越糟。
太可怕了。这个视频一出来,我们在海外的人都会看的,可能一批人就断药了。以后你们北大六院要井喷式地用针了。(笑)
访谈者:十年过去了,你对这个疾病的体验有变化吗?
橙子:有啊,以前看山是山,经过了看山不是山,现在又变成看山是山。我的团队当中有很多抑郁症,但躁郁症就只有我。有一个同事跟我说:既然上天选择了你,你今生要跟这样一种疾病有这样一个缘分,倒不如以你这样一个视角,让我们看看在你这样一个视角下,世界是怎样的缤纷。当时我听完这句话,真的想说:这个女人的大脑好性感啊!
我特别感谢去年一年在墨尔本,吃过的苦,享过的福,每一个人用心跟我讲过的话,我都记得。她跟我讲这句话之前,我觉得我最苦,全世界我最苦,她跟我讲完之后,我有种“原来是这样子的”的感觉。

访谈者:其实作为年轻的医生,我们有时候也会感到困难,病人总是不好,病情反反复复的。你有什么想法?
橙子:首先呢,心态要好,别着急,慢慢来,一辈子呢。慢下来,下半辈子都要和这个疾病去和解。第二点就是方法论的问题。医术你们要继续提高的嘛。这就不用我说了。
总之,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六与高人多对话。提高自己的方式,就是这三条。最后一条是我自己加的。命是我命中注定得了这个病,是改不了的;运是可以改的,我觉得越努力越幸运;三风水,北京风水好炸了,就不用说了。四积阴功,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积阴功嘛,很多小的事情都是,随手帮助别人。五读书,一定要多读书,大量的读书,选择的标准就是,能读死人的就不要读活人的,你们这种学术性的嘛,能读论文就不要看百度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加的,我发现有的人既不爱读书,也不积阴功,还是能有所建树,原因就是与高人多对话,比如说老板的司机,常与高人在一起,也就变得很厉害。
访谈者:我当精神科住院医不到半年,你是我管过的第三个双相患者。我常常很忐忑,很害怕,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担心我的一些言行,会恶化我们之间的关系。
橙子:你要大声地和你的病患去传达你很努力、很积极在为患者治疗,这是很美的感情。你要大声地说出来,因为这个世界太嘈杂了。你要去寻找方法,最好的方法是有效沟通,直接、及时地沟通。你看我都住院一周了,你憋了那么长时间,何必呢?你这小小的身体还要装这么多东西。你刚刚的表达方式就非常好,非常直接。
访谈者:你能够接受,医生也会有不确定性?
橙子:明白的。我刚工作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还有一点,我观察了一下,得这个病的人都很善良,我有时候会觉得是因为太善良了所以得了这个病(笑),我们会把得病的原因都归自己身上,自责。
你可以最开始就直接告诉我你的感受,你可以这样说:这也是我第一次管这样的病人,我也有一些不确定,我们一起合作,尽快好起来。你有什么不确定的因素,因为我是您的主管医生,您必须告诉我你的真实的病情,我们治疗团队一起帮您。
这个病太需要帮助了,我真的是死过很多回,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访谈者:死过很多回是指?
橙子:自杀过。还有是因为,躁狂的时候五天只睡了17个小时,我还出去,因为很亢奋嘛,体能就跟不上,食物也没有及时补充,真的可能就死在外面了。我经常就随便躺在地上,真的很病态。最可怕的是我还不自知。我不知道这是病态,我以为常人都是这样子。
至此访谈结束。
访谈后记:
橙子作为一个典型的双相障碍患者,病程长达十年,仍然保持着非常好的社会功能,工作能力很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她和她整个家庭对于疾病以及治疗一直有一个开放的态度,不断地努力去尝试配合医生的治疗。这对于双相病人保持情绪的稳定状态、维持正常的社会功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双相障碍这一疾病的病因学机制还亟待进一步研究,但目前药物治疗是确切有效的。双相障碍的就诊率和识别率都还很低,这个疾病并没有那么可怕,就像橙子所说,我们应当用科学和知识来保护自己。
每个病人对疾病的理解和归因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康复是共同的目标。在当前的大环境中,医生和患者共同面对疾病,形成治疗联盟本就困难,而这一联盟往往十分脆弱,一击即垮。而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却是治疗的最最重要的基础,这需要医生的努力,也需要患者的努力。
精神疾病由于自古带来的“神秘”,直击人类最脆弱的内核,我们以为我们即使失去了身体的自由,也能保有心灵的自由,但是,当我们连心灵的自由也会失去的时候,我们当如何面对呢?
本文作者:橙子、LLJ、HY
指导老师:马燕桃(北大六院主任医师)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