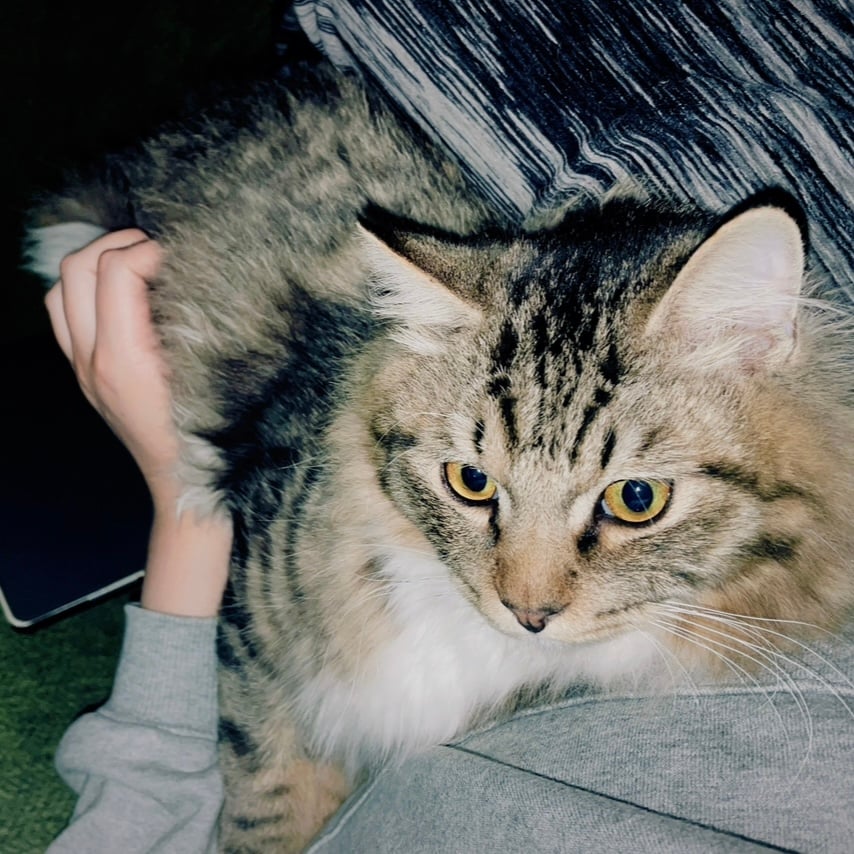我不愿春天的到来变得无关紧要
很久没在公众号上发文了,有两个原因,两个原因都指向我的工作。年底和年初,工作上迎来了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导致我比较忙碌,虽然并不是忙碌到一点东西都没空写,但人在忙碌之后总是希望能够做点不动脑子的事情的。另外,工作上的写作也耗费了一些写东西的冲动,而仅有的空闲时间里所写的东西,我的第一选择是投稿,如果成功了,也就没有机会再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了。
如果是投稿,我会考虑这篇文字要放到什么地方,考虑对方需要的是什么,我想写的东西需要做什么取舍。在最近的几个月,我似乎经常以这样的思路在下笔,感到些许疲惫后,我开始想念无目的的写作。
春天,与我苏醒的“无目的写作”的冲动共同到来。

柳树苍白的枝条开始泛起嫩绿,透白的坚冰化为一池春水,尽管我知道自己突如其来的写作冲动跟春天的信号并无直接的逻辑联系,但我十分乐意将其扯上一些关联。也许我就是被唤醒了呢?
今年的春天来得很突然,似乎没有任何过渡。一夜之间,羽绒服变得不合时宜,我试探地换成大衣走出门,发现外面的风已经变得和煦、温暖,不会试图吹掉我的外套,将寒冷渗进我的体表。整个人不自觉间轻盈、跳跃起来,无师自通了春天的脚步。
一切都变得亮堂堂的,冬日里自然也有晴天,那种亮和春天的亮不一样。深冬的亮是苍白的,虽然亮但没有温度,看上去温暖,但走进其中才发现受了骗,人被风吹得打颤、直不起腰,要是有一片云飘过来遮住了太阳,那冷便更彻底,从脚底一直蔓延上来。春天的亮是有热度的,洒在背上,暖洋洋、热烘烘,让人舒服也让人懒,天上的云一朵朵一簇簇,柔软温和,偶尔挡住阳光也很快就飘远,生怕让地上的少晒了太阳。
虽然已经换上了不适合在北京的冬天穿的衣服,感受到了春风的温和,但我迟钝的大脑还是没有意识到春天已经杀了我一个措手不及的事实,我还必须得承认,在我穿了一周属于春天的外套之后,依然没有“春天来了”这个念头。我埋头于生活,只想到“穿这个会冷吗”,不冷,那就继续穿吧。
春天大概都嫌弃我笨,已经坦坦荡荡站在我面前了,我还没认出他来,于是给了我一个最直观的线索。
我现在住的房子在较高的楼层,阳台窗户外正好对着一个公园。入住以来,从窗户望出去总是干枯、苍凉的一片,冬风冷峻,为了留住屋里的暖意我几乎不会打开窗户。然而,这几天屋里的温度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温暖变成了闷热,我把窗户打开一个缝隙透气——这窗户太久没擦,覆着一层浑浊、乳白的雾气一样的水痕,让我看不清窗外的变化。从这一缕缝隙望出去,那样清晰、那样明朗,仿佛近视的人戴上了眼镜,我望到了对面突然出现的绿。
远处的树顶竟已经冒出一层娇嫩的黄绿,那是绿的前奏,是春天冲锋的号角,在这抹颜色摇晃在我狭窄的一缕视线中时,我才迟钝地意识到——
春天来了。
来得那么快,来得我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在我的记忆中,前两年的春天是来得很缓慢的。我不知道多少次咒骂臃肿笨重的羽绒服,不知道多少次仰头寻找秃枝上冒出来的绿苗,不知道多少次凝视只剩枯黄草根的土壤,在无尽的期待,无尽的渴望中,在我几乎要渴死在没有一丝绿意的冬天时,春天才姗姗来迟。因为这样的等待,春天的到来格外让我欣喜,让我感动。
等待是一种期盼,它赋予了接下来到来的事物更为厚重的意义。如果没有长久的等待,那变化也显得无关紧要。
我不愿春天的到来变得无关紧要。

我开始反思,为什么今年对春天如此迟钝,甚至成为一种冷遇。我觉得比较体面的答案是,当进入比较稳定的工作状态之后,人已经养成固定的作息——什么时间做什么事,都是具体而明确的。
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人自然不会对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有更多的好奇和窥探。
我每天都走同一条路,每天都坐同一路地铁,每天都在天黑后才回家,每天都在步行时翻阅歌单研究接下来该听什么,每天到家后都吃饭、往床上一躺……除了站在衣柜前找衣服时搜索接下来几天的温度发现它们纷纷越过20,又有什么时候能接收到春天的预告呢?
对习惯之外的漠然,让我失去了对春天的盼望。如果不是开窗户的那一瞥,我又会在什么时候发现春天的到来?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哪怕是看到春天的绿意在与冬天的萧索的战争中胜出,我也毫无感触呢?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我又该如何自处?
我不知道。
虽然我自认没有在毕业后的工作中学会社会人所必需的“成熟”,但我的确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考虑相较于过去最在意的问题更加现实的东西。比如说,当我所向往的工作在现实层面上难以实现时,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我现在能做的工作——在这里就不做“人人都可以在工作中实现个人价值并且获得足够的物质报酬与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乌托邦幻想了。
现在的情况下,比较容易被我们接受的一个解释是,工作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生活,也就是说,工作其实是我们通向理想生活的桥梁。而工作赚得越多,人也就越“自由”,即拥有足够的钱去实现自己向往的“自由”。
大家都很关注如何实现,往往忽略了多数人或者说近乎所有人,一辈子都在桥上。我们以为工作是方式而非目的,但当我们真正置身其中,却发现工作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目的本身。
我畏惧习惯,畏惧的就是“工作变成了目的本身”。齐美尔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我从来没想过要生活在桥上,我知道我想要走到桥的对面,也一直(自以为)努力(但其实也算不上有多努力)地走,但偶尔,我会发现自己站在桥上一动不动,甚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停下的,抬头望去,桥的对岸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
在将窗户推开一条缝,看见远处树顶的绿色时,我惊异于自己对春天的到来毫无察觉,惊异于当下的生活节奏已成为一种默认的习惯,惊异于又是一年过去,也惊异于我好像就是生活在桥上,也只能生活在桥上。
我不愿春天的到来变得无关紧要,而我所能做的只是重拾对它的期待,重拾一种近乎愚蠢的勇敢——往桥的尽头走,哪怕永远无法抵达。
文/谢峮岚
2024.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