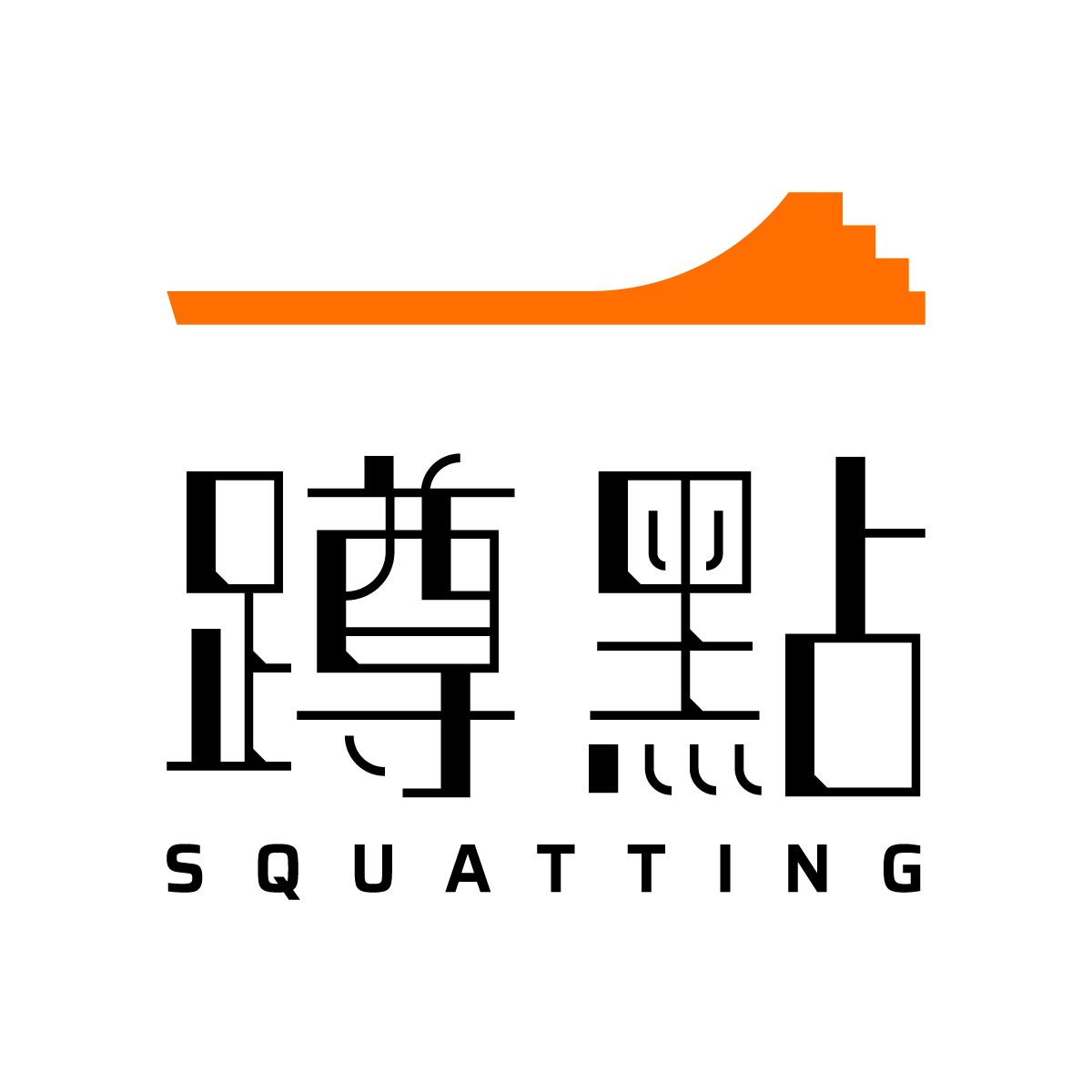桑德斯沒有輸,但左翼接下來如何去贏?

文/不重要
桑德斯宣布他將停止競選後,使政治中間派的前副總統拜登成為總統大選民主黨的候選人。其實,在過去幾週內,桑德斯退選早已成為定局。他不僅在基於票數的選舉人(delegates)數量上幾乎無法追上拜登,並且被越拉越遠。隨著疫情在美國的加重,候選人無法進行競選集會,多州推遲了民主黨初選候選人的投票,黨內外對他退選的壓力變得更大。
美國的左翼對桑德斯第二次競選失敗,難免有些失望。尤其是這次與四年前的情況很不同,當時希拉里從開始便被認為是毫無質疑的領先者,桑德斯的逆襲即使最終失敗,也足以使左翼受到鼓舞。而這次,在民主黨初選前期,桑德斯從前幾個州投票時便一直領先,其他進步和中間派的民候選人,分散了余下的選票,幾乎奠定了桑德斯的勝利。就連一直避免報導他的美國主流電視台,也不得不承認他的優勢。
超級星期二,選舉人最多的幾個州的同時投票,是逆轉的開始。民主黨黨內意識到如果多個候選人分散選票的趨勢持續下去,桑德斯幾乎無法再阻擋。為了阻止他,幾乎所有其他候選人,包括相對領先的人,都在幾天內同時退出選舉,公開支持拜登。民主黨的建制再次阻止了黨內最左翼的候選人,選擇了中間派。從那時起,分析桑德斯為什麼失敗的文章,就已經已經開始出現。目的不乏是解釋為什麼他其實並不那麼受歡迎,以及去抹去掉他背後的運動。
桑德斯帶來的改變
但回顧桑德斯在過去五年間兩次參加民主黨候選人的競選,以及在此之間他的而且確成為新的左翼運動興起的精神領袖,他不僅沒有輸,他對左翼和美國社會的影響是長期的。
他能走到這麼遠不難理解。在幾十年自由主義對美國社會的攻擊下,社會激烈分化隨處可見。全球經濟危機後,華盛頓的統治精英不僅沒有抑制經濟的不平等,而反而激化了更深的矛盾。也許自由主義在名字上死去了,但作為統治理念並沒有受到嚴重動搖。所以,美國社會幾乎是在等待像桑德斯那樣站在主流政黨政治外,關注最基本經濟和民生問題的人。這是桑德斯,也是特朗普,能在過去幾年得到這麼多支持的重要原因。
他不停重複地主張,如全民醫療保險(Medicare for All)、經濟不平等、學生債務、提高小時工資等等,用他的說法——before it’s fashionable——種種在四年前還是民主黨也不願意去碰的話題,現在已成為任何民主黨候選人都無法避免的議題。雖然這些問題在桑德斯之前,尤其是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早已被提出,但桑德斯使這些成為更主流的話題。同時,他把民主社會主義重新放到政治言語中,不但使社會主義這個詞不再那麼容易被抹黑,並且吸引了一批年輕人參與到運動。這本身在作為在甚為反左翼政策和意識形態的美國,無疑是很重要的勝利。
在這之前,美國的左翼運動,也在一個漫長的重組過程中。一方面,信奉革命的左翼組織,大多都停滯不前或者無法更新換代。或者,像曾是托派在美國的最大組織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在去年年初因為多年前領導層對一個性侵害事件的掩飾,造成了機構內部的危機,最終成員通過投票選擇解散了組織。但即使不是這個原因,傳統革命左派的衰退在美國不是偶然。面對從八十年代以來長期社會運動的低潮,九十年代共產主義國家的瓦解帶來的西方共產主義政黨的解散,雖然反史太林主義的托派組織存活了下來,但長期處於相對停滯的狀態。當中雖然不乏很優秀的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者,以及組織能力很強的運動者,但這些組織本身始終未擁有足夠社會和政治力量。
隨著五年前桑德斯競選,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注:雖然架構類似政黨,但是註冊為一個非盈利機構)的會員在過去從幾千增長到超過五萬。雖然看起來會員數量絕對不大,但在自由主義下的美國,絕大多數的左派組織都在幾百人到幾千人之間,甚至更少。之所以能吸引到新會員,很大原因是作為非列寧主義政黨架構,DSA內並不需要高度的政治思考統一。此外,隨著DSA興起的左翼期刊,例如很流行的Jacobin和更理論化的Catalyst等的出現,也讓左翼的思想和分析在更大範圍散佈。
DSA出生在冷戰中,主旨是社會民主主義,甚至帶有反共的色彩。但它的迅速增長,吸納了其他有組織的和無組織的左派,從托派到無政府主義傾向,以及很多意識形態很模糊的左派,都加入了進來,幾乎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新組織。比起桑德斯選舉本身,DSA有更加明確的反資本主義政治。但在包容多元左翼思想的同時,也造成了組織內部的矛盾。這種矛盾,在DSA把精力都投入到推舉民主黨裡面支持民主社會主義的候選人下,被暫時擱置下來。桑德斯的退出,和接下來難免的策略討論,將是對DSA很大的一個考驗。
當然,這並不僅是一場桑德斯的或者一個組織的政治運動。在經歷了幾十年的低潮期後,美國的工會運動有所復甦。很多年來,美國工會的覆蓋率一直在降低,只在百分之十上下。工會覆蓋率在公共部門較高,但在私營企業要更低,幾乎在企業中很難看到工會。同時,很多現存的大工會結構趨於僵硬,已經拋棄了組織工人,反而把精力放在和雇主的談判上。但在過去的兩三年,美國工人罷工的次數明顯增加,是八十年代以來的最高峰。其中很多是比較進步的地方工會,或者是工人頂著工會內部的阻力,推動工會積極的動員。野貓式罷工越來越多,尤其是美國多州教師工會在違反法律的狀況下進行罷工。因為運動的激烈性以及社會的廣泛支持,並未受到法律打擊。此外,女權運動、反種族歧視運動、保護非法移民的運動等等,都在過去的幾年中有更多的動員,深層次地改變美國社會。這些運動的參與者中,不乏受到桑德斯影響的青年運動者。但桑德斯的退出,並不會對這些運動產生很深的影響。
桑德斯遺留下來的問題
雖然桑德斯沒有輸,但美國的進步主義者怎麼能贏,又再次變得模糊。
一方面,疫情歇斯底里地暴露了美國社會的問題。政府全面支持醫療、保障人們的工作和收入等遙遠的問題,在短短幾週內變成了人們生存下去必需要面對的事情。在過去三週內,有過一千六百萬人申請失業保險,並且實際失業人數遠遠不止。本來這些在服務行業工作就幾乎沒有保障,根本無法承受這麼大的經濟波動。在這麼短時間的上升的失業率,即使在二三十年代大蕭條時也沒有經歷過。同時,在接下來的一到兩個月,對於絕大多數都是沒有存款的人來說,面臨的是承擔不起房租導致被驅逐出的後果。
這些問題,從來也都不僅僅是即使桑德斯當選總統能解決的。他要面對的不僅僅是民主黨內右翼和中間派的阻力,只可能面對比此前對更中間派的奧巴馬更有敵意共和黨,以及其代表的資本主義利益。他自己看得很清楚,也一直強調如果社會運動不施加壓力,他的主張是無法實現的。運動不時需要桑德斯這樣的人物,去傳輸和推動社會的訴求。但沒有了他,這些訴求和伴隨的運動並不會消失。
在一定意義上,桑德斯剛好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
在過去的一個月,美國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民眾自我組織,抗議和罷工,以及自發的互助。最初很多的抗住起源於要求雇主提供對員工的健康保障,但運動的邏輯會帶來越來越多更激進的對社會的徹底思考。而越來越多社會互助的自我組織,是最有效地對自由主義個體化的反擊。人們不再是互相競爭的關係,而是互相協助如何共同存活下去。當然, 疫情使群體運動變得複雜,在街頭抗議暫時不可能的情況下,大家都在探索如何繼續去做組織工作。這個民眾自發運動的時刻,也許不再需要,也不應該去需要,一個領袖來帶領運動。甚至也許我們幸運地避開看到一個當選的桑德斯總統,面對阻礙不得不與反對力量和資本進行談判和和解的情景。那樣的情況,會比現在桑德斯的退選,可能會對社會進步運動打擊要更大。
桑德斯從這個舞台的退出,也許是把改變社會的任務交還給社會運動本身最好的時刻。
但怎麼能贏,仍然沒有捷徑,需要左翼結合當下自發民眾運動下思考。
美國左翼目前把運動精力聚焦在疫情下,無暇甚至說在一定程度上逃避思考這個問題。但左翼需要審視在過去幾年中對於通過結合社會運動,利用中間偏左政黨選舉出左翼候選人,來奪取政治權力來影響公共政策的策略。街頭,還是選舉箱子,這是左翼一百多年來不斷需要面對問題。並且,在不同社會狀態下,需要考慮的因素也都會不同,所以從未有四海皆準的答案。隨著美國和英國選舉嘗試的失敗,試圖影響中左翼政黨的嘗試大概會暫時畫上一個句號,但這並不證明選舉和街頭是對立的。我們可以看到選舉和社會運動之間的張力:運動影響著選舉的候選人和爭論的話題,而選舉通過把主張宣傳出去等,擴大了社會運動動員和左翼思想的影響力。但當運動過於依賴選舉時,勢必會造成運動被選舉擺控的問題。
隨著選舉道路暫時的關閉,左翼必須要更加立足在社會運動中,在疫情帶來的社會災難面前,推動社會運動更加徹底地尋求對社會的反思和改變。